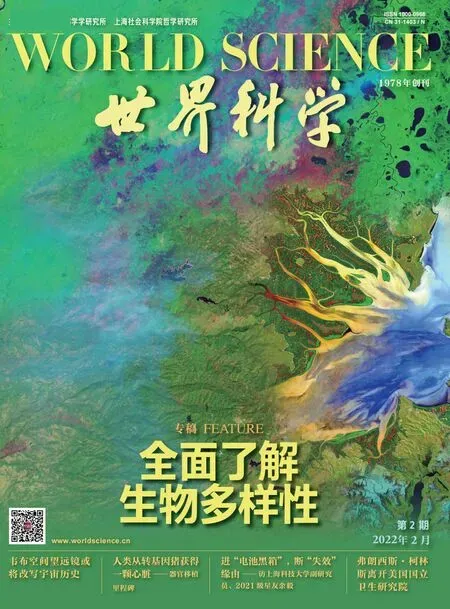置身于追求完美的市場中的神話創造者們
編譯 苦山

珍妮佛·杜德娜(左二)
亨利·基辛格、本杰明·富蘭克林、史蒂夫·喬布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列奧納多·達·芬奇,這些男性不僅都是他們所屬領域和時代的巨擘,而且還有另一個顯著的共同點,那就是都從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那里獲得了完整的生平記述,后者是美國最多產的創造性天才的人生記錄者。在艾薩克森那時間跨度長達數百年的“萬神殿”中,珍妮佛·杜德娜(Jennifer Doudna)是第一位加入的女性,盡管她并不認為自己的名字值得登上任何宣傳橫幅的第一行,但她毫無疑問是艾薩克森的最新著作《解碼者:珍妮佛·杜德娜、基因編輯與人類的未來》(The Code Breaker: Jennifer Doudna,Gene Editing,and The Future of The Human Race)的主人公。這本書詳細記述了科學偵查、突破性發現和聲名之爭。
在艾薩克森之前的作品中,他筆下的男主角們是通過各自的超凡個性塑造了自己的成果,使它們具有了永恒的地位,史蒂夫·喬布斯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他以歪曲他人現實的能力而聞名。但對于杜德娜,艾薩克森更多地將她描述為一個由自身成果塑造的女性,這一點可以從書名《解碼者》中窺得一斑。在艾薩克森的敘事中,大部分內容都致力于闡明這樣一個驚人的觀點:杜德娜圍繞RNA的化學成分所進行的“解碼”是重塑“人類未來”的關鍵。她利用基于RNA的CRISPR技術發現了基因編輯的秘密,這對艾薩克森來說是僅次于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于1953年破解基因密碼的一項壯舉,他希望我們相信,比起后者,杜德娜的成果會更為深刻、徹底地改變我們對于人類存在意義的認知。
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世界各地有少數研究細菌和其他微生物DNA的科學家首次發現了CRISPR這個生物學謎題。他們在這些生物的基因組中發現了神秘的DNA重復序列(也就是“CRISPR”這一縮寫中的“重復”)。在這些斷斷續續的重復之間有一些更為熟悉的DNA序列,他們稱之為間隔序列。在大多數細菌中,CRISPR序列的兩側都有一段和CRISPR關聯的基因(Cas基因),它編碼了一種Cas酶。科學家們最終發現,CRISPR-Cas系統是這些細菌用來保護自己免受入侵病毒侵害的適應性免疫反應。這些間隔序列被宿主細胞轉錄成短小的CRISPR-RNA,通過與Cas酶關聯來引導它們找到包含特定間隔序列的新入侵病毒。這些病毒隨后會被引導酶復合物滅活,后者會切斷前者的目標基因物質。
2012年,公眾對CRISPR的認識急劇增加,那一年,杜德娜和埃瑪紐埃勒·沙爾龐捷(Emmanuelle Charpentier)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開創性的文章,詳細解釋了涉及Cas9酶的一種特定細菌的CRISPR-Cas系統的潛在機制(她們最終共同獲得了2020年諾貝爾獎)。這篇文章還表明,Cas9酶可以與合成引導RNA分子結合,然后輸送到細胞中,在特定的目標位點上找到并剪切——或者說“編輯”——任何生物體的DNA鏈。
CRISPR基因編輯功能經常被比作文字處理器的拼寫檢查功能,它很快就被視作比傳統基因工程更快、更廉價、更高效的替代品。RNA引導的分子機制的多功能性和精確性預示著生物技術的革命性進步。斯坦福大學的律師、生物倫理學家亨利·格里利(Henry Greely)著有《CRISPR人:編輯人類的科學和倫理學》(CRISPR People: 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 Editing Humans)一書,據他說,CRISPR“遠遠超越了現有的工具,也許沒有從石斧跨越到鏈鋸那么遠,但也差不離”。
像許多科學寫作者一樣,艾薩克森和格里利都是科學領域里喜歡多管閑事的旁觀者,他們有著緊挨著科學大發現中心的前排座位,也有能力打開實驗室的神秘世界,讓那些不如自己有特權的人一窺其真貌,還以此為樂。在打亂了時序的一段段有趣敘事中,艾薩克森把自己描繪成一位置身于科學家群體中的科學家,在傳記主角們的工作場所里時就和主角們一樣極為自在。他的書里有著滿滿當當、形形色色的人物,還給大大小小每一位科學家都配了圖,他們都在將CRISPR從一個想法轉變成一種可運用技術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為了讓杜德娜在這個萬花筒般的陣列中脫穎而出,他有時會在她的競爭對手身上少費些筆墨。沙爾龐捷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例。艾薩克森把她描述成一個害羞、時髦、法國味十足的人,與他筆下的杜德娜所具有的勇敢、關注性別議題、具備市場洞察力、道德意識顯著、擁有戰略眼光的人格大相徑庭。如果說沙爾龐捷也有自己的科學遠見和學術熱情,艾薩克森并沒有對我們多提。
格里利與他筆下的角色保持了更遠的職業距離,但他也煞費苦心地和自己故事中的角色熟絡了起來。在他的敘述中,不時會插入一些有關CRISPR科學家的文字框,內容簡短又八卦。在這些文字框中,他解釋了他是如何了解到每一個人物的,更有趣的是,他描述了自己個人對他們的態度。(例如,他“起初并沒有立刻喜歡上”大衛·巴爾的摩,但是“如今已漸漸變得很喜歡、很尊重他了”。)
在 CRISPR的眾多用途中,艾薩克森和格里利最著迷于它治愈基因缺陷、完善甚至改進自然的潛力。他們認為CRISPR第一次把我們的遺傳控制權交到了我們自己的手中,而且他們似乎接受了基因決定人類未來的觀點,而并非更強有力的、持相反立場的生物學和社會學觀點。因此,這兩位作者提出了類似的核心主張:CRISPR是地球上生命的游戲規則改變者,它將被用來深刻地改變人類這一物種。唯一的問題在于,是否應該對它的使用加以限制。格里利和艾薩克森都沒有表現得太過謹慎,只要掌控著這項技術的人在他們看來心懷責任感即可。
讀者是否應該輕易地認同這些自信的斷言呢?需要重新評估。有點自相矛盾的是,艾薩克森還在書中介紹了生物黑客喬西亞·扎伊納(Josiah Zayner)的事跡(從“生物黑客”這個名頭就能看出,此人的研究超出了科學的常規道德準則),提出當胚胎的基因組被有意編輯時,“我們的人性”就“永遠改變了”。艾薩克森將扎伊納與史蒂夫·喬布斯相比,引用了蘋果“非同凡響”系列廣告中的臺詞,提及“不適應環境的人、叛逆者和麻煩制造者”“推動人類向前發展”。但是如果相關科研人員只是簡單地吸納了這個非常美國式的、通過破壞性創新來達到進步的圖景,并依此行事,那么他到底犯了哪些罪呢?
這個問題要求我們認真反思人類遺傳學領域中的“改善”和“進步”意味著什么。然而,艾薩克森和格里利都沒有解釋,為什么編輯基因編碼序列應該被視為等同于推動人類前進。兩人都沒有提及基因決定論的科學和倫理局限,也不曾談起私人資金和私人權力在美國科學界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也許這就是為什么,他們都略帶自滿地認為科學家應該自己制定規則來指導自身研究的方向和應用,即使這項研究涉及對人類遺傳動手腳。
對于艾薩克森來說,事情很簡單。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過得最好。艾薩克森筆下的女主人公杜德娜在自己組織的會議上進行了一次“道德之旅”,她在早期曾對人類胚系基因編輯心懷厭惡,認為這是違逆自然的,但父母們拼命為孩子尋找治療方法的樣子幫助她克服了這種心理。艾薩克森認為,她有能力引導我們,因為她現在能夠自在地兼顧科學家和人文主義者的身份。艾薩克森隱晦地承認,我們的集體選擇可能會讓我們“像我們的西紅柿那樣,變得寡淡無味”。沒有跡象表明,父母對身高、眼睛顏色甚至智力的偏好可能是由于對種族、階級或性別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態度而產生的偏見。
格里利知道事情要復雜得多。正如他的著作所記載的那樣,法律很重要,但法律主要是作為一個神秘的系統發揮其重要性,它必須由像他這樣的專家擔任知識淵博的向導來使用。的確,科學發現并不是完全脫離社會現實的。有各式各樣的背景規定,比如在美國有禁止植入轉基因胚胎的禁令,迄今為止還未有人破戒,但是這些還不夠。格里利主張在國家層面對編輯人類胚系基因立法,主要是基于實用主義的理由。他更喜歡清晰的規則,并煞費苦心地教育讀者了解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在管轄權上的變幻莫測——它的局限性、它的模糊性以及它在問責能力上的失敗。這是一幅形式上正確但沒有靈魂的圖畫,格里利以此說明了管制CRISPR使用的原因,但對反對其使用的社會、文化和道德層面的論點卻不甚公正。我懷疑格里利的說法只會鼓勵自由主義者,他們認為科學——格里利說到這個詞時用了首字母大寫——應該自行規劃其發展道路。
這些輕松隨意的書讀起來很容易,但它們幾乎沒有觸及技術科學革命的表面——它們更多地在關注我們如何利用新技術,而非我們為什么應該或不應該利用新技術。這恰說明了過分沉湎于科學寫作這種視角和方式本身的危險。為了探究CRISPR對人類的威脅和可能帶來的美好前景,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對探索勇敢新世界高聲歡呼的故事,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探討兩個問題:“誰的知識最重要?”以及“這些知識該指引我們走向何方?”
資料來源 American Scient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