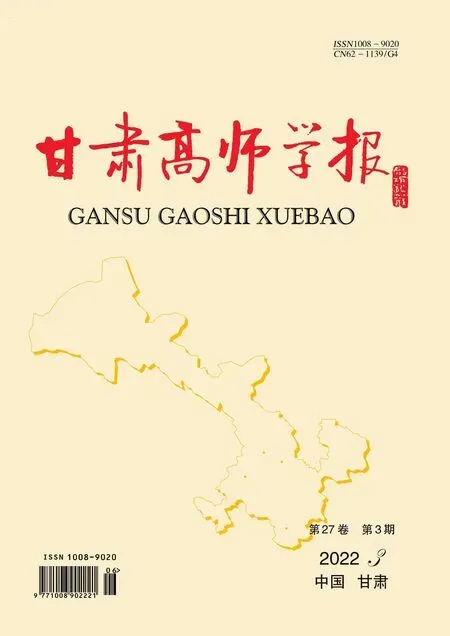基于敦煌出土文獻的西北方音研究述評
尹 雯
(1.蘭州工業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蘭州 730050;2.西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甘肅蘭州 730070;3.南方科技大學 人文科學中心,廣東深圳 518000)
二十世紀初,敦煌藏經洞因發現大批唐代前后的文獻而舉世聞名。這批文獻既有失傳已久的古代字書、《切韻》系韻書、音義類寫本殘卷等,也有古書傳抄本、敦煌俗文學作品、佛經、醫書、算經、日歷以及各類社會經濟文書、軍事文書寫卷,還有藏文、粟特文、突厥文等其他文字對音材料。因多為手寫本,抄撰者和翻譯者在傳抄過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方言痕跡。它真實記錄了唐五代時期語言文化的方方面面,是許多傳世文獻所不能比擬的。張涌泉先生表示:“敦煌語言文學研究與敦煌文獻整理,是敦煌學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幾個領域。”[1]從羅常培先生用敦煌文獻來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開始,學者們認識到敦煌文獻的語言學價值。王新華在其博士論文《唐五代敦煌語音研究》[2]中用圖表形式對照了周大璞、張金泉、周祖謨、羅常培四位先生整理的韻部,但沒有對基于敦煌出土文獻的西北方音研究進行細致述評。
根據《敦煌吐魯番學著述資料目錄索引(1909—1984)》[3]《敦煌吐魯番學著述資料目錄索引續編》[4]《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08—1997)》[5]和網上學術資源刊布顯示,涉及敦煌文獻的漢語方言研究論著有40 余篇(部),多數為語音研究。本文進一步梳理與敦煌出土文獻相關的西北漢語方言語音研究成果,以期能深入挖掘其語言學價值。
一、基于敦煌對音材料的方音研究
敦煌文獻中有不少吐蕃人學漢語用的經卷,譯者方言能代表唐五代時期流行于西北的一部分方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繼鋼和泰的《音譯梵書和中國古音》(1923)、汪榮寶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1931)之后,羅常培先生利用漢梵對音來擬測漢字古音,著《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6],開啟了利用敦煌文獻研究區域方音史的學術新風尚。羅先生將漢藏對音《千字文》殘卷、《大乘中宗見解》殘卷、藏文譯音《阿彌陀經》殘卷、藏文譯音《金剛經》殘卷、《開蒙要訓》及《唐蕃會盟碑》拓本對音材料與《切韻》音系對比,系統擬測了敦煌對音材料所代表的方言音系。羅先生還將山西的興縣、文水,陜西的西安、三水(今旬邑縣),甘肅的蘭州、平涼六地方言與擬測的唐五代西北方音進行對比。
沿著羅常培先生開啟的研究之路,一代代學者前赴后繼。日本語言學家高田時雄在其《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1988)[7]中以漢語音韻史研究方法為縱軸,以基于敦煌文獻的實證為橫軸展開,進一步補充和修訂羅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漢藏對音材料,并嘗試復原九、十世紀中古時期的敦煌及河西方言面貌。
儲泰松先生在《梵漢對音概說》(1995)[8]中分析了敦煌對音文獻梵文中的輔音,認為譯主既結合方音來譯經,也兼顧了流行于當地的通語,這些梵漢對音材料反映的是北方方言。在《唐代音義所見方音考》(2004)[9]一文中關注了敦煌出土文獻里的玄應《眾經音義》、窺基《妙法蓮花經音義》、云公《涅槃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等唐代佛典、史書音義中的方音現象。這兩篇文章涉及文獻較多,都基于對譯者方音的研究,讓我們了解了唐代方言分區的主要輪廓、語音差別、北方方言特點以及南北方音的差異,認為中唐以后南北方音的差別加大,而北方內部的方音差異縮小。
我國境內所出土的粟特語文獻年代最早的是斯坦因在敦煌得到的一些信件。聶鴻音的文章《粟特語對音資料和唐代漢語西北方言》(2006)[10]將粟特語對音材料結合同時代的波斯語—漢語對音進行音韻學分析,認為這些資料可以用作研究漢語西北方言史和晉語史的參考。他的另一篇文章《漢語西北方言泥來混讀的早期資料》(2011)提到:“在敦煌藏經洞所出的漢字注音本《開蒙要訓》里也可以見到泥來混讀的現象,溺注音為歷、罐注音為農。這里泥來混讀不限于洪音,不過看不出是讀n-還是l-。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P.3861 號佛經寫卷中的咒語把梵文音節nam音譯為攔或梨難,這似乎表明當地方言是把泥來二母混讀成了n-。”[11]
此外,博士論文有史淑琴的《敦煌漢藏對音材料音系研究》(2008)[12],通過整理分析21 種敦煌出土的漢藏材料,對其所反映的語音系統及藏語的特點作了細致的研究。
總體來看,學者們已經意識到敦煌對音材料里有大量方言痕跡,方言范圍不外乎西北方言。在研究過程中都結合了漢語語音史相關研究成果,嘗試在文獻中探索西北方言里n、l 不分等情況。這些研究中使用的方言例證不多,且大都不是一手田園調查材料,如日本學者論對音材料里的河西方言,恐有偏差。
二、基于敦煌韻書、字書以及經部文獻的西北方音研究
敦煌本《文選音》包括P.2833 號與S.8521 號兩個寫卷。周祖謨先生撰文《論<文選音>殘卷之作者及其方音》(1966)[13],討論了西北方音問題;張金泉先生關注到了“重字反切”[14];韓丹、許建平等學者沿此路深入討論“切上字重”“切下字重”[15],認為《文選音》具有重要的音韻文獻價值。
龍晦先生通過細致校對羅常培先生所未見之材料:吐魯番出土的唐代卜天壽《論語》,進一步分析144 對互注字,發現只有15 對字有音變,認為八世紀西北語音與內地基本一致,晚期的變化比較大。[16]
《字寶》是唐五代時期民間流傳的一種字書,全書總計3738 個字,按四聲收入434 條常用詞語,并注以反切或漢字直音。劉燕文的《從敦煌寫本<字寶>的字音看晚唐五代西北方音》(1989)[17]一文對《字寶》中的反切和直音進行分析研究,探求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特點。張金泉在《敦煌遺書<字寶>與唐口語詞》(1997)[18]一文中進一步將《字寶》注音及其被注字與《廣韻》音對比,找到了一些羅常培先生所歸納的止遇二攝互注等唐西北方音。
許建平先生在《唐寫本<禮記音>考》(1991)[19]里指出,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元韻轉入寒類,與寒、桓、刪、山、先、仙六韻通押,入收聲消變,[y][u]分化。
黃易青先生《<守溫韻學殘卷>反映的晚唐等韻學及西北方音》(2007)亦從出土韻書入手,認為“此卷還反映晚唐西北方音,其中有確鑿材料反映晚唐輕唇已在輕唇十韻中分化完畢,正齒音二三等相混,正齒音濁塞擦音床與濁擦音禪相混,洪轉為細與濁塞擦轉為濁擦有關;覺、藥合流,職德與陌麥昔錫相近”[20]。
徐朝東、唐浩在《敦煌韻書P.2014、2015 異常反切考察》(2015)[21]一文中利用敦煌韻書P.2014、P.2015 的不同與其他韻書的異常反切,推求唐五代時期西北方音,發現全濁聲母清化、知二與莊組相混、同等韻合并,佳韻部分喉牙音字歸入歌麻韻,元歸入仙先韻、影喻疑三母相混、仙先合并、入聲尾消失、濁上已變去等,并積極求證于同時期其他語言材料。
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采用分析互注字、觀察反切、與《廣韻》對比等方法,總結其中的語音變化規律。學者們還積極求證于同時期其他語言材料,將其放入漢語史中作進一步研究。
三、基于敦煌詩歌、俗文學中的方音研究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邵榮芬先生以《敦煌變文集》《敦煌曲子詞集》等材料中的別字異文為觀察對象,作《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1963)[22]一文,為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作出了卓越貢獻,其后一些學者尋此路關注敦煌俗文學中的各種語言現象。張金泉在《敦煌曲子詞用韻考》(1981)[23]中認為,敦煌曲子詞純樸自然的語言,保存著古代西北口語。他對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所收錄曲子詞的韻腳進行了歸納整理,得出18 個韻部。孫其芳的文章《敦煌詞中的方音示例》(1982)[24]認為,敦煌詞表現了一些西北方音,特別是甘肅方音,主要體現在一些同音致誤的字詞中,抄錄者在抄錄時,隨聲致誤,如《天仙子》中“如”作“無”、《獻忠心》中“仙”作“香”等,文中結合甘肅方言作了簡要分析。汪泛舟在其文章《敦煌曲子詞方音習語及其他》(1987)[25]中認為,敦煌曲子詞與唐五代邊地一些方言詞不無關系,這從許多詞篇的押韻中可以看出,如《望江南》《定風波》等,他還提到敦煌詞出現了四聲通葉的詞以及雙疊詞、慢詞。陶貞安的學位論文《敦煌歌辭用韻研究》(2004)[26],以任半塘先生的《敦煌歌詞總編》為基礎材料,進一步分析唐五代北方語音。霍文艷的學位論文《敦煌曲子詞用韻研究》(2008)[27]通過研究法藏、英藏、俄藏以及部分甘肅藏敦煌文獻中917 首敦煌曲子詞用韻狀況,進一步揭示元入寒先、“濁上變去”、“入派三聲”等北方通語的語音演變情況,關注-m、-n、-η 三韻尾相混等唐五代西北方音特征。徐朝東在《敦煌韻文中陰入相混現象之考察》(2011)[28]里羅列了敦煌曲子詞中4 例、變文中2 例陰入混押的材料,認為入聲字同陰聲字合押在敦煌曲子詞與變文中并不多見,而敦煌詩歌中則無一例此現象。曲子詞和變文中的陰入混押,體現了唐五代時期西北尤其是河西地區的方言里入聲韻尾已開始消變。
學者們以項楚先生校注的《王梵志詩校注》、張錫厚先生的《王梵志詩校輯》和徐俊纂輯的《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為語料,分析敦煌詩的押韻情況,開展語言學研究。都興宙的文章《王梵志詩用韻考》(1986)[29],通過對王梵志詩全部押韻字的歸納排比,得出25 個韻部,認為王梵志詩韻部所反映的初唐時期北方語音既與《廣韻》音系有所區別,與晚唐五代變文、曲子詞所反映出的北方實際語音又有不同。苗昱在《王梵志詩、寒山詩(附拾得詩)用韻比較研究》(2004)[30]中認為,王梵志詩中出現了效攝和流攝、效攝和蟹攝、果攝和蟹攝、止攝和假攝通押等情況,-m 尾向-n 的靠攏已經露出端倪;江部與東鐘部近,與陽唐部遠。丁治民、趙金文的文章《敦煌詩中的別字異文研究——論五代西北方音的精見二系合流》(2009)[31],補充映證了羅常培先生所說的精、見二系自五代起開始合流。
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韻,方法多為對韻腳的系聯、整理、分析,也有學者關注聲與調。黎新第在系列論文中討論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入聲韻尾、個別聲母以及異等韻母相混的情況,如《入收聲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應已趨向消失——敦煌寫本愿文與詩集殘卷之別字異文所見》(2012)[32]。其《對幾組聲母在五代西北方音中表現的再探討》(2015)[33]一文,分析了精、莊、知、章、見五組聲母在五代西北方音中的分合與擬音,對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新的支持與補充修正。
徐朝東的文章《敦煌世俗文書中唇音問題之考察》(2018)[34],認為輕重唇音在隋唐五代的音義材料里可以分成兩種情況:一種是《切韻》系列韻書里輕重唇聲母切上字仍有相混;另一種是實際口語中,輕唇音和重唇音分化已經完成,明微分化的速度稍慢,全濁奉母開始清化,非敷奉合流已成為河西方音重要的語音特征。
四、基于敦煌變文、愿文的方音研究
變文是唐五代民間流行的一種說唱文學,其形式多種多樣,有“講經”“論議”“轉變”“說話”等。敦煌變文更接近當時口語,是中古漢語研究中的代表性語料。其中的別字異文和韻文資料極為豐富,具有重要的語言學研究價值。周祖謨先生的文章《敦煌變文與唐代語音》[35]羅列了52 種講唱韻語,辨析其韻類,歸納出二十三個韻攝,并借用《四聲等子》十六攝的名目按陰陽入三聲的次第,將各攝摘要舉例排出,認為中唐以后北方的音韻系統已經不同于《切韻》,變文的押韻部類代表北方實際語音,現在北方普通話的韻母系統就是在這二十三攝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周大璞先生的《<敦煌變文>用韻考》(1979)[36]系列論文也對二十三個韻部作了分析,并與《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的二十三攝五十五韻和《漢語發展史》的晚唐韻部二十七韻作比較,分析了“鄰韻通押”的情況,最后談了入聲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逐漸消失,濁上已經開始變去。都興宙先生的文章《敦煌變文韻部研究》(1985)[37]得二十四部,并與《廣韻》進行對比,認為雖然有入聲字混用現象,但不能說明入聲字混而為一甚至消失。變文所代表的韻部,不僅僅是西北或某一地區的方言韻部。楊同軍先生的學位論文《敦煌變文的語音系統》(2003)[38]從聲母、韻部、聲調三個方面歸納了敦煌變文的語音系統,探討其特點和性質,認為敦煌變文的語音系統與《切韻》音系已大有不同,如輕重唇音分化、全濁聲母消失、韻部系統大大簡化、入聲韻尾弱化、濁上變去已經形成等。
敦煌愿文是敦煌文獻、石窟題記和絹書、幡繒中的請愿文章,它數量大,內容廣,材料豐富,記錄了唐五代時期西北地區的語言面貌。李海玲的學位論文《敦煌愿文別字異文材料所反映的語音問題》(2013)[39]以《敦煌愿文集》為底本,以同音替代為選取標準,對愿文中的別字異文材料進行分析,并與同時期其他敦煌文獻、現代西北方言比較,發現了一些語音現象,如輕唇音分化、非敷奉合流、知章組合流、精組見系相混、云以代用、濁音清化、止攝不分、-n 與-m 尾開始相混、鼻音韻尾有消變跡象、全濁上歸去、入聲開始消失等。
以上學者均將敦煌變文、愿文看成統一整體去研究其中的語音特點。但是,這一部分的材料多為口耳相授所得,講經人很可能來自中原等佛教傳播較為廣泛的地區,如當時的長安、洛陽等地,抄經人的籍貫也各異。如此看來變文、愿文里的方音會因講經人、抄經人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嘗試區別對待這些材料。
五、結合敦煌文獻的現代敦煌漢語方言語音研究
許多學者在研讀敦煌文獻的過程中,將其與現代方音聯系起來。儲泰松在其著作《唐五代關中方音研究》(2005)[40]中將敦煌文獻與現代關中方言對應。這些研究絕大多數是借用現代方言學者的研究成果。語言學家李藍先生則用實地調查得來的第一手敦煌方言語音資料,結合敦煌文獻進一步對羅常培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成果展開對比研究。他在《敦煌方言與唐五代西北方音》(2014)[41]一文中認為羅先生的研究雖然運用了現代方言,大致建立了現代方言與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對比關系,但是他手中的甘肅漢語方言的調查材料非常有限,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用到敦煌文獻嫡傳地——現代敦煌方言的調查材料。因此,李藍先生繼續沿用羅先生的研究方法,將親赴敦煌調查所得的現代敦煌方音乃至甘肅全省的方言,與敦煌文獻、《切韻》音系聯系在一起,細致構建對比關系。他認為,雖然現代敦煌方言并非唐五代時期敦煌方言的嫡傳后裔,但其來源不外乎清中葉甘肅56 州縣移民帶來的甘肅方言,總體來看仍與甘肅及其他西北方音一致,屬同一方言區域,所以仍可用比照研究《切韻》音系的方法,把敦煌方言和甘肅省境內的其他漢語方言視為一個整體,將其看作是敦煌文獻的基礎方言,以此為基礎來研究現代甘肅方言與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對應關系。
六、結論
基于敦煌出土文獻的西北方音研究,將中古漢語語音研究、西北漢語方音歷史演變研究、現代西北方言語音研究有機統一在一起,總體呈現以下特點:
1.敦煌出土文獻蘊藏著豐富的西北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
作為唐代陸上絲綢之路重鎮的敦煌,在當時國際交流頻繁、民族融合深入。敦煌出土文獻里的對音材料集合著藏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于闐文、龜茲文等多民族語言文字,這些語言和漢語間的譯音也隨之興起。從本文介紹的這些研究成果來看,譯者多為北方人,且兼顧了當時的通用語,所以北方方言是其語言翻譯基礎。敦煌詩歌、曲子詞、變文等中大量的別字異文為西北方言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語料。所以,敦煌出土文獻體現了西北方音已成為學界共識。這些基于敦煌出土文獻的西北方音研究不僅有助于進一步認識《切韻》、觀察唐五代“官話”以及梳理中古漢語語音發展史,亦可用于研究藏語等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發展史。
2.敦煌出土文獻與現代西北方言,尤其是甘肅漢語方言之間能互證互通
周祖謨先生認為研究現代北方話與普通話發展史應從敦煌出土文獻時期的語音狀況研究起。羅常培、李藍、儲泰松、王新華等學者都嘗試將敦煌出土文獻與現代西北方言,尤其是甘肅方言聯系起來進行對比研究,李藍先生認為疑母讀同見母這一條是甘肅漢語方言確為敦煌文獻、唐五代西北方音基礎方言的鐵證。還有一些學者在敦煌出土文獻中尋找西北漢語方言詞匯的蹤跡。雖然五代后敦煌等西北地區喪失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出入口功能,從而導致歷史文獻的斷層和居住人口斷層,但這并不影響現代西北方言可以為敦煌文獻的整理提供互證校勘研究。李正宇文章《敦煌方音止遇二攝混同及其校勘學意義》(1986)[42]運用敦煌方音止遇混同的規律校勘敦煌遺書,舉50 例求本字,體現敦煌方音的校勘學價值。王耀東、敏春芳的《敦煌文獻的方言學價值》(2011)[43]一文舉例說明可以利用敦煌文獻擬測唐五代西北方言,研究現代西北地區的方言,反過來看還能解決同期傳世文獻中有關方言的一些難題。
3.敦煌出土文獻有效助推漢語語音史研究,尤其是西北方音歷史演變研究
基于敦煌出土文獻的漢語語音史研究、西北方音研究,總體上還是沿著羅常培先生開辟的研究之路在走。研究方法大致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通過觀察敦煌出土文獻里的押韻、譯文、別字異文等,尋找有關語音的文獻例證,并進一步深入到語音史層面展開對比研究;另一種是用現代西北方言、已有的語音史研究成果去印證解釋敦煌出土文獻里出現的語音現象,對文獻進行校勘學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唐代語音有二十三韻部,已經開始了從四聲八等到四呼的簡化過程;已有輕唇音,出現濁音清化現象,逐漸區分送氣與不送氣音,全古濁聲母仄聲送氣,泥來相混,疑母讀同見母;陰入混押,入聲韻尾開始脫落,-n,-m 尾開始相混;梗攝與齊韻、宕攝與果攝有合并現象,魚止通轉、止蟹二攝韻母合流等等。敦煌出土文獻印證了聲調方面濁上歸去的重要規律,這一時期入聲在西北方言里逐漸消失并開始分派四聲。
基于敦煌出土文獻的西北方音研究仍有許多值得繼續研究的地方,如敦煌文獻中的別字異文非常多,尚未整理窮盡;羅常培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中諸多觀點需要更多的敦煌文獻材料例證與現代漢語方言例證;在漢語語音史研究方面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繼續探索,如西北方音鼻韻尾的演變情況、韻母混押的規律、精見二系合流情況、泥來混讀、來母字為什么會譯為d-等等。還可以進行基于敦煌對音材料的北方少數民族語言研究。西北方音研究亦可用于對敦煌出土文獻的校勘,上文所述的“互證”研究當有可為。張涌泉先生認為,今后的敦煌語言文學研究以及敦煌文獻的整理,應從“資料更全、研究更精、圖版更清晰”三個方面繼續努力,那么基于敦煌出土文獻的西北方音研究隨著資料的豐富與方言調查的深入,將會有更多、更新的成果,這也是我們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