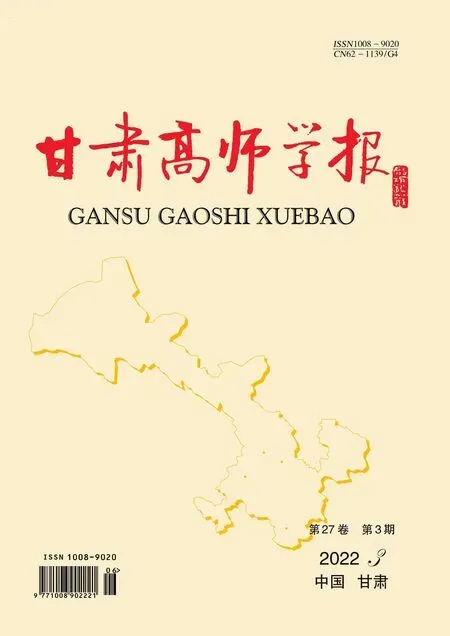論《共產黨宣言》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邏輯之維
張嘯鵬,趙繼龍
(1.蘭州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蘭州 730000;2.蘭州城市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蘭州 730070;2.西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400715)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要)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敢于斗爭,善于斗爭。”[1]新的時代背景下,進行偉大斗爭首先要強基固本,堅守思想陣地,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地位。“當今時代,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時并存,先進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織,社會思潮紛紜激蕩。”[2]因此,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洞察解構各種社會思潮、肅清西方意識形態對我國社會發展的裹挾、從根本上認清資產階級實質仍是理論領域不可忽視的問題。然而,隨著國際環境的深刻變化,“社會趨同論”“階級斗爭熄滅論”“歷史終結論”等主張一度甚囂塵上,“顏色革命”、歷史虛無主義以及由新自由主義引發的諸多動亂事件也并未退出歷史舞臺,因而重新摭拾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資產階級的批判,以科學眼光從典籍中汲取現實力量,成為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應有之念。有鑒于此,本文嘗試以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代表性著作《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為例,通過解構馬克思恩格斯對資產階級批判的歷史之維、實踐之維、理論之維,還原兩位經典作家“資本邏輯”批判的背景、過程及意蘊,為當下意識形態工作的開展貢獻學理支持與理論定力。
一、歷史之維:以雙向視野厘清資產階級功過,確立批判起點
資產階級是以無償占有生產資料和工人勞動為特征,依靠雇傭勞動不斷攫取剩余價值的資本家階級。即便是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從表面上看是職業、身份和地位之區別,實質仍是階級之差異”[3]。換言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層級分化仍以資本剝削和財產占有為分野,從歷史發生學的角度講,這種分野有其自身的邏輯:揆諸《宣言》全文不難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對資產階級的考察本身就內含一種“縱橫雙向整合的歷史觀”(the historical view of two-way in length and breadth)。
(一)以縱向視野肯定資產階級的歷史貢獻
就縱向歷時維度而言,《宣言》指明相對于封建社會,脫胎于行會師傅、工場主的現代資產階級“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政治理念方面,資產階級掙脫了封建牢籠的桎梏,它以世俗化的行為取向斬斷了各種封建羈絆,將“神本”思維和宗法觀念徹底嫁接到了資本之上,以一種“利益至上”和“有限自由”的原則重構了社會框架,實現了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跨度,“民主”“平等”“法權”等政治觀念也由此興起,統一性的政府、法律、關稅國家得以建立;思想文化方面,隨著資產階級活動范圍的擴大,資本主義擺脫了“保守”“愚昧”的窠臼,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的相關知識不再是某一民族、某一區域的“專屬”,逐漸演變為“公共財產”,“世界性文學”也逐漸形成。可以說,資產階級構建起了文明溝通的早期橋梁。
然而,資產階級最卓著的貢獻體現在生產力的極速發展上,“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4]。作為產業革命的執牛耳者,英國率先啟動了以機器解構舊世界的工業革命。在這個過程中,機器、鐵路、化工、電報、輪船、河川開墾等新興行業崛起,生產工具、生產關系實現了重大突破。資本邏輯的支配下,資本控制了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全過程,創造了“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5]405的經濟財富。同時,資本的全球擴張構建了世界性的貿易消費市場,它打破了地區、民族、國家之間的封建壁壘,促使國際關系和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嬗變,以西方資產階級為主導的世界經濟有機體由此確立,資本主義一體化時代導致“東西方大錯位”格局形成,“民族歷史”突破了地域限制,逐漸擴展為“世界歷史”,人與人之間的地理、空間距離“突變式”縮減,“資本邏輯”的積極性得到了盡致體現。
(二)以橫向視野揭露資產階級的現實弊病
就橫向共時維而言,資產階級取得的歷史功績背后,都有一個與之相對應的“陷阱”:它在經濟發展、政治構架、思想文化和對外關系上的成就實則是與其弊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首先,資產階級掙脫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卻創建了新型的政治壓迫。中世紀由教會所把持的基督教宰制被推翻后,“宗教”并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從18 世紀到19 世紀,新世界的外殼中依然存在舊的剝削樣式,19 世紀建立起的所謂的“人民政府”體制,真正擁有權力的并不是人民,而是政府官員以及各級代表,真正的人民依舊是被宰制的對象。但同時,尋求政治權力壟斷的過程也培育出了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無產者。其次,生產力的“顯性發展”仍舊未能突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隱性藩籬”。資本積累的不斷加劇、資本技術構成的不斷提升使得“勞動異化”“科技異化”日趨嚴重,造就了新的“社會控制形式”和紛繁蕪雜的社會問題,“絕對貧困”“相對貧困”成為工人無法掙脫的生存困境。再者,資本主義社會所謂取代舊式道德的新式道德,不過是“資本至上”的金錢崇拜,它將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等原始情感物化成了利己主義,家庭關系、職業溫情、名譽感等原有情感也成為“物化”的現金交易。最后,世界歷史的開辟實質是以資本主義為中心的輻射圈。“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流通空間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更多地消滅空間。”[6]世界市場的擴張,不僅使得“鄉村從屬于城市、東方從屬于西方”,也造就了“人從屬于商品”的事實,“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5]404,使資本的爪牙在全球擴散,企圖讓世界成為其資本擴張的操練場。換言之,資本主義帶來生產力發展的另一面,是由資本邏輯引發的全球性“時空失序”,批判資產階級、超越資本邏輯已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必須直面的重大命題,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此“二律背反”的窘境中確立了批判起點。
二、實踐之維:以現實論戰清算資產階級謬論,揭露批判本質
“政治上采取誠實態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采取欺騙態度,是軟弱的表現。”[7]因此能否真實反應自身的主張往往是一個階級、政黨本相的重要體現。《宣言》立足于當時共產主義面臨的現實境況與挑戰,對資產階級污蔑、誹謗共產主義的言論進行了精彩批駁,這些駁論以“財產占有、分配”的經濟維為基點,關涉“祖國”“民族”“政權”等政治維以及意識形態、哲學思想等文化維,以實踐論戰的方式推動了資本主義批判,詮釋了《宣言》批判本質的實踐邏輯。
(一)“財產、自由”之爭:共產黨人真正要消滅的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
“財產、自由”之爭的焦點在于“消滅私有制”消滅的是個人財產、個性、自由還是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針對資產階級的詬病,馬克思恩格斯從三個方面對其命題進行證偽:第一,財產來源的混淆。即資產階級財產從何而來?兩位經典作家嚴格區分了小資產階級、小農的財產與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指明前者已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自動退出了歷史舞臺,共產主義真正要消滅的是資產階級靠雇傭勞動創造的私有財產,因此資產階級所謂“共產黨人要消滅個人財產”之主張是一個偷換概念、錯置條件的偽命題。第二,財產歸屬的錯位。即資產階級財產最終去向何處?作為人為制造的貧民,雇傭工人的勞動不可能給自己帶來財產與自由,其唯一任務就是給資本家增殖。資產階級以剝削手段控制了財產去向,所以就財產歸屬來看,由異化產生的“顛倒錯位”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將資本家占有的社會財產歸還給社會,實質上是對“錯位”的轉正,它并沒有消滅財產,只是改變財產的占有權和歸屬而已。第三,政治借口的嫁接。即共產黨人的矛頭對準的是誰?在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勞動造成勞動主客體的倒置,支配人的“現實的活的勞動”,人成為物的奴隸;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被倒置的主賓關系得以糾正,“生產社會化”的另一端不再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人的主體性得以回歸,不再受物的支配。質言之,共產黨人要消滅的根本不是人的個性、自由與合法財產,它要消滅的自始至終都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以及建立在這種剝削關系之上的“變態”的個性與自由。
(二)“家庭、教育”之爭:共產黨人要消滅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和不正常家庭關系
“家庭、教育”之爭的焦點在于共產黨人是否真的要消滅一切教育、家庭、實行公妻制。資產階級首先在教育問題上對共產黨人展開了攻擊,宣揚共產黨要消滅一切教育,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產者唯恐失去的那種教育。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把人訓練成機器”[5]417,這種教育將終極目的訴諸于維護階級統治,與真正意義上的“開啟民智、傳播文化”相差甚遠。其次,資產階級誹謗共產黨人“要消滅家庭”,認為共產黨人用社會教育代替家庭教育,是以社會吞噬家庭組織、親密關系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指明,資產階級家庭“只是在資產階級那里才以充分發展的形式存在著,而無產者的被迫獨居和公開的賣淫則是它的補充”[5]417-418。換言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家庭的完備形式只是資產階級的專屬,貧困的無產階級沒有能力組織家庭,因此被迫獨居或者公開賣淫。另外,“消滅家庭親密關系”的真正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為正是“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5]403。最后,《宣言》有力回擊了資產階級所謂“共產黨人要實行公妻制”的謬論:馬克思恩格斯聲明,“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公妻制”之間并不存在任何必然聯系,將自己的妻子看作單純的生產工具是“資本邏輯”的產物,共產黨人無意產生這樣怪誕的想法,“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8]647,馬克思主義的使命之一就是要消滅將婦女僅僅視作生產工具的狹隘觀點,使婦女獲得真正的解放。
(三)“民族、祖國”之爭:共產黨人要消滅的是民族對立的根源
“民族、祖國”之爭主要圍繞“工人沒有祖國”之命題展開,早在《自由與和諧的保證》一書中,魏特琳已經指明:“現在我們沒有祖國,只有到社會以平等的一視同仁的方式照顧到它一切成員的生活的時候,我們才會有一個祖國。”[9]到了《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沒有的東西”[5]419,這句話卻被資產階級過度解讀為“共產黨人要取消民族,消滅祖國”。事實上,對于該命題應緊扣“工人”與“祖國”兩個關鍵詞來理解:一方面,在資本主義語境下,“工人”成為被剝削、壓迫的對象,作為“人為制造”的貧困階級,經濟上的一無所有決定了政治上的被宰制,他們是被鎖鏈束縛的階級,“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國的、不是英國的、不是德國的民族性,而是勞動、自由的奴隸制、自我售賣在國內,貨幣是工業家的祖國”[10],因此,在一個資本至上的社會中,“工人”始終是“帶著鎖鏈,被整個官方社會壓榨、宰制”的階級,政治地位無從談起;另一方面,“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根本不具備“真正的共同體”之功能,“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5]402。因此,“工人沒有祖國”意指資本主義社會中根本不存在保衛工人的利益共同體和國家機構,只有當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后,才談得上自己的祖國。可見,資產階級以有意或無意的方式蒙蔽該命題的本質,進而在理論上駁斥共產黨人的主張,實質是為消散其統治危機而進行的政治操弄。
(四)“意識形態”之爭: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
資產階級不滿足于僅用上述問題攻擊共產黨人,還將責難的觸角“上升”到了宗教、哲學等意識形態領域:他們鼓吹共產黨人主張“宗教消滅論”“廢除真理論”“取消道德”,認為共產主義的出現是違背歷史進程的怪事。為了對其進行批駁,馬克思恩格斯確立了如下的批判理路:第一,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之原理指明了資產階級的根本性錯誤。“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了解嗎?”[5]419-420即是說,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由其所處的經濟地位所決定,無法跳脫“資本邏輯”的歷史怪圈。第二,以“階級斗爭思想”預告了資產階級理論的破產。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盡管社會上涌現出各種形形色色的社會意識,但是共產黨人能夠通過階級斗爭掌握政權,捍衛科學社會主義真理,到那時,階級對立將完全消失,資產階級各種參差不齊的理論學說也將宣告破產。因此,資產階級所謂的美好主張,只能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才能真正實現。第三,以“兩個決裂”徹底聲明了共產黨人的革命主張:消滅私有制以及私有制基礎上的傳統觀念。可以說,“意識形態”之爭是馬克思恩格斯與資產階級論戰的高度總結,它將資本主義批判上升到思想文化層面,回應了共產主義社會中全體成員身體、精神共解放的偉大目標,是對《宣言》中資本批判的至心性表達。
三、理論之維:以文獻剖析解蔽“社會主義”學說,深化批判意旨
19 世紀上半葉,由于資本主義自身的弊病加之時代的錯綜嬗變,在西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各種以社會主義為幌子的學說流派,馬克思恩格斯基于其產生的階級根源和利益立場,以理論批判的方式揭露了其實質,豐富了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基理。
(一)“反動的社會主義”是資本邏輯的倒退
封建的社會主義企圖將歷史退回到封建時代,作為被資產階級排擠掉的王公貴族,他們宣揚封建時代的輝煌,實質上是為落后制度唱挽歌,“可憐的貴族老爺們,因淪為暴發戶的手下敗將,無力于政治斗爭的他們,唯一的抗衡工具便只剩文字斗爭了。”[11]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盡管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均是“剝削時代”,但是就歷史發展進程而言,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是進步的體現。從現實角度來看,封建貴族們言行不一,他們同樣參與到鎮壓無產階級的行列中去,剝削工人階級,是比資產階級更為落后的群體。
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企圖將歷史退回到“小私有制”時代,即主張用小生產來代替資本主義大生產,恢復中世紀的小手工業和小農經濟,他們搖擺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并常常倒向資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評論它是“工業中的行會制度,農業中的宗法經濟”[5]426,兩位經典作家的表述內含這樣的言外之意:就資本主義發展來看,它大體經歷了行會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大機器工業三個階段,小資產階級的主張實際上是鼓動人們回到資本主義的“初級形態”——行會手工業中去,這種主張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最終只能淪為“一種怯懦的悲嘆”。
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則企圖將歷史退回到空想、思辨的“語詞”時代,這類主張以“愛的說教”展現其超階級性,卻陷入了形而上學的窠臼:他們將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獻機械復制到德國,試圖掩蓋階級矛盾,看不到解放社會的革命主體和力量,只是一味地詛咒資產階級的競爭、新聞出版自由、法律及代議制國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它只是“嚇唬來勢洶洶的資產階級的稻草人”[5]428,其抽象又不切實際的“語詞游戲”根本無法解決現實問題,最終只能淪為資產階級政府“用來鎮壓德國工人起義的毒辣的皮鞭和槍彈的甜蜜的補充”[5]428。
(二)“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是資本邏輯的變體
“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企圖引領人們走進“新的耶路撒冷”,這些包括經濟學家、博愛主義者、人道主義者、慈善事業組織會、戒酒協會等在內的各種“小改良家”,他們認為消除社會弊病的最佳方式不是暴力革命與階級斗爭,而應該是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的“改良主義”,即以資產階級內部的改良方案緩和、拯救資本主義矛盾。法國政論家、經濟學家蒲魯東于1846 年寫成的《貧困的哲學》就是其典型文獻,該書主張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商品交換是任何社會都必須的,社會需要的是以改良主義來消除弊病,而不是無產階級的政治斗爭。實際上,這種社會主義只是對資產階級管理國家的粉飾,它無意也無力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歸根結底,不過是資本邏輯的變體。他們主張自由貿易、保護關稅和監獄改革,表面上看是為無產階級所做的聲討,其實真正目的在于誘使工人放棄一切政治運動,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恩格斯諷刺地說道:“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個論斷:資產者之為資產者,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5]430即是說,作為一種改良主義主張,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非但沒有觸及社會主義的核心,反而在維護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其真正目的在于使工人階級放棄一切政治斗爭和維權運動,以方便資產階級通過局部調整統治方案而維護社會運行,實質上不過是資本邏輯的變體,變相地為資產階級說話而已。
(三)“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醞釀資本邏輯的核爆
“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以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的主張為代表,它內含“批判”“空想”雙層含義。“批判”即指此類思想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上升到了質的層面,較之以往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它具有不可忽視的歷史進步性;“空想”則指它沒有觸及解放社會的現實力量和現實渠道,仍然有其局限性,以三位思想家設計的未來藍圖為例,“實業制度”“和諧制度”“公社制度”等固然表達了早期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愿望,卻無法將其訴諸于現實的革命行動,只是短暫的思想實驗。但不可忽視的是,正是這種社會主義的先聲醞釀出了資本邏輯的核爆——科學社會主義。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深入到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與私有制,曾創造性地提出消滅城鄉對立、私人經營、雇傭勞動等設想,這些主張已經具備共產主義社會的雛形,因而也被馬克思恩格斯稱為“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體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國的理論上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站在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三個人的肩上的他們天才地預示了我們現在已經科學地證明了其正確性的無數真理。”[8]37事實上,空想社會主義也成為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的直接思想來源,即孕育了資本邏輯的核爆。
四、余論
事實上,《宣言》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內含“為真理、解放、自由而斗爭”的價值旨歸。早在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時期,馬克思恩格斯就對平均共產主義理論家魏特琳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輕視理論必將導致科學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受阻;在《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一書中,馬克思又深刻批駁了蒲魯東的改良主義;《宣言》則通過學理性的批判肅清了各種誹謗共產主義的現實問題與理論學說,捍衛了科學社會主義真理,展現出“捍衛真理、追求解放”的科學精神。即便是在經濟全球化日臻成熟的今天,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的極端異化也并未消失,“壟斷資產階級在全世界到處投機套利,不僅使世界經濟結構越來越來越虛擬化,導致實體經濟空心化”[3],進而使得金融寡頭與普通勞動階級間的貧富差距愈加縱深化,因此,全球范圍內工人力量的集結與突破資本異化的斗爭仍未停止,持續推進勞動形式的重塑,變雇傭勞動為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實現“勞動不能再變為資本、貨幣、地租,一句話,不能變為可以壟斷的社會力量”[5]416之設想,仍舊是“人的解放”的重要使命。
當前,面對中國發展國內外環境的新劇變、新風險、新挑戰,我們理當以《宣言》對資本主義的多維批判為循理,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一方面,要透視資本主義本性及發展規律,警惕西方意識形態滲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思想輿論領域大致有紅色、黑色、灰色‘三個地帶’。紅色地帶是我們的主陣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帶主要是負面的東西,要敢于亮劍,大大壓縮其地盤;灰色地帶要大張旗鼓爭取,使其轉化為紅色地帶。”[2]要善于從馬克思主義典籍中汲取力量,以階級分析、階級批判為武器,積極防范和應對風險挑戰,高度防范“黑天鵝”“灰犀牛”事件。另一方面,要敢于消解資本邏輯的負面影響,堅持共同富裕原則,在勞動過程中注重人的主體性,避免因貧富差距擴大而產生“馬太效應”“食利者階層”,著力破除資本弊病,卸除GDP 主義的“緊箍咒”,綜合考慮發展的質量、結構、規模、速度、效益、安全等系統性要素,將“生產力發展”之“本”與“各經濟要素”之“標”相結合,為協同發展做好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