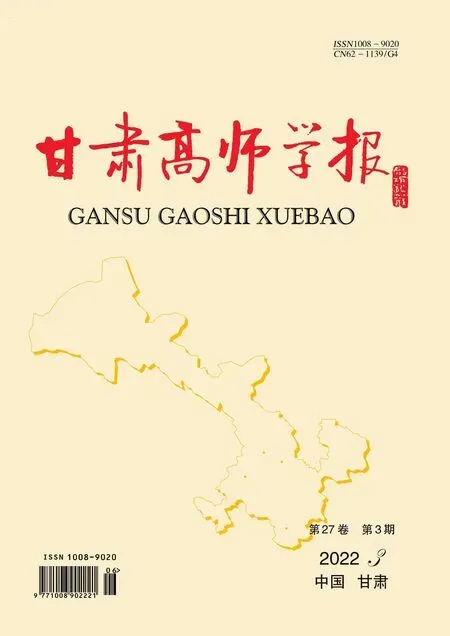再論教育研究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何學斌
(甘肅民族師范學院教育科學系,甘肅合作 747000)
學術研究的起點是問題,問題的提出由研究對象的特殊矛盾引發;教育研究的對象是教育現象,教育現象的矛盾既有局部微觀層面的表面性、淺層次矛盾,又有整體宏觀層面的體系性、根本性矛盾。教育研究的意義在于不僅要為教育實踐者提供指導教育實踐的理論支撐,還要解決教育實踐領域出現的各種現實問題和矛盾。在教育研究中,統籌好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兩者的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教育研究的理論意義
要討論教育研究的理論意義,需要先對“理論”的概念作進一步的辨析。所謂理論,是指人們按照已有的知識經驗,通過一定的方法對自然、社會現象進行的合乎邏輯的可靠總結。需要注意的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理論建構邏輯是不同的,自然科學通常基于純粹理性,指向公理式的原則和方法,而社會科學往往基于價值理性,指向信念般的原則和方法。[1]281更有學者指出,社會科學的生命力主要表現為對相關社會現象的解釋力和批判力。[2]164所以,作為社會科學的教育研究,其理論意義就在于研究者能否按照已有的知識經驗,通過一定的教育研究方法對教育現象這一特殊研究對象進行合乎邏輯的可靠總結。基于以上觀點,教育研究的理論意義主要包括兩方面,即就學科理論體系建設而言,在知識體系的建構和研究方法的使用兩個層面是否有創新點。其中學科知識體系層面的創新是指其研究結論要么能夠對宏觀層面的教育體系性和根本性的矛盾作出一些新的、合乎邏輯的解釋,要么能夠有預見性地指出教育現象的內部矛盾可能呈現出的某種新趨勢,并提出相應的解決策略。同時,一個學科領域的發展,特別是理論體系的發展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其研究方法的發展。而對于教育研究而言,基于教育現象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通過有效融合內化其他學科和領域的研究方法進行教育研究方法的創新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依據。一般而言,能夠達到這兩個方面要求的教育研究成果就可以看作對教育學科知識體系的建構有創新和貢獻,這樣的教育研究成果就是有理論意義的。同時,理論有其評價標準,在愛因斯坦看來,評價科學理論的兩個標準是“外部證實”和“內部完備”。所謂“外部證實”是指理論不應當與經驗事實相矛盾,這是衡量理論的外部標準;所謂“內部完備”是指基本概念及其理論本身的邏輯自洽性、簡潔性,這是衡量理論的內部標準。[3]10-11從“外部證實”和“內部完備”這兩點來審視教育研究的理論意義,就要求教育研究產生的理論必須具有普遍適用性和高度概括性。所謂普遍適用性是指這種創新理論必須是能夠普遍適用于學前教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等眾多教育層次中的某個層次,也就是應當至少與某一層面教育實踐的經驗事實相符,滿足“外部證實”;而所謂高度概括性是指這種理論能夠簡潔明了地揭示教育體系內部矛盾的因果關系或內在規律,也就是邏輯自洽并簡潔明了的,滿足“內部完備”。總之,一種新的教育理論的形成,往往標志著教育研究者對教育現象本身的矛盾和發展規律有了更進一步、更深層次的認識和把握。
教育研究往往可以從教育現象的系統性、根本性矛盾問題的研究中衍生出一系列次生問題,進而呈現出研究邏輯上的問題鏈,推動教育研究以由淺入深、逐次遞進的形式向更加微觀具體和更深層次的方向推進。教育原創理論因其高度概括性和普遍適用性,在一些教育微觀領域的深層次、具體問題的研究當中,就能扮演類似理論支撐、邏輯基礎或研究范式、原則的作用,為微觀層面的教育問題研究提供基本的前提和遵循,同時也能為同一類型的教育研究提供研究方法上的“原型”和“模板”。所以,筆者認為,教育研究的理論意義主要體現在“原創性”“創新性”,這種“原創性”“創新性”既包含對教育系統性、根本矛盾性問題的合乎邏輯的創新解釋,從而產生新的教育理論,也包含以教育基本理論的創新為教育微觀領域相應問題研究提供的新理論架構和新研究方法。[3]30-37
所有學科的發展其理論體系的建構總是處于不斷的積累、補充、發展、變化過程之中的,正如前述“社會科學的理論往往基于價值理性,指向信念般的原則和方法”,賦予教育研究理論意義是教育研究的應有之義。在教育研究中產生的眾多的教育理論中,從層次看,既有宏大理論,也有中層理論,還有微觀理論;從表現形式看,大致包括教育思想、教育學說、教育學術流派、教育觀點、教育主義等等;從教育理論的產生過程和途徑看,有借鑒其他學科理論產生的,有運用多學科研究方法產生的,有通過案例研究凝練總結的,也有對原有理論進行深加工產生的;從教育理論表現出的成熟程度而言,有相對成熟的理論、有些是尚不成熟的半成品,還有些只能視為理論加工的原材料。但不論是何種階段、何種層次、何種途徑、何種形式的教育理論,對教育理論體系的建設來說都是有價值、有意義的。也就是說,賦予教育研究一定的理論意義應該成為所有教育研究者的一種基本意識,而且這對進一步提高學科成員的學科自覺、學科認同和學科情感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教育研究的實踐意義
貝爾納通過對人類科學史的研究,指出:“科學的社會功能由兩條途徑來實現,其一是通過科學研究促成的技術改革,直接地和自覺地對社會產生作用,其二是通過思想的力量,不自覺并間接地對人類社會產生作用。”[4]513這里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他提出的“技術途徑”和“思想途徑”也清晰地闡明了科學對于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產生影響的方法和路徑。但問題在于,現實的社會實踐活動當中,社會及市場對“技術途徑”往往持一種極端實用主義的態度,人們對新技術的產生往往是熱情高漲,趨之若鶩,但對“思想途徑”因為其作用和影響不那么顯而易見,往往又表現得不夠重視,經常處于無人問津的尷尬境地。這樣導致的后果是,會讓我們對科學研究的意義在認識上出現偏差,而這種情況在教育研究領域尤為突出。
教育從本質上來講是培養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參與教育活動的利益相關方通常包括國家層面的教育管理和決策部門、地方層面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各級各類學校層面教育組織與管理者、教育實踐活動的參與者——老師和學生,還有更廣義的教育參與者——社會家庭層面的各級各類學生家長。但無論是那個層面,普遍存在的問題是,人們對教育研究通過所謂的“技術途徑”體現教育價值存在嚴重的誤解,主要表現為大多數人認為教育研究成果的意義在于,不但要能為教育決策者的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實踐活動的直接參與者開展教育實踐提供科學的理論和事實依據,還要做到無縫銜接,拿來即用,甚至要求召之即來,即插即用。這種極端實用主義態度無疑是對科學研究“技術途徑”的最大的誤解,更是一種功利主義導向下的惰性思維。要知道即使是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也無法實現科學研究的理論成果向市場最終產品的直接轉化,而是要依賴相關企業根據科學研究的理論成果結合市場進行進一步的研發投入,才能最終實現終端產品市場化。而眾所周知的是,社會科學領域研究成果的社會功能性相較自然科學領域而言,更具潛在性、隱藏性和間接性。社會科學的性質決定了其研究成果不可能在社會實踐領域直接應用,而是需要有具體的參與者、實踐者結合自身實際和特定情境進行進一步再研發、再創造。比如教育研究微觀領域的教法研究,研究者研發出來某種先進的新式教學方法,想要使用這種新教學方法的教師是無法在自己的課堂上毫無保留地照搬套用的,想要用好這種教學方法,還需要使用者以這種新教學方法為藍本,結合具體的教學科目、教學內容和受教育者的實際情況進行教案的再設計,這個針對教案的再設計過程實際上就是對新教法研究成果的“再研發”。再比如,在教育宏觀領域的教育政策研究中,其研究成果本身也不能直接作為教育政策來頒布實施,從初步的研究成果到成文的教育政策,中間也需要教育管理和決策部門結合當前社會發展的現實和教育事業的現狀進行再創造、再研發,才能形成符合國情、切合實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文本。可見,不論是教育微觀領域的研究還是宏觀領域的研究,研究成果在通過“技術途徑”彰顯其實踐意義方面,因學科性質導致的潛在性、隱藏性和間接性是非常明顯的,這種無可避免的潛在性、隱藏性和間接性導致人們普遍對教育研究實踐意義的態度多多少少有些急功近利。
教育研究的實踐意義更多的是通過“思想途徑”來實現。所謂“思想途徑”,就是通過研究成果,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以理服人,讓教育實踐者接受新理論、新觀點、新方法,通過影響教育實踐者的教育理念、提高對教育本質和規律的認識、改進教育教學方法等使教育實踐者的專業能力不斷提高。“思想途徑”是教育研究最重要的社會功能的體現。比如,教育研究在宏觀層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邏輯體系明確、系統化的理論知識,這些知識本身就具有強大的思想力量,能夠對人的教育理念產生強烈的沖擊和影響。教育研究成果以“思想途徑”彰顯著其重大的實踐意義。這種意義從內容上講,可以讓教育實踐者更深刻地理解教育實踐活動的本質特征,更全面地掌握教育實踐活動的基本規律,并指導教育實踐者樹立正確的教育價值觀,堅定其從事教育事業的理想信念。從方式上講,有些教育研究成果以潤物無聲、潛移默化的形式影響教育實踐者的思想觀念和教育價值觀,有些則以讓教育實踐者對教育實踐中出現的一些困擾和復雜問題產生“頓悟”的方式得以表現出來。從結果上講,如心理學所闡明的,人的心理活動中認識層面與行為層面的邏輯關系一樣,認識是人一切心理活動的開端,同時也是行為的先導,教育研究成果通過改變教育實踐者對教育實踐活動的認識,引發情緒情感的變化發展,進而形成某種態度上的傾向性,最終引導其教育行為(意志行動)的改變。從范圍講,教育研究成果在通過思想途徑傳播的過程中既有廣泛性,也有普遍性,教育實踐領域的實踐者和利益相關方,從教育政策的決策者、制定者,到地方教育管理部門,再到各級各類學校的師生員工,間接參與教育實踐活動的各級各類學生家長,都會受到這些教育研究成果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會超越學科邊界,影響與教育密切聯系的社會各界、各層次的廣大民眾,形成“破圈”效應。
三、教育研究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的統一:困境與反思
從教育研究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的關系維度來審視和反思教育研究,從而促進教育學的學科發展是當前我國教育研究領域的著力點,由此也產出了大量的學術成果,這些學術成果對于指導我們科學高效地開展教育實踐活動,實現教育事業的高速發展發揮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眾多的教育研究中,也確實存在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脫節的現象。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是部分教育研究者秉持一種“理論至上”的誤區而忽視教育研究的實踐意義,這類研究者癡迷于概念的演繹和思辨的邏輯推理,并將理論邏輯不假思索地套用于實踐邏輯,這樣不僅造成前述理論與實踐的脫節,還造成教育實踐活動的兩個主體——理論主體和實踐主體之間的嫌隙甚至敵對,實踐者在理論者面前自慚形穢、不敢發聲,理論者在實踐者眼中紙上談兵、百無一用;其二是由于學科制度化和傳播機制,當前主流的教育研究主張采用固定的程序和范式,這種程式雖然有利于教育學學科知識的整合,但無形中造成教育不同層面與內容之間的割裂。專業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學科知識的產出是單向輸出的,實踐主體被排除在知識生產之外,良性的雙向溝通匱乏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區隔。[5]63在學科制度形成之前的社會中,如古希臘和中國先秦時期的教育中就不存在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問題。當然,學科制度的發展和形成是人類認識能力和科學發展的大勢所趨,在“科學”語境下是不可逆的存在,由此造成的教育研究領域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難以有效統一的矛盾畢竟也只是外部因素。
關于教育研究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關系的解答,有一種非常貼切的比喻,有學者將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比作酒與糧食之間的關系,酒雖然作為實踐的產物由糧食釀造而成,但不能簡單的在這兩種東西之間劃等號。同樣,教育研究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所遵循的邏輯基礎不同,理論遵循推理的邏輯,而實踐遵循事實的邏輯。學者石中英對這一命題有更精辟的說明,“教育實踐的邏輯即非一種純觀念的存在,也非一種純實體的存在,而是一種介于兩者之間或兼容主觀性和客觀性的文化的存在”[6]9。所以,教育研究的理論意義絕不應該簡化為一般的應用型理論,而是以“思想途徑”發揮其實踐影響。當人們接受了科學思想就等于是對人類現狀的一種含蓄的批判,而且還會開辟無止境地改善現狀的可能性。[7]514教育研究的“思想途徑”所表現出來的實踐意義,實際上正是從理論到實踐,從研究者向實踐者,從學術研究機構到全社會的傳播過程。所以,我們也可以把教育研究的這種“思想途徑”看做是“技術途徑”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或者說這體現的是教育研究在更廣義上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的統一,既可以豐富教育學科知識理論體系,也能更好地為教育實踐活動提供理論依據。從這一層面講,只要能夠實現教育研究思想力量和行動力量的結合,也就能實現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統一。這就要求教育研究者(理論工作者)秉持一種充分尊重和共情的態度,更多地貼近實踐工作者的立場來觀察、體驗和談論教育實踐及其邏輯,扮演教育實踐的“建議者”而非“指導者”。也要求教育實踐者,特別是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師和管理隊伍更廣泛地參與到教育研究中來,教研相促,努力實現教育學知識生產的雙向互動,扮演教育理論生產的“參與者”而非“旁觀者”。
要使教育研究兼具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教育研究的選題、方法應該走向多元化,強調開放性,注重整體性,既鼓勵用實證方法從微觀的課程、教法、個體的心理變化等微觀問題入手研究解決教育實踐中存在的現實問題,也要提倡運用理論思辨的推理方式從教育體系的宏觀性、根本性矛盾問題著手研究豐富、創新教育思想和理論體系。倡導多學科、多層次、多角度研究共生共存,取長補短、相互競爭、相互促進,是教育研究最理想的狀態,也是有利于教育學科繁榮發展的最佳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