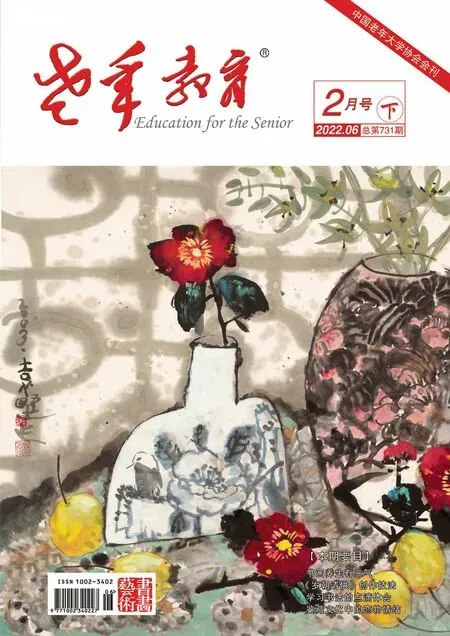圖說小楷技法(三十三)
□ 劉小晴
“勢”是中國書法一個極為重要的美學范疇,其藝術內涵十分豐富。勢產生于“氣”,“氣”本于天賦,基于學力,成于修養而流露于筆墨間。
古人很早就觀察到自然界中有種無形的力量左右著事物的發展,一切變化都按其內部規律運動著,這就是“氣”和“勢”的作用。老子《道德經》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其中的“道”即太虛,“一”即元氣,“二”即陰陽,“三”即陰陽和諧,和則潤生萬物,變化出焉。這種樸素的辯證思想對中國的美學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古人又深刻地認識到,人的一切活動都必須順應自然的客觀規律,只有這樣才能于規律中獲得絕對自由。孟子首先提出“吾善養乎浩然之氣”。“氣”是潛伏于事物內部的一種客觀規律,因而很自然地被運用到文藝中。曹丕《典論》中說:“文以氣為主。”在書法理論中,東漢蔡邕首先提出“勢”的概念,他在《九勢》中說:“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構成書法藝術最本質的“氣”是由陰陽而產生出的“形”和“勢”。西漢王充《論衡》中提出“陽氣主為骨肉,陰氣主為精神”的論斷,這種思想實際上是書法中“形質”和“神采”的濫觴。
所謂“筆勢”,是研究用筆中點畫合乎情理的運行軌跡,這種軌跡雖然沒有固定形狀,但必須符合客觀規律。勢由結構、行氣、章法所構成,點畫與點畫之間的內部聯系組成“結構”,字與字之間的內部聯系組成“行氣”,行與行之間的內部聯系組成“章法”。“勢”在書法中大都是無形的,在行草中雖偶爾顯露出“勢”的形跡,但也只是用虛的手法表現出來。“勢”雖然隱以神運,大象無形,但在書法藝術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作小楷最要講究豐神,古人觀察到“神”與“氣”的關系最為密切,如東漢茍悅《申鑒》中說:“凡言神者,莫近乎氣。”氣不但是生命運動中力的表現,也是一個人精神氣質的表現。清代包世臣《歷下筆談》中說:“字有筋骨血肉,以氣充之,精神乃出。”所以字有氣有勢,則整幅章法,精神貫注,意態活潑,一氣團練,藩籬完密。雖然書寫小楷并沒有行草那樣磅礴萬物、揮斥八極、酣暢淋漓、氣吞河岳的氣勢,但它卻潛伏于里,于端莊靜穆中蘊藏著一種動勢,這與行草是一脈相通的。

小楷貴于自然,點畫與結字在形態上雖然千變萬化,但筆法是因筆勢的作用而產生的,所謂因勢生形,故凡得勢的作品,分肌劈理,因勢利導,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風出巖岫,無心而有態。每一個點畫都被安排在恰當的位置上,十分熨帖,合乎情理,所謂“文從理順,操縱自如,造化在筆端也”。只有合乎情理、順乎勢道的作品,才能合乎自然。
小楷難于生動。生動雖然涉及用筆的規律、姿態的跌宕和筆力的充沛,但最關鍵的莫過于氣勢。氣盛則縱橫揮灑,筆機流暢,生發不窮,其間韻自生動焉。清蔣衡《拙存堂題跋》中說:“夫書,必先意足,一氣旋轉,無論真草,自然靈動。若逐筆安頓,雖工必呆。”清代的館閣體小楷,雖以工整見長,但是勢不靈動,字無姿態,至有“算子”之謂,故小楷最忌平排無勢。
由上可見,筆勢是表現書法藝術內涵的空間意境,是氣韻生動自然的重要表現手法。下面我們就來談談小楷筆勢和貫氣的具體方法。
初學小楷,當以形求勢,得勢后方能因勢生形。以形求勢,首先要熟,熟在法而不在貌。筆法圓熟,方可入筆勢之門。清方薰《山靜居畫論》中說:“收畫至神妙,使筆有運斤成風之趣,無它,熟而已矣。”熟則大小長短,高下欹正,隨筆所至,自然貫注成一片段,而筆勢自生。古人作小楷,運筆如飛,而點畫周到,結字妥帖,行行有活法,字字皆生動,只一個“熟”字。
字要有勢,又當以“力”為后盾。“氣”來源于筆力,“韻”流露于修養。唐太宗《論書》說:“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王羲之小楷無一筆不到而能處處流轉,無一筆粗俗而能字字用力。有勢則筆意酣暢生動,有力則點畫沉著飛翥,故學書者當首重氣、力二字。
字欲有勢,必先意足。所謂“意足”,即在作書前,意在筆先。當先培養其興致,興致勃發,勢乃合拍。胸有成竹,至臨寫之時,興會之際,機神所到,隨其意態,以成其妙。得勢則隨意經營,生發無窮;失則極力收拾,滿幅皆非。當其落筆之際,時覺手心間有勃勃欲發之勢,便是機神初到之兆,此時最要善于把握住這一稍縱即逝的創作靈感。這種方法在書寫行草時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但在書寫小楷時,亦當富有這種興致,不可為法度所囿。

《自書告身帖》唐·顏真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