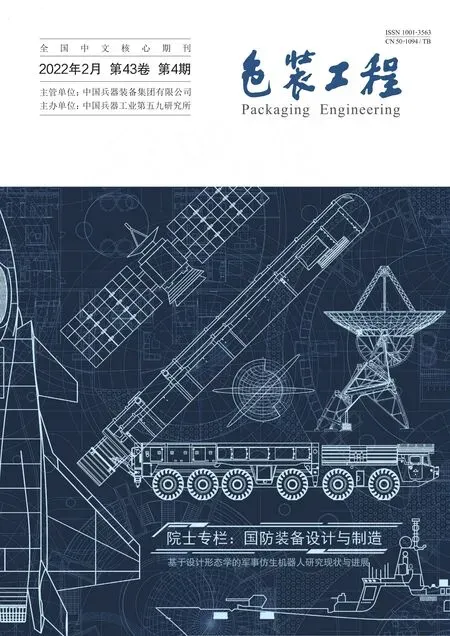基于HAAT 的運動性失語癥老人溝通輔具設計研究
蔣旎,李然,劉春堯
(1.西南交通大學,成都 611756;2.西南財經大學天府學院,成都 610052)
運動性失語癥又稱布洛卡失語癥(Broca’s Aphasia,BA),為腦卒中疾病常見后遺癥之一,臨床特征以口語表達障礙為突出特點,但聽力、理解力不受影響[1]。據NESS-China 調查顯示,我國老年人已成為腦卒中發病的主要人群[2],而患運動性失語癥的老人無法與人正常交流,嚴重影響其身心健康。面對這一問題,借助溝通輔具,可有效改善患病老人的溝通能力,從而達到減輕家庭照護負擔,增進家庭成員親密關系的目的。中國已進入老齡化階段,并逐漸向重度老齡化轉變[3]。這意味著,我國對老年溝通輔具的需求是巨大且急迫的,堅持和發展輔助器具的科研開發既是國家政策,更是市場需要的必然體現[4]。
1 溝通輔具概述
溝通輔具是協助言語障礙者參與溝通互動,滿足其表達思想、交換信息、康復訓練、維護人際、保持尊嚴等需求的輔助器具。根據應用技術特征的不同,溝通輔具可分為低科技溝通輔具(溝通薄、溝通圖卡、溝通板等)和具有打印或聲音輸出功能的高科技溝通輔具(計算機溝通系統、語音溝通儀、智能鍵盤溝通系統等)[5],常見的幾類溝通輔具見圖1。低科技溝通輔具簡單易制,成本低,但溝通內容受限;高科技溝通輔具個性化強、溝通內容豐富,但成本偏高。隨著電子產品的普及化,高科技溝通輔具逐步向以計算機、平板電腦、智能手機為載體置入輔助溝通系統軟件的形式轉變,而非僅僅研發專門的、單一功能的溝通輔助儀器,導致成本大大降低,開始發揮其溝通輔助的價值和優勢。

圖1 常見的幾類溝通輔具Fig.1 Common types of communication aids
國內輔具研發由于缺乏對設計的重視與投入,造成產品品種較少、質量與檔次不高的行業現狀。溝通輔具作為其中一類,其產品研發所面臨的困難則更為明顯:首先,溝通輔具多由職業康復師、特殊教育者牽頭研發設計,注重功能實現,但在系統交互、界面、視覺設計方面難以帶給用戶良好的體驗;其次,溝通輔具用戶側重面向自閉癥、孤獨癥、腦癱等特殊兒童,產品功能以語言學習和表達訓練為主,界面風格普遍偏低幼化,并不適合老年人。要設計出適用于運動性失語癥老人的溝通輔具產品,國內設計領域應當給予更多的關注與投入。因此,本文引入康復學中HAAT模型的基礎理論和概念框架,并從設計學領域的角度,提出輔具設計的策略與方法,再以之為指導展開對運動性失語癥老人溝通輔具產品的設計實踐。
2 HAAT 模型理論發展與應用
人類活動輔助技術模型(Human Activity Assistive Technology Model,簡稱HAAT 模型)于1995 年由Cook 和Hussey 提出[6],它是對Bailey(1989 年)描述的人因工程方法的一種改編形式,用于輔具的設計、開發、用戶評估和效果評價,被視為是一種理論依據及實踐操作指南。
HAAT 模型是一種輔助技術模型,其由人(功能障礙者)、活動、情境和輔助技術四個核心要素組成,即在特定的情境下,人(功能障礙者)通過與輔助技術的相互配合,從而完成一定的活動,最大限度地達到生活自理和社會參與。HAAT 模型三個發展階段見圖2。Cook 和Hussey 于1995 年首次提出HAAT 模型,見圖2a;Cook[7]與Miller Polgar 于2008 年對模型進一步推演,見圖2b;Giesbrecht.Ed[8]于2013 年的HAAT 模型改進方案,見圖2c。Giesbrecht.Ed 的改進模型在前兩個階段的基礎上,更明確了HAAT的要素地位和理論內涵:代表“人(功能障礙者)”的球體位于模型中央,突出了“人(功能障礙者)”在模型里的中心地位;“活動”和“輔助技術”相互交織于中間區域,表示需要優化兩者之間的匹配,其中,人機界面是關鍵;外部球體是包絡其他三個要素的所有情境,展示出情境對其他要素的廣泛影響。

圖2 HAAT 模型三個發展階段Fig.2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HAAT model
Chang Y J 和Wang T Y[9]運用HAAT 模型指導設計了一款基于藍牙和掃描技術的尋路測向設備模型,為認知障礙者提供導航服務,并通過測試得出該模型人機界面友好、尋路功能可靠;Routhier 等人[10]通過HAAT 模型分析輪椅的設計和結構,探析影響輪椅移動的各種因素,提出評估輪椅移動性能的概念框架;Louie 等人[11]利用HAAT 模型闡釋專為一個中國先天性上肢缺陷婦女設計的喂養裝置,參與者在使用定制喂食裝置后,表示具有良好、積極的體驗。
3 基于HAAT 模型的運動性失語癥老人溝通輔具設計策略
HAAT 模型中的四個核心要素,“人(功能障礙者)”“活動”“情境”“輔助技術”,從設計領域的角度可具體表達為“運動性失語癥老人”“溝通任務”“使用情境”與“溝通輔具”,運動性失語癥老人溝通輔具設計的HAAT 模型要素及內容見圖3。由此,依據Giesbrecht.Ed 改進模型的理論內涵,分析各要素的主要內容及特點,結合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理念,提出基于HAAT 模型的運動性失語癥老人溝通輔具設計策略。

圖3 運動性失語癥老人溝通輔具設計的HAAT 模型要素及內容Fig.3 HAAT model elements and contents in the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aids for the elderly with Broca’s aphasia
3.1 以用戶為中心全面評估功能特征
不同的運動性失語癥老人在個體功能特征上存在較大差異,他們在感官功能、認知功能、運動功能等方面的強弱,會對溝通輔具的使用效率產生直接影響。因此,設計師需積極配合康復師,參與到全面評估老人功能特征的過程中,通過獲取與分析影響因素,指導設計以提升溝通輔具的易用性與適用性。運動性失語癥老人評估內容見圖4。

圖4 運動性失語癥老人評估內容Fig.4 Assessment of Broca’s aphasia in the elderly
1)感官功能。老人隨著年齡增長,感官功能下降,對外界事物的敏感度減弱,刺激閾值增加,意味著需要更強的感官刺激才能引起機體反應。感官功能衰弱是不可逆轉的客觀生理規律,但通過設計可以加強、輔助與支持他們在視覺、聽覺、觸覺方面的功能,幫助提升自身的生活自理能力。例如,視覺方面,加大界面目標文字或圖片的尺寸,增加目標主體顏色與背景色的對比度,突出目標的視覺焦點信息。聽覺方面,提供語音信息幫助用戶更好地認知和指導產品操作,運用樂音、自然音等反饋方式做出功能提示或提醒[12]。觸覺方面,在產品表面增加必要的凹凸感、顆粒材質,或增加振動、溫度變化等方式給予老年人易于感知的提示。
2)認知功能。當交互界面設計與老人的認知特點不符合,存在認知上的不匹配時,老人在使用產品過程中就會遇到各種問題與困難,造成焦慮、排斥、恐懼等負面情緒。因此,溝通輔具設計應當以老人的使用經驗、記憶、學習能力和識字能力等為指導,在產品界面設計中采用適合他們認知方式的輔助性溝通符號。輔助性溝通符號,是利用身體以外的符號來完成溝通過程,從具體到抽象,包括實物、模型、照片(彩色、黑白)、圖片(彩色、黑白)、文字[13]。例如,文字與圖片組合是界面信息設計的常用方式之一,對于老人,文字辨認率最好的是宋體、黑體和中圓體,楷體字較差[14]。對于識字能力差的老人,可減少文字的使用,用圖片、照片予以替代。關于圖片的使用,一方面,真實事物的照片、與實際生活關系密切的圖像能夠和老年人的經驗認知進行較好的匹配,讓他們無需太多的思考便可以理解其所代表的含義[15],而另一方面,結構、元素簡單的繪制圖片,往往又比真實圖像更清晰,更易辨認。左側的繪制圖片較右側的真實照片更易辨認,見圖5。因此,設計師需要根據老人的實際情況,保證輔助性溝通符號在易于辨識與易于理解間找到最合適位置,選取更為合適的信息內容與形式,才能設計出合格的溝通符號。

圖5 左側的繪制圖片較右側的真實照片更易辨認Fig.5 The drawn pictures on the left are more recognizable than the real photos on the right
3)運動功能。運動性失語癥老人不僅存在溝通困難,部分還伴有肢體運動功能障礙。運動由人體肌肉收縮牽拉骨關節而形成,評估骨關節活動能力和肌肉張力、耐力、協調性可以衡量老人的運動能力。作為執行操作最頻繁的部位,手(手指)成為評估運動能力的首選,手的運動能力對設計操作界面目標信息的數量、大小及目標之間的間隔距離有直接影響。例如,上肢震顫老人在點擊界面目標時由于手部震顫易發生誤操作,因此界面目標信息數量宜少,尺寸、間距宜大;偏癱老人,可將常用內容設計于健側界面,如右側偏癱者應將常用內容設計于左側界面。若老人手部運動能力差,可依次對其頭部、嘴、腳等部位進行評估,并輔以頭杖、嘴杖等工具配合用于點擊界面。若以上部位運動能力均較差,老人還可靠眼部凝視,采用眼動交互式方法進行操作。另外,沒有能力進行移動、持握、攜帶溝通輔具的老人,可考慮將輔具固定(安置支架)于輪椅、床頭等長期坐、臥的地方。
3.2 圍繞溝通任務選擇人—機輸入方式
對于運動性失語癥老人,常見的溝通任務有生活護理、病情交流、情感溝通、社會交往、突發事件等。不同的溝通任務,其優先級和特點有較大的區別,因而人—機輸入方式有所不同,溝通任務類型的輸入方式見表1。與生活護理相關的溝通任務在信息架構中的優先級最高,且根據其特點應以最少的交互步驟、最短的時間幫助使用者傳達信息和任務,如將入廁、吃飯、服藥等信息以圖片—詞組組合的形式直接展示于界面讓用戶點擊,通過語音輸出告知照護者。與病情交流、情感溝通相關的中頻任務,雖對象較固定(醫生、家人或朋友),但溝通語言不再是簡單的詞組,多以句子為常見,可采用以詞組—詞組組合為句子或文字書寫的輸入方式。與社會交往、突發事件相關的低頻任務,因其對象、內容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采用文字書寫來表達不同的溝通需求。七鑫易維“眼控平板一體機”溝通輔具三種輸入方式見圖6,分別是文字書寫、詞組—詞組組合為句子、圖片—詞組組合。

圖6 七鑫易維“眼控平板一體機”溝通輔具三種輸入方式Fig.6 Three input modes of Qixin Yiwei's “eye control tablet integrated machine” communication aids

表1 溝通任務類型的輸入方式Tab.1 Input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task type
3.3 使用情境對溝通輔具的廣泛影響
產品的使用情境是人們的心理動作及行為在特定時間、特定環境及實踐內發生的狀況,在情境中的人、物、環境一直處于交互關系狀態[16]。老人使用溝通輔具的過程中,使用情境包含場所、時間情境、物理情境三個部分。(1)場所。產品使用是在特定的場所中進行的。特定的場所,老人會產生特定的溝通需求。例如,老人走進超市,會產生向工作人員咨詢某種商品價格的溝通需求;老人去到醫院,會和醫生交流與自身疾病相關的治療方案。設計師應當充分挖掘不同場所中老人易觸發的溝通需求,為設計提供精準化、差異化的內容預設,使溝通服務更為專業與便捷,真正滿足老人在特定場所中的需求。(2)時間情境。時間是用戶需求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老人在日常生活自理中的溝通需求,與時間點有著較為顯著的關聯性,呈現出較一般人更加遵守作息時間、恪守成規的特性。基于老人的時間特性,考察他們一天的基本活動,分析出其中較為固定需求的時間點或時間段,如吃飯、睡覺、吃藥,將其納入溝通輔具設計的提醒事項,通過系統個性化設置,協助老人提高日常生活自理能力。(3)物理情境。影響溝通輔具使用的物理情境因素主要有聲音、光線、溫度。理想的溝通輔具,應當具備自動檢測當下情境中的物理信息,并做出適用于老人的即時處理。例如,在嘈雜的菜市場和安靜的書店里,系統能自動升高或降低輸出聲音的分貝;在明亮的廣場和昏暗的臥室里,屏幕自動調節光亮程度等。
4 運動性失語癥老人溝通輔具設計實踐
4.1 用戶評估
在成都市運動性失語癥老人調研過程中,設計師與康復師共同參與其功能特征評估階段,以溝通障礙者需求判定樣本問卷為依據,結合訪談對老人的身體功能、日常活動、使用智能產品情況、生活困難、溝通需求進行全面、準確地評估。從問卷和訪談資料中,篩選出對溝通輔具設計有指導意義的項目內容,用戶調研信息及評估結果見表2。

表2 用戶調研信息及評估結果Tab.2 User survey information and evaluation results
4.2 方案設計
設計實踐產品為IPAD 端溝通輔具APP——“心語”,“心語”APP 交互界面見圖7,與傳統溝通輔助儀和系統相比,其成本更低,適配性更強,易于下載與更新,普及性高。

圖7 “心語”APP 交互界面Fig.7 Interactive interface of “Xinyu” APP
“心語”APP 由生活護理、溝通交流、病情診斷和個人中心四大功能組成,功能數量適宜,操作方式簡單,交互層級少。根據調研,按照老人功能需求的高低布局功能區域面積,主頁見圖7b。“生活護理”為日常最頻繁使用的功能,因此設計其功能區域面積最大,易于點擊操作,而“個人中心”使用頻率最低,設置其區域面積最小。其次,據表2 結果得知,老人右上肢運動能力強于左上肢,以右上肢主導界面操作。為減少活動范圍和減輕操作負擔,常用功能及導航欄均設置于界面偏右側。
“心語”APP 的人—機輸入方式為圖片—詞組組合、詞組—詞組組合、文字書寫三種。“生活護理”溝通任務使用頻繁,內容簡單,采用圖片—詞組組合形式輸入;“病情診斷”“溝通交流”內容復雜多樣,設計為詞組—詞組組合成句的輸入方式;文字書寫雖輸入效率低,但具有可靈活表達溝通內容的優點,因此設置于狀態欄中,文字書寫見圖7 h,不占用界面空間的同時方便老人隨時調取使用。
APP 界面的中文字采用老人易于識別的黑體。界面主色選用綠色和白色,色調簡潔柔和,對比清晰,避免了色彩復雜,以及易造成的視覺疲憊感的高亮色。考慮到老人對圖形的識別和理解能力有限,圖標在簡化的基礎上設計形象生動的圖形符號,并附加文字力求信息傳達的準確性,而圖7b 的功能區圖標面積占比較大,可搭配實物圖片,與老人的經驗認知更好地匹配。
5 結語
國內目前現有的溝通輔具存在功能定位的偏差和交互、界面、視覺設計的缺陷,給運動性失語癥老人的使用帶來諸多困擾,難以真正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通過引入HAAT 模型,深入分析溝通輔具設計的“運動性失語癥老人”“溝通任務”“使用情境”與“溝通輔具”之間的關系,從而提出適用于運動性失語癥老人的溝通輔具設計策略與方法。結合對失語癥老人的調查訪談和功能評估,設計出一款溝通輔具應用軟件——“心語”APP,旨在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溝通提供更為輕松、便利的方式,體現了作為設計師對特殊人群的關心與關懷。此外,HAAT 模型在運動性失語癥老人溝通輔具的設計與應用上的嘗試,也將有助于該理論在輔具設計領域進一步拓展,為研究帶來新的方向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