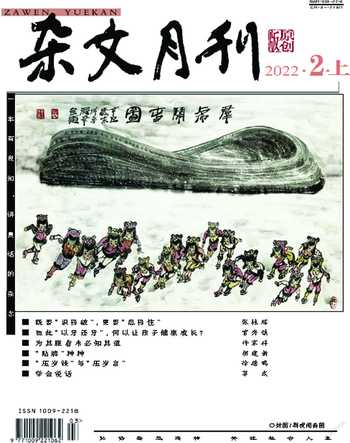才從才來
游宇明

很喜歡某位老教育家說過的一句話:才從才來。
依個人理解,此話應該包含兩種含義:一是杰出的學生是水平高超的老師教出來的,只有老師優秀,學生才可能出類拔萃;二是人才需要施展拳腳的舞臺,他在抵達大造化之初,得有其他人才賞識、舉薦、使用。換句話說是:“千里馬”必須遇上自己的“伯樂”。
沈從文是有世界影響的大作家,據馬悅然回憶,他曾經進入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之列,然而,沈從文初到北平的時候,寫的稿子得不到發表,也找不到別的合適工作,有時連吃飯都沒有錢。徐志摩做《晨報副刊》主編時,從自由來稿中看到了沈從文的作品,非常喜歡他清麗、婉轉而又細膩、優美的文風,曾經在一個月內連用他7篇作品,這對于沈從文,無疑是雪中送炭。后來,沈從文的處境日漸改善,相繼任教于武漢大學、青島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由講師而副教授、教授。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徐志摩這個“伯樂”,沈從文的文學夢想之路一定會艱難許多。
國畫大師徐悲鴻也是提攜“千里馬”的典范。吳作人讀高中開始,就非常喜歡徐悲鴻的畫。聽說徐悲鴻在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他跑去旁聽。因為接觸過某些左派人物,吳作人被學校驅逐,徐悲鴻便推薦他到巴黎學畫。民國政府教育部規定:申請出國護照,必須有大學的畢業文憑。這難住了吳作人,徐悲鴻便讓他去找田漢,田漢給其補發了一張已停辦的南國藝術學院畢業證書。經過半年的準備,吳作人考進了巴黎高等美術學校“西蒙教授工作室”。該校學費高,吳作人一籌莫展,徐悲鴻打聽到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還有一個“庚款助學金”名額,便將吳作人推薦給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院長巴思天教授,使吳作人圓了自己的留學夢。吳作人沒有辜負徐悲鴻的栽培,后來他成了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美術家之一。
任何社會都難免有一定的保守慣性,這種慣性使“千里馬”在剛冒出來的時候常常被人忽視,此種時候,“伯樂”第一時間站出來,以自己的方式表達關切,“千里馬”成長的速度就會快上許多。宋代的蘇洵、蘇軾父子以及王安石、曾鞏等人,在歷史上都很有作為,除了自我努力,與歐陽修的極力舉薦分不開。其二,國家的發展需要各種“千里馬”的支撐,而“千里馬”又是散落在不同區域的,有人發現了,我們某方面的事業才有合適的主事者、拼搏者,我們的現代文明才可能熱火朝天、蓬蓬勃勃。
做發現“千里馬”的“伯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既依賴才,更依托品。說它依賴才,是因為一個人沒才,就無法練就一雙銳利的眼睛,很難像徐志摩和徐悲鴻一樣分清誰真的有幾板斧,誰只是繡花枕頭一包糠,使自己的推舉變得精準。退一萬步說,自己沒能耐,就算你的眼力沒問題,別人也可能誤以為你推薦的人與你是一丘之貉。才華不只是代表發現的眼光,許多時候也代表你在群體中的話語權。說它更依托品,是由于相對“千里馬”,“伯樂”一般都是年紀較大、地位較高、成就較為突出的,最初舉薦的時候,“伯樂”具有明顯的優勢,得到機遇之后,“千里馬”在努力、環境等因素的加持下,其成就、地位、影響力很可能反超你,倘若“伯樂”時時刻刻都想做老大,沒有足夠的平常心,沒有開闊的格局,他的心態就會失衡,也就很難將“伯樂”長久做下去。
當“千里馬”之才不易,做“伯樂”之才更難,無論哪一種“才”,都值得我們傾心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