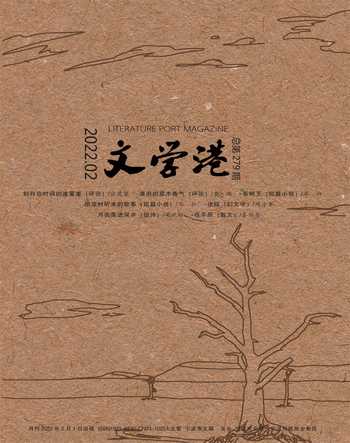凜冽的草木香氣
李璐
小說(shuō)中,在一個(gè)年假的時(shí)間長(zhǎng)度里,“我”走近了布朗山,也走近了一位守山的老茶人的生活,某種程度上解決了難以釋懷的一些情結(jié)。這一切,可能由于“我”在布朗山度過(guò)的這些時(shí)日,也由于那株神秘的“茶樹王”。
小說(shuō)敘事者是“我”,一位人像攝影師。“六十年六十人”的拍攝任務(wù)讓“我”來(lái)布朗山尋訪這位守山五十年的老茶人宋易安。老人說(shuō)自己害怕照相,拍攝限于停滯。于是“我”干脆在老人這兒住了下來(lái),平日或在周邊山林轉(zhuǎn)悠,或在門廳聽雨喝茶,偶爾與老人喝至“茶醉”的境界。某日,“我”得知山中有一棵樹齡在一千七百年以上的“茶樹王”。在親眼見到那棵千年茶樹之后,“我”又由老人的描述而神遇了另一棵生在神秘窈遠(yuǎn)、難以尋覓之地,更古老的“茶樹王”。此時(shí),老人在偏僻村寨中教書的女兒,與“我”記憶中一位不告而別的有天賦的品茶師的形象也漸漸疊合。
老人與“我”慢慢熟稔,以及“我”的轉(zhuǎn)變,都源于山中草木蟲魚、人物情態(tài)對(duì)“我”的熏染。所以,布朗山諸般景物、陰晴冷暖,以及老人的生活狀態(tài),是小說(shuō)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shuō)形成了一種類似于小說(shuō)“人物”的功能。而布朗山種種意蘊(yùn),又集中地在“茶樹王”的形象上象征地表現(xiàn)出來(lái)。讀《茶樹王》,仿若走入了一片深山茶林,云山霧海中青翠欲滴,沉沉霧氣沾衣,浸透了往來(lái)山上的人影。
讀小說(shuō)時(shí),時(shí)時(shí)有一條由綠色植物鋪成的道路,或者說(shuō)線索,接引讀者進(jìn)入小說(shuō)世界。作者從山上的蒼翠草木、氤氳水汽,寫到漫天大雨,松針清泉煮好茶,以及群山中的大湖,雨夜的松脂香、茶香,碧綠渾圓的茶樹,紅色漿果,細(xì)小魚蝦,喝茶度日的老人,清澈鮮亮的茶湯……山中景致擷入文中,細(xì)膩幽微的感觸和描摹讓整篇小說(shuō)彌漫著草木的香氣。如果將這些書寫景物的文字都標(biāo)上顏色,就可看出一條線索,在各段落中清晰地浮現(xiàn)出來(lái)。這是以山中景物編織成的暗線,卻可以視為小說(shuō)情節(jié)主線的推動(dòng)力量,是整篇小說(shuō)情境、氛圍的質(zhì)地。
正是“我”對(duì)布朗山的親近、對(duì)門前十六株茶樹的精微感知,打破了“我”和老茶人之間初為陌生人的隔膜,老人將過(guò)往生活向“我”敞開,向我講起了那棵存在于幽僻難尋之地的“茶樹王”。
小說(shuō)其實(shí)寫到了兩棵古老的茶樹。一棵,是老人帶著“本地茶葉協(xié)會(huì)的秘書、茶廠廠長(zhǎng)助理以及縣文聯(lián)的作家”,還有“我”,穿過(guò)密林,在一片空敞場(chǎng)地上看到的千年古樹。這棵樹,已經(jīng)滿足了我對(duì)于“山之靈”的想象和期待。小說(shuō)描寫“我”繞著這棵茶樹一圈圈行走,發(fā)興奮之心情:
我想象那個(gè)地下世界,在泥土深處定然存在著一個(gè)綿延萬(wàn)里的隱秘空間,所有茶樹的根系被緊密聯(lián)結(jié)在一起,……而所有生機(jī)的源頭就在這棵高達(dá)十幾米的古樹上。
讀至此,可能以為小說(shuō)題目里的“茶樹王”講的便是它了。但有趣的是,小說(shuō)在老人的敘述中,走向了一棵更神秘的老樹。這一棵,先是有論壇上尋古樹不遇的文章作鋪墊:“(一群驢友和向?qū)В┰诹肿永镌庥隽嗽幃惖臅r(shí)間,被一股隱秘的力量所阻止,怎么也無(wú)法目睹茶樹王的身影。”接著,老茶人向“我”說(shuō)起他如何在迷路的絕望中發(fā)現(xiàn)了古茶樹,無(wú)數(shù)苔蘚、藤蔓仿佛將古木“封存在時(shí)間的迷霧里”。每年他都去看它,并在門前種下一粒最飽滿、光潔的茶籽,紀(jì)念他去世的妻子。但某次植物學(xué)家、茶葉研究專家專程尋訪時(shí),他帶著他們,卻怎么也找不到這棵“他見過(guò)的最古老的樹”了。
這如“桃花源”一樣只因機(jī)緣偶爾向世人顯現(xiàn)的“茶樹王”,便因此被草白藏入了小說(shuō)深處。其實(shí),布朗山的草木世界原已形成了一個(gè)與塵囂人世迥異的存在——山外世界,有天賦的品茶師被當(dāng)成搖錢樹,不得不超負(fù)荷工作,最終喪失了品茶能力;而山中世界,于旬日間便蕩滌了“我”的世間風(fēng)塵,這里,有老茶人一年年安靜地種下古老的茶籽,長(zhǎng)出與別處不一樣的茶樹。
但盡管如此,草白并不放心,她在罕有人至的深山繼續(xù)設(shè)置了一個(gè)更難尋繹的神秘的“小世界”,將真正的“茶樹王”安放在這里。這只存在于老人講述中的“小世界”,仿若一個(gè)理念世界,可以看作對(duì)現(xiàn)實(shí)中存在的布朗山的進(jìn)一步提純,它是“只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的,只有秉持真純的心意才可能打開——在茶山中隱居多年的老人,可以偶然遇見它;在山中游蕩多日的“我”,有幸在老人的描述中摹想它。它不輕易向世人打開,尤其不向帶有鮮明目的性的世人展示。
讀者也許會(huì)想起,小說(shuō)前段,“我”驚覺山中臨時(shí)雨水積蓄的水潭里有童年時(shí)代所見的細(xì)小魚蝦時(shí),就隱晦提到過(guò)這個(gè)“藏”的問題——
已經(jīng)多年未見它們了,沒想到居然躲在這臨時(shí)水塘里。我蹲下身,默然凝視著它們。某一刻,它們似乎定住了,一動(dòng)不動(dòng)了,幻變成水草的顏色、沙礫的顏色、山林的倒影色,把自己藏起來(lái)了。待凝神再看,試圖伸手掬水,只見水面微微一晃,漣漪蕩開,所有一切乍然消失了。
這段“我”的擬想中,打破了時(shí)間、空間的障壁,讓童年溪流里的細(xì)小魚蝦在此時(shí)的山中復(fù)活;追溯和思念它們的心思不可謂不真純。而小魚蝦即使到這個(gè)時(shí)候也試圖“把自己藏起來(lái)”,且一晃神間,隨時(shí)會(huì)消散。草白在這里隨手制造了一個(gè)小幻境。加上“我”始終未見的“茶樹王”,這一切就給讀者一個(gè)強(qiáng)烈的印象——雖然布朗山如此深窈,植被草木如此蔥蘢,可以疏瀹五臟、澡雪精神,但這山、這草木其實(shí)可能只是障眼法,藏起了“茶樹王”,藏起了草白創(chuàng)造的這個(gè)“理念小世界”。而小說(shuō)結(jié)尾,“我”似乎與周圍環(huán)境達(dá)成了一定的和解,但其實(shí)是因?yàn)閷ふ业搅诉@“不足為外人道”的理念小世界,而悄悄保持了與世間的對(duì)峙。
這里,我們可以感覺到草白一種深深的憂慮。這小世界藏得有多深,草白的憂慮就有多深。這憂慮,給全篇的草木香氣帶來(lái)一種凜冽之感。這是對(duì)人事深切觀察后生出的憂慮,它沉著冷靜,不可輕易動(dòng)搖。
深切的思慮,以文字出之,亦是沉實(shí)深切的。表現(xiàn)在文字上,一個(gè)特征是,草白偏愛短句、實(shí)詞,密密深縫,聲聲切響。
一般情況下,寫景細(xì)膩的文章,往往用的是綿延的長(zhǎng)句,以具有特征的修飾詞疊加,烘托出細(xì)致的效果。而草白愛用實(shí)詞、短句,節(jié)奏快,信息密集,如一根根針插入布匹,針幾乎替代了線,編織成有特色的形式,一種特殊的簡(jiǎn)練蘊(yùn)藉的效果。譬如下面這一段:
他在一個(gè)簡(jiǎn)陋的泥爐子上煮茶喝,燃料是干松針,水是林間的清泉,以一根剖開的竹子,引到家中水缸里,整日叮咚作響。這是一個(gè)近乎廢棄的茶廠。廠房周遭荒草連天,外墻爬滿藤類植物,無(wú)目的地瘋長(zhǎng)。簡(jiǎn)陋的制茶車間里,還擺放著銹跡斑斑的揉茶機(jī)、烘茶機(jī)、切茶機(jī)等機(jī)器,有些已被拆成零部件,露出里面黃燦燦的銅絲,像灰燼里抽出的一點(diǎn)火星。
第一句,先用兩個(gè)“……是……”,最簡(jiǎn)單的判斷句式,將“燃料”“干松針”“水”“林間”“清泉”等一列實(shí)詞安入,接上“以一根剖開的竹子,引到家中水缸里”。這里,“竹子”是“剖開”的,修飾“竹子”的形容詞是一個(gè)動(dòng)賓短語(yǔ),并且,“以”字迅速接上“引到”,這更高一層動(dòng)作,并快速滑至下一層語(yǔ)義,帶出“整日叮咚作響”的效果。這一句,短句子的節(jié)奏非常快,句中所指涉的事物相當(dāng)密集,密雨打圓荷,聲聲切響。這是實(shí)詞與動(dòng)作的“密”。
再后面,“廠房周遭荒草連天,外墻爬滿藤類植物,無(wú)目的地瘋長(zhǎng)”。“荒草連天”“爬滿……”,這亦是以動(dòng)作、一種動(dòng)態(tài)來(lái)寫整個(gè)環(huán)境的荒廢情況。接著,視角轉(zhuǎn)向制茶車間,一一數(shù)出幾種不常見的機(jī)器名目,冠以“銹跡斑斑”的形容詞,很有質(zhì)感。接著是一個(gè)比喻。先抓取出機(jī)器的筋骨——“黃燦燦的銅絲”,再用一個(gè)有力的比喻“像灰燼里抽出的一點(diǎn)火星”,以“抽出”的動(dòng)作、動(dòng)態(tài)的火星,將這種廢棄感寫得十分生動(dòng)。
并且,“灰燼”可以隱喻廠房和機(jī)器的廢舊狀態(tài),“火星”又帶有“雖已廢棄,骨子里不屈不撓”的意味。這是文字的力量感。一系列意象不僅十分沉實(shí),也產(chǎn)生一種廢棄中的堅(jiān)守感,與小說(shuō)中老茶人的形象形成對(duì)應(yīng)。這樣用密集的實(shí)詞、動(dòng)賓短語(yǔ)、快節(jié)奏的短句,造成速度感、沖擊力及物質(zhì)的重量感,仿佛“猶自帶銅聲”,產(chǎn)生一種凜冽的氣息。
此外,沉默喝茶的老茶人,獨(dú)自在山中穿行、安靜觀察山林各類來(lái)訪者的“我”,都是邊界清晰、冷眼觀人觀世的人物,這也奠定了小說(shuō)敘述的一種冷調(diào)子。
于人事上冷靜地觀察,以漫山云霧、草樹為障,藏起一個(gè)更深的理念的“小世界”,只偶爾、緩緩向有機(jī)緣的人道出——這一切讓整篇小說(shuō)具有一種凜冽的草木香氣。老茶人“宋易安”的名字也饒有意味——“宋”,是以木為家;“易安”,同時(shí)具有字面上的“安”以及由字面必然自問的一聲“易安否?”,也暗示了小說(shuō)結(jié)尾“我”的狀態(tài)——“很快,我就對(duì)各種展覽喪失興趣。每次看見人像背后虛化的綠影,眼前總會(huì)浮現(xiàn)出布朗山的草樹與云霧,我沒有見過(guò)的茶樹王似乎也置身其間。”“我”以一種自然沖淡的方式將“茶樹王”藏在了意識(shí)深處,整篇小說(shuō)幻化成一重綠意籠罩其上,一股凜冽的草木清香便從紙上撲面而來(lá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