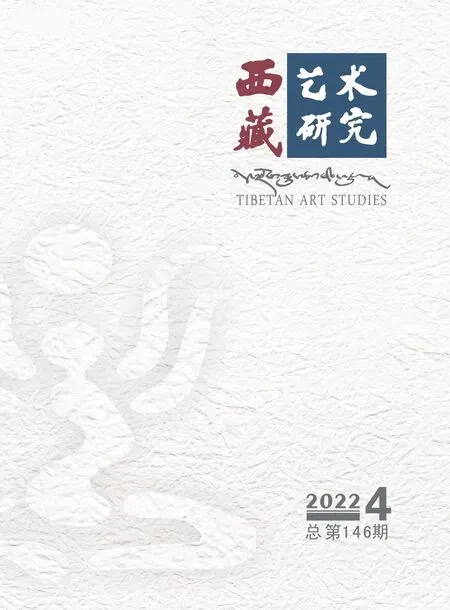在希望的田野上
——人類學田野反思
白瑪措
人類學的田野,對遠方的書寫總是很多。這是一門以研究陌生人社會為己任的學科①趙丙祥.將生命還給社會:傳記法作為一種總體敘事方式[J],社會,2019年第一期,第39 卷。。即便筆者生活工作的城市離田野不算遠,然而我的田野點“牧區”在書寫中依舊還是那個遠方。當我們不在遠方田野的時候,還有一片田野卻被忽略了。那就是“自己的日常和這日常的附近”。
人類學家項彪曾提出現代社會都有一種趨勢,就是消滅附近。自己身邊的世界逐漸成為一個要拋棄,要離開的一個場景。②“項飆:我們在沒有“附近”的世界里生活”https://xw.qq.com/cmsid/20220617A029K800.其實這個“消失的附近”對人類學學者的影響不可忽視,它不但形成了人類學家對遠方田野的理解和思考,也構筑了人類學學者從遠方田野歸來后如何呈現那片空間的敘事過程。研究者時而在田野的劇中更多時則是在田野的劇外,故而怎么能不去凝視這片附近的田野。借用維特根斯坦的那句話:世界的意義必定在世界之外,于我,田野的意義必定也在田野之外。
夢境
最不被納入的附近就是人類學學者的“夢境”,這個奇思妙想完全源于我的一次閱讀經歷。2022年,我在偶然閱讀多爾斯·艾根(Dorothy Eggan)發表于1949年的一篇文章叫做《人類學對夢境研究的重要意義》③The Dorothy Eggan,“Significance of Dreams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American Anthropology,Vol.51,No.2,1949,pp.177-198.,艾根在這篇文章中提及了他所記錄的印第安霍爾比人的夢,以及夢者對其夢境的文化解釋。作為人類學家的艾根認為這個他者社會有著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社會解讀夢境的文化體系,艾根甚至批評了當時流行的佛洛依德關于夢和象征性的那套理論。艾根的文章讓我突然想起一個和我人類學學者身份有關的夢境,霍爾比人會怎么解釋我的夢境?這個夢境對我如何呈現“遠方田野”的思考和“田野歸來”的寫作一直產生著奇妙的影響。
夢境中的我走在一片霧氣彌漫的草原上,此刻我完成了一次田野訪談,正在趕往去下一個牧場的路上。霧氣彌漫,讓我有些害怕,心想著萬一遇到壞人,應該怎么應付,不由得加快了腳步。我手上還握著一份自己寫好的文章,這是一篇草原生態系統存在Naga 的論文。此刻,天色漸黑,寒風襲來,突然看到前方有個影子。我納悶著在這空曠無垠的草原上,會不會是放牧的牧民。不由得加快腳步,走近這個影子。是一位老人。他瞟了一眼我手中的文稿便已通讀完內容,與此同時他用意念在我文稿里寫進了他想象的幾個概念。接著老人遞給我一杯水,讓我喝下去,我在完全無助的狀態下喝下了這杯水。頃刻之間,周圍出現了幾個張牙舞爪似人形的東西欲置我于窒息狀,我用沉默奮力掙扎。另一個我告訴自己“你被老人投毒了”,因為這個老人認為沒見過Naga,Naga 就是不存在的。而且老人一直以投毒延續其影子存在的狀態。那一刻,我好像從歷史的時空看到無數這樣飄蕩著的影子。我不由得擔心自己會不會就這樣憑空消失。前方,我看到有一條陽光鋪灑的小徑,準備走向那里,一個看不見的聲音說被投毒之人不允許進入。
夢境里沒有空間界定,猶如一個劇場,一個舞臺。此刻,我身處在一個環形劇場中。舞臺中央是一位拉二胡的老太(有點像某縣春晚那個拉二胡的何伯伯)。我旁邊的藝術家告訴我,她就是傳說中的“魔音小公主”。“小公主”可能是看到我和藝術家低聲細語,突然指著我說:你留過學,不能坐在這里。我看到了這個圓形劇場中走動著類似《盜夢空間》中的那些防衛者,他們負責在潛意識的夢境中審查我殘存的意識。我摸了摸頭頂,醒了過來……
榮格認為夢可以將我們帶到人類文化的昔日狀態,就是潛意識。情結以人格化的形象出現在我們的夢里,情結是我們夢中的行事人,面對他,我們束手無策。榮格認為這些情結是我們在意識狀態下那些感覺不到的,被否定的,被壓抑的意識(記憶、或者創傷的記憶)①【EP146 夢! 潛意識的神秘語言! 榮格心理學維蕾娜.卡斯特-嗶哩嗶哩】https://b23.tv/k9epmK0.。
我很希望這個夢境就是電影《全面回憶》中那個植入的回憶,但無論如何這個夢的情結顯然在意識狀態下左右著我行走遠方田野的思考以及呈現田野場景的寫作思路。因為,非夢場景下的我,在田野期間會下意識的想起那個影子,而在思考如何呈現田野的寫作過程中,“魔音小公主” 也會時常飄過我的腦海。
夢是不是一種經驗? 我想起維特根斯坦關于語言邏輯的那句話“凡是能夠說的事情,都能夠說清楚,而凡是不能說的事情,就應該沉默。”。
污名
人類學學者從遠方的田野回來,再進入書寫話語的那個過程中,腦海中會時常閃現出一個模糊卻又揮之不去的背影。但是,你無法去聚焦這個背影,因為田野始終你都沒有能夠接近這個背影。但它會以非常清晰的輪廓成為田野經歷的一部分。我依舊如此清晰的記得草原上的那個輪廓,那位被稱為“瘋子”的人,那個我始終沒敢前去說過一句話的牧民。
初入田野點,我的資訊人就善意的告訴我,這里有一個“瘋子”,有時會有點“危險”,所以要離她遠點。資訊人進一步提供了“危險”的合理性,說周圍的人一般都不會接近她。所以讓我不要指望和“瘋子”有正常的交流,更不要抱有訪談的幻想。
“瘋子”是一位70 多歲的牧人,總是一個人竊竊私語,周圍人聽到過她描述她眼前看到的幻覺,偶爾也出現過攻擊性行為。平常,她總是獨來獨往,天不亮就會背著一個很沉的行囊,拄著拐杖遠途,傍晚才回到居所。
在田野地蹲點的幾個月,我和“瘋子”沒有過一句交流,離她最近的幾次社交距離就是從她的居所前疾步路過。關于她的故事,需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詳述,在這里我要寫下的是田野歸來我一直在反問自己為什么沒有走近“瘋子”,沒有試著去訪談她。這個疑慮讓我在田野之后又重讀了人類學的污名研究的文獻。自己在挪威卑爾根那個細雨連綿的冬季讀過的戈夫曼的《Stigma》,前言中那位因面部缺陷而被排斥在正常社會關系之外的16 歲女孩①歐文戈夫曼.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M],宋立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現在回想起來,“瘋子” 被我列入訪談對象之外的原因竟然與這位女孩非常的類似。當資訊人警告我遠離“瘋子”時,我的腦海中就下意識的將這個“瘋子”和“危險”分類在了一起②Emile Durkheim,Marcel Mauss,Primitive Classification,Rodney Needham(Tra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這一分類是我的本能,還是后天習得中社會建構給我的信息(social information)? 戈夫曼認為社會會建構一套關于“瘋子”的信息,讓“瘋子”這個名稱本身代表著不名譽的特征,使它具有超越常規和規范可能性的特征。我同“瘋子”周圍的人一樣,將她的癥狀(竊竊私語、幻覺描述、過激行為)視為規訓之外的行為,將規范化的社會關系對“瘋子”封閉起來,無形之中進一步強化其異類特征③Douglas Mary: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Routledge Classic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66.。這種標簽讓我在田野始終懼怕“瘋子”會沖破社會規則和公共秩序而對我產生危險,危險感讓我將“瘋子”排斥在了訪談對象之外④Goffman Erving.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New York: Prentice Hall,1963.。我不由得想起北京大學郭金華博士在精神病醫院做田野調查時,以及在與那位精神分裂癥患者偉華進行對話時,內心是否曾產生過一絲危險感⑤郭金華.于疾病相關的污名:以中國的精神疾病和艾滋病污名為例[J].學術月刊,2015年,Jul 07,第47 卷。,我對那些在精神病和艾滋病污名從事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同行心生敬佩。
2022年,我回訪了生活在“瘋子”周圍的一位資訊人。關于她的信息依舊零星破碎,但其中的一些只言片語突然讓我意識到這位“瘋子”被污名的過程需要從時間的縱向緯度理解她,將她放置在游牧社會史的縱向視野才有可能展示這位污名化主體的具象化呈現⑥郭金華.污名研究:概念、理論和模型的演進[J],學海,2015(02):10.。因為,我想到了自己附近的一位人類學學者被污名化的經歷,以及自己附近的那些污名的田野案例都有著時間縱向緯度的原因。
一位人類學者因為用故事解釋人類學理論而被冠以“腦子不正常”,這種“不正常”的污名如果從時間的縱向緯度思考,就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一直存在的對話鴻溝,人類學的研究因為沒有數據和模型的推理論證,故而在“不正常”和“非科學”的分類中①白瑪措.撞死一頭牛:民族認同在西藏民間的故事[J],中國藏學,2019(1).。
人類學家涂爾干和莫斯認為人類是通過分類建立起一套秩序,并通過這套秩序認識自身和周圍熟悉的環境。例如,城市通過分類建立起了一套秩序,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則通過這套分類熟悉秩序中所包含的意義。在熟悉的城市環境中,面對熟悉這套城市秩序的人,我們的興趣點通常都會集中在個體上,而一旦面對不熟悉這套秩序的行為或面對不符合我們通常社會習慣的人,我們的興趣點就會從個體的人轉向區域、偏向于群體②Sapir,Edward.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Culture and Personality,edited by David G.Mandelbaum.Berkeley(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9;趙丙祥,將生命還給社會:傳記法作為一種總體敘事方式[J],社會,2019年第一期,第39卷:57.。這種興趣點的轉向過程中就有可能將時間縱向角度中已有的偏見疊加在污名化的產生過程中。如,在拉薩乘車,我不止一次聽到不同的司機抱怨藏E 車牌的車。在拉薩街頭如果看見藏E 開頭的車牌號代碼,“E”不僅表示所在地的地市一級代碼,暗含著在路中央會車時停車聊天,以及其他不遵守城市交通規則,還象征著牧區、牧民等諸多信息。這一信息的疊加過程應該產生自現實生活中駕駛藏E 車的人在城市駕車的行為方式越過了城市秩序之外,這對于那些熟悉這套秩序的人而言,這個越軌的藏E 車司機就代表了他所屬的那片區域和所屬的牧民群體,于是興趣點從越軌的司機轉移到了區域和群體并完成了污名化的一個微妙過程。
印象派
評論家路易·勒魯瓦在1863年說:那是一群根本就不懂繪畫的畫家,莫奈的《日出·印象》完全就是憑印象胡亂畫出來的,其他人也附和著說,這些畫家統統都是“印象主義”。在人類學的田野經驗中,難免不會遇到類似路易·勒魯瓦和附和他評論的人,我稱之為印象派人類學田野經驗。
我的最近一次的印象派田野經驗是在2011年,也是我的一次生活在場的“田野經驗”③彭兆榮.‘我’在‘他’中[J],讀書,2022年2月9:105.。這年,從一次遠方的田野歸來后,我寫了《大地藝術家北方牧人》。這篇文章的田野經驗,我自詡為“印象派人類學田野經驗”。
這個經歷讓我想起在游牧世界的柏柏爾人中從事田野工作的拉比諾。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反觀田野工作,在其《摩洛哥田野反思》(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1977)重新思考了田野工作者和訪談對象之間的關系,提升了資訊人在田野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強調了人類學家與資訊人之間應該以一種平等的關系呈現④盛燕.反思田野作業-讀‘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9月15:197.。然而拉比諾的這種反思,并未得到其導師格爾茲的認可⑤張海洋.好想的摩洛哥與難說的拉比諾——人類學田野作業的反思問題[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VOL.30,NO.1.。不管拉比諾的觀點是否落入了人類學自說自話的內卷空間⑥《悼念:馬歇爾·薩林斯與保羅·拉比諾》,2021年4月7 號https://tyingknots.net/2021/04/sahlins-rabinow/,至少,格爾茲讓拉比諾感受到是人類學專業領域中的“印象派”。
《大地藝術家北方牧人》 中的主人公曲英多吉是我的資訊人,與曲英多吉的官方接觸則要感謝一位知道費孝通先生《江村經濟》的boss,這位和藹可親的領導疏通了官方層面的溝通。這一疏通比起那種單打獨斗的人類學田野進入,節省了人情時間和枉費的精力。然而,如何獲得資訊人和資訊人周圍群體的信任,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對象怎樣凝視田野工作者。于是,我有了兩條并行線的角色:角色A 是要對得起boss 對我的信任,拿出一份沾滿田間地頭泥土味的田野報告①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于解決現實問題、回答現實課題。——2019年3月4日,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的講話。;角色B 是通過對牧民的理解,繞道來理解作為本土人類學者的我。
遠方的田野歸來,我完成了遞交給boss 的田野報告,也完成了一份突出資訊人在田野過程中發揮重要性作用的文本。
那份遞交給boss 的田野報告,非常接近于格爾茲所述:田野作業中從最細微的對話、日常繁瑣的事情著手,期望達到更為廣泛的解釋,力圖做到“事實材料”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類學家在田野作業中(也是之后)對“事實”的選擇、理解、分析和解釋②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M],韓莉譯,譯林出版社,2017.③彭兆榮.‘我’在‘他’中[J],《讀書》,2022年2月9 號:101.。Boss 對這份田野報告倒是很滿意,當它轉到了具體的分管者手中,便開始了我的印象派人類學田野經驗。這份田野報告被“降維打擊”(借用劉慈欣《三體》 中語)(僅僅是沾滿泥土味的第一手資料,并不至于降維打擊)。很顯然,專業人類學者傾心完成的田野報告如果在非人類學的權威那里一錘否定,且一旦有人給人類學這門學科貼上“資產階級學科”的標簽。本土人類學者終有一死,人類學是錯的。也許猶如薩林斯曾打趣過的那樣不幸言中,“至少在人類學的發展歷程中,有兩件事是確定的:一,我們終有一死;二,我們都是錯的”At least as far as Anthropology goes,two things are certain in the long run: one is that we’ll all be dead; but another is that we’ll all be wrong④Marshall Sahlins.Waiting for Foucault,Still.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⑤趙蘊嫻編輯|黃月.告別“行動著的理念人”: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與保羅·拉比諾本周相繼離世,界面新聞,2021-04-0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6432050468993624&wfr=spider&for=pc)。即便如此,我依舊感謝帶我走進“人類學” 這門學科的中國民族學界前輩學者和我的人類學同行2009⑥楊圣敏.中國民族學的歷史經驗與未來展望——基于1978年以來的總結與反思[J].西北民族研究,2009,(03):16-32。“2004年第16 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學習會邀請兩位民族學家講課和胡錦濤主席在學習會上號召全黨全國都要加強學習民族學知識的講話,說明中國政府和黨中央最高層領導已經認識到民族學在我國社會中的作用。”:27.。
降維打擊后,面對凝視著我的資訊人和他的群體,我得有一份文本交代。我想起了那些在權威藝術沙龍落選的畫家,卻在“落選者沙龍展”中獲得了認可。這激發了我將更為抽象的分析放在《大地藝術家北方牧人》文本中。
《大地藝術家》文中主人公曲英多吉于我類似那個引導拉諾比進入摩洛哥阿拉伯牧民社會的阿里,作為游吟詩人的曲英多吉也是漂泊在“我文化中”的“他者”,也是這次田野過程中我得以進入和了解北方游牧文化最直接的、具體的觀察和體驗對象⑦彭兆榮“.我”在“他”中[J],讀書,2022年2月9 號:98.⑧克里福德·格爾茨.事實之后: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M],林經緯譯,2011.。田野的“事實”不是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終點,而是這個“事實”之后的“解釋”成為田野工作的某一個終點⑧。故而,文本中我通過資訊人展開了對他所處的游牧文化的一種解釋:游牧群體面臨著當下社會共有的癥結:一種與過去社會意義的被割裂和主動的割裂①維克多·弗蘭克爾.追求意義的意志[M],司群英,郭本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我不由得想起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在《詮釋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的觀點:研究的直接焦點不再是我的主觀過程的意向對象(曲英多吉和他的牧人社區),或者說甚至不再是個人經驗的象征表現(我的田野經驗),而是全部書寫話語的一個領域,一種文本和類似于文本的領域②保羅·利科.詮釋學與人文科學[M],J.B.湯普森編譯,洪漢鼎譯,2021年8月。。
這份文本應該是和牧人的感受對上號了③“21世紀的社科研究一定要是對話式的,那種話語操作式的理論生產,跟百姓的感受對不上號。”谷雨實驗室:“獨家訪談著名學者項飆:在海外“講解中國”,拆解中國年輕人的痛點”,2022年8月。,我的資訊人和他的牧民群體、人類學同行、藝術界、文學界朋友的認可中形成了另一個空間的“落選者沙龍”,讓我經歷了一次飽滿的印象派人類學田野經驗。
2021年,彭文斌教授來拉薩,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后,曾問過我:“你這個賣火柴的小女孩,是怎么活下來的? ”人類學前輩的提問都是幽默中充滿深意!那個午后,我猛然對安徒生的童話故事有了哲學意義上的理解。
……
人類學學者的“田野”除了遠方,還不應遺忘附近和日常。因為,這附近和日常往往會影響如何最終呈現那遠方的“田野”。戈夫曼以劇場延伸的人類學理論中將社會活動分為臺前臺后④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馮鋼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我將田野的最終呈現理解為臺前的那部藝術作品,而臺后則可能有一連串與臺前行為不相關的事件,附近和日常的田野就好比這些發生在臺后的事件,但它們也影響著最終呈現給讀者的那個遠方的田野。在這個整體的田野過程中,那些縈繞人類學學者的靈感、那些讓荒誕黯然失色的生命意義便是希望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