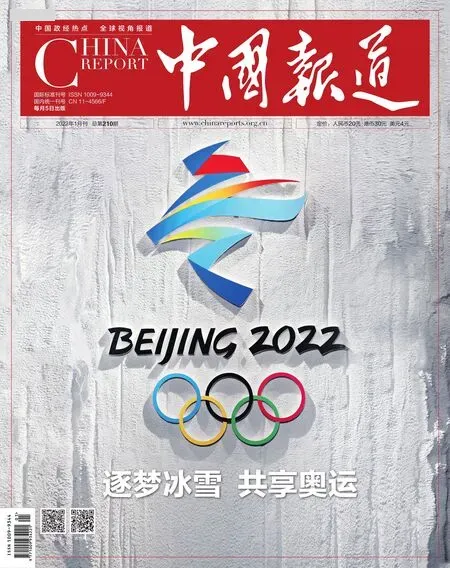世貿組織向何處去?
文︱《中國報道》記者 陳珂

2001年11月9日至13日,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四次部長級會議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在這次會議上,經歷了表決、簽字等儀式后,隨著歷史性的一聲槌響,中國結束15年復關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并在當年的12月11日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
彼時,以會議舉辦地多哈命名的多哈回合談判也被提上議程,這是WTO成立后啟動的新一輪全球多邊貿易談判,旨在推動全球農業、制造業和服務貿易的自由化,被認為是“為國際貿易改革訂下了頗為進取的改革計劃”。中國加入WTO后便開始參與這一談判。然而,多哈回合談判自啟動以來,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農業政策問題上始終無法彌合分歧,致使其歷經多次談判也沒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并被擱置至今,這也讓WTO進入低潮期。
多哈回合談判2008年陷入停滯以來,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成為世貿組織最權威且有效運轉的部分。但在2019年12月,WTO爭端解決機制因上訴機構法官人數不足,被迫陷入停擺;2020年12月,上訴機構最后一位成員任期屆滿離任。如今,無法正常運轉的WTO深陷危機之中。
舉步維艱的多哈回合談判
多哈回合談判的啟動并非偶然。
由于農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特殊性,始于1986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開始后,農業便成為中心議題之一,最終在1993年12月達成了包括《農業協議》在內的烏拉圭回合一攬子協議。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貿組織研究院院長屠新泉看來,直至1995年WTO成立,WTO多邊貿易談判仍有一些未決問題沒有討論出結果,且主要集中在農業和服務業方面。
“按道理講,WTO成立之后就應該開啟對這兩方面問題的談判,但在后來的討論過程中覺得只談這兩個問題還不夠。經過了很長時間的爭論,多哈回合談判的議題最終有19個,涉及農業、非農產品市場準入、服務貿易、知識產權、規則談判等。”屠新泉向《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他認為,盡管多哈回合談判在2001年如期開啟,但是談判本身基礎比較薄弱。從當時的部長宣言起草過程看,各方分歧很大,但出于多方原因,多哈回合談判最終被成功發起,“尤其是‘9·11事件’給當時的國際安全形勢投下了濃重陰影,迫使人們尋求一種團結氛圍。”
多哈回合談判建立在烏拉圭回合談判制定的《農業協議》基礎上。市場準入、國內支持和出口競爭是烏拉圭回合《農業協議》的“三大支柱”——市場準入指在多大程度上允許別國商品或服務進入,國內支持指成員采取國內政策支持為農業生產提供補貼和支持,出口競爭指成員為農產品出口所提供的各種形式的補貼。
“出口競爭問題目前基本上解決了,主要是關稅和補貼的問題。”屠新泉告訴記者,農產品貿易的理想模式是發達國家減少補貼,發展中國家降低關稅,但是雙方的動力都不太足。“《農業協議》原則上要求發達國家削減補貼,但發達國家基本上沒有兌現承諾,得到補貼的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出口,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很難去競爭的。”
日前,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發布的一份有關全球農業的報告顯示,2013年至2018年間,平均每年對農民的補貼支持為5400億美元,其中87%(4700億美元)是“有害的”。這包括對特定牲畜和作物的價格激勵、對化肥和農藥的補貼,以及扭曲的出口補貼和進口關稅。
屠新泉表示,我國在入世前屬于觀察員,加入初期力量比較薄弱,但作為最大的發展中成員,也積極、全面地參與了多哈回合談判,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包括舉行多場小型部長會議、高官會議,推動談判進程,并在農產品和非農產品關稅減讓領域提出關稅削減公式,解決不同國家適用同一減讓公式的公平性問題。
但由于各方利益的頑固性沖突,2008年7月,多哈回合談判終因美國在發展中成員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上拒絕讓步而陷入僵局;同年12月,由于無法彌合分歧,世貿組織決定年底前不再召開小型部長會議;2015年,162個WTO成員國的貿易部長在肯尼亞內羅畢參加第十屆部長級會議,他們沒有重申回歸多哈回合談判,這是多哈回合談判啟動以來的首次。
20年后再看多哈回合談判,屠新泉坦言,這期間沒有取得大的進展,從側面表明WTO的規則沒有進步,但成員的經貿水平、技術水平卻在不斷發展,“新問題只能參照舊規則解決,這無疑會削弱WTO的影響力”。
多邊貿易體制仍是國際貿易的基石
在世貿組織上訴機構原主席、大法官張月姣看來,危機體現在決策機制失靈,不足以應對多哈回合談判中成員間多方利益的復雜博弈;領導力真空,核心成員從塑造和推動者到體制撼動和破壞者;包容性欠缺,欠發達、最不發達成員融入體制困難等。
屠新泉也認為,多哈回合談判之所以失敗,既有WTO機制的不健全,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領導者缺位。“WTO決策機制遵循協商一致原則,從20多年實踐看,如果領導者足夠強大,該原則更傾向于‘強迫一致’。”他表示,美國在2008年以前承擔了WTO的領導者角色,此后便力不從心。尤其是特朗普之后,國內社會矛盾的積累帶來了美國對國際組織、對全球化的態度改變,美國產生“全球化不利己”的認知問題。
“美國失去迫使別國接受它的領導的能力,其他國家目前尚缺乏領導能力,多哈回合談判只能暫時擱置。這是核心問題。”屠新泉強調說,全球化有高潮就會有低谷,當前一方面仍要促進國際合作,通過WTO和其他國際機構解決雙邊、多邊以及全球性問題;另一方面,美國等國家應看到需求、突破壓力,進行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
有輿論認為,多哈回合談判無限期暫停,是多邊貿易體制漸成“雞肋”的一個縮影,雙邊合作、區域合作是當今主流。屠新泉分析,作為替代的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更容易出結果”,有市場是正常現象。
世貿組織副總干事張向晨則指出,雙邊合作、區域合作可以成為多邊貿易體制的有益補充,但前提是世貿組織必須健康、強有力。他強調,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選擇。各國的經濟利益需要協調,有很多綜合性問題,如農業補貼,沒有任何一個區域或雙邊協定可以處理,只能在多邊框架下解決。“多邊貿易體制是國際貿易的基石,作用不可代替,這是絕大多數成員的共識。”

以規則為基礎、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一直是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基石、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保障。圖為坐落在瑞士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總部。
“螞蟻搬家”式尋求解決方案
世貿組織官員曾估計,如果多哈回合談判成功,全球消費者和企業每年可少支付1250億美元關稅。法國經濟研究機構CEPII估算,多哈回合談判帶動貿易全球化可使世界經濟每年增長將多出430億美元,與此有關的服務貿易自由化還將帶來300億美元額外產出。
多哈回合談判艱難而復雜,尤其處在當前逆全球化、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疫情導致全球經濟分化、動蕩的情況下。專家表示,這也正是推動WTO機制改革的時機所在。讓WTO重新成為在世界貿易秩序中有影響力的中間角色,是所有成員國共同的責任。
張向晨指出,WTO規則需要與時俱進,但WTO改革不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WTO的核心價值尤其是非歧視原則必須堅守。對于全體成員一時達不成一致的議題,應允許部分成員先行先試,探索新的路徑。但諸邊方式不是多邊談判的替代品,最終目標仍應是形成多邊規則,使每個成員特別是發展中成員不被落下。
在談判策略上,屠新泉告訴《中國報道》記者,當前形勢下,希望多哈回合談判達成那種面面俱到的一攬子協定已經不可能。“針對一些小的、成功概率高的單議題面向局部成員談判,‘螞蟻搬家’式地尋找解決方案更為可行。”
事實上,多哈回合談判并不是毫無成果。2013年,世貿組織第九屆部長級會議達成“巴厘一攬子協定”,被稱為多哈回合談判的“早期收獲”,該協定包括10份文件,內容涵蓋了簡化海關及口岸通關程序、允許發展中國家在糧食安全問題上具有更多選擇權、協助最不發達國家發展貿易等內容;2015年,世貿組織第十屆部長級會議就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最為關切的農業出口競爭達成共識,162個成員首次承諾全面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時任WTO總干事羅伯托·阿澤維多稱這是世貿組織成立20年來在農業領域最為重要的成果。
2021年12月2日,WTO“服務國內規制聯合聲明倡議”談判在日內瓦正式簽署協議,協議聚焦與服務貿易有關的許可要求,程序、資質要求和程序以及相關技術標準,旨在促進相關措施的透明度、可預見性和便利性。屠新泉認為,談判僅用時4年就結束,為WTO帶來一抹亮色。
在他看來,對于多哈回合談判不必過于悲觀,即便不談判,既有的規則成果也還在繼續發揮作用,大多數貨物貿易依然受WTO規則管轄。“有些可能有點過時,但還是能作為一個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