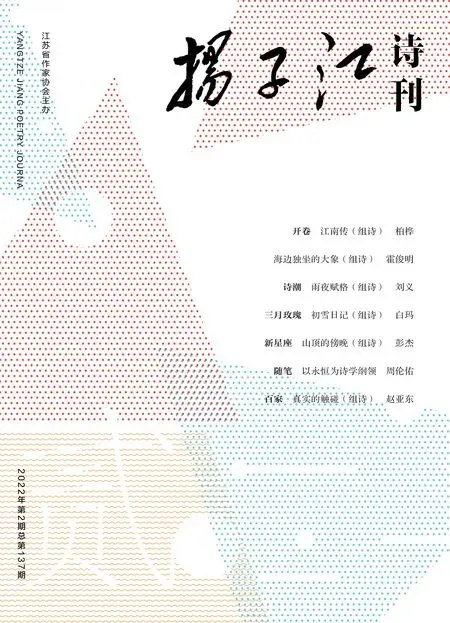游記詩(組詩)
林苑中
過宜興
良田萬頃,碎銀一地。
在很久前就聞名于世,
甚至早于典籍。
有鮮衣良人,有酒持續入壺,
古代的靚馬并不驚叫,
就有了生命熱情的漿液,
在多情的橋頭,
在通俗的河畔。
一直在想,去這座城,
見那個誰?
盡情把盞,或許
在春天撲面時唱上一段?
雖飛馳如電,綠野靜默成謎。
這其實是時間的勝利,
一切的,只是衣裳翻新,
你我都是語調相仿的古人。
四月十九日游琵琶湖記
雨是剛下完
傘還抓在手里
生活有時候不需要隱喻
你的心是一口池塘
在四五月里
我騎馬走一千里
也照樣聽得見
湖水的皺褶下
一個又一個小風暴
田野上的呼吸
縮在驚蟄過后的平原
午后的光線
在夏天般巨大的陰影下
猶如吝嗇的入侵者
山巒等著河道
河道等著游客
水深千尺
時常有溺水者的呼喊
在萬千葉片上
像不疾不徐的雷聲
城墻上的藤蔓
是另外的瀑布,自下而上
在垛口之外
充滿了凜冽與驕傲
藍天像是遺漏的
一二丈粗糲的布匹
花在靜靜開
竹林無一個腳印
亭榭里,一個中年人在打盹
那邊樹下的垂釣者
發出一聲大叫
于是我們在風里醒來
看著衣衫襤褸的自己
發呆,直到雨滴
再次將視線里的一切
模糊成一片
原來愛情早己杯盞狼藉
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不要仰頭,真的不要,
在破碎的瓷片里,
就看見了那美妙的尖頂,
天色近晚,但車流如炬。
我這個鑿開時間之墻壁的人,
乘著五月的光亮,從語言的舷窗上
跌落,就像從一片草原
跌落在另一片草原上的羔羊。
靜謐的,還有靜止的,
那些小小燈盞異常整齊,
后面以及里面都有單薄的面孔,
還有靈魂纖細的雙手。
如你所見,柵欄就像身體一樣,
每個人就像秘密的人生小販,
耳語自內而外的,是這樣的小溪流,
讓蒼穹無頂,下起父親的雨。
夜游秦淮河
牌坊一側,道路是平的,
一直鋪著六朝夜色,
波光粼粼的上面,
那防火的樓墻已修葺一新。
唯月亮亙古不變,
還是那般大,那般圓,
橋梁上的人群,
與美人靠上的都是那舊相識。
朱雀人家,烏衣巷斜
只在那些一成不變的唱詞里,
光亮一如鋪滿繁花,
轟鳴的機駁船照常身披彩帶。
那邊僻靜高臺,青衣獨舞,
槳聲燈影,
依稀看得見酒酢四溢的地方,
書生喧嘩。
被預設的一場場艷遇,
那冠冕堂皇的燭照,
是美人面影那啟齒的笑容,
穿越經年,典籍紛飛。
就像一道道白光,
在遙遠的朝代,
而在人影憧憧的街頭,
遠隔的人們如一枚枚堅果。
從那墜入深淵,
經過彎曲十八廊橋,
寥寥可數的照壁
與高高的牌坊,交相輝映。
躍出人流,
到那燈火乍裂的街頭,
不顧身后秦淮河上,
那小小的得月古樓。
元月二日傍晚訪水陸寺
天還沒晚,
他們散去,
我留下,
何止是一份固執。
在宇宙的中心,
我款款而行,
能聽到的鐘聲,
從暮云里來。
那樸素的橋上,
行香火的人不知所蹤,
廟宇之外,
有田埂與炊煙升起。
廟門緊閉,那些廊柱林立
倒是比金剛清醒,
只看到縫隙里一個個菩薩,
燦燦一桌。
大雄寶殿俯下身子,
僧舍里無一人應答,
我一人猶如
走在回家的路上。
天隆寺有雨
車內的溫度早調成春天,
而那桃花開得正好,
公共汽車站臺已一簇簇人。
天隆寺像是在山的深處更深,
“撲啦啦”,雨點梵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