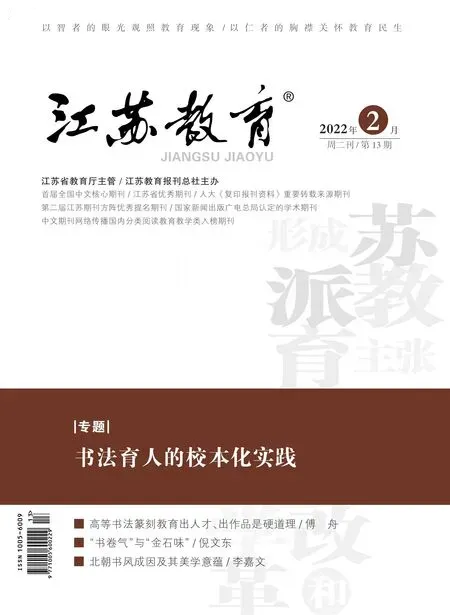新蔡葛陵楚簡書寫風格研究
王韜霖
《新蔡葛陵楚簡》(以下簡稱《葛陵簡》)是1985年在河南省新蔡縣葛陵故城出土的戰國竹簡。現在對《葛陵簡》的文字釋讀、文本內容、簡牘形制、抄寫年代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基礎研究,已具備開展相關書法學研究的學術條件。同時,《葛陵簡》由于數量大、文字多、抄手情況復雜,有助于我們整體地把握當時的書寫情況。據判斷,《葛陵簡》抄寫于戰國中早期之交,這正好彌補了這一時期戰國楚簡的缺環,因此,對于《葛陵簡》的相關書法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它上承戰國早期的曾侯乙楚簡,下啟戰國中后期的包山簡、郭店簡、清華簡、上博簡,不僅有助于將戰國楚簡的書法研究形成一個更完整的序列,而且有利于梳理戰國以來毛筆筆法的淵源及變化。本文擬基于《葛陵簡》書法形態學的形式分析,進行相關先秦書法材料的對比研究,將《葛陵簡》置于戰國書法系統下進行綜合分析,以期從個案研究的角度著眼,一窺先秦文字的書寫情況和風格流變。
一、《葛陵簡》的書寫特征——書法形態學的分析
《葛陵簡》系搶救性發掘,竹簡出土時已因盜墓擾亂而全部殘斷。該簡的內容多為卜筮祭禱,所以簡與簡的文本內容沒有連續性。加之《葛陵簡》數量較多,一共有1571枚竹簡,這樣復雜的情況導致我們無法準確地判斷有多少個書手,也不確定是哪位書手寫了哪幾支簡,這為《葛陵簡》的書寫風格分析增加了難度。但是,這也帶來了一個好處,就是使我們更能突破單一書手書寫習慣的局限來把握當時的整體書寫情況。所以,我們先對《葛陵簡》中不同風格的字跡做一個分類,分別描述其書寫特征及其對筆畫、字形的影響,然后對《葛陵簡》的整體面貌和特點進行分析,這樣能從書法形態上更好地把握《葛陵簡》的書寫特征。
(一)豐富多樣的筆畫形態
從出土的1571枚竹簡來看,《葛陵簡》系多個書手書寫,字跡之間的特征差異明顯。考古人員曾這樣描述:“大部分墨跡清晰。由多人書寫而成,字體或秀麗或奔放,字距或密集或稀疏,顯示出不同的書寫風格。”這是對于《葛陵簡》書寫風格的一個基本的判斷,在進行下一步書寫風格研究之前,還需要做一個更加細致的分類。但是,由于《葛陵簡》的內容散亂,即使對那些書寫風格很接近的簡,我們也不能斷定其由同一書手所寫。以下字跡分類,主要按照筆畫形態的差異來劃分。
在《葛陵簡》中,按筆畫形態的差異,大致可以可將單字分為以下幾類:






由此可見,不同的用筆方式在戰國中早期的《葛陵簡》就已有充分的體現,而作為日常的手寫體,這樣的用筆很可能是書手無意識所為,大概是由于個人生理機能的不同,在下筆的輕重、控筆的穩定性上存有著差異才形成這樣千姿百態的筆畫形態。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這些差異性書寫背后的同一性,即《晉書·束皙傳》所載“頭粗尾細,似蝌蚪之蠱”的“蝌蚪文”筆法。但“蝌蚪文”筆法只能是一種概括的說法,在這一筆法系統的內部,由于書寫者、書寫工具材料、書寫用途等因素的不同,筆畫形態又有著比較細致的分化。而在戰國中后期的典籍簡中,我們同樣看到了這些不同筆法的延續,也看到了各種書寫方式更加成熟、穩定的表達。
(二)方扁的字形和文字的使用
1.字形多呈方扁之勢。

這樣呈方扁的字勢在楚文字中很常見,特別是在文書類簡中,呈橫勢的字形有著絕對的優勢。下面我們選出一些《葛陵簡》中的常用字與其他楚簡進行比較,這樣能比較直觀地看出《葛陵簡》字形方扁化的特征。


表1 戰國簡常見字形對比
關于字勢呈方扁,叢文俊先生認為“在楚系墨跡書法中,字形或縱長,或方扁,并無一定規律,或什么特別的意義。楚簡帛字形或方或扁,系書寫者的個性風格使然”。這是將字勢的不同歸因于書手的個性差異,但也有另一派學者,如三峽大學美術學教授王祖龍先生認為“楚簡體勢橫逸寬扁,橫波微露向右下回曲的出鋒線條增加了通篇的律動感,實際上已有力地暗示了隸變的消息”。他還說:“如果結體上字形趨扁,直線多于弧線時,則有可能對大篆構成破壞。”這是將這些呈橫勢的字形看作是隸變的特征之一。現在看來,不能簡單將這種現象歸因于“隸變”,因為隸變的根本依據還應該落實到文字構型上。但是這樣大量方扁的字形寫法也不能完全歸結于書手的個性差異,特別是我們不能忽視出土的楚地日常文書簡中,呈方扁的字形有著絕對的優勢,這樣的現象背后一定有著深層次的原因。那么為什么在《葛陵簡》中有這么多方扁呈橫勢的字形呢?我推測原因有二:一是為了適應日常書寫較快速的需要,二是為了使文字適應簡的形制。書手在一條狹長的竹簡上書寫時,橫方向的筆畫是幾乎沒有限制的(因為最多也就是橫跨整簡),而豎方向的筆畫則需要考慮上下字的空隙,所以只能較方扁化地書寫。這導致在快速書寫的情況下,橫向的筆畫干脆一筆到底,豎向的筆畫則簡短筆程,迅速收筆,所以在葛陵簡中,我們常常看到字的兩邊撐滿整簡、上下留空的章法安排,也明顯感覺到越寬的簡上字勢就越寬。這樣的書寫方式有利于保證簡文單字的獨立性,使字與字的空隙拉開,雖然有利于簡文的識讀,但是也會使字勢變得方扁。可能這樣的書寫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當時文字的形體,以至于在戰國后期的楚金文和楚帛書中,字形已完全呈現方扁之勢。
2.繼承西周古文字的寫法。

二、《葛陵簡》相關對比研究——先秦文字視域下的綜合考察
在戰國簡牘的書法研究中,相關的對比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畢竟戰國文字離今天有著兩千多年的距離。我們時常會對這些同屬于漢字系統但是又有著明顯的時代和地域特征的古老文字有陌生感,所以研究時我們必須盡可能抓住每一個能看見的材料,將其置入戰國書法研究系統中加以全面綜合考察,相互對照、相互參考不同的戰國文字資料,這樣才能跨越時間的長河盡可能認識它們的真實面貌,理清其發展線索。
總的來說,《葛陵簡》的書寫質樸自然,極少修飾,姿勢方扁倚側且章法不穩定,是最接近日常書寫狀態的墨跡。將這些日常書寫的典型文本與其他戰國典籍簡和同出于葛陵墓中的銘刻文字對比時,能更加真切地窺察毛筆筆法的日漸成熟和當時文字的實際使用情況。
(一)與戰國簡牘中典籍簡的比較——書寫的不同狀態
1.與《上博簡》《郭店簡》的比較。
按照文本內容和書寫目的,可以把戰國簡帛文字材料分為自述型筆跡與非自述型筆跡。從用途上來說,戰國卜筮、祭禱、文書、遣策等材料上的字跡屬于自述型筆跡,而戰國簡帛古書上的字跡多屬非自述型筆跡。所以自述型筆跡一般能準確反映當時的字體演變情況,書寫較為自然,而非自述型筆跡情況則要復雜得多,對抄寫底本、書寫用途、書手態度等因素都需要考慮。
正如前文所述,《葛陵簡》中已經存在不同風格的用筆方式,而將作日常記錄之用的自述型字跡《葛陵簡》與作傳抄古書之用的非自述型字跡《上博簡》和《郭店簡》相對比時,我們發現,一方面這樣豐富的用筆方式在戰國中后期的典籍簡中能找到更清晰、成熟的表達。如下圖1所示,《葛陵簡》與《上博簡》在筆畫形態上多有暗合之處,這大概是“筆軟則奇怪生焉”下的“巧合”與“偶然”。但是這些偶然性的后面正是對于毛筆性能的不斷開發和用筆方式的逐漸成熟。

圖1 《葛陵簡》與《上博簡》《郭店簡》的比較
另一方面,我們在這些典籍簡中也能看到在《葛陵簡》中少見的明顯帶有美化、裝飾性質的書寫方式(表2)。

表2 葛陵簡與不同風格典籍簡的單字對比
相較來說,引筆的拉長使文字擁有了一些莊重典雅的氣質,符號化的裝飾則使其平添了一份圖畫般的美感,筆畫粗細的強調讓字跡更顯活潑姿媚,卷曲蜿蜒的寫法則賦予文字一絲曲徑通幽的神秘感。這些特點的變化不僅使文字的風格呈現出巨大的差異,同時也在提示著我們:此時的書寫不僅僅是作為一項紀錄文字的技術,同時還有了表情達意的功能。書手在書寫的過程中,時而正襟危坐、凝神屏息,一絲不茍;時而興致勃勃、縱情恣肆,龍飛鳳舞。在日常記錄中往往不拘一格,落筆即成;而在轉錄典籍時,常常精意覃思、刻畫入微。
2.書寫水平的提高與筆法解放。
李松儒將戰國時期的書寫者分為實用型從業者與史官、諸子等學者,并指出這兩類人都有著一定的書寫能力和文化水平。春秋時期,士階層的下移、諸子學說的傳播、書寫工具的進步等因素促進了社會識字能力和書寫水平的提高,隨之而來的便是毛筆筆法的日益成熟與解放,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能在狹長細小的簡牘上看這么多精彩紛呈的墨跡。《葛陵簡》在戰國簡牘的書法研究中比較容易成為一個坐標和參照物,日常的手寫體有著較快速的書寫需要,其筆墨大多數是無意識的自然流露。而典籍簡受到各方面的影響,刻意的成分較多,兩相參照則能有很多新發現。同時,戰國墨跡書寫情況的對比研究也為我們還原了書法藝術發生前的原始技術積累,正是在這樣的情景中,書法獲得了生長的條件:人們有意識地美化文字、裝飾文字,開始在文字書寫的過程中主動抒發自己的情感;以竹片、木牘為主的漫長簡牘歷史也將要走向終點,毛筆即將迎來最適合發揮其性能的書寫材料——紙;筆法也逐漸從先秦萌芽而越發成熟解放,書寫由無意識的“自然流露”而轉向為有意識的“起行止收”。雖然此時的書寫不可能完全脫離實用的功能而成為一種“純藝術”,但是在這些簡牘墨跡中,我們能明顯感覺到個性化書寫方式所傳遞的“人”的溫度。所以到了漢代,書法藝術漸趨自覺,書法逐步擺脫了實用而走向純美。而在這之前的先秦時代,也正如叢文俊先生所說的“春秋以后,舊秩序的崩壞,為實用書體提供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隨之而來的,就是書寫水平的提高,書體及其書法美的獨立”。前文所述的這些不同書手的差異性書寫,和后世的“顏筋柳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這時候的簡牘書寫還處于以實用為主的階段,書寫方法也沒有被文人士大夫系統化、理論化地表達。但這些個性鮮明的字跡啟發了后世,這些豐富多樣的筆畫形態成為后世書法筆法的濫觴。
(二)與同時期銘刻體的比較——文字使用的不同場景
1.與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的其他書法材料對比。
新蔡葛陵楚墓中還出土了其他有文字內容的器物,這些材料和《葛陵簡》一齊起為我們提供了當時文字使用的一個橫截面。墓中出土的戈上所鑄銘文有兩種風格,一是典型楚系鳥蟲篆的風格,字勢狹長,線條蜿蜒曲折卻又排布規律,但它不似蒍子倗尊缶、蔡侯產戈上銘文的明顯鳥形裝飾,更像是王子午鼎銘文的延續,即一種獨立使用的蟲書,如戈N:220、戈N:180上的銘文(見下頁圖2)。還有一種是接近西周金文的風格,字勢不似鳥蟲篆狹長,也不加修飾,如戈N:198、戈N:239上的銘文(見下頁圖2),這種文字應當視為當時的正體,一方面是因為其字形和西周金文一脈相承;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些文字未因鳥蟲篆化地繁縟修飾而變得晦澀難認,也沒有因手寫體快速抄寫而變得簡率,理應保留著文字最大的辨識度和正統性。可見,即使在銘刻書體中,文字的風格也會有較大的差異,鳥蟲篆的文字風格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楚人的圖騰與信仰,其背后是奇詭華麗的楚文化,而無修飾的正統文字風格則代表了秩序與規則,對稱、均勻、整齊的審美趨向。

圖2 葛陵楚墓出土銅戈銘文
當我們將同樣書(鑄)有主人名字“坪夜君”“坪夜君成”的文字進行對比時,可以看到青銅戈上的銘文與《葛陵簡》上的字跡有著更加明顯的風格差異(見圖3)。兩者的用途、制作工藝、器物和文字作者等各方面的差異都影響字跡(銘文)風格的形成。與齊整凝重的青銅器銘文相比,《葛陵簡》上的文字的確更加活潑自然。在有美化性質的文字中,修長均衡仍然是人們的審美偏好,而日常手寫體則顧不上這么多,方扁倚側變成了明顯特征。王祖龍先生曾指出:“(楚書法)這種大篆系統主要呈現為三種以上的書體形態……其一是正體……其二是草體……其三是美化裝飾性書體……”葛陵楚墓中的文字圖像為這一觀點提供了又一佐證。

圖3 不同載體上的“坪夜君”與“坪夜君成”
2.手寫體與銘刻體發展的不同序列。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在篆書時代,實際上并行著正篆和草篆兩種樣式,正篆主要適應政治集團的需要,往往受官方的規約,它的演變相對穩定;與正篆并行、通行于民間的草篆則相對活躍,是隸變的主要推手,后經過積年動態的流變,漸漸演變為秦漢時代的簡牘帛書。”盡管這個觀點還有待修正,但確實敏銳地指出了作為銘題禮器的鑄刻文字和作為日常使用的手寫體有著不同的發展序列。當我們將葛陵楚墓出土的銘文和簡文分別進行歷時性考察時,能清晰感受到這一點。按照學界楚系青銅器和銘文的分期研究,葛陵楚墓中出土銅戈上的銘文可以看作楚系銘文成熟期的產物,同期還有楚王舍章鐘銘文、曾侯乙編鐘銘文可以作為參考。這一時期的楚系銘文“逐漸形成自身特色,字體趨向修長,仰首伸腳,筆畫富于變化,多波折彎曲,富有美術字體風味,以后更以鳥蟲書見長……”。隨著楚國國力的逐漸強盛,楚人將其強烈的文化自信和鮮明的民族特色熔鑄到了這奇妙詭譎的文字符號之中。楚系金文的風格演變經歷了沿襲西周金文風格的繼承期、風格彰顯的萌芽期再到此時形成典型楚系風格的成熟期,然后到簡略草率的衰落期,最終和楚國一起湮滅在歷史長河里。可以說楚系銘文風格的演變史深刻反映了楚國國力的興衰史。
而當時的手寫體同樣有著其自身的發展脈絡。從用筆方式上來看,如徐利明先生所指出的:“(蝌蚪文)這種形態,可上溯殷商朱書、墨書,本為一脈相承,逐步演變而來……這種形態在春秋戰國的手寫體中已有很大變化……‘頭粗尾細’的蝌蚪意態也相應地顯得比較平和了”。可見,在手寫體里,“蝌蚪文”筆法作為內在線索貫穿其中,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漸成熟。從文字構型上看,如上文所說,《葛陵簡》文字在這一時期仍然接續著商周文字的傳統寫法,與《曾侯乙竹簡》《信陽楚簡》上的文字保持著高度的一致,而在戰國中晚期,楚文字才逐漸形成自己的區域性特征。雖然戰國晚期經過秦文字的統一,對楚文字的形體產生了顛覆性的沖擊,但是楚文字中遺留的許多用筆方式仍然可見于秦漢的隸書中,并且隨著文字發展的脈絡一直傳承到今天的楷書、行草書之中。
同時,盡管有著各自的發展線索,戰國時期手寫體與銘刻體也時常會有交集,如清華簡《保訓》篇就有著明顯與銘文鳥蟲篆相同的修飾符號,上博簡《用曰》和《鄂君啟節》在字形上也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在戰國后期楚系銘文與手寫體也有過短暫“合流”。這樣看來,銘刻體與手寫體、正篆與草篆、正體與草體正是在歷史進程中對應統一地前進著,它們互相影響、交織但又保持著自己相對獨立的發展路徑,從三代的青銅、秦漢的石刻、六朝的碑版,在后來的刻碑刻帖;從先秦的簡牘、兩晉南北朝的殘卷,到后世的紙箋信札,這些構成了中國文字、書法史上的兩條主要線索,以至阮元在《北碑南帖論》中提出“是故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這不僅僅是“帖”與“碑”的差異,更是手寫體與銘刻體辯證發展的結果。
《葛陵簡》的出土為我們揭示了戰國中前期日常手寫體的基本面貌。隨著戰國簡的不斷出土、公布,人們越來越希望通過這些塵封已久的竹簡木牘來一探當時的書寫情況。雖然現在的戰國書法研究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相關學術論文也層出不窮,但仍然還有很多問題有待研究。如在《葛陵簡》等文字圖像里,能看到不同場景中,當時人們對于文字的造型、書(鑄)寫態度有著巨大的差異,那么這樣的情況是否會導致楚文字里也存在類似秦書八體的現象?又如現有秦地和楚地出土的墨跡材料較多,我們能明顯感受到秦系文字和東方六國文字有著書寫風格上的差異,那么在六國文字的內部是否也有著這樣的書寫差異?還有六國文字的用筆方式又是如何具體影響后世隸書、楷書和行草書的筆法?這些問題,一方面還需等待更多文字材料的出土,另一方面則需要基于現有材料進行更加細致的對比研究、更加精確的圖像學分析、更加宏觀的綜合考察,唯有這樣才能還原當時的真實情境,早日揭開歷史的神秘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