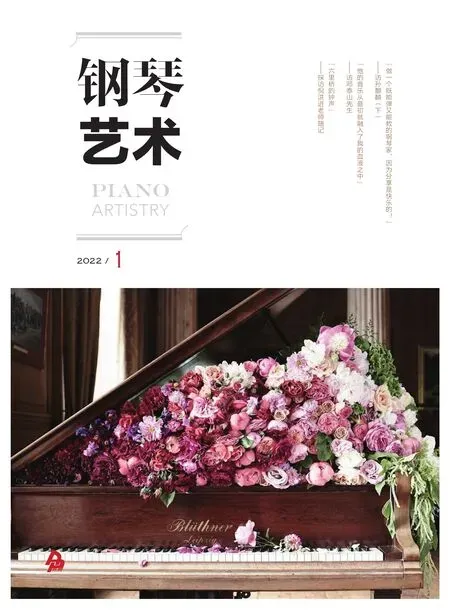琴鍵母子行(七)
文/ 程 莉

琴譜上的豬耳朵和小蝌蚪
W老師經常夸獎Ducati,說Ducati的識譜能力很強。Ducati到底識譜強不強呢?我來描述一下。Ducati開始和W老師學習時,前半年用的教材是599、布格繆勒、巴赫初級,后半年用的教材是849、299、巴赫創意曲、莫扎特奏鳴曲,還偶爾學習些老師復印的樂曲。所有這些曲子,Ducati都是直接合手練習,練習兩三天即可以達到熟練流暢的程度(當然,錯音和錯的節奏時有發生,要等回課時才能發現)。
我和Z老師、W老師都咨詢過關于分手練和合手練的問題。我知道大部分的孩子練琴時都是先分手練習,兩手都練熟了以后,再雙手配合慢練直至流暢。而Ducati練琴時都是先合手慢練直至流暢,然后再針對其中較為困難的章節進行分手細練。于是,我問老師,是否應該要求Ducati也從分手到合手?兩位老師都給了我否定的回答,她們都說,既然Ducati能夠直接合手,那就讓他先合手練,這樣不僅能幫助快速識譜,而且合手練也能有助于他完整地感受音樂。
于是,在老師的授意下,Ducati一直都是直接合手練的。新的譜子,Ducati看一眼譜號,眼睛同時看著兩行譜,兩手便直接開始彈奏了,如果彈錯了音,靠著耳朵的提醒,大多也能發現,并很快能改正過來,甚至是巴赫的三部創意曲,Ducati彈起來也不費力氣。我有時會忍不住問Ducati,你的眼睛是怎么看的?怎么能同時看兩行譜、三個聲部呢?Ducati至今也沒法清楚地告訴我他是怎么做到的。主要原因是在學琴過程中的關注和興趣。也許只有我知道,在剛開始學琴的時候,為了幫助Ducati記住C大調的do在哪里,re在哪里,mi在哪里,我們費了多大的勁啊!
5歲多的孩子最喜歡亂涂亂畫,家里有好幾套水彩筆,Ducati沒事就在畫本上東涂涂、西畫畫。于是我在紙上畫上五條線,讓Ducati在里面畫“小蝌蚪”,一邊畫一邊唱do、re、mi。
畫好了,我對Ducati說:“我們給小蝌蚪取名字吧。”Ducati一邊思索,一邊開心地回答:“Do叫小紅,re叫小黑,mi叫小黃。”
而我,有時會和Ducati一起商量,“我最喜歡fa這個音了,我也最喜歡綠色,那就叫fa小綠吧”。
……
Ducati很快給“小蝌蚪”們起好了不同的名字。我幫他把每個“小蝌蚪”的名字記錄在畫本的邊緣。
我又說:“好吧,那請Ducati給小蝌蚪們穿上五顏六色的衣服吧。”
Ducati開心地應允,拿出水彩筆,開始涂色,do涂上紅色,re涂上黑色,mi涂上黃色,fa涂上綠色……剛開始涂的時候,會有些吃力,Ducati需要先從do開始一線一間地向上數一數才能找到音,然后對照著畫本邊緣上記錄的名字想想這個音應該穿什么顏色的衣服,才能開始做他最喜歡的事情—涂色。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Ducati還饒有興趣,可是畫了幾個后,Ducati便不太樂意了。
于是,我問Ducati:“要不要我來幫‘小蝌蚪’們穿衣服?”
Ducati當然愿意。
于是水彩筆傳到了我的手上,我也裝作識譜很慢的樣子,每個音都從do開始一線一間地向上數,“do、re、mi、fa,啊!這是我最喜歡的fa,應該是,小綠,綠色的水彩筆呢?”
Ducati在一旁看著,雖然他沒有自己數,聽我數也是一樣的。
有時我故意數得慢一些,Ducati便會迫不及待地提醒我:“這是mi,這是mi,是小黃是小黃。”
在我恍然大悟的時候,Ducati已經將黃色水彩筆遞到我的眼前了,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樣。有時我故意數錯,拿錯顏色,Ducati便會自信滿滿地給我指出來:“不對不對,這是fa,應該穿綠色的衣服。”
玩了一會兒,我裝作有些累的樣子,于是水彩筆又回到了Ducati的手里……
要識譜,必須記住高音譜號和低音譜號
我畫高音譜號和低音譜號給Ducati看,這兩個譜號長得很奇怪,一個像豎琴,一個像耳朵。Ducati也想畫,但那時他才五歲,握筆寫字的能力還比較弱,于是他畫出了一個又一個胖胖瘦瘦、歪歪斜斜、奇形怪狀的豎琴和耳朵。我們一起瘋起來:“這個是豬耳朵,那個呢?是驢耳朵,這個是小人國的豎琴,那個是巨人國的豎琴……再畫一個,哈哈!這是蒼蠅的耳朵,那是蚊子的豎琴……”
一邊瘋著,一邊就牢牢地記住了兩個譜號,也記住了高音譜號和低音譜號中央C的位置。
游戲玩著玩著,Ducati已經不需要一線一間地去數了,很多音能直接看出來,只是速度還不夠快,我們繼續玩游戲,這次來玩搶答題。
拿著琴譜,我用鉛筆隨意指出琴譜上的一個音,我和Ducati來搶答,誰先說出這個音,誰就獲勝,獲勝者的獎勵是可以去鋼琴上彈出這個音,以及用鉛筆在琴譜上指出下一道題,而另一個人只能坐在一邊聽。Ducati搶答得很順利,大部分時間都是由他來告訴我音名并彈奏給我聽。我一副不認輸、不服氣的樣子,一直要挑戰Ducati。
如果說,剛開始比試時,我還多少讓著Ducati贏,可是比著比著,我便真的敗下來了。這個游戲玩了沒有多長時間,我便發現Ducati識譜的速度太快了,幾乎只要看一眼,便能立刻彈奏出來。
單手、單音識譜順利過關了,我們來提高難度,一是雙手單音,一是單手多音。
那時學的曲子都很簡單,每首曲子都很短,左手的音尤其少,右手也大多是單音,沒有和弦。Ducati練習時,常常眼睛看著兩行譜,同時彈奏出左右兩個手的音,一開始雖然慢些,但此能力隨著樂譜難度的提升也逐漸增強。
曲子越學越難,和弦越來越多,有時同時彈兩個音,這是比較簡單的,可是需要同時彈三個音、四個音時就難多了,Ducati又開始一個音一個音地去數,比如右手的和弦,Ducati會先找到根音,放好大拇指的位置,然后找上面一個音,放好食指,然后再上面一個音……
于是,我給Ducati出了一個主意:直接看最低音和最高音,確定大指和小指的位置,中間的音憑自己的感覺,不要一個一個地找。
Ducati按照我的建議試了試,剛開始正確率不高,中間的音會彈錯,可是彈著彈著大概找到了感覺,正確率越來越高,漸漸的只要沒有太多的升降號,Ducati都能一把彈出正確的和弦了。
后來學的曲子越來越難,Ducati的識譜能力也越來越強,比如巴赫的三部曲,即使是第一次看見的新曲子,Ducati也能同時看左右手的音符,并且直接進行合手彈奏。
不過,合手練琴也好、分手練琴也好,還是應該聽從老師的意見。Ducati的識譜能力固然和合手練琴有很大的關系。但我想,在Ducati后來的練琴生涯中,彈琴不夠細致、不夠關注細節等這些缺點都和分手練琴少、合手練琴多有著很大的關系。因此,到了學琴后期,我會不斷地提醒Ducati一定要盡可能分手慢練。
別給鋼琴撓癢癢
琴童手指的力量太小,而且往往不知道如何發力,如果琴童媽媽一味地提醒“用力、用力”,最明顯的結果是琴童手指會很緊張,如同雞爪一般緊繃著,看上去用了很大的力氣,彈出來的聲音卻是悶的,不飽滿、沒有顆粒感。
Ducati第一次跟著W老師上課,W老師就一針見血地指出:“Ducati彈琴的最大問題是聲音不好。”
上了一段時間后,我才慢慢理解了老師所說的“聲音不好”的意思,也就是音色不太好,原因大概是Ducati的手指用力方式不對。
在老師的指導下,我仔細觀察Ducati的手指,按照老師的要求高抬指,但是在下鍵的那一瞬間卻慢慢地按了下去(是“按鍵”而不是“彈琴”)。
W老師分析說,Ducati是為了高抬指而高抬指,這是錯誤的,應該為了彈出好聽的聲音而高抬指,Ducati雖然做出了很好看的高抬指動作,卻忘記了高抬指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按下琴鍵那一瞬間的力度。
Ducati已經養成了這樣的習慣,所以他的彈奏總是給人一種飄忽不定的感覺,有的音能彈到底,有的音一帶而過,尤其是速度較快,或者幾個音一起按的時候,就一定會“吃音”。
怎么能讓Ducati理解高抬指是為了按鍵那一瞬間的力度呢?
我對D u c a t i 說:“小男子漢,我們來練拳吧。”Ducati不解地看著我,不知道媽媽怎么“發瘋”了?
我故意不作解釋,抱起一個枕頭,鼓勵他:“沒事,你用力打我一拳,看你的拳頭有沒有力氣?”
Ducati握起小拳頭,在我的枕頭上輕輕一碰。
我夸張地大笑:“哈哈哈哈哈,癢死了癢死了,你這是撓癢癢。”
我又說:“你看,我學你啊,給鋼琴撓個癢癢。我學著Ducati的樣子用一個指頭在琴鍵上輕輕一碰,沒出聲音。”
Ducati依然不解,只是跟著我傻笑。
我鼓勵他:“沒事,你用點兒力氣,看你到底有多大的力氣?”
Ducati用拳頭在我的胳膊上用力一頂。
我說:“嗯,有點兒力氣了,不過好像不太疼。你看,我學你啊。”
我把指頭放在琴鍵上,用力一按,發出了沉悶的聲音……
試了很多種方法。
最后,Ducati放開了一點兒,揮舞著拳頭向我抱著的枕頭砸來,每次都是使勁地揮舞拳頭,真正砸向我的時候卻不敢使力。
他每打一次,我都照著他的樣子彈一下琴。
突然,我裝作恍然大悟的樣子:“哦,媽媽明白了,你看你舍不得用力打媽媽,和你舍不得用力彈琴鍵是一樣的,你是不是怕把媽媽打疼了?”
Ducati點頭不語。
我說:“你看,打拳時,先是把拳頭向后縮,然后突然使力向前,打人才會疼,對不對。這和彈琴一樣,抬起指頭,然后突然發力向下,才能彈出聲音。拳頭先向后,是為了更好地向前發力;指頭先向上,是為了更好地向下發力。”
Ducati一邊砸著枕頭,一邊體會著如何發力。
他試著拳頭不向后,直接慢慢地向前頂,或者用力地向前砸;又試著拳頭先向后,然后慢慢地向前頂,或者用力地向前砸。
慢慢地體會、嘗試,Ducati漸漸地理解了高抬指、后發力按鍵的感覺。
不過,一次是改不過來的。每次,Ducati又開始高抬指后軟綿綿地下鍵時,我便夸張地作出緊握拳頭向后一縮,一副要揍他的樣子,然后又緩緩地向前伸,頂住他的胳膊。
Ducati會心一笑,不用言語,每次我做出這個夸張的動作,Ducati便明白了。
除了高抬指的彈奏方法,指尖用力的方向也同樣重要
W老師經常告訴Ducati,彈琴時,指頭不是向前用力,也不是向后用力,應該是向下用力的。彈奏時應該感覺聲音向下穿透了整架鋼琴,一直穿到了琴鍵的下方。在彈雙音時,指頭也應該站好,然后向下發力,而不是向后拉,或者向后扒。我仔細盯著老師的手指,看老師給Ducati演示,仔細記下了老師對于“向下發力”的解釋。
為了理解老師的意思,陪Ducati練琴的時候,我便把手掌放在琴鍵的下方,感受觸鍵時整個琴鍵底板跟著一起微微震動的感覺,心里默默地想象著各種聲音的線路。
有的聲音是向下“彈”出來的。
有的聲音是向前“頂”出來的。
有的聲音是向后“扒”出來的。
Ducati看我把手掌貼在琴鍵下面,也學著我的樣子,一只手彈琴,另一只手貼在琴鍵下面,自己體會。
有的時候,Ducati按照老師說的,高抬指然后向下發力,讓聲音穿透鋼琴,彈完一個音后,他會和我說:“媽媽,我感覺剛才那個音穿透了鋼琴。”
有的時候,Ducati彈雙音時,把兩個手指貼在琴鍵上向后一扒,不等我開口,Ducati便主動問我:“媽媽,剛才那個音是不是不好?”
其實,我并不完全明白“穿透”的感覺,可是我想,我陪著兒子一起慢慢地體會、慢慢地找感覺,他一定會比我更快找到“穿透”的那種聲音和感覺。
跟著W老師學琴兩年,開始練習740。有一天,老師表揚Ducati:“聲音有了顆粒感。”
我很開心,這個難題終于有了進展!(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