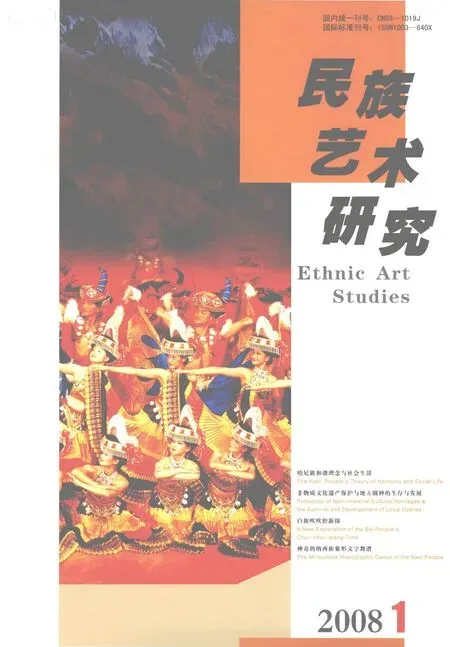歷代“繪事后素”注釋新解
馬 悅,陳 星
“繪事后素”是孔子在《論語·八佾》中提出的觀點,原文如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①[春秋]孔子:《論語·八佾》,載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第1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57—160頁。
雖然孔子是以繪畫之事作比喻談禮的重要性,并非就繪畫藝術談個人見解,但“繪事后素”歷來都是中國畫論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命題,有關它的注解與辨析亦是眾說紛紜,一直沒有定論,這使得“繪事后素”成為一個歷久彌新的論題。
一、“繪事后素”注解中的“先素”與“后素”之爭
歷史上有關《論語·八佾》中“繪事后素”的注解頗多,東漢經學大師鄭玄在前人的基礎上給出了這樣的解釋:
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②[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頁。
鄭玄認為“后素”是指在描繪色彩的工序上應先使用其他顏色,最后再將白色畫在這些顏色之間,從而形成清晰的紋理,“素”釋義為白色。此后這一觀點一直被沿用。
自北宋開始,學者們重新注解“繪事后素”,對以往被沿用的鄭玄的解釋產生了新的理解。邢昺在自己的《論語注疏》中不僅認可鄭玄的解釋,還引用了《考工記》以進一步佐證鄭玄的觀點,確切地說是佐證他自己的觀點:
案:《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繢之事,后素功。”是知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間,以成文章也。①[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 —論語注疏》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頁。
顯然,邢昺在色彩工序問題上沿用了鄭玄的解釋,不僅如此,他又以《考工記》原文來確立鄭玄與自己觀點的合理性。盡管鄭玄本人并未表明自己的解讀是基于《考工記》。北宋官員陳祥道并不認同鄭玄的說法,在他為《論語》作的注解中說:“倩盼,質也。有倩盼,然后可以文之以禮。素,質也。有素質,然后可以文之以繪。”②[宋]陳祥道:《論語全解》卷2,左周校,《欽定四庫全書》經部8,線裝書局,2012年版,第51頁。不同于鄭玄和邢昺,陳祥道認為女子的“倩盼”是首先需要具備的素質,在此本質基礎上才能更好地施行禮教。同理,在繪事上,應當先有一個較好的基底,然后才能在其上進行描繪,此處“素”理解為素質。北宋哲學家楊時對“素”的理解與陳祥道一致,他同樣認為:“甘采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茍無其質,禮不虛行。”③[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二,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3頁。楊時以甘可以調和眾味、白色之上可以描繪其他顏色這兩件事來分別作比喻,實則說的是較好的素質對于學禮之人是基礎且必要的。這里的“素”仍含素質之意,但具體理解為素白,因為楊時指出了繪畫上白色作為底色的道理。
直至南宋,朱熹沿循陳祥道的思路,并吸收了楊時的觀點,在二者基礎上對“素”作了更具體的注解:
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后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后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后可加文飾。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④[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二,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3頁。
朱熹認為繪畫需先有“素地”,這是顏色得以描繪的前提,那么這個“素地”到底是指什么呢?此處“素”被理解為“粉地”,朱熹保留了“素”作為白色的這一層意思,并將它與“質”相結合,也就是白底子,正如繪畫的開始首先需要一張潔白的畫紙,然后才能在其上繪出五彩顏色。由此來看,若說陳祥道的“素”是指一種相對抽象的審美性的話,楊時則指出了“素”具體的物質性層面,那么到了朱熹這里,“素”已經基于前人抽象的審美理解和具體的物質性啟發,在內容上更明確、內涵上更豐富了。需注意的是,朱熹同樣引用了《考工記》作為自己的參考,卻和邢昺的理路完全相反,可見二者對《考工記》的理解并不相同。至此,有關“繪事后素”的注解呈現出一種分歧,即分別以鄭玄和朱熹二人的說法為代表。從他們的解釋看,鄭玄確實是“后素”,而朱熹實則是“后于素”,也就是“先素”,問題的焦點就在于是“先素”還是“后素”。
元明時期,有關“繪事后素”的理解往往沿用了朱熹的說法。明朝張居正就在繪畫工序上認同了朱熹的說法,他認為:“如今繪畫之工,必先有了質素的地,然后加以各樣的彩色,是素在于前,絢在于后。”⑤[明]張居正:《四書直解》,王嵐、英巍整理,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頁。清朝以后,考據學的興盛使得學者們重新反思“繪事后素”的注解歧義問題,不論是基于鄭玄、朱熹二人所處年代距離孔子時代遠近的考量,還是二人對文本原意的還原度,學者們多認可鄭玄的解釋,尤其是他們認為宋人在解經時存在誤讀和主觀理解的問題,并重新考察了《論語》《考工記》和《禮器》三者中有關“繪事后素”的說法,力圖回到原初語境中探討“繪事后素”,由此也展開了從鄭說與從朱說的爭論。清人凌廷堪和全祖望分別是“從鄭說”和“從朱說”的代表,然而全祖望認為朱熹雖然對《考工記》的內容有所誤解,卻并未誤解《論語》本義。
近代以來,這一爭論仍未中斷,錢穆、伍蠡甫等人皆是從鄭說的代表,錢穆認為:“古人繪畫,先布五采,再以粉白線條加以鉤勒。或說:繪事以粉素為先,后施五采,今不從。”①錢穆:《論語新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60頁。錢穆是從繪畫工序上明確表示不認同朱熹解法的。伍蠡甫則認為:
總的意思是,先用五種顏色,涂成若干的面,因為面和面之間不免交錯、重疊,所以再用白色線條界畫清楚,把面和面之間的界限加以修整,顯得更有紋理,到了這時候也就獲得“后素功”了。又因為白色較易融化,須等五色繪好并且干了,才可加上。換句話說,“繢”(繪)指涂顏色,“畫”指以素色(白色)畫線條。
……“繢”產生的面,被動地反映客觀現象;“畫”產生的線條,則主動地綜合主觀和客觀,體現了……意和筆的主從關系。②伍蠡甫:《伍蠡甫藝術美學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頁。
伍蠡甫雖沿用了鄭玄的基本意思,但他重新加入了對繪畫創作方法的思考,賦予了“繪事后素”一個新的注解維度。豐子愷、李澤厚則是從朱說的代表,豐子愷認為:“‘繪事后素’,就是說先有白地子然后可以描畫。這分明是中國畫特有的情形。這句話說給西洋人聽是不容易被理解的。因為他們的畫……不必需要白地子的。”③豐子愷:《繪事后素》,載陳星主編、劉晨編《豐子愷全集17藝術理論藝術雜著卷11》,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頁。豐子愷是立足于中國畫的傳統解讀,并且他深知中國畫中“素地”的特殊審美意趣。李澤厚的理解是:
“禮”如是花朵,也需先有白絹(心理情感)作底子才能畫也。總之,內心情感(仁)是外在體制(禮)的基礎。④李澤厚:《論語今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94—95頁。
李澤厚亦是沿用朱熹的基本意思,但他的側重點放在了對儒家思想中仁、禮關系的分析上。也有學者認為鄭玄遵循荀子的“性惡”論,認為人性并不是完美的,需要以“禮”來規范,所以是“后素”;朱熹遵循孟子的“性善”論,認為人性是善的,正像一張無瑕的白紙,可以畫出最美的圖畫,所以是“先素”。⑤李慶本:《強制闡釋與跨文化闡釋》,《社會科學輯刊》2017年第4期。二人在讀解時皆存在主觀預設的問題,所以并不符合孔子的原意。
總體來看,有關“繪事后素”的注解之爭,主要呈現出兩種觀點:或是以經典為參考,將其簡單地看作是工藝美術流程中的一個先后問題,實則是為了尋找符合孔子儒學思想的解讀;又或是以孔子的儒學思想為依據,通過哲學的思辨推論何種解讀更準確。其實不論是這兩種角度中的哪一種,所追問的都是孔子的儒學思想,而不是“繪事后素”。并且在這一過程中,孔子的儒學思想成為了“繪事后素”唯一的評判標準。也就是說,“繪事后素”的注解雖然在鄭玄的“先素”說和朱熹的“后素”說中出現了分野,但是實質上被爭論的并不是“繪事后素”本身,而是隱含在其背后的孔子的儒學思想。這里不得不提到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儒家經典文本在字義訓詁和義理闡釋之間始終存在著緊張關系。雖然字義訓詁與“漢學”二者并非必然對等,但是主張字義訓詁者必然反“宋學”,而主張義理闡釋者必然反“漢學”,此為事實。⑥吳根友、孫邦金等著:《戴震乾嘉學術與中國文化(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913頁。那么在這種學術背景下,“先素”與“后素”之分究竟是否符合孔子以素喻禮的儒學思想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二者都是將承載孔子儒學思想的文本作為論述依據的,只是在具體論述過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角度,那就是字義訓詁和義理闡釋。雖然這會導致二者在闡述思路上的不同,但并不會影響符合孔子思想這一前提。顯然,孔子在這段對話中意在強調禮之重要性是毫無疑問的,鄭玄和朱熹二人雖是以不同的出發點理解孔子的“繪事后素”,但無論是“先素”還是“后素”,二人實則殊途同歸,他們的解讀都符合孔子重“禮”的本意。
值得一提的是,伍蠡甫從繪畫創作的角度為“繪事后素”開創了一種新的讀解方式,即通過繪畫的技法與美學思想的結合給出全新的解釋。至此,圍繞“繪事后素”展開的爭論,所思考的內容其實早已突破探究孔子原意問題的局限。豐子愷更是將“繪事后素”置身于中國畫傳統中解讀,甚至與西洋畫傳統對比探討,使得“繪事后素”得以逸出原有語境,同時也面向其他繪畫傳統,不僅僅是局限于中國畫的范疇。所以對于“繪事后素”的思考,如果純粹只是探討孔子原意,則往往會忽視對“繪事”本身的關注;若僅僅只是將其放置在儒學經典和思想的領域中,又會使得對“繪事后素”的理解陷入單一化的層面。其實不論“繪事”所指是工藝美術還是繪畫藝術,都不可忽略“繪事”本身對于理解“繪事后素”的重要意義。從“繪事”的角度探討,也必然會為“繪事后素”的讀解創造一個更為寬廣的空間。
二、“先素”與“后素”是《考工記》中不同的工序
雖然說“繪事”在孔子那里是作比喻之用,但世人在爭論“先素”與“后素”的問題時仍離不開“繪事”本身,尤其是“繪事”過程中的工序問題。何以鄭玄與朱熹二人都引用了《考工記》,卻得到完全不同的解讀呢?難道確實如清人全祖望所說,是朱熹誤解了嗎?《考工記》是春秋戰國時期記載手工業技術的文獻,其中對設色工序的記載頗為詳盡。設色的工序較為繁復,共分為“畫、繢、鐘、筐、巾荒”五個工種,這五個工種都與練染工藝密切相關,這些工序的解說具體通過《畫繢》《鐘氏、筐人(闕)》《巾荒氏》三篇來記述。首先是《畫繢》篇:“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后素功。”①聞人軍:《考工記譯注》第11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頁。從原文即可看出“畫繢”工序同時包括繪畫與刺繡,并且強調顏色的搭配。《鐘氏、筐人(闕)》篇:“鐘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②聞人軍:《考工記譯注》第11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頁。“鐘”是指給羽毛、絲、帛等染色的工藝;而“筐”條文已缺,可能是記載印花的工藝。《巾荒氏》篇:“巾荒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以欄為灰,渥淳其帛。”③聞人軍:《考工記譯注》第12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頁。“巾荒”是指練絲、帛的工藝,主要用水練和灰練的方式。顯然,制作一件精美的服飾,在工藝上按邏輯順序應當先是巾荒,通過精煉的方法使絲綢布帛變得柔軟潔白;其次是鐘和筐,對柔軟潔白的布料進行染色和印花;最后是畫繢,通過顏色的搭配在已經印染好的布料上進行描繪和刺繡。
從目前出土的漢代考古文物和造紙術的發明時間來看,紙質繪畫在當時并不是常態,所以鄭玄所指的繪畫,并非是人們通常理解的紙上繪畫,而是指在已經精煉和印染好的優質絲綢布帛之上進行繪畫。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紗絲錦袍將印花和彩繪方法相結合(如圖1),完整地呈現了當時的“畫衣”傳統⑤印花敷彩紗絲的制作工序是在敷彩之前先用鏤版印花模子在素凈的絲綢上印好枝蔓,然后再進行彩繪。如用銀灰色勾畫出蓓蕾,用棕灰勾繪苞葉,再用粉白勾繪。先秦“畫衣”屬皇后專用,但這件漢代墓出土文物采用了同樣的工藝。參見張競瓊、李敏編著《中國服飾史》,東華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那么結合《考工記》的內容,可以知道鄭玄的注解是對應了畫繢這一步,他在制作工序上理解為“后素”完全沒有問題,一來白色本身容易被其他顏色污染,二來白色可作最后勾勒花紋之用,素作為“白色”這層意思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此一來,似乎朱熹的“先素”是錯誤理解《考工記》所記載的“畫繢”之意了?

圖1 馬王堆漢墓出土印花敷彩紗絲錦袍湖南省博物館藏④圖片來源:湖南省博物館官網,http://61.187.53.122/collection.aspx?id=1361&lang=zh-CN。
其實再次翻閱《考工記》中關于設色工序的記載,就會知道首先是“巾荒”,其次是“鐘”和“筐”,最后是“畫繢”。而在整個過程中,涉及到“素”的流程并非只有最后一步“畫繢”,還有第一步“巾荒”,因為“絲和絲綢必須經過精煉,它們種種優美的品質和風格如珠寶的光澤,柔軟的手感,豐滿的懸垂態以及特有的絲鳴,才能顯露出來,才能染成鮮艷的色澤。”①陳維稷:《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頁。如此看來,陳祥道所說的“素”正是指“素質”,這與絲綢精煉的過程是對應的,正如需要絲綢呈現出“種種優美的品質”,繪畫也需要一種優質的載體。而楊時所認為的“白受采”,將素作為“白色”來理解,也是與絲綢的精煉和印染密切相關的,因為只有素白的優質絲綢才能更好地對其進行染色。畢竟潔白的畫卷上才能更好地展現色彩原本的瑰麗姿態,不會讓色彩因畫卷的底色而在視覺上發生改變。那么吸收了二人觀點的朱熹,將素理解為“白底子”也就可以理解了。從整個設色工序來看,“白底子”正是呼應了那被精煉后潔白質優的絲綢。朱熹的理解恰恰是因為他關注到了第一步在整個設色工序中的重要性,所謂的“先素”,在此基礎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如果從設色工序的角度來理解“繪事后素”,“先素”和“后素”并不意味著對錯,而只是就分別立足于整個工序中的不同步驟而言的。
由此,朱熹雖然在設色步驟上與鄭玄關注的不同,但是其解讀也是成立的。所以,如果從《考工記》與繪畫的角度來看“繪事后素”的注解,鄭、朱二人在解讀上的偏差,并非是因為某種知識認知上的不同,而是這一問題本就蘊含多種解讀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技法和媒材等發生變化后,又能夠在注解上給予“繪事后素”更多創新的可能。
三、繪畫的技法與媒材的變化賦予“素”新的內涵
在繪畫問題上,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鄭玄對“后素”的理解基于當時的媒材和技法都是成立的,而朱熹身處的南宋時期絹畫亦是非常普及的。也就是說,以絲帛絹布為媒材作畫對于鄭玄和朱熹來說都是非常熟悉的一種作畫方式。那么,二人在繪畫設色程序的解讀上有所不同,顯然并非是媒材引起的,更有可能是因為繪畫技法在發展的過程中對此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里或許應當對絹畫技法上的一些特點有所考量。
從當時的一些團扇作品(如圖2、3)看,白色顏料確實是最后疊加上去的。一方面是因為花朵本身即為白色的,需要多次疊加才能獲得潔白的顏色效果;另一方面這也是白色用于最后調整畫面的一種功能,這與鄭玄所說的“后素”在方法和目的上并無二致。所謂“后素”這一方法或也可說是對前人設色技法的沿用,但是至宋代,這一技法已然不是絹畫設色過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中國古代傳統絹畫的繪制首先進行白描勾線,然后再上色。相對于鄭玄所處的漢代,宋代絹畫的上色技法已經有所發展。絹畫在設色過程中極為講究步驟,尤其是在繪制工筆畫時,第一步往往需要先做好打底工作,用白粉在畫卷上打底正是一種常用的方法,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調劑一下明度,特別是某些淺色的花和枝葉,都可以根據需要,薄薄地打一層粉底,然后著色。”①袁志權:《國畫基礎》,四川美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頁。事實上,白粉不僅可以用于正面打底,還可以在描繪人物、花卉等形象時于畫卷的背面進行托色。所謂托色也就是上色時需要在絹畫的背面先做一層底色,尤其是當畫的正面用了一些較淺的顏色時,往往會在其背面先涂一層白色的底色,然后再于正面進行多次暈染,以保證畫面顏色呈現出干凈鮮艷的效果。當然,“有的花著完色后,還可以用白粉提染……使花朵顯得更加鮮艷,更有精神。”②袁志權:《國畫基礎》,四川美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頁。那么,從這一設色步驟的技法特點看,則完全可以理解朱熹為何會提出“先素”的說法了。

圖2 宋佚名《夏卉駢芳圖》絹本設色故宮博物院藏② 圖片來源:《宋畫全集》第1卷第8冊,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頁。
其實,除了繪畫技法的發展,還有一個較為顯著的變化,那就是紙逐漸成為繪畫的主要媒材。鄭玄所處的漢代紙上繪畫定然不多見,但南宋時期紙質繪畫早已普及,媒材不同,觀念和技法也會隨之發生改變。按照當時的繪畫思維,在白紙上作畫,又何須最后用白色描繪花紋?白紙底色已然潔白,甚至設色時的粉底也可免去,一張質地上乘的白紙成為了關鍵。那么對朱熹而言,他必然需要重新考量“后素”在步驟上是否仍適用于紙質繪畫。
南宋時期紙上繪畫已然是常態,在其上描繪五彩顏色時不一定需要最后再用白色勾勒,因為在紙本上畫家可以憑借巧妙的留白來表現合適的內容,盡管這對畫家的技法、構圖和審美觀念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梅花的設色為例,在絹上(如圖3)和在紙本上繪制(如圖6)設色方法就完全不同,絹上梅花的花瓣需最后用白色多次疊加,但紙本上可以預先將白色的花瓣部分勾畫后空出來,透出紙張本身的白色即可。媒材的改變會直接影響到繪畫方法,但是涉及到畫面構圖中的改變,往往并不會受媒材的限制,留白的構圖方式正是一種審美觀念的體現。藝術家豐子愷在《繪事后素》一文中曾談及中國畫構圖中的留白:“請看中國畫,大都著墨不多,甚或寥寥數筆,寥寥數筆以外的白地,決不是等閑廢紙,在畫的布局上常有著巧妙的效用。這叫做‘空’,空然后有‘生氣’。”⑤豐子愷:《繪事后素》,載陳星主編、劉晨編《豐子愷全集17藝術理論藝術雜著卷11》,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以馬遠、夏圭為代表的南宋時期山水畫家,他們的作品在構圖上就體現出了這種“空”的“生氣”。馬遠和夏圭的作品在構圖上多呈現出“一角”和“半邊”的特點,馬遠的《水圖》(如圖4),一共有12幅小圖合為一長卷,集中表現江河湖海中水的多種形態特征,在構圖上較為簡單,基本都是遵循著“半邊”的構圖法則,內容集中在畫面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多是空白。夏圭的《松溪泛月圖》(如圖5),前景是松樹局部的精細刻畫,稍遠處是一葉扁舟和泛舟之人,中景已經沒有多少筆觸;整張畫的主要內容都集中在前景中,或者說是畫面的左下角,留有大量空白處。正因為這種構圖上的留白,馬遠在描繪近處水的形態時得以保留遠處水的一望無際之感,而夏圭在留白處反而營造出更空闊的意境,這正是“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①[清]笪重光:《畫荃》,[清]王石谷、惲壽平評,吳思雷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頁。可見,畫家有意識地在創作中借助媒材的特質創造出了新的繪畫方式。這或可以說明,媒材的改變已然為繪畫的技法和觀念提供了更多創新的可能。這也意味著,繪畫中如媒材、技法、觀念等諸多因素的改變,都會為“繪事后素”的讀解提供新的可能。

圖3 宋佚名《折枝花卉圖》(局部)絹本設色故宮博物院藏③ 圖片來源:《宋畫全集》第1卷第8冊,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頁。

圖4 馬遠《水圖》(局部)絹本設色故宮博物院藏③ 圖片來源: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第1卷第4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31頁。

圖5 夏圭《松溪泛月圖》絹本設色故宮博物院藏④ 圖片來源: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第1卷第4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頁。

圖6 佚名《百花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② 圖片來源: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第1卷第7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頁。
如果細看朱熹在自己的注解中所引用的《考工記》內容,就會發現他已經為自己試圖重新解讀“繪事后素”作了鋪墊。朱熹所引用的那句話是“繪畫之事后素功。”并且他只引用了這一句內容,而這一句中有兩個關鍵詞,那就是“繪畫”和“后素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朱熹將原文中的“畫繢”二字改為了“繪畫”二字,在意思上必定是與原文不同的,那么他將這兩個字進行替換是引用錯誤還是有意為之呢?顯然,朱熹并非是錯誤引用了《考工記》中所記載的內容,雖然“繢”通“繪”,但“繢事”卻并不等同于“繪事”,這一轉換,意味著朱熹在讀解“繪事后素”時,是將其置于繪畫的層面中考量。至此,不得不再次提及鄭玄所討論的“繪事后素”,因為細讀原文會發現他所討論的對象其實也是“繪畫”,而非邢昺所引用的“畫繢”。由于鄭玄也是在繪畫的層面里讀解“繪事后素”,所以他們二人所討論的對象是相同的,那就是繪畫中的“繪事后素”。“畫繢”問題涉及的主要媒材是絲綢布帛,且多以設色或刺繡的方式表現,是更具綜合性的工藝美術。而“繪畫”涉及的媒材則絕不僅僅是單一的絲綢布帛了,它的媒材更加豐富,表現方式更為多樣,同時還會不斷被賦予各種藝術觀念,是一種專門的藝術門類。這意味著原先的“素”在朱熹的時代則需要面對新的媒材、技法和繪畫形式,整個繪畫藝術的語境已經發生了變化。如果仍是基于《考工記》解讀“繪事后素”,對朱熹的時代而言,彼時“畫繢”中的“素”已經不能完全適用于此時“繪畫”中的“素”了。此時的“素”雖仍是主要指白色,但是素白的內涵卻變得豐富了。素白不僅是具體的一種物質色彩,如白顏料和白紙,它還可以是一種抽象的審美色彩,如畫面中內容豐富的空白。
之所以“素”在內涵上能不斷被賦予新的內容, “繪事后素”能產生“先素”與“后素”的讀解,正是因為繪畫藝術的時代環境在不斷改變。或許可以這樣理解,朱熹所面臨的情況,正是需要將“繪事后素”重新放在當時的繪畫藝術語境里來解讀。他的解讀在繪畫藝術的技法上必然會與前代《考工記》中的設色工序有所重合,所以對《考工記》的借鑒是必要的,但是亦有大量新的內容是《考工記》無法涵蓋的,因此他給出了新的創見。
結 語
盡管圍繞“繪事后素”注解產生的爭辯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但是在以孔子的儒學思想為前提的情況下,對于“繪事后素”意涵的辨析更多是停留在思想的層面,而糾結于“先素”還是“后素”則是因為對孔子談論“繪事后素”時的作者意圖的不斷追問。事實上,孔子的真實意圖,我們早已無從得知,留給我們的唯一可以確證的只是文本,這就意味著在讀解上具有更多的闡釋空間。如果只是從孔子的儒學思想入手進行學理上的推論,則必然使得孔子的儒學思想成為唯一可以解讀“繪事后素”的依據。但是“繪事后素”在漫長的歷史、文化和藝術的演變過程中,已經逐漸脫離了孔子儒學思想的限制,不論是工藝美術、繪畫藝術還是其他藝術,亦不論是采用畫布、畫紙或其他材料工具,它早已獨立成為一種在不同的門類藝術和不同藝術媒介中皆有一席之地的美學思想。可見,“繪事后素”具有跨門類性和跨媒介性,它所涉及的領域是非常寬廣的,絕不僅限于儒學思想。正是因為在時間的長河中,不同門類藝術的特點和媒介不斷變化的綜合作用,賦予了“繪事后素”一種時代性,致使其能夠源源不斷地產生新的內涵,在每一時期都煥發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