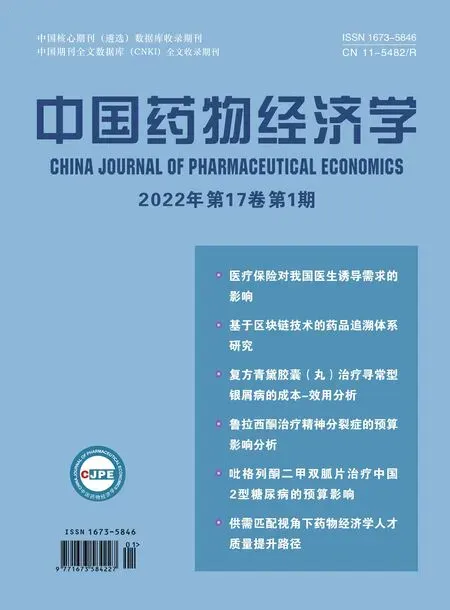槐耳顆粒與索拉非尼聯用對原發性肝癌術后復發患者的作用效果及對甲胎蛋白、甲胎蛋白異質體-L3水平的影響
韓大志
原發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PHC)在惡性腫瘤中發病率較高,對患者的生存預后影響較大[1]。手術治療對非晚期患者具有較好作用,但有數據顯示,術后患者在5年內的復發或轉移率是40%~70%,而術后復發時癌癥多進展至中晚期,較易喪失再次手術和介入治療機會[2-3]。針對此類患者,以往臨床多選擇分子靶向型藥物索拉非尼等進行治療,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腫瘤生長。近年來,隨著人們對祖國醫學知識的深入發掘,槐耳顆粒因其具有活血消癥、化瘀消滯,以及促進癌細胞凋亡等作用逐漸引起了臨床醫務工作者的關注[4-6]。鑒于此,本研究就槐耳顆粒與索拉非尼聯用對PHC術后復發患者的作用效果及對甲胎蛋白(AFP)、甲胎蛋白異質體-L3(AFP-L3)水平的影響進行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在朝陽市中心醫院接受治療的PHC術后復發患者114例作為觀察對象,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各57例。觀察組男37例,女20例;年齡41~59歲,平均(46.57±1.34)歲;KPS評分65~93分,平均(81.27±10.36)分;肝功能Child-Pugh分級:A級47例,B級10例。對照組男39例,女18例;年齡42~62歲,平均(46.60±1.41)歲;KPS評分64~94分,平均(81.33±10.27)分;肝功能Child-Pugh分級:A級50例,B級7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納入標準:1)已接受PHC手術治療,且存在可測量的病灶,無法再次實施手術切除;2)年齡≥40歲;3)KPS評分超過60分,且預計生存時間超過3個月;4)患者或其家屬已充分知情,并已簽署了同意書。排除標準:1)其他類別的惡性腫瘤;2)心、腎及造血系統相關疾病;3)資料數據缺失;4)無法耐受藥物治療。
1.2 治療方法
對照組給予索拉非尼(拜耳醫藥公司,國藥準字H20090846,0.2 g/片)口服治療,0.4 g/次,2次/d。觀察組在此基礎上另給予槐耳顆粒(啟東蓋天力藥業公司,國藥準字Z20000109,20 g×6袋)治療,20 g/次,3次/d。兩組以1個月為1個療程,治療2個療程。
1.3 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療效,治療前及治療2個月后的AFP、AFP-L3水平,以及不良反應。其中AFP及AFP-L3水平通過購自日本日立公司的7600型全自動生化反應分析儀及配套試劑實施測定,AFP的檢測采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法,而AFP-L3的檢測則選擇微量離心柱法。
1.4 療效判定標準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制定的實體瘤療效判定標準實施評價,主要分為完全緩解(CR)、部分緩解(PR)、進展(PD)、穩定(SD)。CR為瘤灶已完全消失,且持續時間≥4周;PR為瘤灶縮小≥50%,且持續時間≥4周;PD為瘤灶縮小<50%,或增大≤25%,且未發現新病灶;SD為瘤灶增大>25%,或發現新病灶[7]。其中客觀緩解率(ORR)=CR例數+PR例數/總例數×100%。而疾病控制率(DCR)=CR例數+PR例數+SD例數/總例數×100%。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1.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療效比較
觀察組的ORR、DCR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療效比較
2.2 兩組AFP及AFP-L3水平比較
治療前兩組AFP及AFP-L3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AFP及AFP-L3水平降低,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AFP及AFP-L3水平比較(±s)

表2 兩組患者AFP及AFP-L3水平比較(±s)
AFP(μg/L)AFP-L3(%)組別 例數治療前 治療后 t值 P值 治療前 治療后 t值 P值對照組 57 550.20±53.63 406.44±60.37 13.441 0.000 20.13±4.07 13.97±5.09 7.136 0.000觀察組 57 543.77±52.19 357.28±61.79 17.408 0.000 20.15±3.49 11.24±4.34 12.079 0.000 t值 0.649 4.296 0.028 3.081 P值 0.518 0.000 0.978 0.003
2.3 兩組不良反應比較
觀察組不良反應發生率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比較
3 討論
臨床上,PHC屬于十分常見的一類惡性腫瘤,其發病機制主要與乙/丙肝病毒的感染和長期暴露于有毒化學物質環境中,以及黃曲霉素的污染等因素有關[8-9]。目前,隨著肝癌治療水平的逐漸提升,經皮肝穿刺的射頻消融術已發展成臨床的主要術式,亦可獲得一定的療效[10-11]。然而患者在術后5年內的復發率仍然較高,給予新型藥物綜合治療可能有助于患者的預后生存。
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的ORR、DCR高于對照組,提示觀察組應用槐耳顆粒以及索拉非尼綜合治療后的療效更佳。分析原因,考慮可能與這兩種藥物的藥理機制有關。其中索拉非尼是一種小分子的靶向型藥物,其也是多類激酶抑制劑,能夠對蘇/絲/酪氨酸激酶等受體產生作用,抑制瘤灶新生血管形成,同時,其能對Raf/MEK/ERK等信號通路發揮強力抑制作用,從而直接阻礙肝部腫瘤的進展。槐耳顆粒作為一種中成藥,其含有較多的有機成分,此類成分能夠阻斷癌細胞的EMT信號通路,從而有效抑制腫瘤細胞的進展性侵襲和轉移過程,同時其還能抑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表達,最終通過阻止腫瘤形成新生血管,改善肝細胞的損傷狀態和有關免疫功能,達到較好的治療效果[12-13]。AFP屬于一類糖蛋白分子,也是評價肝癌的特異性指標,隨著肝癌的惡性程度加劇,其水平也會呈現出明顯的升高狀態。同時,AFP的糖鏈合成及降解需在細胞中完成,且其糖鏈的結構具有異質性,AFP-L3即為其異質體的一種。相對于AFP,AFP-L3對于肝癌的檢測往往更加敏感,檢測的AFP-L3比例若越高,則表示癌癥的惡性程度也越大。本研究發現,治療后兩組AFP及AFP-L3水平降低,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提示觀察組的用藥方案能夠有效降低AFP及AFP-L3水平,從而更好地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究其原因,索拉非尼作為多激酶抑制型的靶向藥物,其口服后富集在肝部的瘤灶區域,可阻滯酪氨酸激酶受體,阻止癌細胞增殖,同時能抑制酶與受體相互結合,最終阻止新生血管形成,控制病情進展。槐耳顆粒的主要成分包括多糖蛋白,具有活血消癥、化瘀消滯等功效,其有效成分還能對血管內皮細胞產生作用,繼而影響其增殖和遷移,以及附壁和血管形成的能力[14-15]。此外,其還能加速癌細胞的凋亡,促進免疫細胞不斷分化,提升免疫力,并能強化機體的抵抗力,糾正患者機體中的內環境失衡,并使腫瘤細胞發生轉化,最終優化并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本研究中,觀察組不良反應發生率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提示觀察組的用藥方案還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原因主要考慮是因為觀察組增加的槐耳顆粒藥物屬于中藥制劑,其存在多類有機成分及礦物質,藥物的不良反應較少,不會對患者機體造成損害,因此安全性也較高。這與相關報道一致[16-17]。
綜上所述,槐耳顆粒聯合索拉非尼對PHC術后復發患者的作用效果較好,還可明顯改善患者機體的AFP和AFP-L3水平,安全性也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