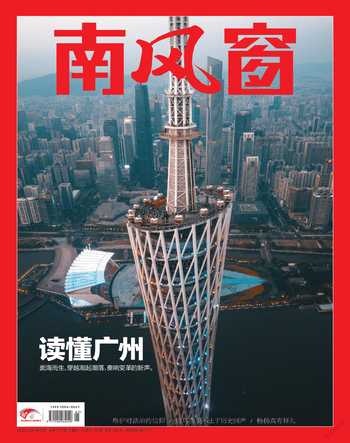制度的力量—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與收入分配公平感的演化
制度的力量——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與收入分配公平感的演化
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黃健、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鄧燕華
本文選自《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1期
民眾的分配公平感關乎國家的政治安全與社會的和諧穩定。中國社會保障的制度構建引導了居民分配正義的價值取向進一步偏向平等與需求原則,人們對資源分配狀況的判斷也越來越取決于其對政府的社會保障職能的滿意度。通過分析2005年和2015年GSS調查數據發現,民眾對政府社會保障職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社會收入分配狀況的評判,即對政府社會保障職能越滿意的個體,越有可能認可當前社會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
相比2005年的情況,2015年民眾對社會收入分配狀況的感知態度更為積極。在社會保障建設投入增速更快的省份,個體的收入分配公平感提升得更為明顯,而社會保障職能滿意度所起的作用也更為突出。相關發現豐富了制度文化論的研究,也為社會保障制度具有價值引導和塑造作用提供了經驗證據。
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和利益格局已經并將繼續發生深刻調整,如何有效維護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凝聚社會價值共識,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和高質量社會發展必須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社會福利制度作為各方利益的交匯點,不僅能夠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而且可以引導和塑造民眾在分配正義上所持的價值取向。一般認為,經濟市場化的深入會導致利益分化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擴展,這也使人們擔憂收入分配不公感會隨之上升。
本文的研究顯示,雖然中國的市場經濟在21世紀以來獲得縱深發展,利益結構調整也隨之進一步深化,但民眾并未因此而對社會收入分配狀況產生更多負面感知。相反,伴隨社會保障制度的重構,民眾分配正義的價值取向更加偏向平等原則和需求原則,他們對于社會收入分配狀況的感知態度也變得更為積極。本文的研究充分說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與凝聚以公平正義為取向的社會價值共識并非相互沖突的兩個過程,協調二者關系的關鍵在于建立優越的制度,以人民為中心,為改革開放找到最大公約數。
“裝在盒子里的人”:“Z世代”盲盒消費景觀及其形成機制
福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劉森林
本文選自《中國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
Z世代因成長于經濟富裕、科技發達、少子化的社會環境中,在消費市場中成為最大的消費主力軍,并且在價值取向與行為選擇上呈現出別具一格的亞文化特征。洞悉Z世代群體在社會結構變遷中與市場消費過程中的亞文化現象,能夠從機理上把握Z世代的價值取向和行為特征。
盲盒相較于美食、游戲、網絡文學等新潮流成為“Z世代”最“燒錢”的愛好中排名的第一位,究其原因除了盲盒所特有的美感、神秘性和不確定性這些屬性,更重要的是隱藏在盲盒消費里的“文化工具箱”,即“Z世代”亞文化。“文化工具箱”理論認為,文化是一種工具,為行動過程提供策略,而不是作為理念塑造行動者的行動目標。盲盒的特質確實吸引了“Z世代”,但“Z世代”作為行動者并非是被動消費的“文化傀儡”,而是根據盲盒的特質和群體本身亞文化與心理需求主動選擇的結果。因為“Z世代”有社交的需求、喜歡高顏值的物品、重視體驗感和自我表達,所以他們才選擇了可以滿足這些需求的盲盒,而不是其他。
面對這一新型的亞文化現象與消費現象,我們應該充分肯定盲盒消費給“Z世代”群體帶來的諸多益處。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盲盒消費特有的不確定性、隨機概率機制等特點導致的“Z世代”群體在盲盒消費過程中存在的賭徒心態和成癮性行為。這是亞文化消費被平臺經濟形塑的體現。平臺資本擁有極其強大的動力生產相關的內容產品,用以滿足不同用戶的需要,但為了平臺生存和資本增值的需要,平臺經濟及其資本推行消費文化,運用帶有極具誘導消費性質的角色養成、符號競爭與意識形態引導等策略去賺取利益,這就導致消費者的情感有可能被誘使、被綁架、被規訓。而“Z世代”正是被誘使與被規訓的脆弱的消費者。因為他們原本只是希望在盲盒消費這一亞文化所創建的世界中找到快樂、歸屬感和自我認同感,其潛意識是對他們所處的現實社會的主導權力系統的一種逃避與反抗。
粉絲——明星關系感知的影響因素與作用機理: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晏青、廣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付森會
本文節選自《國際新聞界》2021年第10期
近年來,中國興起一批不同于演藝科班出身的傳統明星的“養成類明星”,他們大多14~25歲。這種崇拜年輕偶像的現象始于韓國電視劇,2010年左右開始在中國流行。養成類偶像崇拜的獨特性在于,“偶像”成長是在粉絲的參與、“培養”和支持下實現的。此類偶像在青少年群體中的影響很大,綜合近五年的《騰訊娛樂白皮書》年度數據來看,從2015年起,位列網絡熱度前三的都屬于養成類明星,鹿唅、王俊凱、易烊千璽、蔡徐坤、肖戰等的網絡熱度,超過楊冪、范冰冰等傳統明星。在這種粉絲文化中,粉絲與明星之間的關系出現了新模式,粉絲自稱是明星的媽媽、姐姐、妹妹、哥哥、女兒等,相對應地分為媽媽粉、姐姐粉、妹妹粉、哥哥粉、女兒粉等群體,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一定的角色責任和義務,有學者將這種關系被稱概念化為“擬親屬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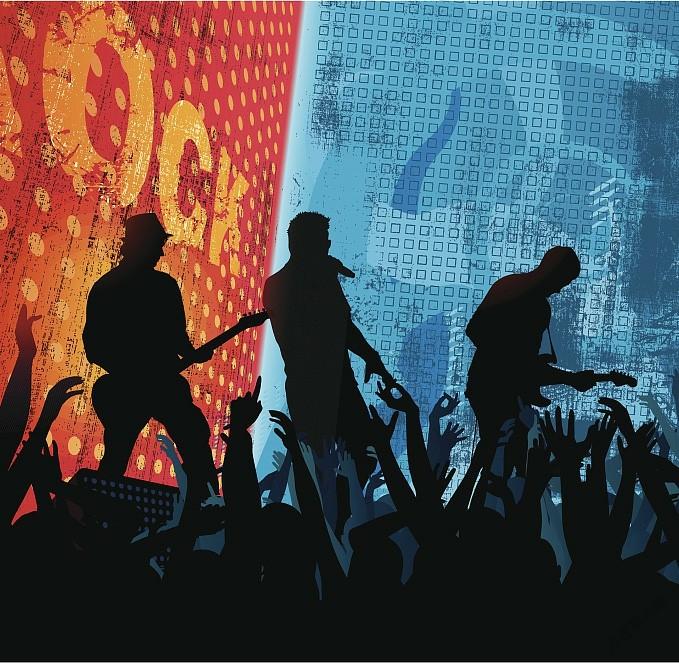
明星吸引感與粉絲對擬親屬關系感知具有正向強顯著關系,明星的外在形象、內在品質都是關系感知的重要因素。明星吸引感包括來自明星的作品、外在形象、精神風貌三個維度。這一發現印證了已有研究中明星崇拜更關注外在形象的論斷。但本研究對此論斷有進一步發現,明星的內在品質對粉絲感知也具有較強影響。也就是說,粉絲對關系感知,不僅會同時關注明星外在形象,也會同時關注內在品質。究其原因,與傳統的粉絲——明星關系不一樣,擬親屬關系感知除了涉身性之外,還包括明星的精神風貌、性格、品性,這些會強化這種關系的合法性,也使得粉絲能夠對擬親屬關系具有更高、更正面的感知。
本研究發現,關系卷入度(信息了解程度、線上線下活動參與程度)對粉絲的明星關系感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新浪微博上,粉絲與偶像通過轉發(13.2%)、留言(15.9%)和點贊(70.9%)等方式進行互動。粉絲可以通過社交媒體時刻關注偶像動態的更新,并與之互動,甚至深入參與偶像的形象生產、關系維護和事業發展,這讓粉絲感到偶像像家人一樣總是在場的。
亨利·詹金斯、大衛·吉爾斯等將其視為“參與式文化”。但是,他們所討論的參與式文化的實踐對象是粉絲小說、歌曲或其他媒介文本,而在本研究中的參與生產的對象是明星,即參與宣傳、支持、生產偶像,這也是關系卷入度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依據四個變量的相關系數與標準化路徑系數來看,也印證了關系卷入度對明星關系感知的重要影響。另外,不可忽視的是,社交媒體在關系卷入中的作用,因此在考量這種新型的粉絲——明星關系時,如果忽略新媒體這一情境,及其情境下的互動特質,將無法了解這種粉絲文化的內在特征,也容易落入受眾“商品論”的論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