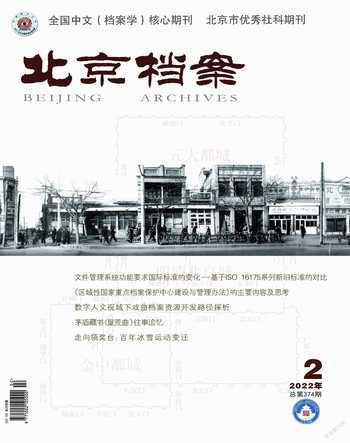北京戒臺寺史譚
朱國兵

2021年9月,位于北京門頭溝區馬鞍山麓的戒臺寺中的戒壇殿完成修繕并正式對外迎客,這里被譽為“天下第一壇”。所謂的“戒壇”是何意,又為何能稱譽“第一”?據傳戒臺寺為隋唐時所建,當時命名為慧聚寺。明朝宣德九年(1434)重建馬鞍山廢寺,正統五年(1440)賜名為萬壽禪寺。清代又因乾隆皇帝作詩而得名戒臺寺。千百年來政權更迭,戒臺寺的變化看似僅在名號,但其間卻有特定的歷史內涵。歷史上戒臺寺雖幾易其名,但俗稱一直為“戒壇寺”,可見戒壇之于寺廟的影響力。戒臺寺歷經千年風雨,有何古今滄桑變幻,寺名變換之間又有什么耐人尋味的歷史淵源?讓我們在歷史文獻中尋找答案。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戒壇是曇摩迦羅與曇帝二僧于三國時期在洛陽設立,二人善律學,曇摩迦羅更是被奉為律宗始祖。律宗著重研習及傳持戒律,戒壇由所謂的律宗先祖推動修建也是合乎其宗。北京戒臺寺戒壇位于大雄寶殿西北的戒壇殿中,始建于遼咸雍五年(1069)。根據殿外簡介可知,該戒壇為遼代律宗高僧法均大師所建,與福建泉州開元寺戒壇、浙江杭州昭慶寺戒壇并稱為“全國三大戒壇”,其中北京戒臺寺戒壇規模居三座戒壇之首,故有“天下第一壇”之稱。戒壇是高僧講經,考察僧人學識、僧人受戒之所。隨著僧人學識修為的提高,經過考試合格,所受戒律等級也相應提高,從沙彌戒到具足戒,直到菩薩戒。不同等級的戒壇具有授予不同等級戒律的資格,戒臺寺戒壇可以受佛門最高等級的菩薩戒,是佛門的最高學府。受具足戒的僧人可以修成羅漢果,受菩薩戒的僧人可以修成菩薩果,菩薩修為達到一定程度可以升級成佛,因而高僧又被稱為“佛子”。戒壇是培養高僧之所,故而有“選佛場”之稱。在明清兩代,戒臺寺開壇受戒必須持有皇帝的敕諭,可見其地位之高。
據目前戒臺寺所能見到的碑刻,其朝代最早能明確追溯到遼代法均赴門頭溝馬鞍山開戒壇。在某種意義上來講,法均才是戒臺寺的開山祖師,戒臺寺以“戒壇”而著名正是他的功績。關于法均的生平,今戒臺寺中立于遼大安七年(1091)重立于明正統三年(1448)的《(遼)故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壇主法均大師遺行碑》有所記載:“法均俗姓無可考,在其出家后,拜遼燕京紫金寺律宗高僧非辱律師門下為徒。”師法高僧奠定了法均日后傳戒的基礎。遼清寧七年(1061)春,法均開始嶄露頭角,先是被朝廷欽命校對佛典章疏,后又被推薦為燕京三學寺的論法師。在任期結束后,遼道宗賜予法均紫色袈裟并賜德號——嚴慧。
此后,盡管法均在燕京(今北京市)西邊的馬鞍山隱居修行,但許多信眾卻慕其修為而云集馬鞍山。經過法均的傳播,佛教深入燕京地區的官民。咸雍五年(1069),遼道宗命法均為輔佐燕京僧錄的僧判。皇帝的這一任命可謂奪其志,是法均所不愿意的。于是他在信眾的請求下,于咸雍六年(1070)在馬鞍山創設大乘菩薩戒壇,這也是戒臺寺的戒壇得名之始。由于法均精通律宗戒律、修為高深,并且眾生平等皆可受戒。不但契丹境內百姓蜂擁而來從法均那里接受菩薩戒,而且宋朝、西夏的信眾也紛紛而來,在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法均傳戒之盛也引起了遼道宗的注意,皇帝不久便接見了法均。在法均的影響下,遼道宗和皇太后都接受了法均的菩薩戒。接著遼道宗又賜法均以崇祿大夫守司空官銜及“法均”這一法號。在得到皇帝的認可之后,法均巡游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興中府,西京大同府等,向眾生傳受菩薩戒。
大康元年(1075)三月,法均在馬鞍山圓寂,享年55歲。法均雖然開戒壇只有五年,但當時在社會上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法均之后,裕窺、悟敏等大師作為戒臺寺的住持,延續了當年的鼎盛。遼帝封法均繼承者裕窺為崇祿大夫檢校太尉并賜御制《菩提心戒本》給他受戒;金代的悟敏大師同樣獲得了金朝皇帝賜的“紫色袈裟”和“傳戒”法號。[2]經過法均幾代人的傳戒,戒臺寺名揚在外。這也使得菩薩戒和律宗在遼境內大為盛行,達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發展成為全民受持的佛教戒律。[3]
迨至明初,戒臺寺早已是浮屠塔斷、古廟垣殘。其實遼金之后戒臺寺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在歷史長河中沒有留下多少痕跡。明宣宗宣德年間,司禮監阮簡等太監前往西山游覽,面對遺跡感慨萬千,意欲重建戒臺古剎。于是,司禮監太監王振、阮簡等人在前朝、內廷募集善款修建戒臺寺。寺廟重建之時,司禮監的太監們便邀僧錄司講經的知幻大師主持這名山古剎。知幻先是堅辭不許,但在了解戒臺寺的來龍去脈之后,喟然嘆曰:“釋迦如來三千余年遺教,幾乎泯絕,吾既為佛之徒,豈忍視其廢而不興耶?”而后毅然組織戒臺寺的重建工作。此次修建始于宣德九年(1434),成于正統五年(1440),修建了正殿、左伽藍殿、右祖師殿、齋堂、僧舍等,一座嶄新的廟宇在伽藍灰燼中重新屹立。由于王振是明英宗近侍,明英宗特賜廟額為“萬壽禪寺”。這一官方寺名也一直延續至今,如今戒臺寺山門的匾額便是“萬壽戒臺禪寺”。從“禪”字也可看出,戒臺寺正式由遼金以來以律宗為主體的寺廟轉變為以禪宗為主體的禪寺。
明亡清興,傍依清統治者,戒臺寺香火依舊鼎盛。清初,戒臺寺依舊由知幻大師的法裔主持著寺內大小事務。清定鼎中原后,統治者很快就注意到這一古剎,康熙皇帝多次前往戒臺寺進香并下旨修繕保護該寺。如康熙御制碑記禁止在戒臺寺附近采煤,以“葆靈毓秀山川”,并御筆親題“蓮界香林”于大雄寶殿。深山古剎孕育了戒臺寺獨特的松景,吸引乾隆皇帝多次游幸并留下諸多詠松詩作,如《初至戒臺六韻》等。除統治者的重視外,民間的供奉也使得清代戒臺寺香火不斷,這一切都記錄在寺內遺留的捐贈碑中。
清末,盡管社會動亂、餓殍遍野,但戒臺寺香爐不滅。這既得益于統治階層對戒臺寺的重視,卻也是對清統治者莫大的諷刺,不顧蒼生卻信神佛。光緒十年(1884),恭親王奕因中法戰爭失利被慈禧革去議政王和領班軍機大臣職務。奕為避權力紛爭前往戒臺寺“養疾”,在此期間他對羅漢堂、千佛閣、慧聚堂(牡丹院)等進行修建。隨著封建社會的謝幕,戒臺寺也迎來新生,服務于勞動人民。
戒臺寺從遼代法均和尚開壇以來,歷經遼金兩代香火鼎盛并聲名遠播。后雖淪為廢墟,但在明代又得以重建,歷經幾百年不衰,離不開千百年來信眾們虔誠地供奉和戒臺寺的“宗教精義”。從明代至新中國,各個政權對該寺都持保護的態度,如曾禁止在戒臺寺附近開窯采煤等。千年滄桑巨變,如今經過科學保護的戒臺寺依舊是天下第一壇。
*本文系2019年度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北京學研究基地開放課題“三山五園地區地名研究”(項目編號:BJXJD-KT2019-YB01)部分成果。
參考文獻:
[1](唐)道宣撰,續高僧傳[M].郭紹寧,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4:699-700.
[2]遼寧省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遼金歷史與考古第三輯[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11:245-262.
[3]彭瑞花.論遼代菩薩戒的流行[J].宗教學研究.2018.1: 90-95.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