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良:躬身沃土辟新路

朱兆良的小學生涯是在抗日戰爭的淪陷中度過的。
當時流行的實業救國思潮以及父母潛移默化的教育,讓朱兆良從小就認識到只有國家強盛才能不挨打受欺辱,要有“本事”才能立足社會。
1947年暑假參加化學補習班,是朱兆良轉向化學的關鍵。補習班教學生制作日用化學品,如肥皂、雪花膏等,使他對化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二年級時經院和系領導同意,他如愿轉到大學理學院化學系,由此也開啟了系統學習化學的大門。
在化學系的三年里,朱兆良師從劉椽、劉遵憲、徐國憲等一批優秀教師,不僅學習了化學系所開設的全部課程,而且由于對物理化學感興趣,還旁聽了幾門物理系和數學系開設的課程,并于1953年順利畢業。大學的學習經歷,不僅為他以后工作打下了扎實的專業基礎,而且也培養了他科學的思維能力。
1953年9月,朱兆良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以下簡稱“土壤所”)工作。
最初,他想自己是學化學的,卻要搞土壤研究,心里感覺別扭,甚至還想著換單位。
后來得到李慶逵和于天仁兩位老師的引導,尤其是李慶逵,要他尋找工作、理想與專業結合點。
李慶逵告訴他,國際上杰出土壤學家很多是學化學出身的,你有化學基礎,很適合開展土壤研究,在這個領域將大有作為。
于天仁安排朱兆良做一些土壤化學分析方法的改進工作,以便發揮他的專長,并希望通過耳濡目染培養他對土壤學的興趣。
此外,為了加強對包括朱兆良在內的農化室工作人員業務能力的培養,李慶逵還安排他們補學了礦物學和統計學等課程。
在兩位先生的幫助和周圍環境熏陶下,朱兆良在學術上慢慢成長,但仍沒有完全認同自己的研究對象。
1958年對朱兆良來說是其事業的重要轉折年,這一年他完全認同了自己的工作對象。
當時中科院號召搞農業的研究人員要到農村蹲點,向農民學習。朱兆良被安排在常熟市農村蹲點。
在勞動、學習和研究過程中,他看到了學科發展前途,了解了農業的重要性,認識到自己工作對農業發展的作用,明白搞土壤研究也可以為國家發展做貢獻,這與自己實業救國的思想相吻合,內心深處也就認同了自己的工作。
在漫長的歲月中,無論經歷什么事情他都泰然處之,潛心于自己的研究,不斷開拓研究新領域,逐漸成為我國土壤氮素學科帶頭人。
在李慶逵學術思想的引導下,他始終認為“土壤學是一門應用學科,應主要圍繞國家經濟建設、農業發展的需要來搞研究;既要強調理論研究,也要強調應用研究,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發揮理論專長,從基礎理論方面來研究解決生產發展中提出的問題,既要有理論深度,又要有應用前景,就這樣,10年、20年、30年,一直走過來。”
20世紀八十年代,他創立了用15N標記土壤礦化釋出的銨態氮的15N豐度作為參比值方法,在盆栽試驗中測出在無氮區水稻吸收氮中,約有20%是來自水稻全生育期間的非共生固氮作用,為稻田土壤供氮能力的定量解析研究提供了基礎數據。
如果說朱兆良對土壤供氮能力的研究,使他在國內土壤氮素研究領域漸露頭角,那么1979年10月在泰國清邁舉行的“東南亞季風區氮素循環學術會議”就是他初次展現我國土壤氮素研究實力的國際舞臺。
在此次學術會議上,朱兆良做了題為“中國江蘇蘇州稻田中氮素循環和氮肥去向”報告。
報告首次展示了中國土壤氮素研究的水平和實力,引起國外參會人員的重視。
朱兆良也因此認識不少國外專家,如國際水稻所業務所長D.J.Greenland、澳大利亞CSIRO的R.Wetselar和J.R.Freney。
這也拉開了我國土壤氮素研究領域同國外專家、學者和相關機構合作的序幕,如1980年在南京召開的由中科院土壤所主辦的水稻土國際學術會議,就邀請國際水稻所和澳大利亞CSIRO的專家前來參加。
朱兆良并沒有停止在已有的成績上,他深知我國在氮素方面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更主要的是作為學科,需要有一個長遠發展規劃。
他把農田生態系統中氮素的轉化和遷移的研究與我國農業中的氮素科學管理問題相結合作為自己工作的中心,通過解決實際問題促進氮素研究,也利用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增強我國影響力。
1987年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尿素肥料會上,朱兆良做了題為“中國作物生產中尿素的效用”的報告,受到與會專家的高度評價。
1990年,他應邀在國際土壤學大會分組會議上做“稻田的氮肥管理與氮素轉化的關系”的報告,受到會議主持人、當時國際水稻所首席科學家的高度贊譽。
朱兆良一次又一次在國際舞臺上做學術報告,既提升了我國土壤氮素研究工作者的國際地位,又促進了與國外的合作。
在他的努力和積極爭取下,2004年10月第3次國際氮素大會(The 3rd International Nitrogen Conference)在南京召開,并簽訂《南京宣言》。
除自己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外,朱兆良還不斷為學生和同事爭取到國外進修或者參加項目合作的機會,為他們提供成長平臺,如自20世紀八十年代起他先后派陳德立、蔡貴信等多位學生和同事到澳大利亞參加合作項目或攻讀博士學位。
自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國糧食產量成倍增長的同時,氮肥施用量也在逐年增加,近幾年來氮肥施用總量已高達全球氮肥施用總量的近三分之一。
進入21世紀后,我國農業面源污染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作為土壤氮素專家的朱兆良也深知在糧食安全壓力下,我們施用太多化肥,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
朱兆良知道要控制農業面源污染,首先得解決我們的糧食問題,因為我們既不能像地多人少的國家那樣可以通過犧牲作物產量來保證生態環境,又不能不顧環境質量片面追求高產,所以尋找既要保證生態環境又要保證糧食產量方法是一條艱辛道路,也是我國有關學科的科學家面臨的嚴峻挑戰。
朱兆良認為,在種植業方面,我們必須切實貫徹“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指導思想,走出一條既能保證作物持續增產、農田生產力不斷提高,又能保持良好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保證糧食安全量和保護環境的雙贏目標。
在朱兆良看來,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是充分科學地利用有機和無機養分資源,提高肥料的利用效率,同時還要在施肥區域布局上進行科學考慮。
因為將來想在有限的高產田上如太湖地區再進一步提高產量有相當難度,并且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都較差。
根據第二次土壤普查結果綜合評判,我國2/3耕地屬于中低產田,其中中產地區約占耕地面積的1/3。
為此需要加強農田基本建設,改善灌排條件,消除存在的障礙因素,以充分發揮施肥的效果。
同時,在低產地區國家也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土壤改良和農田基本建設,消除限制因素,提高農田土壤肥力,以發揮肥料的增產作用。
因此,朱兆良認為,提高中低產區糧食產量將是未來我們爭取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共贏的重要舉措。
60多年來,他始終秉持嚴謹、認真治學的態度,執著為國家建設和農業生產貢獻自己力量的理念,默默關注和支持學科發展;他既堅持任務帶學科,解決農業實際問題,促進國際合作,又高瞻遠矚為學科發展未雨綢繆;他帶動我國土壤氮素研究工作不斷向縱深發展,為氮素研究開辟新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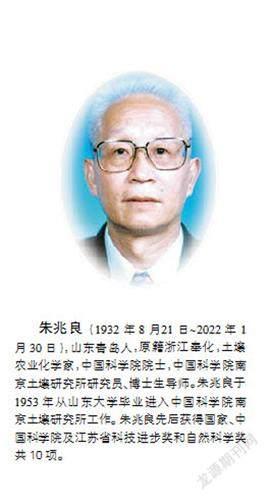
院士其實就是在一個領域里有些經驗而已,離開這行,也是小學生。
科學研究是探索未知,科研人員既要有嚴肅、嚴密和嚴格的學風,又要有敢想、敢干和敢闖的精神。二者不可缺一。
在種植業方面,我們必須切實貫徹“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指導思想,走出一條既能保證作物持續增產、農田生產力不斷提高,又能保持良好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保證糧食安全量和保護環境的雙贏目標。
我們搞土壤研究,目前最重要是如何保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保護好耕地,使耕地可持續利用。
土壤學是一門應用學科,應主要圍繞國家經濟建設、農業發展的需要來搞研究;既要強調理論研究,也要強調應用研究,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發揮理論專長,從基礎理論方面來研究解決生產發展中提出的問題,既要有理論深度,又要有應用前景,就這樣,10年、20年、30年,一直走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