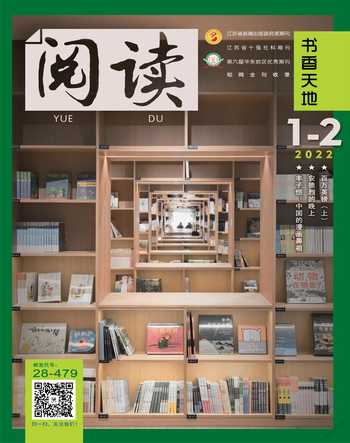宋神宗與王安石,請別再誤解這對君臣
陳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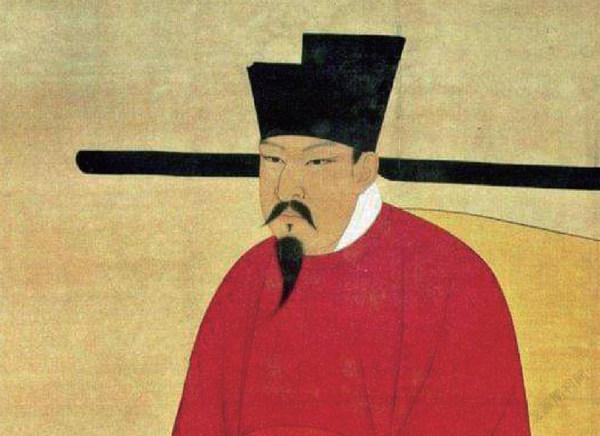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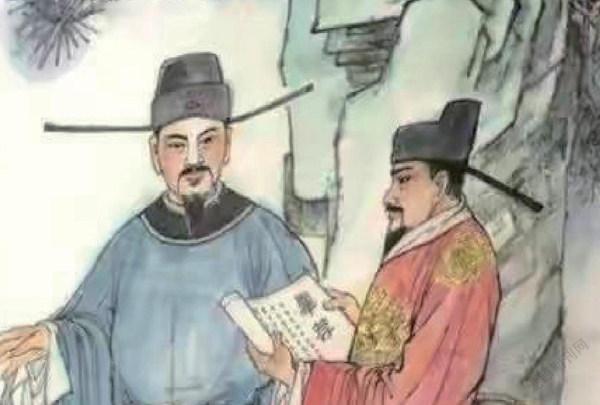
大宋第六代天子趙頊,在許多文臣眼里頗有喜功尚武的印象,據說,他曾身披鎧甲問曹太后:娘娘,你看我穿這副甲胄好不好?所以,在以后駕崩之日,臣子們為其選下了“神宗”的廟號。此廟號含有神武的意思,而按當時的價值觀衡量的話,神宗的廟號要比仁宗遜色些,其實這正反映了當時文官集團對神宗皇帝的一種評價和看法。
神宗的確與前幾代守成君王的風格有所不同,神宗之所以能有不同于真、仁兩代天子的性情,很可能與他來自宗室旁支的出身有關,也就是說他在少年時代沒有繁文縟節的約束,能夠更多地獲得個性的發展空間,對現實也可以有更多的了解。神宗最初對朝中老臣寄予厚望,他在即位不久曾問富弼有關國防的問題,沒想到三朝老臣卻說,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這不免使血氣方剛的年輕天子大為失望。這樣,神宗便將希望寄托在一些要求改革的普通官員身上。
祖籍臨川(今江西撫州)的王安石,是宋朝歷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不同于當時的大多數文人學子,他沒有完全沉溺于應付科考的程文學習之中,而是懷著一種探索治國之道的精神讀書,他曾直言不諱地說:善學者讀書,在于求其道理,“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不敢從”。
神宗皇帝君臨天下沒幾天,就下詔起任王安石知江寧府。時隔幾個月,天子因急于見到王安石,又將他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就這樣,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王安石來到了京師,君臣可謂相見恨晚。據記載,神宗因欽慕唐太宗的功業,便向王安石問道:“唐太宗如何?”滿腔抱負的王安石則鼓勵年輕的皇帝向更高境界的堯舜看齊。翌年二月,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再過一個年頭,便升任宰相。王安石從進入中書之日起,就開始實施自己思考已久的“富國強兵”措施。其中富國方面的內容包括推行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市易法及方田均稅法等新法,旨在通過興修水利,向農民發放低息貸款,改善東南上供運輸管理,實行以錢代役制度,政府參與商業貿易活動及清理隱匿農田稅等重要手段,以增加政府收入,并壓制大地主與大商人勢力的過度膨脹。
在實施各項財經制度改革的同時,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又對國防進行了較大范圍的改革,即實行所謂“強兵”策。當時,朝廷推行的強兵策內容頗多,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項:
其一,精簡軍隊。王安石針對長期以來存在的軍隊人員冗濫,而戰斗力低下及軍費開支龐大的諸問題,采取了合并與裁汰相結合的手法,將大量兵額不足的禁廂軍番號撤銷,并將老弱無力的士卒清除出軍營。按照新的規定,用于作戰的禁軍中馬軍一營(或稱指揮),編制為300名軍兵,步軍一營有400名定員。改革之后,全國禁軍編制由872營減為625營;另外,對原來規定61歲退役的舊制加以改變,規定凡50歲以上的士兵一律裁減為民,45歲至50歲之間體弱者也令其離開軍隊。與此同時,對承擔工役性質的廂軍也實行裁減老弱人員的措施。經過數年的努力,到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時,全國軍隊總數為796315人,其中禁軍人數為568688人。軍兵總額比仁宗朝減少了45萬多人,比英宗朝也減少了36萬多人。裁減冗員之后,不僅提高了軍隊的整體素質,而且節省了大量的軍費,據現代學者估計,每年因此節省的軍費大約為千萬緡。
其二,將兵法。為了解決開國以來沿襲已久的“更戍法”的積弊,宋廷在變法期間逐漸取消了各路軍隊互相更換防區的傳統做法,通過設立比較固定的將領和指揮機構的制度,以加強對本地區軍隊的訓練,并密切武官與部屬之間的聯系,從而提高各地駐屯軍隊的戰斗力,以消除昔日“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帶來的惡果。值得指出的是,將兵法的起源乃在于昔日范仲淹在延州地區帶兵時的經驗。將兵法推行后,北方地區的將官通常可以統管六千至一萬名士卒,并配有副將以下部署將校;南方地區將官管轄的兵員則少得多,大約不過四五千人。
其三,保甲法。自中唐以來,募兵制逐漸取代了以往兵農合一的兵制,至宋朝創建后,募兵成為軍隊的主體。由于全社會長久歧視軍兵,加上刺字等恥辱性制度的存在,使軍營里充斥著失業流民,甚至形形色色的罪犯,即所謂“無賴奸猾之人”。久而久之,軍旅中往往存在著一些不良的兵痞風氣,對軍心和戰斗力都產生了消極影響。同時,募兵制的存在,還對朝廷財政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曾任仁宗、英宗兩朝三司使的蔡襄指出:當時軍費負擔常占朝廷財政支出的十分之六七。有鑒于此,王安石早在給仁宗皇帝的“萬言書”中就提出了以民兵替代募兵的構想。他在主持大政之后,遂推行了保甲法,以便逐漸培養出一支新型軍隊。按照這一新法規定,民間每五戶編為一保,由其中一戶強干者做保長;每五保編為一大保,選擇一人為大保長;每十大保編為一都保,委任其中兩名強干及有財力者做正、副都保正。在保甲制之下,民戶有兩丁以上者,選一人為保丁,自備弓矢,平時由大保長監督訓練、巡警,防止民間暴動,而在河北、河東及西北沿邊的保丁,在戰時也投入戰場。從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以后,各地陸續在農閑時集中訓練保甲兵。經過一段時間的操練,保甲兵的武技往往超過禁軍,特別是騎兵的表現更為突出。
其四,保馬法。針對宋朝官方養馬成本高而收效低下的老問題,由朝廷下令在北方五路保甲戶中鼓勵民戶養馬,以節省開支,并提高戰馬的成活率。依照相關制度,民戶如自愿養馬,馬匹由政府提供,或由政府提供買馬資金,養馬戶因此可以減免一些賦稅負擔。通過推行保甲中養馬的辦法,不僅減少了朝廷的開支,而且還訓練了一批善騎的保甲兵。
其五,創設武學。開國以來,培養文官的各級學校和科舉制度已日臻成熟,但在抑制武夫方針的影響下,有關培養武官的體系卻長期無法得到正常培育,從而進一步制約了軍隊將領素質的提高。在仁宗之前,天子雖也在邊防危機的情況下,親自在宮中測試一些軍官乃至于上書論兵的文人,并當即授以軍職,然而這些始終屬于一種權宜做法,還沒有相應的制度加以保證。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朝廷實施武舉制度,允許文武官員舉薦人才參加武科考試。但這項制度延續到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便在一些文臣的非議中被取消。到英宗即位初,在樞密院的呼吁請求下,朝臣們經過近一年時間的討論,武舉才獲得恢復。不過,考試的內容主要側重于“弓馬武藝”,而不注重策論及兵略等,體現了對武官頭腦水平的輕視。至于培養武學人才的學校,最早創設于邊防危機加劇的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五月間。武學的校址就選擇在京城內供奉武成王(姜子牙)像的武成王廟內。遺憾的是,這年八月,當宋朝與遼、西夏關系緩和后,僅僅存在數月的武學便被解散。
為了提高武官的素質,就必須建立一套選拔培養制度。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六月,神宗首先批準了設立武學的建議,校址仍選擇在武成王廟內。按照有關規定,武學設一百名生徒名額,招收無職事的武職使臣、官員子弟以及民間人士,當然,入學還要有一定的考試限制。在這所學校里,教官們主要講授古代各家兵法、歷朝用兵例證及許多忠臣的事跡,另外,也分給學校一些士兵,以用于操練陣法。三年學習期滿后,原有使臣出身者可以馬上獲得巡檢、監押一類軍職;原無官銜出身的士子,則須在軍隊中見習三年,才能取得巡檢等職務。
在恢復武學的同時,宋廷又對原來的武舉考試條例進行了改革。據記載,在恢復武學之前,樞密院對參加武舉“不能答策”者,改考兵書墨義。所謂墨義,乃是當時科考中對儒經的一種考試方式,它要求應試者將經書的原文及注疏全部背熟,以回答有關問題。王安石素來對墨義之類死記硬背的考試方法極為反感,他入主中書后,已在科舉考試中廢除了此法,自然不會同意在武科中再加以實行。王安石向神宗指出:考試武藝本已不難,如果再只要求背誦一些章句,便很容易通過。但假如“收得如此人作武官”,又能對世事有何補救?于是,在王安石的堅持下,武舉除了考試武藝外,并要測試應試者回答策論的水平。
此外,王安石還要求天子打破按部就班選拔武將的舊規,大膽任用有才略的將領,以激勵將校勇于進取的精神。
最后,設立軍器監。在變法期間,朝廷在中央設置了軍器監的機構,專門負責制造各種兵器。據時人反映,以往兵器制造由各地承擔,因為各地官府或不經心,或偷工減料,致使生產出來的武器多令人失望。甚至于有的地方提供給軍隊的甲胄,竟用紙與麻縫制而成,根本不能抵擋流矢的射擊;還有的地方粗制濫造的刀槍,用不了多久就破朽不堪。因此,軍器監通過招募天下的能工巧匠對兵器的制造進行專業化和規范化,來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兵器質量低劣的問題。可以說,軍器監的設置,對改善軍隊的裝備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經過以上深入廣泛的改革,宋朝的實力有明顯的增強,不僅極大地加強了中央的經濟實力,而且在國防上也取得了超越以往的發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果,自然是與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分不開。據記載,每次王安石遇到阻力表示辭職時,天子都真誠地加以挽留,同時將反對派趕出朝堂。神宗甚至還把王安石比作輔佐阿斗的諸葛亮。尤為難得的是,此時,帶兵將領得到了神宗皇帝和主政大臣的有力支持,可以獨立作戰,于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一場罕見的大膽遠征活動—熙河拓疆。
熙寧后期是宋朝守成以來武功最盛之時。當時,在王韶經營的基礎上,西線又不斷取得戰果,除了以往歸順的木征等吐蕃首領外,以青唐城(今青海西寧)為勢力中心的吐蕃領袖董氈及鬼章等首領也先后接受了朝廷的招撫;在南疆,大將郭逵率領的宋朝軍隊不僅擊退了交趾人的侵略,而且深入對方境內,洗馬富良江(今越南境內紅河),迫使交趾國王投降。在取得了以上一系列成功之后,急于雪恥的神宗皇帝便開始考慮對西夏用兵。
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四月,西夏國內發生政變,國主秉常失位被囚,其母梁太后及外戚控制了政權。當這一消息傳至開封后,神宗與大臣們便決定借此機會對西夏發動全面進攻。此時,王安石早已賦閑于江寧,王韶也病死多時。朝中決策大臣乃是宰相王珪及知樞密院事孫固等人,前線的統帥則是天子的親信宦官李憲,主要參戰大將有種諤(種世衡之子)、高遵裕、劉昌祚及宦官王中正等人。七月,李憲督率朝廷三十萬兵馬分五路大舉出擊,與此同時,董氈也率吐蕃兵助戰。天子在戰前下達的詔令中,表達了一舉滅亡宿敵的意愿。然而,這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主動出征行動,并沒有取得成功。
這便是“永樂之役”。有關“永樂之役”損失的情況,有幾種不同的記載,有的稱戰死蕃漢命官約230人、士兵約12300人,有的說死傷軍民20余萬,還有的則記錄為10余萬人。第一種說法見于宋朝典籍,而后兩種資料則取自西夏人的記錄。這種記載上的分歧,很可能在于宋朝官方只記錄死亡的官員與軍隊的數量,而西夏人則除了清點消滅的對手軍人外,同時也大致統計了打死打傷的民夫人數。這樣看來,“永樂之役”是神宗開邊以來單次戰斗中損失最慘重的一次,因此,此役給神宗的打擊也最為沉重。
當西北前線的噩耗送達開封皇宮后,性格剛強的神宗皇帝悲痛異常,連飯也吃不下去。早朝時,他竟當著臣下的面失聲痛哭,在場的文武官員都不敢抬起頭來。可以說,在經受了此前靈州慘敗的打擊后,再遭此折磨,神宗的身心遂蒙受巨創,從此重病纏身,無心武備。拖著這樣的病體,神宗勉強支撐到第二年的三月,終于抱恨而亡,時年僅三十八歲。史官們稱:每當用兵之日,天子常常徹夜難眠,隨時閱覽邊關奏疏,對戰場的一舉一動都要親自過問、指示。這位神武天子原指望在剿滅西夏之后再圖北伐,不料卻出現“永樂之役”的慘敗。由此,他知道用兵艱難,“于是亦息意征伐矣”。而神宗的駕崩,也標志著宋朝大規模重振國防努力的終結。神宗死后一年多,王安石也病故于金陵。
(摘編自重慶出版社《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與北宋興亡》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