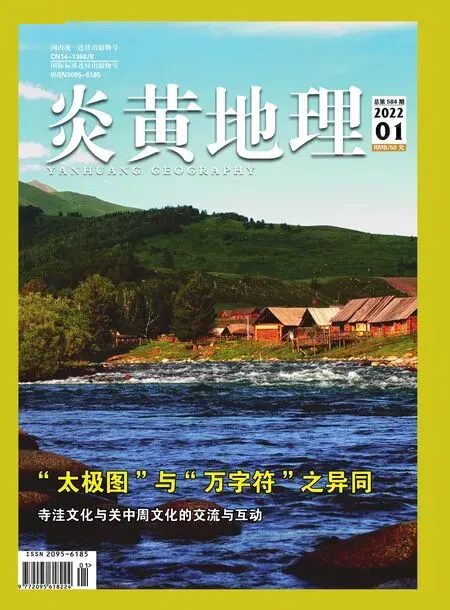漢代三枝俑銅燈鑒賞與復制
惲小鋼 尹航




多年前,筆者接到一件西漢三枝俑銅燈的復制任務,多年后再與其相遇,回顧自己年輕時的復制經歷,隨即寫下這篇文章。在對漢代人俑型銅燈鑒賞的同時,著重介紹以三枝俑銅燈為代表的傳統青銅器復制過程,其中包括翻模、鑄造、做舊等傳統工藝步驟。
1980年,筆者惲小鋼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1983年起進入文保科技部(原修復廠)開始接觸青銅器修復和復制技術,師從青銅器修復專家趙振茂先生。1989年11月,云南省個舊市出土一尊青銅跪俑燈,1995年國家文物局文物鑒定組確認其為一級文物中的稀世國寶,命名三枝俑或三支俑銅燈(圖1)。隨后,故宮博物院接到三枝俑銅燈的復制任務,作者跟隨師兄賈文超先生一同復制此件青銅器。
2021年7月,筆者受邀前往云南省博物館進行“云南省博物館館藏青銅文物保護修復深化設計方案專家評審會”,時隔二十多年再次見到了此件三枝俑銅燈,思緒萬千,遂寫下此文,在對漢代人俑銅燈進行鑒賞的同時,與同仁分享三枝俑銅燈的復制過程。
漢代人俑型銅燈
漢代燈具。我國古代燈具的最初形態大多是從青銅器中的盛用器皿(如鼎、盤、盂、豆等)演變而來的。漢代燈具除了對戰國和秦的繼承外,又有新的發展和創新——在注重實用性的同時,也十分講究造型的藝術性。
由于兩漢盛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喪葬觀念,作為日常生活用品的燈具也成了隨葬品中的常見之物。由全國范圍內歷年來出土漢代燈具資料和漢畫像石上圖案可知,這一時期的燈具數量顯著增多,并且具有諸多特點:材質較多,有銅、鐵、陶、玉、石、木等各類;種類豐富,出現許多造型,除了豆形、鼎形、簋形、奩形等仿日常實用器具的燈具外,另有以人物和動物為造型的燈具;十分注重環保和科學設計、外形美觀,獨樹一幟;制作技術得到很大提高,既有一次性制作而成,也有分部制作、套接拼插設計等。
漢代的人俑銅燈。漢代出土的以人俑為造型的燈,在古代燈具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既注重外在的造型設計,又強調內在神情的刻畫,題材多樣,形式繁多,這些人物刻畫細膩、特點突出、內涵豐富,人俑動作大多做持燈狀,持燈的方式也各式各樣,絕少雷同。
身穿胡服的少數民族和卑微的奴婢形象:西漢當戶銅燈(圖2),整體造型為銅人跪地托燈,銅人半跪,左手按在左膝上,右手上舉托起燈盤。“當戶”是北方少數民族匈奴的官名,銅人衣服裝束與胡服類似,腳穿長靴,身穿貼身直襟短衣,推測是匈奴官吏形象。在燈具上鑄造半跪匈奴官吏舉燈的形象,真實深刻地反映了漢與匈奴尖銳的民族矛盾。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戰國鎏金銅人擎燈(圖3),人物形象性格溫順,俯首貼耳,傳神地表現出奴婢對主人的恭敬與服從,體現了仁義、忠誠的儒家韻味。
神話形象:東漢羽人銅燈(圖4),燈座用鏤線刻出三力士騎怪獸飛躍奔騰的圖案,中間有一身披羽毛的高鼻異國士。羽人這一意象在古代較常見,《楚辭·遠游》記載:“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漢代道教盛行,羽人作為一種獨特的人物造型,賦有濃重道教色彩,有“羽化成仙”之意。
環保和科學設計:滿城漢墓出土的西漢長信宮燈(圖5),整體造型是一個跪坐著的宮女雙手執燈,神態恬靜優雅,造型構造設計合理,許多構件可以拆卸。宮女的左手托著燈座,右手提著燈罩,右臂與燈的煙道相通,以手袖作為排煙炱的管道。寬大的袖管自然垂落,巧妙地形成了燈的頂部。燈罩由兩塊弧形的瓦狀銅板合攏后為圓形,嵌于燈盤的槽之中,可以左右開合,這樣能任意調節燈光的照射方向、亮度和強弱。燈盤中心和釬上插上蠟燭,點燃后,煙會順著宮女的袖管進入體內,不會污染環境,可以保持室內清潔,既有環保和實用的功能,又極具審美價值。
漢代的多枝燈盤。人俑持燈盤從一個至三個不等。燈盤有圓環凹槽形、盤形等各種形式,推測是從古代豆型青銅器的造型演變而來。漢代的燈盤中間一般都立有支釘,稱為“釬”,起到支撐燈具主體和插持蠟燭的作用。
多枝燈,即是有多個燈盤的燈。這種燈在戰國時期已經出現,漢代仍在流行。《西京雜記》卷一《飛燕昭儀贈遺之侈》篇載有“七枝燈”,卷三《咸陽宮異物》篇載有“青玉五枝燈”等。多枝燈的燈盤少的有三個,多的則達十三個,甚至更多。不少漢代燈具都可拆卸組裝,便于清洗、攜帶,多枝燈更是將拆卸設計發揮到極致。燈盤與燈體主要通過鑄接、榫接、鉸鏈等拼合。一些復雜的多枝燈,除了鑄接、榫接外,還采用分鑄套合組裝的設計。
三枝俑銅燈。本文所介紹的三枝俑銅燈即是一種多枝、可拆卸的人俑型銅燈。西漢三枝俑銅燈,是云南省博物館館藏精品。高42cm,寬48cm,重6.3kg,出土于云南省紅河州個舊市卡房鎮黑馬井村西老硐坡頂部東漢墓葬44號墓。
燈座主體是一赤裸上身的男子作跪坐姿態,頭昂立,戴帽,腹部和跨下有帶纏繞;頭頂上立一圓形燈盤,兩肩伸開上曲,手中各執一圓形燈盤呈對稱狀,手臂可拆卸;三枚燈盤構成“十”字型形體,上部呈山字狀。
銅俑整體造型古樸生動,線條粗獷,表情恭謹嚴肅,神態古拙,尖臉、大眼闊鼻、高顴骨,眉毛、連鬢胡用線刻手段加以細致刻畫,臍部也有線刻的斜帶交叉紋飾。頭部纏繞一圈斜格紋絲帶束發,在額前結成豎立小髻。此銅燈雖是漢式題材,但跪俑形象卻饒有“胡風”特點,具有明顯的西南紅河少數民族特征。
銅燈分四部分拼合而成,手臂、頭部均可與軀干分離,拼縫整齊,造型準確,線條流暢。圓形燈盤中各有一支釘形小柱,供點燃用。三個燈盤分置銅俑的頭頂及雙手,燈光可交相輝映,燈與俑搭配和諧,給人一種美感,猶如花枝招展。
三枝俑銅燈的復制過程
文物復制的要求是能夠做到與原物盡量相同,其目的和意義在于對文物的保護和弘揚祖國傳統文化,與青銅器修復技藝雖是相輔相成,但也大有不同。青銅器的復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出土青銅器的復制,新出土的器物,由于埋藏環境等因素造成青銅器表面有比較嚴重的銹蝕,表面相對粗糙,俗稱“生坑”。另一類是對傳世青銅器的復制,傳世青銅器是指出土后的器物經過人為去銹處理或未經埋藏長期把玩,器物表面顯得細潤光滑,俗稱“熟坑”。
此件三枝俑銅燈是新出土的器物,視為“生坑”器,它的復制過程主要包括翻模、鑄造、打磨、做舊等步驟:
翻制。在秦漢時期,由于當時的技術條件有限制,當青銅器發生損壞時,即使修補也難以恢復原狀,而工匠為破解該難題,便發明出分模鑄造的辦法,他們會將青銅器部分進行鑄件,如果一個部分壞掉,可以直接換掉該部分,而不用將整體拋棄,視為秦漢時期的“模塊化生產”。三枝俑銅燈即為這種“模塊化”的產物(圖6)。
在對這件銅燈翻模時,相當于翻制了五個零配件,這就需要翻制的配件銜接處十分吻合,拼插之后不能太松會發生掉落,也不能太緊給拼插增加難度。
中國傳統銅器的翻模材料選擇黃土翻模、沙翻模、石膏紅磚粉混合翻模、石膏翻模,在隨著新材料的不斷革新,九十年代開始,業內都逐漸改用硅橡膠進行翻模,硅橡膠翻制細節,外加石膏固定形態。硅橡膠的翻制技術的不斷成熟,可以幫助翻制細節較多、體積較小的零部件。以古代青銅器為原型翻制模具,制出蠟模。
此件銅燈表面有肉眼可見的墊片,在文物復制的時候也要做到有墊片的感覺。所以在制蠟模的過程中,根據銅燈墊片的位置,打磨出去一些方孔,待澆鑄青銅后,用方孔等大的銅片補回去,制作出一種有墊片的視覺效果。
鑄造打磨。古代青銅器多是用銅、錫、鉛的合金鑄造而成。在九十年代初期,科學檢測技術沒有十分完善的情況下,沒有條件逐一檢測待復制青銅器的具體成分比例。在鑄造青銅配件時,根據文字和資料記載,配置相應比例的青銅材料,大致為紅銅70~80%,錫25%左右,其余為鉛。
利用之前翻制好的蠟模澆鑄出器形、大小、紋飾與原件非常接近但表面未經任何處理的青銅配件,就是常說的毛坯。鑄造好的毛坯要經過非常精細的打磨,用不同的鋼銼、不同目數的砂紙、包括椴木炭等工具和材料逐步完成,直至磨到器物表面光可鑒人,方能為下一步工序打好基礎。
表面做舊。咬黑:打磨后的毛坯用化學試劑腐蝕,形成一層黑褐色的氧化層。這個工序主要有兩個目的,其一是為了遮蓋銅器本身的光亮;更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后期所做的銹蝕能夠與器物表面結合得更加緊密。
悶銹:利用化學藥品在潮濕環境下對銅的腐蝕來復制銅器表面銹蝕,具體的做法是把銅件放在一個較為密閉的箱子內,調好一定比例的化學藥品溶劑刷涂在復制品上與原件上有銹蝕的同一部位,箱底部墊有黃土,箱子內澆上水,密閉好,定期觀察調整銹蝕層的顏色、厚度等,這一過程將持續數天。
做高銹:用蟲膠漆調和礦物顏料或是硝基的漆調和出與原件底色、銹蝕顏色基本一致的顏色,用毛筆等工具有層次的在復制品表面作出與原件非常接近的顏色效果。用蟲膠漆(漆皮)和礦物顏料以及黃土等混合,在地子上需要的地方做出各種顏色和效果的高銹。
細節處理:待顏色干燥后,對其表面進行細節處理,顏色,加固封護銹蝕層。
制作古代青銅器銹蝕的方法有很多種,根據不同的青銅銹蝕產物,選擇最為合適的手法制作,以達到最佳的復制效果(圖7)。
三枝俑銅燈是一件既實用、又美觀的漢代燈具珍品,設計之精巧,制作工藝水平之高,體現了古代中國設計者匠心獨運的智慧,向世人證明,拆解技術在漢代已經成熟,并應用到青銅器制作上。讓人們見識到漢代青銅文化的輝煌與成就,為后人研究青銅器的“模塊化”生產,提供了詳實的物證。
對這件三枝俑銅燈的復制,是一次全流程的青銅器復制過程,對筆者而言是難能可貴的復制經驗,為之后多年的青銅器復制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離這件三枝俑銅燈的復制已過去二十余年,回首復制的過程,當年受到材料、技術等因素的制約,仍有諸多不完善之處。隨著科學檢測技術、材料的發展和制作技術的不斷革新,如今的青銅器復制技術已經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傳統技術和現代科技相結合的未來,青銅器的復制技術定會在下一代修復師手中有序傳承、發揚光大。
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
3507500338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