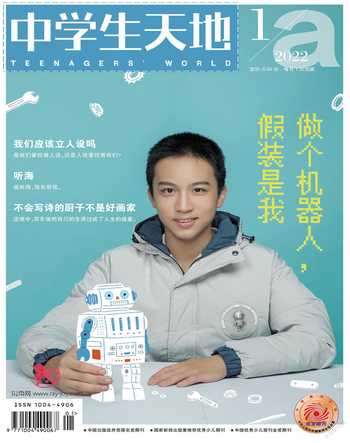我是珊瑚裸尾鼠, 這是我最后的故事
任輝
我是珊瑚裸尾鼠。你們大概從未聽過我的名號,我們之間更沒有一面之緣。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只生活在距離你們萬里之遙的一座熱帶珊瑚礁上,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我已經和你們揮手告別多年。
是的,我和伙伴們已經滅絕了。
2019年2月,澳大利亞政府對外宣布了我們滅絕的消息。他們認定,我們是全球第一種因為人類活動帶來氣候變化而導致滅絕的哺乳動物。我已經能想象到你們錯愕的表情:氣候變化對生物的生存環境產生威脅的故事,想必你們都知道一些,比如北極的北極熊因為升溫而難以覓食,南極的企鵝因為冰蓋的融化被阻擋了前往灘頭繁殖的道路。乍看起來,好像只有適應了冰天雪地的極地生物才更畏懼溫度的攀升。而我,一種生活在熱帶的小老鼠居然成了氣候變化的犧牲者,這當然超出了你們慣常的認知。
別急,就讓我來講述自己最后的故事吧。
我的故事,要從一只蝴蝶
講起
其實,氣候變化可能會導致物種滅絕這件事,人類科學家早就有所認識。20世紀90年代,生活在北美的一種蝴蝶——季諾格紋蛺蝶就曾遭受過這樣的威脅。當時的研究發現,這種蝴蝶的幼蟲必須以一種特有的植物——矮人芭蕉為食。隨著持續惡化的氣候變化問題帶來的高溫和干旱,矮人芭蕉的分布范圍不斷縮小。因此,季諾格紋蛺蝶的未來在當時是不被看好的,人類科學家認為它的滅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然而,這種頑強的蝴蝶顯示出了驚人的適應性。2015年的研究發現,小蝴蝶不僅改變了自己的食譜,還遷徙到了氣候更為涼爽的高海拔地區繼續生活。
但你們也能想到,這種看似幸運的故事,其實是不能持續的。蝴蝶或許可以在短期內不斷改變自己所處的海拔高度來獲取足夠涼爽舒適的環境,但山地的海拔總歸有限,如果氣溫持續升高,就連山頂都被熱浪吞噬,等待它們的結果又是什么呢?
我的故事就印證了這種假設。
頻繁的風暴潮,是我們滅絕的喪鐘
和小蝴蝶的棲息地相比,我的故鄉要矮小得多,在澳大利亞東北部外海的一座小小礁盤上。它的最高處只有3米多,在僅有的0.036平方千米面積中,一半還被沙灘覆蓋,能供我和伙伴們棲息的地方只有剩下的一半面積上的零星植被。
許久之前,這片珊瑚礁剛剛露出海面時,我的祖先還生活在幾十千米之外的巴布亞新幾內亞。或許是一次偶然的洪水,被沖入河水的祖先只能攀附在一根浮木上漂流入海,意外地來到這里,并頑強地生存了下來。歷經幾十萬年歲月,被孤立在小島上的我們已經在獨立演化中變得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近親們截然不同,我們也成了這座礁盤上獨有的特殊生物。
這里并不是多么廣闊的家園,而一個棲息地的承載能力是有限的。在大陸上,生物可以不斷向周圍適合的棲息地擴散,但島嶼上并沒有這個條件。很顯然,小小的珊瑚礁上養活不了太多的“鼠口”。1845年,人類首次發現我們的時候,我們總共只有數百只。1998年,澳大利亞的人類科學家又對我們進行了一次“鼠口普查”,那時我們只剩100多只。隨后的幾年里,更多的人類學者來到礁盤上,想對我們進行深入的研究,但我們已經越來越難以被他們尋覓到了。2009年,是我們最后一次出現在人類面前。10年之后,人類宣布了我們滅絕的消息。
你或許想問,為什么我們會走向滅絕呢?這座珊瑚礁幾乎未被人為開發,現存人類設施只有一座無人值守的燈塔,這里沒有受到過外來物種的入侵。把我們推向滅絕的“兇手”,恐怕正是近些年愈演愈烈的氣候變化。畢竟在這座制高點只有3米的珊瑚礁上,一次肆虐的風暴潮就能把小小的陸地橫掃一通。而由氣候變化大背景帶來的氣候極端化現象,讓風暴潮來得更頻繁,也更猛烈了。一次又一次的風暴潮掃蕩過后,我們終于難堪重負。
氣候變化愈演愈烈,
誰能獨善其身
我們并不是唯一被氣候變化逼上絕路的熱帶生物。同樣生活在澳大利亞的粗卷尾袋貂很可能即將步入我們的后塵。這種只分布于昆士蘭北部路易斯山上的有袋類動物非常喜歡在當地涼爽的雨林中晝伏夜出,但近十幾年來,這個地區遭受了多次前所未有的熱浪襲擊,極大地威脅了袋貂的生存。2005年底的一次熱浪襲擊過后,它們瞬間銷聲匿跡,直到2009年,人類才又發現了4只幸存個體。此后的幾年中,粗卷尾袋貂的數量緩慢恢復。但在最近幾年,澳大利亞的熱浪越來越強,這些幸存的袋貂是否還能熬過去就很難說了。根據氣象監測,路易斯山山頂的溫度甚至可能攀升到39℃,而以往的研究認為,當溫度超過29℃就有可能導致粗卷尾袋貂死亡。
正如我前面說的,提到氣候變化對生物的威脅時,你們總是把目光聚焦于極地的生物。我們這些生活在熱帶地區的生物的悲慘故事應當能警示你們:在這場全球化的劇變中,沒有哪個角落可以幸免,也沒有哪個物種可以獨善其身。
這就是我的故事。我和伙伴們已經走完了作為一個物種的一生,這個故事對我們已經毫無意義。但其他萬千生物——當然也包括你們人類自己——還會繼續面對氣候變化的威脅,你們的故事是否會和我們截然不同?這需要你們自己尋找答案了。
3825501908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