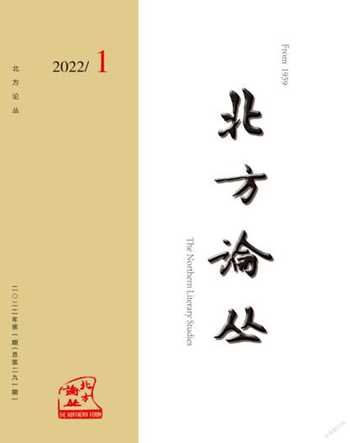危機與突圍:人工智能時代的馬克思勞動幸福觀
[摘要]馬克思勞動幸福觀認為,“勞動是生命的樂趣”,勞動幸福是人類的真正幸福。而人工智能的發展給馬克思勞動幸福觀帶來新的危與機,在資本的驅動下,智能機器削弱勞動者的主體性、資本邏輯加深勞動的異化、異化勞動導致人的痛苦,形成對勞動幸福的遮蔽之勢,使馬克思勞動幸福觀受到質疑。但若人工智能技術得到合理使用,它將提高勞動效率、優化勞動關系、推動勞動解放,助力勞動幸福的實現,進而確證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基于此,我們要化危為機、把握契機,推動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理論創新,加大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宣傳力度,倡導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自覺踐行,從而實現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理論突圍。
[關鍵詞]人工智能馬克思勞動幸福觀危機理論突圍
[作者簡介]張淼,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上海200433)
[DOI編號]10.13761/j.cnki.cn23-1073/c.2022.01.003
在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看來,作為人的存在方式,勞動是自由自覺的活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也是使人區別于動物的本質特征。勞動本身就是一種幸福,它既是幸福的應有之義,也是實現幸福的手段。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馬克思關于勞動幸福的觀點被絕大多數勞動者所接受。而在資本的驅動下,智能機器不斷更新,取代了部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引發技術性失業,沖擊勞動者的主體性地位;異化勞動損害勞動者的身心發展,“勞動”變得不幸福,這使一些人開始懷疑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正確性和適用性。與此同時,人工智能的發展,也為勞動幸福的實現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質而言之,危與機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在人工智能時代,馬克思勞動幸福觀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我們只有直面挑戰、抓住機遇,才能推動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創新發展,進而彰顯它的時代價值。
一、資本驅動:人工智能遮蔽勞動幸福
在資本的推動下,智能機器逐步取代重復性的勞動崗位,將一些勞動者限定為一個個“智能零件”以發揮作用,在削弱勞動者主體性的同時,加劇了勞動異化。而異化勞動又造成人的痛苦,形成一種對勞動幸福的遮蔽性力量。
(一)智能機器削弱勞動者的主體性
機器大工業時期,機器的大規模使用,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使資本主義國家迎來一波發展高潮。表面上來看,機器減輕了人們的勞動負擔,實質上也對部分勞動者構成危險。因為通常情況下,“進入商品[價值]的機器的價值,要小于(即等于較少的勞動時間)它所代替的勞動的價值”[1]281。智能機器是機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高級形態,它的成本低于部分勞動力價值,它產生的實際價值遠高于一些勞動者的勞動價值,因此部分勞動者的工作崗位將被代替。他們的勞動不是沒有價值,只是對于資本增殖來說,不如智能機器有價值。由此,這些勞動者的主體性被弱化,他們不再像以前一樣在勞動過程中占主體地位,他們的能動作用也難以發揮。
第一,資本逐利的本性推動智能機器的迭代升級。作為一種勞動工具,智能機器的使用,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勞動生產率、縮短生產周期,進而提高資本周轉速度和剩余價值率。不同于傳統的機器,智能機器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對于部分工作流程,它可以脫離人的輔助獨立運行,而且它的工作效率遠遠高于同類的勞動者。與人相比,智能機器既不需要物質報酬,也不需要休息時間,它“心甘情愿”為資本增殖服務。相比之下,資本更傾向于購買和使用智能機器,而選擇淘汰一部分技能較低的勞動者,這是資本逐利本性決定的。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一大批資本流入智能機器的研發與生產領域,促使智能機器不斷更新換代。從第一代機器人到第三代智能機器人,智能機器的技術越來越成熟、功能越來越多、自主性和適應性越來越強。由于這些智能機器的應用,無人車間、無人工廠及無人酒店等紛紛出現。在資本獲利的同時,部分勞動者正在面臨失業的危險。
第二,不斷更新的智能機器取代部分勞動者。隨著智能機器的不斷發展與廣泛使用,大約50%的人類工作將會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其中從事翻譯、助理、保安、銷售、客服、會計、司機、家政等幾種職業,預計將有90%的人被人工智能取代[2]157。智能機器的迅猛發展引起全世界的關注,科學家史蒂芬·霍金預言,人工智能將在百年后超過人類。當前,在部分行業,有一些程式化的勞動已經被智能機器替代了。缺乏技術性的和創新性的勞動者被日益完善的智能機器所排擠,淪為“相對過剩人口”。這些失去工作的勞動者變成了無所事事的游民,他們不僅喪失了勞動的機會,也被剝奪了人的存在方式,這致使他們的主體性日漸失落。因為人是通過勞動來實現自身發展的,沒有勞動就無法確證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也就無從體會勞動的幸福。
(二)資本邏輯加深勞動異化
資本邏輯即資本擴張邏輯,它追求剩余價值的最大化。在資本邏輯的宰制下,智能機器不斷發展、推廣,使一些勞動者被迫下崗、另一些勞動者淪為智能機器的“附庸”,這使得勞動異化現象更加凸顯,具體表現為:人與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勞動本身的異化、人與類本質相異化及人與人相異化。
第一,人同人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在人工智能時代,機器越來越智能,具有了人的部分特性,而部分勞動者卻越來越像機器,最后成為智能機器的“零件”、被安置在某個生產環節。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不需要掌握完整的生產技藝,他們被分割在不同的部門、只需執行智能機器的“指令”、重復著簡單而機械的動作。智能機器主導著生產流程,將部分勞動者置于次要地位,抹殺了他們的勞動價值,仿佛勞動產品都是由智能機器生產出來的。事實上,不管是勞動產品還是智能機器,都是由勞動者生產出來,都是勞動對象化的產物。但資本遮蔽了這一點,使勞動產品異化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工人生產的勞動產品越多,反對自身的力量就越強大;工人“創造的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工人的產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3]158。
第二,勞動本身的異化。作為人的存在方式而言,勞動本該是一種自由自覺的活動。但資本邏輯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展,將勞動者作為智能機器的“附屬品”,使他們在勞動過程中的地位每況愈下。在龐大的智能機器體系面前,普通勞動者顯得無力而渺小,他們只能服從資本的安排,從事著一種受動的勞動,以期獲得微薄的生活資料。
第三,人同類本質相異化。與動物不同,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動物的生產勞動是片面的,只為滿足自身的生命需要。而人的勞動對象是整個自然界,“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將自然界表現為自己的“作品”,從而確證人的類本質。而智能機器的資本化運作,剝奪了部分勞動者的勞動對象和勞動本身,使他們失去“類生活”。至此,一些勞動者的“類本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的精神的類能力,都變成了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本質,變成了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3]163。
第四,人同人相異化。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原先復雜的腦力勞動和繁重的體力勞動變得簡單、輕松。智能機器的使用,降低了某些勞動的智力要求和體力要求。以前需要幾個成年男性才能完成的工作,現在只需要一個女性員工或老年員工就可以完成。因此,一部分勞動者將不被資本增殖所需要、成為被裁員的對象。為了爭取勞動的機會,一些勞動者不得不陷入“內卷”,他們之間的惡性競爭由此開始,這致使“一個人同他人相異化,以及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同人的本質相異化”[3]164。
(三)異化勞動導致人的痛苦
人工智能時代,資本和技術的合謀,加劇了勞動的異化。而異化勞動不是人的本質,而是外在于人的東西。就異化勞動而言,人們“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3]159。
第一,在異化勞動的過程中,勞動者是被監視的“勞動機器”。作為智能機器的“助手”,部分勞動者的任務是配合智能機器工作,而不是自主地發揮作用。他們被資本馴化為“機器”,整日從事著單調而枯燥的勞動。此外,研發智能機器或系統的勞動者雖然具有一定的創造性,但他們也被資本圈養在單一的勞動領域、從事著高強度的腦力勞動。在“996”“007”的工作制下,部分勞動者的勞動時間不斷延長、勞動強度不斷加大,致使他們“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勞動中則感到不自在,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3]159。并且勞動者在異化勞動中還不能消極怠工,因為隨處可見的智能攝像頭充當24小時監工,勞動者的一舉一動都會通過智能設備反饋給管理者。這種外在的、強制的勞動一旦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3]159。然而,不幸的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勞動者“只有作為工人才能維持自己作為肉體的主體,并且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3]158。異化勞動既是勞動者的謀生手段,也是他們難以逃離的“怪圈”。
第二,異化勞動的產品加強統治勞動者的異己力量。在資本的主導下,勞動者使用智能機器生產出更多的勞動產品。而這些勞動產品非但不歸勞動者所有,反而成為新的、異己的力量。由此,“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3]157。在資本主義世界,資本掌控著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工人只有成為異化勞動的“機器”,才能獲得勞動的資格,進而得到維持生命存在和繁衍的生存資料。同時,勞動者只有以犧牲身心健康為代價生產更多的勞動產品,才能不至于被智能機器或其他勞動者所取代。因此,在資本和智能技術的共謀下,這種異化勞動導致人的痛苦,使一些人對“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產生疑問,致使真正的勞動幸福面臨被遮蔽的危機。
二、技術賦能:人工智能助力勞動幸福
在資本的驅使下,人工智能加重勞動異化,形成遮蔽勞動幸福的力量,這根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弊端。而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人工智能將被合理使用,它將提高勞動效率和優化勞動關系,進而加快勞動解放和勞動幸福的實現進程。
(一)人工智能提高勞動效率
人工智能原本就是一種勞動工具,只是在資本的裹挾下,才變成異化勞動的“催化劑”。正如馬克思所說:“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幣,砂糖并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4]340。人工智能也是一樣,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是資本奴役勞動的工具。而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人工智能將發揮全部的技術潛能,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因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歸勞動者共有,勞動過程由勞動者主導,勞動產品也歸全體勞動者所有,這使得異化勞動“無處容身”。
第一,智能機器的社會主義運用,提高物質資料生產的勞動效率。21世紀以來,中國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發展。研制出的各類智能機器應用于各個生產領域,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智能機器始終作為勞動工具被絕大多數勞動者所掌握,而廣大勞動者也將智能機器作為自身“器官”的延伸,進而不斷提高勞動效率,生產出更多的物質資料。與資本主義社會不同,我們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將生產的物質資料分配給每一位勞動者,以滿足他們的物質需要、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同時,對于高危的和工作環境惡劣的勞動,將由智能機器人承擔,從而確保勞動者的勞動安全。
第二,人工智能的發展帶動數碼產品的更新,進而提高了文化產品的生產效率。近年來,智能手機、攝像機等數碼產品不斷發展和推廣,使得人人都有麥克風,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電子產品生產、傳播各式各樣的文化符號,這極大地豐富勞動者的精神生活、滿足他們的文化需要、使其獲得精神享受。同時,在社會主義中國,網絡不是法外之地,智能傳播的文化樣態受到了法律的監管,不良的文化信息被及時屏蔽,風清氣正的網絡環境業已形成。因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工智能的發展推動智能機器和數碼產品的迭代升級,使更好的、更多的物質文化資料被生產出來,進而滿足了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使其獲得生理心理層面的幸福。
(二)智媒體優化勞動關系
人工智能驅動媒體融合發展,使智媒體的實現成為可能。所謂“智媒體是基于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大數據、虛擬現實等新技術的生態系統,由智能媒體、智慧媒體和智庫媒體三個部分構成”[5]。智媒體的發展和應用,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勞動關系。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智媒體改善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關系。智媒體不僅為勞動者獲取就業信息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也密切了勞動者與用工單位的聯系。勞動者可以通過智媒體向老板和單位提出意見建議,以此爭取更高的勞動報酬和更舒適的勞動環境。而單位管理者也可以通過智媒體了解勞動者的工作表現、實際需求和生活困難,進而針對性地提高他們的工資待遇、改善勞動環境。智媒體的應用,將為勞動者和用工單位搭建更廣闊的交互平臺,兩者可以通過這一渠道,增進了解、改善關系。此外,對于不合理、不合法的勞動狀況,智媒體可以及時發現和實時曝光,進而引起社會的重視,促使有關部門介入、及時處理勞資糾紛等問題,從而使勞動關系更加和諧。
第二,在再分配中,智媒體助力精準扶貧。兼顧效率,在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既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也有利于勞動關系的優化。而扶貧是再分配的一種方式,智媒體的使用為實現精準扶貧提供了可能性,在脫貧攻堅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從傳播扶貧政策、鎖定貧困戶到記錄脫貧歷程、反饋脫貧數據等,智媒體提供了相關的技術服務。同時,根據不同地區和不同貧困戶的情況,智媒體基于大數據的分析和算法推薦,為當地政府和有關部門提供了可行性脫貧方案、以供參考。在智媒體的助力下,精準扶貧政策落地落實,使得中國消除了絕對貧困,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和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
第三,在人際交往中,智媒體優化了勞動者之間的關系。由于身處同一個工作環境,不同的勞動者之間既有合作關系,也有競爭關系。各自為政、相互猜忌會惡化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加劇惡性競爭,這源于勞動者之間缺少交流。智媒體為勞動者搭建了更智能的社交平臺,同時引導勞動者發現彼此的閃光點,使他們在生活中培養共同的興趣愛好,進而增進友誼和共識。質而言之,智媒體的發展和應用,使勞動關系得以不斷優化,進而使勞動者獲得人際關系層面的幸福。
(三)智能化技術推動勞動解放
技術決定論認為,隨著智能化技術的自主性越來越強、發展程度越來越高,終有一天,人工智能技術將代替絕大多數的勞動者,而他們也將淪為“無用階級”、被社會所拋棄。顯而易見,這種觀點是偏激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智能化技術的發展將推動勞動解放,使人們實現自由全面的發展、從而獲得至高的幸福。人工智能只是一種高新技術,本身不會帶來惡劣影響,關鍵在于誰來用、怎么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引導人工智能朝著利好的方向發展,使其為實現勞動幸福提供強大的推動力。
第一,智能化技術加快自由勞動的實現進程。在某種意義上,勞動可分為必然勞動和自由勞動。必然勞動具有外在性和謀生性,在這里,勞動作為一種謀生手段,勞動者為了滿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需要,必須從事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必然勞動。而自由勞動是在必然勞動的基礎上,自主地完成智力和體力的對象化、在勞動中占有人的全部本質、實現勞動目的。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如果勞動者的大多數時間都被必然勞動所占據,那么就鮮有時間從事自由勞動。而智能化技術推動智能機器、智能產品及智能系統的迭代升級,它們作為強有力的勞動工具為全體勞動者所使用,提高了勞動者的工作效率,縮短了必然勞動的時間。與以前相比,勞動者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可以生產出充足的物質資料,而節省出來的時間將是勞動者自由支配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勞動者可以不在外在性的驅使下勞動,根據自身的個性和興趣從事有益活動,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由勞動。
第二,自由勞動解放人,使勞動者收獲最高層次的幸福。馬克思指出:“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3]527。因此,當我們通過必然勞動完成“第一個歷史活動”,也就是為自由勞動開辟了道路。而自由勞動確證了人的本質,為人之為人創造了條件。異化勞動將人矮化為動物式存在,埋葬了人性;必然勞動雖然滿足了人的生存需要,但很難滿足人的發展需要;只有自由勞動才能使人向人性復歸,使得全體勞動者邁向自由王國。同時,“勞動向自主活動的轉化,同過去受制約的交往向個人本身的交往的轉化,也是相互適應的。隨著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終結了。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上,一種特殊的條件總是表現為偶然的,而現在,各個人本身的獨自活動,即每個人本身特殊的個人職業,才是偶然的”[4]210。必然王國中的職業固化將得以破除,“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將得以實現。在自由勞動中,勞動者不僅充分占有人的本質、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而且通過自身的勞動創造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為其他人的幸福生活創造條件,從而實現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獲得最高階的幸福。
三、理論突圍:人工智能時代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發展路向
資本化運作的人工智能加劇異化勞動,制造“勞動痛苦”的假象,大有遮蔽“勞動幸福”之勢,使馬克思勞動幸福觀面臨理論詰難。對此,我們要巧用人工智能帶來的機遇,推動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與時俱進,促進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智能化傳播,完善踐行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制度保障,從而實現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理論突圍。
(一)因時而變:推動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理論創新
人工智能時代,雖然在勞動領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但這并沒有改變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科學性。而為了更好地指導人工智能時代的勞動實踐,我們也要立足新的實際,不斷推動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理論發展,使其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
第一,揭露人工智能時代異化勞動的新變化,剖析“痛苦”的原因。我們要針對異化勞動的新表現,運用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理論展開批判。一是在資本的驅動下,智能機器在部分勞動中躍升至主導地位,一些勞動者跌落次要地位、成為“機器”的附庸。他們被安排在某個崗位,配合機器重復著相同的動作,失去了勞動的自主性。二是智能機器的生產者和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這些勞動者生產了智能機器等,具有一定的創造性。但他們的勞動產品和生產資料都不歸自己所有,他們生產的智能機器越多,反對他們的力量就越強大,以至于他們不得不聽從資本的擺布。因為只有在資本的加持下,他們才能有條件生產智能機器以獲得必需的生活資料。三是人工智能滲入部分勞動者的學習、生活及工作等方面,成為鉗制他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異己力量。隨著人工智能的普及,一些勞動者不僅在工作中離不開智能機器,在學習和生活中也離不開智能手機、電腦等智能產品。同時,智能媒介為不同的人群分眾推送形式各樣的文化信息,形成信息繭房,將一些勞動者困在“回聲室”中,他們只能聽到有利于資本增殖的信息。而資本又進一步制造虛假的消費需求,誘導勞動者盲目消費。由此,在人工智能時代,資本的力量更易擴張,異化勞動的程度更深,勞動的強制性和外在性更明顯,所以部分勞動者在這種異化勞動中感到痛苦。對此,我們要引導勞動者透過異化勞動的新變化認清其實質、明晰痛苦的根源,進而找尋破解之法。通過批判人工智能時代異化勞動的新表征,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理論深度也得以拓寬。
第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及方法,闡釋人工智能時代勞動幸福的新樣態,從而豐富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內涵和外延。在社會主義中國,我們要盡量消除資本對人工智能的不良影響,確保人工智能技術掌握在全體人民的手中,并使這一智能技術為實現勞動幸福保駕護航。可喜的是,相比于資本主義國家,人工智能在中國發展迅速,推動勞動幸福發展到新的階段。在這個新階段,勞動幸福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智能機器的使用,減輕了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在很多車間,勞動者只需按一個或幾個按鈕,智能機器就會自動運行,而勞動者作為機器的主人、只負責監工和維修等,這減輕了他們的勞動負擔,使其感到輕松舒適。二是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歸全體勞動者所共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無論是智能機器,還是其他的勞動資料都歸人民共同所有。所以勞動者通過智能機器生產的勞動產品也由他們所享有,勞動產品越多,他們的獲益越大。三是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提高了全社會的生產力,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進而提高了勞動者的收入,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水平,使其得以享受生命。四是勞動者通過使用智能技術,在一程度上實現自由自覺的勞動。由于人工智能的助力,勞動者的“器官”被延長,使他們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勞動任務。在其他更多的時間里,勞動者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從事自由勞動,進而實現全面發展、追求至高的幸福。質而言之,我們要用理論話語表述人工智能時代勞動幸福的新樣態,并將其融入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話語體系。
(二)智能傳播:加大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宣傳力度
我們不僅要促進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理論發展、彰顯它的真理性和科學性,還要推動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智能傳播、擴大它的影響力和覆蓋面,從而使其成為廣大勞動者的行動指南。
第一,基于算法推薦,分眾化傳播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算法是指通過輸入特定的代碼、設計相應的程序,從而獲得所要求輸出的解題方案。它是人工智能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被應用于信息傳播領域。如果算法被資本驅使,可能會引發“信息繭房”效應或不良文化的蔓延。因此,我們要合理運用算法,加強對算法設計者和使用者等的監管,消弭算法帶來的消極影響。同時,我們要利用大數據分析勞動者群體的性格、特點及偏好等,從而使用智能算法,為他們分眾推送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內容。在這里,不是將馬克思勞動幸福觀分割成不同部分以實現分眾化傳播,而是根據勞動者群體的不同愛好和需求等,有側重的傳播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理論知識,并且根據勞動者認知水平的不同,采用文字、語言及視頻等一種或多種形式傳播馬克思勞動幸福觀,從而使勞動者更好地理解這一理論。
第二,基于虛擬現實技術,沉浸式傳播馬克思勞動幸福觀。虛擬現實技術是綜合運用大數據和傳感器等智能技術,模擬一種情景再現的傳播技術。我們要充分掌握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的技術,制造一種自由自覺勞動的場景和幸福的勞動畫面,讓勞動者戴上VR眼鏡融入虛擬情境之中,從而獲得具身化體驗。通過這種方式,使得“勞動幸福”的概念具象化為實際的體驗活動,從而讓勞動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馬克思勞動幸福觀所昭示的就是幸福的未來。同時,也要運用虛擬現實技術,營造異化勞動的情境,讓勞動者沉浸式體驗異化勞動的痛苦,從而堅定消除異化勞動的決心。兩相對比,勞動者將更加確信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真理性。
第三,基于智能平臺,交互式傳播馬克思勞動幸福觀。僅有單向傳播是不夠的,我們還要依托官媒、微信、微博、B站及抖音等智能平臺,交互式傳播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理念和思想。作為受眾,勞動者可以通過這些平臺第一時間向信息生產者反饋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惑,而生產者也可以及時為勞動者群體解惑答疑。而作為傳播者,勞動者也可以向政府部門、用人單位及其他勞動者傳播自己對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見解,進而交流學習心得和體會。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對這一理論的認識將不斷加深。正是由于分眾化傳播、沉浸式傳播及交互式傳播的實現,勞動者將逐步從被動學習轉向主動學習馬克思勞動幸福觀。
(三)制度支撐:倡導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自覺踐行
作為一種科學理論,馬克思勞動幸福觀只有被勞動者所掌握、并運用于勞動實踐,才能使這一理論綻放出強大的物質力量,進而沖破技術異化和勞動異化的“圍堵”。因此,我們要建立健全相關的制度體系,為引導勞動者自覺踐行馬克思勞動幸福觀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第一,完善相關制度以防范人工智能技術資本化,為踐行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營造良好環境。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還不是處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4]165。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一些相關的科技公司相繼出現,智能技術的所有者在資本的驅使下推動勞動實踐領域的變革,改變了社會的勞動分工,使智能鴻溝進一步拉大。由此,一些技術素養低的勞動者或是被智能機器所取代、或是被分配到輔助機器的次要崗位。這種對抗性的、強制性的分工加重勞動異化,使勞動與幸福相疏離。對此,我們一方面要加強立法,規范人工智能的研發和應用,破除對抗性分工。不管人工智能發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傷害人類,這是最基本的規定。同時,要健全人工智能技術壟斷法,防止智能技術被少數公司或個人所壟斷,它應該屬于全體勞動者。在人工智能的研發環節,技術人員要確保智能機器等要始終被勞動者所控制,使其作為一種勞動工具被人們所使用,而不能成為“脫韁的野馬”。在應用領域,智能機器的使用不能造成大量勞動者的失業,而要通過人工智能技術為勞動者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也是用人單位的社會責任。倘若各類企業唯利是圖,大范圍裁員或用智能技術壓榨勞動者,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另一方面,我們要完善勞動技能培訓制度,消除強制性分工,使勞動者能夠自主選擇工作。各級各地政府要聯系用人單位,進一步完善職業培訓制度,在職前、入職和職中三個時間段開展系統培訓。職前,要堅持“因材施教”,根據他們的意愿為其做職業規劃,進而針對性地培養他們的勞動技能、提高他們的智能素養,幫助他們找到滿意的工作。在入職時,直管領導和老員工要加大對新員工的幫扶力度,使其盡快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在職中,要建立日常化培訓制度,分為有組織的集中輪訓和自主的分散學習兩大部分,從而不斷提高勞動者的技能,使其緊跟時代發展的潮流。質而言之,要充分發揮法律制度和培訓制度的作用,消除人工智能技術資本化的不良影響,為踐行馬克思勞動幸福觀掃清障礙。
第二,健全相關的體制機制,引導勞動者將“馬克思勞動幸福觀”外化于行。一是要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為實現勞動幸福奠定物質基礎。勞動者的工資要根據當時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水平做相應的調整,這樣才能確保“勞有所得”,使智能技術的發展成果為全體勞動者所共享。相關政府部門要定期調查勞動者的工資情況,著力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督促用人單位逐步提高勞動報酬,使勞動者“衣食無憂”,從而為實現勞動幸福提供物質前提。二是要建立獎懲機制,引導勞動者自覺踐行馬克思勞動幸福觀。對于自覺踐行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企事業單位或個人,我們要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和精神鼓勵。同時,要大力宣揚勞動精神、工匠精神及創新精神,從而在全社會“牢固樹立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觀念,讓全體人民進一步煥發勞動熱情、釋放創造潛能,通過勞動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6]46。相反,對于違背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言論或行為,我們要加大懲戒力度。各級政府要壓實責任,針對破壞“勞動幸福”的現象,既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予以制裁,也要使用“批判的武器”進行批評教育,進而有效杜絕此類現象,為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踐行鋪平道路。概而言之,我們要通過完善相關制度,為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實踐創造相應的條件,進而鼓勵勞動者自覺踐行馬克思勞動幸福觀。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李開復,王詠剛.人工智能[M].北京:文化發展出版社,2017.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瞭望新時代共話新媒體[N].濟南日報,2018-10-11(03).
[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Crisis and Breakthrough: Marxs Concept of Labor Happines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ANGMiao
Abstract:Marxs Concept of Labor Happiness holds that “Labor is the pleasure of life” , and labor happiness is the real happiness of human being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rings new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to Marxs concept of labor happiness. Driven by capital, intelligent machine weakens the subjectivity of workers,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deepens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Alienated labor leads to human suffering, forming a trend of shielding labor happiness, so that Marxs concept of labor happiness is questioned. However, i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used reasonably, it will improve labor efficiency, optimize labor relations, spur labor liberation, and help the realization of labor happiness, thus confirming the scientificity and truth of Marxs concept of labor happiness. Based on this, we should turn risk into opportunity, grasp the opportunity,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Marxs concept of labor happiness, strengthen the propaganda of Marxs concept of labor happiness, and advocate the conscious practice of Marxs concept of labor happiness, so as to realize th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of Marxs concept of labor happiness.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rxsConcept of Labor HappinessCrisisTheoretical Breakthro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