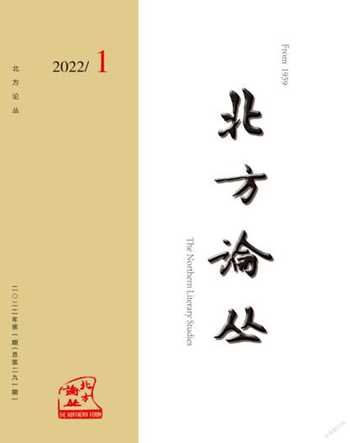林紓譯筆的語言策略
[摘要]林紓譯筆即林紓的翻譯文筆,是林譯小說譯介方式與文學表達的文本顯現(xiàn)。為達到譯文與原文的信息對等,林紓在借鑒“言文合一”觀念的基礎上,有意在文言譯文內(nèi)添加大量的白話俗語。這種“文白相融”的語言策略不僅打破了古文筆法的諸多禁錮,同時也呈現(xiàn)出書面話語的近代變革之勢;譯介層面的雙語轉化夾雜著歐式語言的滲入,林紓譯筆對于歐化詞法和歐化句法的吸收,改變了文言原有的書寫特性與語句框架,進而表現(xiàn)為“新”與“舊”的敘述疊合;新舊交融下的譯介活動又催生了“注”與“評”等譯筆補充形式。這類注評以副文本為表現(xiàn),從而成為林紓針砭時弊、宣揚愛國保種之情的文本場域。林紓譯筆既吸收古文之典雅,又融合今文之新奇,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促進傳統(tǒng)小說文筆的現(xiàn)代嬗變。
[關鍵詞]譯筆語言策略文白相融外語移入文中注評
[基金項目]哈爾濱師范大學優(yōu)秀科研團隊資助項目“中西比較文學創(chuàng)新團隊”(1102120003)
[作者簡介]張書寧,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哈爾濱150025)
[DOI編號]10.13761/j.cnki.cn23-1073/c.2022.01.015
林紓譯筆即林紓的翻譯文筆,是林紓小說譯介方式與文學表達的文本顯現(xiàn)。林紓譯筆具有鮮明的語言延展性,“文白相融”“外語移入”“文中注評”是林紓譯筆語言策略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一方面,隨著近代報刊及印刷產(chǎn)業(yè)的興起,白話文體得到廣泛傳播,在“我手寫我口”和“新文體”等觀念的影響下,林紓譯筆呈現(xiàn)出文言與白話的交替融合,從而增添了譯文的趣味性和通俗性;另一方面,林紓譯筆以“口譯+筆譯”為實踐模式,在基于中外雙語轉換的譯介空間內(nèi),譯筆不可避免地受到歐化語言的影響,進而表現(xiàn)出歐化詞法與歐化句法在翻譯文本中的頻繁交替。這種外語移入不僅豐富了文言譯筆的審美傾向,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清末民初的漢語變革;“文中注評”是林紓根據(jù)客觀事實所產(chǎn)生的譯筆注釋與譯筆評論,“評”與“注”的結合,也因此成為林紓對原文進行主觀闡釋與內(nèi)容解讀的場域。林紓譯筆所采取的語言策略在“古”與“今”、“中”與“西”的交流碰撞中推動著近代小說的文體變革,為傳統(tǒng)書面話語的現(xiàn)代轉型注入了動力。
一、文白相融
文言與白話的融合是林紓譯筆的顯著特色。首先,林紓譯筆對于白話的吸收,在一定程度上順承了文白演進及消長的歷史趨勢,從而達到適應時代需求的目的。其次,近代言文合一的語用現(xiàn)象也為林紓譯筆的文白融合提供了現(xiàn)實的參考與借鑒。黃遵憲所倡導的“我手寫我口”與梁啟超的“新文體”觀,都不約而同地強調(diào)白話口語、俚語、俗語對于文章書寫的審美統(tǒng)攝,這不失為譯筆文白融合的理論來源。總體而言,林紓在翻譯層面對于白話的大膽采用,不僅在于追求文本內(nèi)容的信息對等,同時也是其本人在文學維度上對文言之“雅”和白話之“俗”的中和。白話與文言因為林紓的譯筆而實現(xiàn)了形態(tài)的重組。在清末民初,這種文白融合的譯筆實踐無疑具有巨大的文學價值。
(一)近代言文合一
“言文合一”主張在清代道光年間便已存在,龔自珍曾認為“以后語古,猶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1]204。語言和文字的分離是中國文學史上長期存在的現(xiàn)象,文字的不易性和語言的易變性往往不相協(xié)調(diào),進而造成口頭語與書面語之間的意義差別。這種言文分離也極易干擾讀者對于傳統(tǒng)文本的理解。因此,近代“言文合一”的語言實踐,也就為林紓譯筆中的“文白融合”提供了理論來源。
1.黃遵憲“我手寫我口”
黃遵憲對于言文分離有較為清晰的認識。早在1868年,黃遵憲便在《雜感》中提出“我手寫我口”,認為文言文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口語的傳達。在此基礎上,黃遵憲進一步認為,晚清的書面語言要進行全面的革新,即書面語應有翔實的敘述和傳遞作者思想的文本意圖,所以文章寫作要采用白話俗語,即“不為古人所束縛”“何必與古人同”[2]79。在《日本國志》一書中,黃遵憲則明確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張,認為“文字者,語言之所以出也。雖然,語言有隨地而異者焉,有隨時而異者焉,而文字不能不因時而增益,畫地而施行。言有萬變而文止一種,則語言與文字離矣……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3]809-810。為了達到言文的一致性,黃遵憲甚至試圖“更變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4]1420,以此“欲令天下之農(nóng)、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簡易之法哉”[5]56。黃遵憲的言文合一觀念直指文言“文不達意”等問題,這不僅突破了中國傳統(tǒng)書面語的固有弊端,同時也為裘廷梁的“崇白話廢文言”[6]169提供了思想來源。在晚清印刷產(chǎn)業(yè)和通俗文學的推動下,“言文合一”觀念不僅深入人心,同時也間接影響了近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翻譯。文言的書面地位被進一步解構,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奠定了前期準備。
2.梁啟超的新文體觀
梁啟超是“文言合一”的堅定支持者。梁氏在《新民說·論進步》曾直言:“言文合,則言增而文與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應之,新新相引而日進焉。”[7]179在某種程度上,梁啟超的新文體直接繼承了文言合一的基本精神,意圖破除文言文“深復典雅,指意難睹”特征,從而達到書面通行的目的。1902年《原富》譯出后,梁啟超曾高度贊揚嚴復譯介西學的功績,但對于《原富》所使用的文言字體,梁氏則認為“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效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繼而指出文言文的使用“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童受其益乎”[8]67-68。在梁氏看來,語言書寫的意義不在于追求表面上的辭藻堆砌和繁縟艱深,也不在于因循守舊式地維護傳統(tǒng)儒家之道,而是否易被大眾群體所接受,是否易于傳遞作者的文字意思,才是書面語言的真正價值存在。因此,以“報章文字”為基礎,梁氏的“新文體”表現(xiàn)出“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9]85-86等特點。“新文體”一反傳統(tǒng)文言的諸多禁忌,注重流暢且順達的文字表達,甚至大膽使用歐化詞語。與此同時,新文體也積極吸收俚語俗語,這既是對文言語用的淡化,同時也是對白話文的書面解禁,正如胡全章等人認為:
梁啟超新文體改良文言的努力,首先體現(xiàn)為淺近化、白話化與不避駢偶的語言表達,以及平易暢達、酣放淋漓的文體風格。從語體層面考察,主要表現(xiàn)有三:其一是從眾向俗,為文盡量運用淺近易懂而非艱澀生僻的文言語匯;其二是向俚語開放,吸收諺語、俗話、成語等白話成分,拉近言文之間的距離;其三是不避駢偶,吸收雙聲疊韻語匯,融會駢文時文的偶句排句,增強音韻之美、節(jié)奏之感與整飭之氣。[10]
梁啟超的新文體吸收了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各自優(yōu)點,直指傳統(tǒng)古文的弊病,是晚清語言變革的先聲。林紓譯筆對于“雋語”“佻巧語”“外來新名詞”的使用,也無不借鑒了梁氏新文體的諸多觀點,新文體也成為林紓在翻譯過程中采取“文白相容”策略的理論參考。
(二)白話報刊的出現(xiàn)
白話報刊的出現(xiàn),不僅積極傳播了西方先進的思想和文化,同時也加速了白話文在書面語體中的使用。早在1874年,王韜在其所創(chuàng)辦的《循環(huán)日報》中宣稱:“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即佳文。”[11]31在報紙中使用淺顯易懂的白話語體,可以讓廣大讀者直接且詳細了解報紙所載之事,這是文言所不具備的功能。此外,近代第一份白話報《民報》在某專欄也直言通俗之語的重要性:“此報專為民間所設,故字句俱如尋常說話。每句及人名地名,盡行標明,庶幾稍識字者便于解釋。”[12]隨著言文合一的開展,以及市民階層對于信息獲取的渴求,白話報刊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據(jù)相關統(tǒng)計,1898年到民國時期的白話報刊共有170多種[13]89。這些白話報刊的存在,也為近代小說創(chuàng)作及翻譯的白話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資借鑒之處。
白話報刊作為近代新型的語言傳播媒介,極大拓展了普通大眾的閱讀視域。林紓在《杭州白話報》所發(fā)表的一系列“白話道請”[14]80,正是順應了白話報刊的發(fā)展趨勢。這種前期的白話文創(chuàng)作,也為林紓譯筆的“文白融合”奠定了實踐基礎。報刊的流通和傳播,進一步推動了白話文的應用。這種報刊為載體的白話輻射,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同時期的文學話語,進一步消解了文言文對于近代書面語的操縱,彌補了文言文的原有缺陷。
(三)文白融合的譯筆表現(xiàn)
文言與白話的融合是林紓譯筆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林紓譯筆中所出現(xiàn)的文白融合既是對晚清“言文合一”運動的發(fā)揚,同時也是對其早期白話實踐的延續(xù)和升華。尤其在五四運動之后,林紓譯筆中的文白融合對現(xiàn)代新文學的發(fā)展而言,更具有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近代文言與白話的融合是漢語書面語體發(fā)展的顯著特征。文言與白話在文本中的混雜既不是二者簡單地羅列和堆砌,也不是白話對于文言的強行攝入和移入,而是兩種語言形式寓于文本層面的意義指歸。進一步講,文白融合的實質(zhì)是內(nèi)容上的有效銜接而非形式上的疊加。盡管如此,這種情況的產(chǎn)生也為文白兩種語言的組合帶來一定的困難。姚鵬圖曾在《論白話小說》一文中指出文言與白話的融合窘境:“凡文義稍高之人,授以純?nèi)自捴畷D不如文話之易閱。鄙人近年為人捉刀,作開會演說、啟蒙講義,皆用白話體裁,下筆之難,百倍于文話。其初每倩人執(zhí)筆,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書。然總不如文話之簡捷易明,往往累牘連篇,筆不及揮,不過抵文話數(shù)十字、數(shù)句之用。固自以為文人結習過深,斷不可據(jù)一人私見,以議白話之短長也。”[15]135文言文長期作為書面語的文本標準,其歷史的慣性在一定程度上驅使知識階層采取“雅”的文言范式進行文字書寫,進而少用甚至不用所謂“俗”的白話語言。白話也因為這種歷史慣性而缺少了書面攝入的法理依據(jù),靈活而通俗易懂的白話表達也因此受到限制。在報刊及印刷產(chǎn)業(yè)迅猛發(fā)展的近代社會,文言文較為僵化的文字表達也無不受到時人的詬病。王照在《官話合聲字母》中認為,文言需順應時代的發(fā)展,進行一定程度的變革,因為書面文字的最終目的在于“便民為務”:
吾國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音讀,必與當時語言無二,此一定之理也。語言代有變遷,文亦隨之……無“文”之見存也。后世文人欲藉此以飾智警愚,于是以摩古為高,文字不隨語言而變,二者日趨日遠,文字為語言之符契。[16]
文言文的寫作規(guī)范和文字要求無時無刻不在禁錮著作者的文學意圖和情感表達。盡管文言文的書面語言中正而典雅,其表達方式也努力追求一種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和美學特性,但面對著晚清“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現(xiàn)實處境和近代化浪潮的席卷,傳統(tǒng)士人階層也努力尋求文言和白話的調(diào)和。在文學翻譯的實踐過程中,這種現(xiàn)象更為明顯。翻譯的規(guī)范化和準確化也促使譯者在文言譯文中,不得不采取文白相融的策略:即文言文中加進一些口語化詞匯和語句。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僅稀釋了文言文的僵化表達,同時也便于傳遞原著內(nèi)容。雖然身為古文家的林紓認為文章不能有“凡猥之謂”“拖沓之謂”“輕儇”“狎媟語”[17]92-101等文字表現(xiàn)方式,但在翻譯文筆中,林紓則在文言的基礎上,依據(jù)原文內(nèi)容添加進他心目中的白話口語。文白融合的產(chǎn)生也就使得林紓的譯筆獨立于傳統(tǒng)文言觀念的限制,進而表現(xiàn)出較為活潑、較為自由的文體形式。正如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指出:
譬如袁宏道《記孤山》有這樣一句話:“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林紓《畏廬論文·十六忌》之八《忌輕儇》指摘說:‘“便宜人’,三字亦可入文耶?”然而我隨手一翻,看見《滑稽外史》第二九章明明寫著:“惟此三十磅亦非巨,乃令彼人占其便宜,至于極地。”[18]186
林紓一方面極度鄙視文言中的俗語使用,一方面卻在其譯筆中時常添加白話俗語,這種觀念與現(xiàn)實的巨大反差,絕非偶然。根據(jù)白話口語的類別,林紓譯筆中的文白融合現(xiàn)象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點:
其一,以白話表人物稱謂。所謂“稱謂”,是“交際主體在語言交往中處理主體間關系、進行人際定位的一種語言活動”[19],而林紓譯筆中用白話的形式表示人物稱謂,則是對文本特定人物作口語化通俗化的文字設定,以此達到還原原著情節(jié)、增強譯文感染力、便于讀者理解的目的,例如:
今余有好友一人,托其往省,請馬克姑娘延見之。(《巴黎茶花女遺事》)
我為山木女兒,即言門地,何愧于彼,浪子胡貴于我?(《不如歸》第四章)
爾明日同爸爸及嬤嬤至姨母家觀花可呼?(《不如歸》第五章)
阿父本有兩兒一女,何以言一?(《現(xiàn)身說法》第三十六章)
愛而白脫亦遙顧海夾曰:“媽媽勿哭,媽媽主人善,但去無苦。”(《黑奴吁天錄》第十二章)
林紓譯筆中隨處可見“爸爸”“媽媽”等口語化稱謂,不僅較為忠實地傳遞出原文的內(nèi)容,同時也減少了中國讀者對于域外小說的理解障礙。口語化稱謂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凸顯出說話者的心理特征,強化譯文中的人物形象。這也使得文本人物更加鮮活飽滿,進而符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文化接受。
其二,以白話表示詞句修飾。西方小說常常對文本作諸多的形容性詞句修飾,這些詞句修飾不僅起到豐富文章內(nèi)容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原著的文學感染力。這些修飾性詞語多為平白而通俗的文本表達,且以日常口語的形式進行展現(xiàn),例如:
更聞倭蘭聞我赴英之后,竟與傻伯爵聯(lián)絡親密,而余舊識之伯爵,近亦寓居倫敦。(《巴黎茶花女遺事》)
最親愛之浪子見此……爾最親愛之武男啟。(《不如歸》第七章)
為村間之傖,蠢蠢不審禮衷。(《不如歸》第十五章)
女天真活潑,靜肅有儀,初見殊不能忘。(《塊肉余生述》第十五章)
黑奴名曰瑪海……亦聰明凈潔,忠于所事。(《離恨天》第二章)
“傻”“最親愛”“蠢”等修飾性詞語常常被視為文言文所禁忌的“狎媟語”“佻巧語”而不得登“大雅之堂”。但在林紓的譯筆中,這些所謂的俗語被頻繁使用,不僅形象而生動地展現(xiàn)了原著的文字之美,同時也傳遞出小說人物的體貌特征及人物的心理活動。林紓在翻譯過程中以白話表示原著內(nèi)所出現(xiàn)的修飾性詞句,可以說是對文言文原有禁忌和固有閥限的大膽突破,從而靈活地展現(xiàn)了白話之于文言的建構意義。
其三,大量白話疊詞的使用。疊詞的出現(xiàn),不僅在譯文中充當一類副詞,同時也是對原著內(nèi)容、人物動作、人物語氣的程度修飾。總體來看,林紓譯筆中的疊詞主要以“AA”的格式出現(xiàn),多數(shù)構成形容詞或副詞,例如:
今余請勿問爾事,但得常常晤面,如見吾女可乎?(《巴黎茶花女遺事》)
武男,汝早早歸來也。(《不如歸》第十三章)
湯姆猶在車窗中頻頻出首回顧。(《黑奴吁天錄》第十章)
更遠則作蔚藍之色,浪頭層起作白色,遠遠作聲。(《迦茵小傳》第七章)
迦茵處白日昭昭中,如即長夜漫漫也。(《迦茵小傳》第十三章)
在漢語表述中,所謂的疊詞指“用重疊語素或音節(jié)來構成的詞”[20]。林紓譯筆中的白話疊詞,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這種重疊音節(jié)來強化譯文的語句效果。如“常常”“頻頻”等疊詞在于增強小說人物的行為動作及說話者的語氣狀態(tài)。另外,諸如“昭昭”“漫漫”等疊詞修飾小說中出現(xiàn)的景物,用以在視覺感官上描繪文中景物的特色,進而提升譯文的文學美感,給讀者留下想象的空間。
林紓譯筆中的疊詞不僅用以表達修飾語的程度強弱,同時也多以象聲疊詞出現(xiàn)。這些白話擬聲詞注重模仿原著小說內(nèi)的聲音構成,增強譯文的形象性,例如:
忽聞大聲發(fā)于水上,泡泡作響。(《黑奴吁天錄》第十二章)
小兒仰臥蘿中,自吮其手,嘖嘖作響。(《黑奴吁天錄》第十三章)
淺瀨惡溪,一望見底,而雷噴雪濺之聲,轉嘈嘈震耳。(《黑奴吁天錄》二十七章)
余誕生時在禮拜五夜半十二點鐘,聞人言,鐘聲丁丁時,正吾開口作呱呱之聲。(《塊肉余生述》第一章)
林紓譯筆中的擬聲疊詞種類豐富,樣式頗多。這些白話疊詞生動而形象地勾勒出原著小說聲音發(fā)出者的狀態(tài),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譯文的閱讀趣味。林紓在翻譯過程中將一些較為抽象的文本描寫以淺顯易懂的疊詞形式展現(xiàn)在讀者眼前,既是其本人在原文內(nèi)容的基礎上所作的改譯,同時也是林紓在譯文里努力調(diào)和文言與白話,并試圖將文白融合寓于譯筆建構行為的嘗試。
盡管沈禹鐘認為林紓“生平所譯西洋小說,往往運化古文之筆以出之”[18]27,但林紓所采用的譯筆也并非是完完全全的古文。文白口語的攝入,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林紓譯筆中“雅”的屬性,并改變著傳統(tǒng)翻譯的固有形式。周作人曾認為“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diào)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tǒng)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來。”[21]282但實際上,林紓將文言與白話所進行的融合實驗,就其本質(zhì)而言,更多是帶有俗語的雅致譯文。因此,這種譯筆的文白融合,與其說是林紓對于文言禁忌的忽視,倒不如說是其對白話之俗與文言之雅的調(diào)節(jié)。正如徐時儀認為,“古代漢語和現(xiàn)代漢語的區(qū)別表現(xiàn)在書面上就是文言與白話的區(qū)別……籠統(tǒng)的說來,古代漢語就是文言,現(xiàn)代漢語是白話……文、白的交替反映了漢語書面語發(fā)展的脈絡”[22]1。如果將文言視為古代漢語的書面表達,將白話視為現(xiàn)代漢語的主要載體,那么林紓譯筆中文言與白話的交替使用,則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古代漢語與現(xiàn)代漢語的文本融合。林紓譯筆之于以白話為主體的新文學,無疑具有先驗的語言啟發(fā)作用。因此蔣錫金將林紓稱為五四新文學的“不祧之祖”[23],實則有意肯定林紓譯筆對于中國文學語言的正面影響。林紓譯筆也因為文白參半而具有了語言層面“新舊交融”的特點。林紓譯筆對文言和白話進行自覺或不自覺地融合,實際上也在從側面促成了傳統(tǒng)書面語的現(xiàn)代轉型。林紓譯筆的積極作用不僅表現(xiàn)在通過翻譯維度大膽突破文言文的原有設定和固有規(guī)范,同時也體現(xiàn)在由文白的“雅俗”之分到“新舊”之別的經(jīng)驗導向與文學指歸所引發(fā)的意義延展。
二、外語移入
林紓譯筆中的外語移入主要表現(xiàn)為“歐化詞法”與“歐化句法”兩個層面。從“歐化詞法”而言,林紓對于原文單詞(或字母)多以“直譯”和“意譯”的方式譯出,進而保證翻譯的準確性與審美性;從“歐化句法”而言,林紓有時受到西式語法的影響,在譯文中多表現(xiàn)為文言句式對于長句、排比句、甚至是對原句的接受。“外語移入”是中西語言轉化過程中必然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而林紓譯筆對于歐化詞法、句法的吸收,也表現(xiàn)出其試圖調(diào)和中西語言差異,進而追求翻譯內(nèi)容與翻譯形式的內(nèi)在統(tǒng)一。
(一)歐化詞法
林紓譯筆中的歐化詞法往往以原著英語詞匯的漢語形態(tài)為主體。英語詞匯的形態(tài)變化較為明顯,這不僅體現(xiàn)在英語單詞前后綴(prefix and suffix)的意義多指、功能詞(function word)的頻繁出現(xiàn),同時也表現(xiàn)在詞性的體(aspect)、數(shù)(number)、性(gender)、時(tense)等變化。英語的動詞、副詞、形容詞、名詞、助詞往往相互組合,并受到文本語氣(mood)、語態(tài)(voice)等因素的影響,呈現(xiàn)出詞法的多種功能表達。詞或詞組的變化都要寓于英語語法的嚴格規(guī)范內(nèi),使之適應英語語義的結構層面。此外,詞的使用和書寫也限定于固有的框架,從而造成英語詞法刻意追求在語義和表述上的準確性。“英語是一種更為形式化的語言,它注重形式的變化,善于形式的變化,多用形式的變化。”[24]116-117正是基于英語自身的語言特點,英語單詞多以雙音節(jié)或是多音節(jié)的詞匯為表現(xiàn)形式,英語詞法的歧義相比較于漢語詞法而言,要少之又少。
相比較英語詞法而言,文言文的詞性較為單一,多以單音節(jié)字為獨立單位而不必過度考慮語句的完整性和指向性。此外,文言詞法的另一顯著特點便是字與字之間所呈現(xiàn)的獨立形態(tài),這種詞性的形態(tài)既沒有后綴的修飾,也沒有諸如時態(tài)和語態(tài)的限制。文言詞語的模糊化表述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語法層面的從屬范疇。進而言之,文言詞法不具備英語詞性變化的條件,也不必受制于句法層面的時態(tài)變化。這種穩(wěn)定性的存在,使得文言詞匯在語句形式上很難找到與之對應的主語、謂語、賓語。文言詞法的模糊性和單一性造成文本內(nèi)容與讀者理解之間的闡釋間距,這種“意與言會,言隨意遣”的書面表達,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英漢轉換的最大障礙。
譯介多部西方小說的林紓也認識到英漢詞法之間的巨大差異所導致的翻譯之難。在《中華大字典·敘》一文中,林紓曾直言:“仆嘗謂外國之字典,有括一事為一字者,猶電報中暗碼,但摘一字,而包涵無盡之言,其下加以界說,審其界說,用字不煩,而無所不統(tǒng)。中國則一字但有一義,非聯(lián)合之不能成文,故翻譯西文,往往詞費。”[25]173針對“中國則一字但有一義”與英語詞匯的多音節(jié)性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林紓在翻譯過程中采用“直譯”與“意譯”等方法,試圖在譯筆中調(diào)節(jié)文言單音詞與英語復音詞的意義轉換。以直譯方法為例,林紓譯筆中的源譯語多以純音譯詞為主,如:
密斯來文杰(Miss Levinger)括號內(nèi)的英語皆為筆者添加,下同。下樓矣。襆被部署訖否,然何捷耶?(《迦茵小傳》第五章)
吾為君介紹:見吾兄加必丹(Captain)格雷芙(Graves),及密斯來文杰(《迦茵小傳》第五章)
三母爾洛克(Samuel Rock),吾恨汝次骨矣!(《迦茵小傳》第十三章)
愛嗎(Emma)安琪兒(Angel),汝何事而悲?(《塊肉余生述》第十二章)
密考伯出經(jīng)尺之刀,切檸檬(lemon)皮,納之酒中。(《塊肉余生述》第五十七章)
林紓譯筆中的音譯詞根據(jù)源語文本中的詞匯發(fā)音特點,在漢語中找尋與之發(fā)音相近的單字,繼而羅列而成為多音節(jié)詞匯。除了一些西方專有名詞外,林紓的音譯詞多以西方人物名為主,進而達到譯文與原文在發(fā)音上的相似性。
除了直譯音譯詞,林紓在譯筆中也使用直譯字母詞,即將原文中的字母或詞匯不加翻譯,原封不動地呈現(xiàn)在譯文內(nèi),以此保持譯文對于原文的忠實性,如:
豐子聞言意得,則俯首于席,狀似S字。(《不如歸》第十四章)
然其背上均有鞭痕鱗鱗然,右手有H字。(《黑奴吁天錄》第十一章)
汝視之,余書不言墻上紙剝而下墮耶?紙缺處有書作血色,似以血書者作“Rache”一字。(《歇洛克奇案開場》)
汝殆為第一等之小丑,英文“Buffoon”,滑稽也,“Bufon”,癩蟆也。(《孝女耐爾傳》第五十一章)
雖然后此“A”“B”“C”三字,而又何為?(《洪罕女郎轉》第三十九章)
出現(xiàn)這種直譯字母詞的原因,一方面源于譯者對于原文詞匯的陌生所選擇的翻譯策略,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最大程度地還原原著的情節(jié)內(nèi)容,實現(xiàn)原文與譯文的信息對等。這種英語字母和單詞在譯文中的直接出現(xiàn),既是林紓追求譯筆信實的主觀愿景,同時也是他大膽創(chuàng)新譯筆形式的重要方法。
此外,林紓譯筆中的歐化詞法也以意譯的形式展現(xiàn)。意譯是相對于直譯的翻譯方法,指譯者從跨文化的角度,依據(jù)原文的大致意思所進行的翻譯活動。意譯的使用常見于對一些抽象而復雜的詞句翻譯,尤其當源語和譯入語因文化和思維的巨大差異而出現(xiàn)譯介障礙之時,意譯的作用就顯得格外重要。林紓對于原著小說的詞匯意譯,多表現(xiàn)在其對西方專有名詞的譯介,例如:
則余為南美洲各國之總統(tǒng)(President)矣,惟遲我數(shù)年,務在必成。(《璣司刺虎記》第十二章)
夫子言,將以禮拜六(Saturday)歸。(《不如歸》第十章)
已聞殖民地(colony)已叛英皇,脫其羈絆……(《拊掌錄·李迫大夢》)
迦茵瀕行始付之郵局(post office)也,(《迦茵小傳》第二十一章)
即使爾至亞洲(Asia)中國,亦當知吾之施榻是間,一無改置。(《塊肉余生述》第十章)
這些專有名詞既包含西方社會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同時也涵蓋一些人文社科等常識。林紓在理解原文內(nèi)涵的基礎上,著重采取所謂的意譯方法,此舉既能在形式上符合原著的語境設定,也能在文本意義上照顧中國讀者的認知習慣,以此達到詞匯翻譯的準確與通達。
林紓譯筆中出現(xiàn)的歐化詞法,其實質(zhì)是對西方小說源語詞匯的本土化改造。面對中西文化差異所產(chǎn)生的翻譯障礙,林紓采用直譯與意譯相結合的方法。從直譯角度而言,林紓根據(jù)源語詞匯的發(fā)音特點,通過“漢語一字”對應“英語一音”的原則,以順向排序的方式組成多音節(jié)漢語詞,從而實現(xiàn)譯文的“音譯化”。除此之外,當遇到英語字母和陌生化詞匯時,林紓通過保留源語詞匯,最大程度地在譯文內(nèi)還原原文信息。從意譯角度而言,針對一些西方專有名詞和較為抽象化的詞匯,林紓在理解源語內(nèi)容和詞匯含義的基礎上,根據(jù)漢語的構詞規(guī)律和表達效果,盡可能地使用意義相近、所指明確的詞字予以翻譯,以此方便譯入語讀者對于新詞匯的理解與接受。
(二)歐化句法
歐化句法是林紓譯筆外語移入現(xiàn)象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之一。林紓在翻譯文本內(nèi)對于部分文言句式的歐化,不僅體現(xiàn)出其忠于原著的譯者操守,同時也反映了在中西文學譯介的過程中,文言句式對于歐化句式的接受與改造。這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與碰撞所必然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林紓在翻譯文本中大膽使用歐化句法的嘗試,也間接推動著近代文學語言的變革。
對比漢語句法與歐化句法,二者之間的差別顯而易見。文言句法以意合形式為表現(xiàn),多以短句為主,連詞使用不為明顯,主語可添可減,沒有明確的指向性。這種模糊的集結往往隱含著書寫者豐富的內(nèi)心情感,進而追求一種內(nèi)容上而非形式上的意義彰顯。歐化句法則以形合形式為表現(xiàn),多以長句、主從結構為主,連詞使用較為頻繁,整體句式嚴格按照語言架構進行敘述,進而表現(xiàn)出一定的邏輯性與順承性。歐化句法的出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翻譯行為的推動。彭炫就此認為,歐化句法從翻譯層面而言“是模仿英語(或其他西方語言)的表達形式,或把漢語文字直接套入英語的句子結構模式”[26]。從歐化句法的譯文表現(xiàn)層面來講,林紓對于西方小說的譯介,既有形式上歐化句法的借鑒,也有內(nèi)容上歐化結構的挪用。總體而言,林紓譯筆的歐化句法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以長句為表達的歐化譯筆。西方語言善于使用長句,以此達到對于言語內(nèi)容的詳細傳遞。在西方小說中,長句的出現(xiàn)往往具有進一步解釋、說明作者意圖,潤色文本內(nèi)容的作用。傳統(tǒng)古文不擅長句書寫,因此林紓的譯筆充分借鑒了原著的長句結構,從而形成歐化的文言長句。這種文言長句往往一氣呵成,既形象展現(xiàn)了原著文筆之細膩,同時也較為詳細地刻畫了人物的文本對白,如:
主人爭以燈照余,余回顧尚見愛密柳在漢姆之后送余,且言曰:“行道須留意也”,既遠,司蒂爾福司謂余曰:“女貌殊佳麗,此人家屋既奇矣,而家人尤奇,足令人新奇眼界。”(《塊肉余生述》第二十一章)
自是日中行傭,終以重咎在躬,深形忐忑;迨夜中就枕,心緒彌復潮涌,念此著已無生法,既寡朋儔,亦難告語,終久將為人擯逐,彼缽特又安可示以機密者。(《迦茵小傳》第二十五章)
爾試思此女先慫恿格雷芙登塔,已乃張兩膊以拯其死,見者無不同聲以韙神勇,而吾則甚恨其人。(《迦茵小傳》第九章)
在林紓譯筆中,傳統(tǒng)文言的短句形式被解構被重置,而西方長句注重邏輯表達、善于細節(jié)描述等特性被林紓充分吸收。因此細讀林紓的譯文,不僅未因長句的表述而臃腫,同時也沒有受到傳統(tǒng)文言短句的限制而單一。林紓的歐化句式總體表現(xiàn)出緊密而連貫的語言表達,這也是其譯筆“中西融合”的表現(xiàn)之一。
其二,以排比句式為表達的歐化譯筆。相比較于文言排比,西方語言的排比句多表現(xiàn)在三個或三個以上相同詞字在同一完整語句中的排列。林紓譯筆中的排比句式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介詞排比。
……及爾所嘗之劬苦,及我所被之艱辛,若皆有神,及于能使我薄命之怨女癡男,纏綿膠糾之肺腑神,吾敢一一據(jù)為憑信。(《離恨天》第八章)
……往往思及日中盤桓故居,不覺中心若酸、若梗、若適,不能自名其所以。(《塊肉余生述》第二十二章)
二是人稱代詞排比。
汝之所育羊,今為野羊矣!汝所樹之果樹,今不實矣!汝所飼之珍禽,亦不來巢矣!(《離恨天》第十二章)
我家產(chǎn)也,我性命也,我生世也,都屬葳晴之身。(《離恨天》第八章)
三是動詞性排比。
天下之愛人,計有三種:一為愛美,一為舍己而愛人,一為溺愛不明。(《現(xiàn)身說法》第七十九章)
林紓的歐化排比句式,格式清晰,節(jié)奏鮮明,抒情性較強,充分還原了西方小說的排比特點,總體給人以韻律上的和諧之感。這種歐化排比的攝入,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林紓譯筆的敘事功能,從而豐富了譯文的形式之美。
其三,原文語句的保留。為了增強譯文的閱讀效果,林紓在一些譯著中有意將原著的語句直接挪用于譯文之內(nèi),以最大角度還原原著的故事語境,如:
吾財所儲,待天命,屬于何人者,即出而受之,惟消息至秘,不能豫語:Do not grieve for me,Edward, my son that I am thus suddenly and wickedly done to death by rebel murderers……shall all my treasure be for nought can I communicate.亞達曰:“大佐讀之,宜如何處者?”(《洪罕女郎傳》第四章)
西方文學的引進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國漢語的近代變革。通過翻譯活動,西方語言的使用規(guī)范也攝入到傳統(tǒng)漢語的書面表達。語言學家王力認為,“受西文影響頗深的人,往往不知不覺地,或故意地,采用了一些西洋語言的結構方式。”[27]341這種西化的語言格式在文學翻譯中更為明顯,尤其在涉及西方小說中的人物對話和情節(jié)敘述等方面,歐化語言的使用就尤為重要。譯者對譯介行為的選擇和建構,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西方源語文本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所謂的歐化語言又往往以句法為表現(xiàn)單位,進而在歐化語句中傳遞原著的內(nèi)容主旨。張志公曾在《修辭概要》一書中詳細談及了漢語中的“歐化句法”這一現(xiàn)象:
適當?shù)奈胀鈬Z語法中能夠容納于本國語、而且于本國語的發(fā)展有益的部分,是可以的,必然的,也是應該的……這類歐化句法,一般是先由翻譯作品介紹進來,逐漸影響了一部分人的寫作,寫作再影響了口語。[28]39-40
歐化句法的產(chǎn)生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與碰撞的歷史進程中,歐化句法的存在不僅是推動漢語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中國讀者理解西方文學現(xiàn)象與文本內(nèi)容的關鍵成因。
總體而言,林紓譯筆吸收了歐洲語言的句式特點,這種歐化語句主次分明,結構清晰,有極強的邏輯表現(xiàn),同時句子內(nèi)部各個構成要素之間彼此關聯(lián),嚴格受到語法框架的限制。盡管印歐語系的句式常常局限于所謂的規(guī)則設定,但西方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人物刻畫、景物描寫等內(nèi)容在某種意義上因為歐化長句的使用而增光添彩。歐化句法也就成為林紓調(diào)和歐式語句和古文語句的文本載體,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文言文短句的缺點。這種立足于文言基礎之上的歐化句式,無論是語義表達,還是結構鋪展,都具有一定的文學意義與譯介價值。
三、文中注評
文中注評是林紓譯筆的補充方式。所謂的注評實際包括“注釋”與“評論”兩個部分。解釋說明原著小說中的西方詞句、評論翻譯文本的思想價值就成為林紓闡釋翻譯行為的重要形式。注評不僅是林紓進一步概述原文風貌、詳細說明翻譯過程的語言存在,同時也是林紓脫離于翻譯內(nèi)容的文本羈絆,表現(xiàn)出譯者翻譯之思想和翻譯之價值的意圖彰顯。在某種程度上,文中注評充當林紓譯筆的副文本,進而傳遞譯者針砭時弊、愛國保種的文學精神與翻譯愿景。
(一)注釋
林紓譯筆的文中注評在早期版本中以小字的形式出現(xiàn)在句末。商務印書館在1981年重新再版的林譯小說系列,則多將注評放置于括號內(nèi),以此便于讀者理解。從注釋的角度而言,這種句末括號內(nèi)的文字書寫不僅是對原著西方專有詞匯的解釋,同時也是對一些翻譯內(nèi)容作進一步說明。筆者認為,林譯注釋有兩種表現(xiàn)形式,一種為解釋原著專有名詞,如:
……應得七千鋪得(鋪得者,俄國之斤數(shù))。(《現(xiàn)身說法》第三章)
常化身入乳姑乳筩中,澡其體(乳姑者,取牛乳之女娃也)。(《吟邊燕語·仙獪》)
獨注念于摩阿黑人(摩阿者,回部也……)。(《吟邊燕語·黑瞀》)
彼之主人挾丕丹之權(丕丹者,言專利也)。(《黑奴吁天錄》第十一章)
今輟議,且往由吾(由吾,賭也)。(《黑奴吁天錄》第二十三章)
這種詞匯注解一方面簡要地介紹了原著詞匯的含義,同時也增進了讀者對于譯文的理解,縮小因中西文化差異所產(chǎn)生的語言障礙,從而保證譯文的準確性。此外,林譯注釋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則為譯者對于部分文本內(nèi)容的詳細說明。這種說明既有引述下文人物話語的作用,也有中西風俗的對比、人物指代的區(qū)分、作者意圖的闡釋等功能,如:
舉皓腕,余即而親之(此西俗男女相見之禮也)。(《巴黎茶花女遺事》)
爾當著意吾言,設他……(他指吾父也)……吾深知彼之為人(彼指吾父)。(《現(xiàn)身說法》第十八章)
一既入,復戴面具(西人面具非同中國,中國以紙,西人以皮,戴之如生人,包探多用之)。(《吟邊燕語·獄配》)
天主保佑主母(此西人自明心跡之辭)。(《黑奴吁天錄》第六章)
我安須此!金盞花,汝焉知者(以花喻余年少不更事也)。(《塊肉余生述》第二十章)
通過注釋,翻譯文本中晦澀而難懂的內(nèi)容得到較為詳細的說明和解讀。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語言差異所產(chǎn)生了理解間距,從而豐富了譯筆的精神內(nèi)涵。
(二)評論
林紓譯筆中的評論多涉及反帝愛國等進步思想,這尤其體現(xiàn)在其翻譯小說《不如歸》。在日本,《不如歸》“作為一種家庭小說而受到讀者的歡迎的”[29]36。而該部小說也因為其凄婉的愛情故事,感人肺腑的情節(jié)內(nèi)容而傳播海外,被翻譯成多國文字發(fā)行。林紓在《不如歸·序》中也宣稱:“余譯書近六十種,其最悲者,則《吁天錄》,又次則《茶花女》,又次則是書矣。”[30]1盡管林紓承認《不如歸》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哀情小說,但其在翻譯文本所書寫的評論,卻多與原著小說的內(nèi)容情節(jié)格格不入——甚至帶有譯者愛國情感統(tǒng)攝下的主觀性表達。如在“鴨綠之戰(zhàn)”一章中,當日本少尉發(fā)言不惜與大清誓死一戰(zhàn),甚至譏笑中國人“行事之儒緩”時,林紓分別寫道“中國水師將弁聽之”“中國政府聽之”[30]74,以此諷刺晚清政府的懦弱無能;在“戰(zhàn)余小紀”一章中,當日本天皇蒞臨廣島,召開會議,激勵日本士氣之時,林紓評論道:“由此言之,國會可不開耶?”[30]81以此規(guī)勸清朝當局應重視政治改革,推行維新憲政;在“記旅順口事”和“武男歸朝”等章節(jié),當小說提及日本軍隊占領旅順、威海等歷史事件時,林紓分別寫下“此中國少年壯士大紀念日也”[30]98“中國壯士記之”[30]101“此中國之恥也”[30]101等語句,以此告誡讀者勿忘甲午戰(zhàn)敗之恥。
林紓譯筆中的評論多以諷勸為主要形式,這既包括林紓對于晚清政治腐敗和軍紀渙散的嘲諷,同時也包含其本人對于國家匡扶時弊、再造中興的期望。此外,這種譯文評論除了以“文中注”的方式出現(xiàn)外,也以“林紓曰”的形式置于篇章末尾,進而在譯文之外表達譯者的思想情感,還原真實的歷史現(xiàn)象。如第十八章“鴨綠之戰(zhàn)”結尾處,林紓針對甲午戰(zhàn)爭敗于“水師之不武”作了一番解釋,“以辨其誣”:
林紓曰:甲午戰(zhàn)事,人人痛恨閩人水師之不武,望敵而逃。余戚友中殉節(jié)者,可數(shù)人。死狀甚烈,而顧不能勝毀者之口,欲著《甲午海軍戴盆》以辨其誣。今譯此書,出之日人之口,則知吾閩人非不能戰(zhàn)矣……唯軍機遙制,主將不知兵事,故至于此。吾深恨郎威里之去,已為海軍全毀之張本矣,哀哉![30]80-81
在這段評論中,林紓為甲午戰(zhàn)爭中殉節(jié)的軍人“喊冤”,直言甲午之敗,并非完全在于士兵貪生怕死、望敵而逃,也不在于軍官怯于上陣殺敵。清朝的戰(zhàn)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體制問題,即“軍機遙制,主將不知兵事”。因此,林紓的譯筆評論,不僅具有抒發(fā)譯者思想情感、傳遞譯者諷刺時局的政治情懷,與此同時,這種帶有強烈功利目的的評論也包含“史”的評說成分,從而成為林紓在原著作品內(nèi)容的基礎上,還原歷史真相的“文學工具”。評說的價值也因此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延續(xù)。
譯筆注評在中外語言的轉換內(nèi)形成了一種自由化的、譯者可脫離原著內(nèi)容而隨意施展的場域空間。在這種較為自由的書寫空間內(nèi),林紓的譯筆注評不僅具有解釋、說明原著內(nèi)容的文學功能,同時也成為譯者發(fā)揮其文學想象、表達個人情感和政治思想的文本載體。從這種角度出發(fā),我們也就可以理解林紓在一些評論中展現(xiàn)出和原著小說內(nèi)容并無關聯(lián),但又依托原著情節(jié)和故事背景所開展的針砭時弊、愛國保種等進步思想的原因。林紓譯筆中的注評,也因而成為近代救亡圖存思潮指引下的一類文本表達。
林紓譯筆具有鮮明的語言特色和文化指歸,其對白話俗語、歐化詞法與歐化句法的吸收,不僅顯示了林紓兼容并蓄的譯者風范,同時也豐富了翻譯文筆的表現(xiàn)力與感染力,形象傳遞出原著的文本風格。此外,林紓在譯文中所添加的“注評”,既是譯者在譯介過程中對于原著內(nèi)容的注釋、解讀、說明、評論,也是譯筆在文本維度的空間延伸,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譯筆的重要組成部分。林紓譯筆突破了傳統(tǒng)古文的書寫禁忌,展現(xiàn)了有別于傳統(tǒng)小說的語言形式,這種較為靈活且融合中西方美學規(guī)范的文筆,無疑推動著近代翻譯文學與小說文體的變革。
[參考文獻]
[1]龔自珍.壬癸之際胎觀第三[G ]//賈文昭. 中國近代文論類編. 合肥: 黃山書社,1991.
[2]黃遵憲.黃遵憲集:上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黃遵憲.日本國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4]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二·文字[M]//陳錚.黃遵憲全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5]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二·文學[G]//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文學理論集:一.上海:上海書店,1994.
[6]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G]//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梁啟超.論進步[M]//梁啟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8]任訪秋.中國近代文學作家論[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9]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胡全章,等.晚清與“五四”:從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話[J].中國社會科學,2018(9).
[11]王韜.弢園文錄外編·自序[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2]王洪祥.中國近代白話報刊簡史[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6).
[13]方漢奇,等.中國新聞事業(yè)圖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4]張旭,車樹昇編著.林紓年譜長編(1852—1924)[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15]姚鵬圖.論白話小說[G]//陳平原,廈曉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16]王照.官話合聲字母·序言[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17]劉大櫆,等.論文偶記·初月樓古文緒論·春覺齋論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8]陳錦谷編輯.林紓研究資料選編:上冊[Z].福州:福建省文史研究館,2008.
[19]姚亞平.現(xiàn)代漢語稱謂系統(tǒng)變化的兩大基本趨勢[J].語言文字應用,1995(3).
[20]蔡華.陶淵明詩歌疊詞的翻譯策略[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10).
[21]張中行.文言和白話[M].北京:中華書局,2007.
[22]徐時儀.漢語白話發(fā)展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3]蔣錫金.關于林琴南[J].江城,1983(6).
[24]毛榮貴.新世紀大學英漢翻譯教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2.
[25]錢谷融.林琴南書話[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6]彭炫.“歐化”與翻譯——讀王力先生《歐化的語法》有感[J].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2).
[27]王力.中國現(xiàn)代語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28]張志公.修辭概要·讀寫一助[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
[29][日]吉田精一.現(xiàn)代日本文學史[M].齊干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30][日]德富健次郎.不如歸[M].林紓,魏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Language Strategy on Lin Shu’s Translation Writing
ZHANG Shu-ning
Abstract:Lin Shu’s Yi Bi, that is Lin Shu’s translation writing, it is the text manifest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mode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on Lin Shu’s translated novel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nformation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text, Lin Shu deliberately adds a large number of vernacular say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from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classical language and vernacular language”. This language strategy of “integr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Chinese” not only breaks many constraints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in writing, but also shows the trend of modern reform of written discourse; The bilingu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level of translation is mixed with the infiltration of European language. The absorption of Europeanized morphology and Europeanized syntax in Lin Shu’s translation writing has changed the original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entence framework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then manifested as the narrative superposition of “new” and “old”;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old and the new which gave birth to the supplementary forms of Lin Shu’s translation writing such as “annotation” and “comment”. This kind of annotation and comment is represented as the sub-text, which has become the text field for Lin Shu to point out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promote people’s patriotic feeling. Lin Shu’s translation writing not only absorbs the elegance of ancient literature, but also integrates the novelty of modern literature, which promotes the modern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novel writing in the exchange and colli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Key words:Translation WritingLanguage Strategy the Integr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Chinese the Transferring of Foreign LanguageAnnotation and Comments in Text
3743500338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