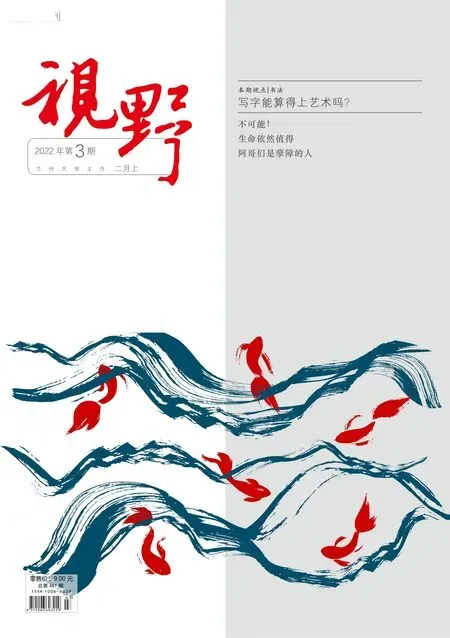后漕橋
我小的時(shí)候,我爸爸在縣城的東邊教書,那個(gè)學(xué)校就叫城東初中。學(xué)校的附近就是國(guó)道,沿著國(guó)道往縣城的方向走,很快就能到達(dá)一座立交橋,穿過立交橋,沒多遠(yuǎn)就是縣城了。那時(shí)候我每個(gè)星期都會(huì)坐在爸爸的自行車上,他載著我,我們從學(xué)校回縣城的家。我坐在二八大杠的三角架上,學(xué)校到家有五公里,剛好屁股坐酸了,就到家了。有時(shí)候趕上下雨天,我爸爸把雨披往車頭一甩,就把我罩了進(jìn)去。雨披的味道不好聞,我于是要把雨披掀起來(lái),哪怕淋雨,也好過悶在里面。后來(lái)有一次,我掀雨披的時(shí)候,雨披順著我的手臂往上抬,我爸爸連叫幾句“看不見了”,我們就連人帶車摔下去了。我再也不敢掀雨披了。
后來(lái)他再騎車載我,我老老實(shí)實(shí)地坐在三角架上,手用力握住車頭上的橫梁,等到我的手不由自主地轉(zhuǎn)動(dòng),那就是轉(zhuǎn)彎的地方了。這樣坐車很無(wú)聊,我前面除了雨披什么也看不了,我只能把眼睛投向地上。這讓我養(yǎng)成了習(xí)慣,我爸爸不穿雨披的時(shí)候,我也低頭看地。因?yàn)橛羞@種習(xí)慣,我撿過不少錢,但也因此駝了背。我現(xiàn)在是悔不當(dāng)初。
等我稍大一點(diǎn),有一次,我爸爸去別的學(xué)校監(jiān)考,他帶著我,從學(xué)校出發(fā),經(jīng)過立交橋,然后快到縣城的時(shí)候,他調(diào)整了一下把手,往一個(gè)我從來(lái)沒有去過的方向。那天一直在下雨,我整個(gè)人躲在雨披下面,開始是激動(dòng),后來(lái)是沮喪。那個(gè)學(xué)校太遠(yuǎn)了,我屁股坐得生疼。而且水泥路慢慢變得破舊,最后索性變成了泥路,坑坑洼洼,地上濺起來(lái)的水很快就把我的褲腳弄臟了;我看到我爸爸的褲腳,也遭了殃。
這不是一趟愉快的旅程,當(dāng)你經(jīng)歷過被父母帶到陌生的地方工作,考場(chǎng)上莊嚴(yán)肅穆,所有人都在有條不紊地做事,只有你,像個(gè)局外人一樣,局促不安。那天的雨很大,大得我擔(dān)心那個(gè)學(xué)校會(huì)被雨淋塌,如果那樣的話,我就會(huì)失去爸爸。我一個(gè)人站在辦公室前的走廊上,對(duì)著大雨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lái)。
后來(lái)我是怎么停止哭的,我已經(jīng)完全記不起來(lái)了。我心事重重地跟著我爸爸回城東初中,路上我很擔(dān)心地問他,你會(huì)死嗎?他哈哈大笑,說(shuō)每個(gè)人都會(huì)死的。
我的擔(dān)心不無(wú)道理,早兩年的時(shí)候,他在上課,干咳了幾下,手捂住嘴,張開一看,都是血,就去住院了。檢查出來(lái)是胃不好,他住了好多天醫(yī)院,我也因禍得福吃了很多零食——都是來(lái)看望他的人送的。他總結(jié)起來(lái)他的胃病,在于小時(shí)候總吃不飽。他曾經(jīng)跟我講他小時(shí)候,趕上村里有人結(jié)婚,主人家站在門口發(fā)喜糖花生,他個(gè)子小,靠力氣爭(zhēng)不過,主人家把喜糖和花生往空中一撒,他就撲到地上,再?gòu)纳碜酉旅鳎讼蔡浅鰜?lái),還沒攥緊,就給大孩子搶走了。他又急又氣,再伸到身子下摸索,摸出來(lái)一顆花生,緊緊抓在手中,轉(zhuǎn)怒為喜,等他一剝開,那顆花生是空的,他哇的一下就哭了。我聽了這個(gè)故事,哈哈大笑,然后跟他說(shuō),假如有時(shí)光機(jī),我一定帶一把“大白兔”奶糖給你。他老人家于是很欣慰,滿面笑容,喜形于色。這個(gè)倒霉蛋,辛苦了一輩子,走的時(shí)候連遺照都是一臉愁容。如果能多留一些他開心的樣子,那該多好啊。
還有一次,我已經(jīng)上了初中,我跟別人起了沖突,在廁所里被很多人圍毆,等人群散去,我驚魂未定地回到我爸爸的宿舍,我想去傾訴、去告狀,想他替我出頭,結(jié)果他臥在床上,不停地咳嗽,我不由得擔(dān)心他會(huì)把肺咳出來(lái)。我顫抖著手,倒了一杯水,一飲而盡,看著床上的父親,輕輕嘆了口氣,就出門了。那時(shí)候我想到他不能保護(hù)我,就有點(diǎn)恨意,又想到他在床上的病態(tài),心就軟了下來(lái)。
我很小的時(shí)候,就很擔(dān)心他會(huì)離開我。這種想法與日俱增,等到他真的罹患絕癥,這種恐懼成真以后,我無(wú)數(shù)次在深夜里驚醒,然后徹夜難眠。他反而過來(lái)勸慰我,讓我要放平心態(tài)。他說(shuō)我應(yīng)該多去外面看看這個(gè)世界,不應(yīng)該這樣悲觀。然后又感嘆我這種性格也不知道隨了誰(shuí)。其實(shí)我性格里更多是像他,敏感、糾結(jié),以及多愁。
那次我們從他監(jiān)考的學(xué)校回去,路上他忽然說(shuō)等會(huì)兒到了后漕橋,他要去給我買個(gè)餅來(lái)吃。我問他后漕橋是在哪里?我其實(shí)不在乎后漕橋在哪里,我在乎的是我什么時(shí)候能吃到餅。他說(shuō)就在立交橋附近。我于是跟他爭(zhēng)論立交橋附近到底有沒有那么一座橋,我甚至懷疑這是他虛構(gòu)出來(lái)的一座橋,目的就是為了哄住我。他于是跟我打賭,如果有那么一座橋,他就給我買餅,如果沒有,就不給我買餅。

我在雨披下面,看地上的路,從泥路變回水泥路,我不停地問他后漕橋到了嗎?他總是回答,再等等。我心里還不確定那座橋是否存在,但我已經(jīng)開始希望它是存在的。后來(lái)我爸爸停下車,把雨披從我頭上掀起來(lái)一些,讓我能看到面前的橋,他假裝遺憾地說(shuō)他輸了。
我吃上餅后,還是覺得那座橋是他變戲法變出來(lái)的。我每個(gè)星期都會(huì)從那條路上經(jīng)過,怎么會(huì)沒有注意過這座橋。英語(yǔ)里有句諺語(yǔ)叫“elephant in the room”,用來(lái)解釋那些常被忽略的事實(shí)。后漕橋就很像是房間里的大象。
我爸爸叫我不要總是低著頭了,應(yīng)該抬頭看看這個(gè)世界。很不幸,那次監(jiān)考后不久,他就收拾東西,調(diào)到了比他監(jiān)考過的那個(gè)學(xué)校還要偏遠(yuǎn)的地方教書了。我們從水泥路到泥路,這個(gè)世界如果是越看越糟,那還有什么探尋的必要。他卻不斷地跟我講,人就是要去多看世界多開眼界。這太滑稽了,他是當(dāng)老師久了,習(xí)慣性地要教育人。
我隨遇而安、知足常樂了很多年,等他離開以后,猛然想起這些,想起那座被我忽略的后漕橋,想起他說(shuō)的多出去看看,忽然就豁然開朗:先有關(guān)注,再有體驗(yàn),這才是他教會(huì)我的真諦。
很多年后我看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里面講到滿地都是六便士,他卻抬頭看見了月亮。我心有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