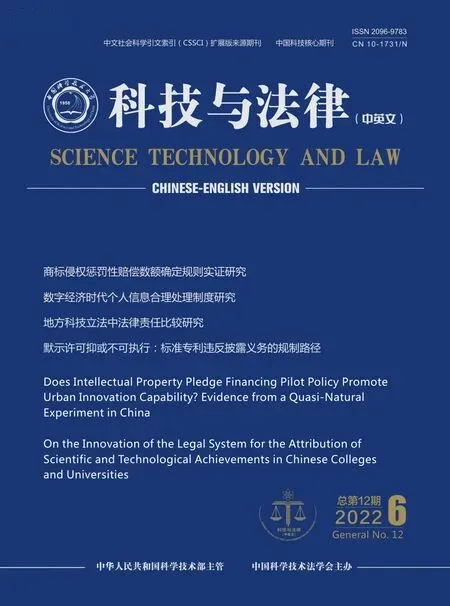默示許可抑或不可執行:標準專利違反披露義務的規制路徑
楊德橋
(內蒙古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10)
一、問題的提出與適用范圍
(一)標準與專利的本旨
標準與專利的關系問題,尤其是標準專利違反披露義務的法律后果問題,日益受到學界和業界的關注①以“標準”“專利”為主題詞檢索中國知網可知,自2006年以來每年發文量均在600篇以上,且呈現逐年遞增態勢;同樣以“標準”“專利”為條件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截至2022年8月8日,共檢索到裁判文書74 159篇,其中2018年至2020年均超過了10 000篇,自2013年以來的逐年遞增態勢非常顯著。。標準和專利本來是兩個相互矛盾的事物,存在著內在的沖突。標準是指為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對活動及其結果規定共同的和重復使用的規則、指導原則或特性的文件②ISO/IECGuide 2:2004《標準化和相關活動——通用詞匯》。。在當代產業發展中,標準化保障了各個供應商的產品之間的可兼容性、互操作性和可重復性,在整個行業的發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③輕視標準而導致失敗的一個典型案例是日本的移動通信業。在2G移動通信時代,因為使用完全“自主創新”的PDC技術,導致其與世界主流的GSM、CDMA網絡無法兼容,成為了信息孤島,日本手機用戶到世界各地都不能漫游,而日本的電信企業也因為把主要精力用在PDC的開發,沒有機會推出市場空間更大的GSM和CDMA產品,從而失去在2G時代發展的機會,導致現在全球五大電信設備商,一家日本廠商都沒有。——引自華為北京知識產權部部長同新在2014年知識產權強國論壇上的發言。。根據標準性質的不同,標準可以劃分為技術標準、管理標準與工作標準。專利就其本質來講,是一種受法律保護的技術方案。所以與專利有關的標準只能是標準中的技術標準。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定義,所謂技術標準,是指一種或一系列具有一定強制性要求或指導性功能,內容含有細節性技術要求和有關技術方案的文件。建立技術標準的目的,是讓相關的產品或服務達到一定的安全要求或市場準入的要求。專利是專利權的簡稱,是指發明創造人或其他專利權人對其發明創造在法定期間內所享有的一種專有權利[1]。專利賦予專利權人排除他人生產、使用、銷售、許諾銷售或進口受保護的發明的權利[2]。“若沒有專利制度,發明會很容易地被公眾復制或實施,但公眾對該發明的研發和完善卻沒有任何的投入,因此公眾能夠以低于原始發明人的價格銷售(專利產品)。這使得發明人無法將其發明轉化為資本,導致不會再有發明的社會環境。”[3]國家建立專利制度的目的,是為了通過壟斷權的授予使專利權人獲得適當的經濟回報,以此激勵科學技術的進步[4]。正確認識標準和專利的制度本旨,是科學解決二者關系的重要基礎。
(二)標準與專利的沖突
標準與專利在多重性質上存在根本性的沖突:(1)公益性與私利性的沖突。標準是為了建立某種共同的秩序,以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具有公益性特征。專利是為了保護權利人對特定產品市場的壟斷,以維護權利人私人利益為目的,具有私利性特征。“專利是由政府創造的有價值的財產權[5]。”美國前總統林肯形象又不失中肯地指出,專利就是給天才之火澆上利益之油。(2)開放性與壟斷性的沖突。標準被定義為技術市場的共同語言,推薦甚至強制所有市場主體普遍采用,開放性是標準的最大特征。專利權亦被稱為壟斷權,是禁止壟斷的一種例外,專利權人正是憑借法律賦予的排他性獨享市場利益,因而壟斷性是專利的生命力所在。(3)無償性與有償性的沖突。標準由國家或非營利組織建立,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目的,相關市場主體一般無需支付任何費用即可采用,具有無償性特點。專利則由市場主體自費研發和申獲,自行承擔風險,其他市場主體實施其專利技術需要依法支付報酬④《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12條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他人專利的,應當與專利權人訂立實施許可合同,向專利權人支付專利使用費。”,具有有償性的特征。綜上所述,標準是一種公共產品,專利則是一種私人財產,兩者在法律屬性上存在根本沖突。
(三)標準與專利的融合
正是由于標準與專利在事物屬性上的根本沖突,兩者一旦結合將會產生難以調和的內生矛盾,甚至可能導致相互瓦解,所以標準組織在制定標準時極力避免專利技術的納入,特別是具有強制適用效力的國家強制性標準。國際互聯網工程任務組⑤互聯網工程任務組(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成立于1985年底,是全球互聯網最具權威的技術標準化組織,主要任務是負責互聯網相關技術規范的研發和制定,當前絕大多數國際互聯網技術標準出自IETF。(IETF)曾經認為,為了避免影響人們采用標準的興趣,有必要在制定標準時,盡量采用非專利技術的優秀技術[6]。《國家標準涉及專利的管理規定(暫行)》第14條規定:“強制性國家標準一般不涉及專利。”但是標準和專利也并非沒有任何共性,無論標準還是專利都應當是一種有市場前景的優秀技術,都要服從市場的邏輯。專利自然不必說,新穎性和創造性是所有專利的共同特征,專利代表了技術市場的新潮,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標準雖然不必然具有技術上的引領性,但是如果與市場流行技術差距過大,就無法滿足市場主體對于產品的生產成本、生產效率和市場吸引力的要求,也就不可能有生命力。在市場力量的牽引下,標準和專利雖各自心存芥蒂,但仍不可避免地走到了一起,標準需要專利提供先進技術。在知識經濟的當今時代,知識產權的重要性被提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高新技術成果幾乎全部被專利所覆蓋,而且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迭代發展。如果舍棄專利,在很多高新技術領域,標準要么無現有技術可用,要么只能采用已被市場淘汰的技術。進入21世紀以來,標準開始主動擁抱專利,著眼于解決標準和專利關系問題的法律文件開始越來越多地被創制出來。專利持有人也發現了新的商機,推動將其專利技術納入標準,試圖借用標準的網絡效應和鎖定效應,擴大專利技術收益的寬度和穩定性,甚至延長專利技術的生命周期。“融專利壟斷性與標準排他性為一體的專利標準化,能夠有效利用標準的制定和推廣機制,最大限度地實現專利的技術、經濟與戰略價值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獲取標準越來越成為技術與市場競爭的制高點,標準化已成為專利商業化活動的基本組成部分。”[7]于是,專利和標準的融合不可逆轉地成為了一種發展趨勢[8]。
(四)問題的提出:標準專利違反披露義務的法律責任若何
專利和標準的融合帶來了新的法律問題,主要是標準的實施者在實施標準時,如何應對其中的專利權。根據目前國際上的通行做法,標準化組織在制定標準的過程中,都會要求參與標準制定事宜的組織或個人披露其所持有的與標準有關的專利技術。根據專利持有人在參與標準制定過程中披露義務的履行情況,上述問題可以區分為兩種情形分別加以處理:其一,專利持有人在標準制定過程中已經披露其專利。此時標準實施者在欲實施標準時,應當先行主動與專利持有人進行協商,專利持有人則應當秉持公平、合理、無歧視(FRAND)的原則,共同議定實施范圍、方式、期限和費用等具體問題,并據此簽訂實施許可合同。德國最高法院在飛利浦公司光刻技術標準系列案中提出了著名的“橘皮書標準”,根據該標準,標準實施者避免專利侵權的第一個條件(步驟)就是,“關于專利許可合同的締結過程,必須由標準實施者先向專利權人發出要約,該要約必須無條件且合理。”⑥BGH,GRUR 2009,694 Rn.30-Orange-Book-Standard.相反,如果標準實施者在未與專利持有人接觸的情況下擅自以執行標準的名義實施專利,則構成專利侵權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4條第1款規定:“推薦性國家、行業或者地方標準明示所涉必要專利的信息,被訴侵權人以實施該標準無需專利權人許可為由抗辯不侵犯該專利權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亦有學者認為,專利標準化后即應當視為專利持有人向所有潛在實施者發放了默示許可,標準實施者未通知專利持有人即實施其標準化的專利技術,并不構成專利侵權,只是一個許可合同糾紛問題。這種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具體理由如下文論述的專利持有人未披露其專利技術時不成立默示許可的理由一樣。其二,專利持有人在標準制定過程中未披露其專利。這種情形的處理方法爭議更大,我國法律法規目前對此沒有明確規定,學術界認識不統一,司法實踐中存在相互矛盾的做法。下文將就該種情形的處理方法展開詳細討論。筆者的總體立場是,此時仍不成立默示許可,但應當對專利持有人進行必要的法律制裁。
(五)問題的適用范圍
對標準專利中的標準和專利的范圍,學界認識并不一致。有關標準專利處理方法的爭議,由于所使用的概念含義不統一,很多時候都是在自說自話,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觀點交鋒。所以,首先應當對標準專利進行概念界定。有學者將標準專利中的標準限定為強制性標準,筆者認為做這種限制是沒有必要的,一方面,強制性標準和推薦性標準均為技術標準,兩者在本質上并無不同;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在處理標準專利的許可問題時,并未對兩者進行區分,立法上對兩者的區分在司法中幾乎沒有實際價值。筆者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標準,如無特別說明,包括強制性標準、推薦性標準和標準化指導性技術文件⑧標準化指導性技術文件是為仍處于技術發展過程中(變化快的技術領域)的標準化工作提供指南或信息,供科研、設計、生產、使用和管理等有關人員參考使用而制定的標準文件。比如,政府實施的各種形式的技術推廣項目。。標準中的專利有必要專利和非必要專利之分。必要專利是指實施該項標準必不可少的專利,即一旦實施標準必然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非必要專利是指存在其他平行方案,在實施標準過程中可以避開的專利技術。目前學術界討論的重點集中在標準必要專利。筆者認為,必要專利和非必要專利一旦進入標準,就都取得了標準的品格,所涉及的法律問題并無本質區別,應當一體討論。相當一些專利權人為了借用標準的力量推銷其專利,故意將非必要專利詐稱為必要專利。Goodman和Myers在研究3GPP和3GPP2標準時發現,在7 796項主動披露的必要專利與必要專利申請中,真正必要的專利僅占21%,其余79%均為非必要專利[9]。對于絕大多數標準實施者來說,由于涉及高度復雜的技術判斷問題,花費巨資聘請技術專家對標準專利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在經濟上并不可行[10]。正是由于必要專利與非必要專利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非司法裁判之所長,法院在處理標準專利案件時,鮮有對兩者進行刻意區分的情況。本文中所指的專利包括必要專利和非必要專利。所以,本文中的標準專利是指所有進入標準文件的專利技術。
二、專利默示許可路徑的證偽
如果專利持有人參與了標準制定,但未按照標準化組織的要求披露其專利,致使標準化組織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專利技術納入標準的,有觀點認為,作為對專利持有人違反誠信義務的制裁措施,此時應當認定專利持有人向該標準的所有潛在實施者統一發放了不可撤銷的默示許可,此后專利持有人與標準實施者圍繞標準專利產生的所有糾紛,都應當作為合同糾紛而非侵權糾紛處理[11]。當然,也存在不同觀點:認為這種做法混淆了默示許可和法定許可的界限[12],或者由于許可內容不確定,無法認定合同關系的存在[13]。筆者認為僅因專利持有人在參與標準制定過程中違反披露義務這一事實,尚不足以在專利持有人和潛在的標準實施者之間成立默示許可關系。具體理由如下。
(一)認定默示許可成立,違背了合同關系的法理邏輯
合同法律關系屬于相對法律關系,雙方當事人都是特定的。這與一方特定、相對方不特定的物權等絕對法律關系存在根本不同。這個特征可以稱之為法律關系主體的特定化。這種特定化體現在,合同法律關系成立當時,雙方當事人都是顯在的,而非潛在的,彼此知悉對方的存在。“合同必須在雙方或多方的特定當事人之間產生,不存在只有一方當事人的合同,或者一方當事人特定、另一方當事人不特定的合同。”[14]違反披露義務的標準專利,專利持有人是特定的,但是標準實施者卻是不特定的,故不滿足成立合同關系的主體要求。之所以要求合同關系在成立時,雙方主體都是特定的,彼此知悉對方的存在,更根本的還在于解決后續的合同履行問題。合同義務主要是一種積極作為義務,只有雙方當事人通力協作,合同目的才能順利實現。如果僅因專利持有人違反披露義務,就推定專利默示許可的成立,專利權人將無從知悉誰是自己的合同相對人,從而無法就技術實施提供具體指導,標準實施者同樣難以了解專利持有人的身份情況,無法履行支付專利許可費的義務,更無從確定專利實施的方式、范圍和期限等重要事項。如果在雙方當事人都不了解對方身份信息的情況下推定合同關系成立,結果只能是從合同關系成立伊始,雙方均陷于因合同義務不履行的違約狀態,這種結果是不可接受的。再者,合同關系的成立一般要經過要約承諾程序達成合意[15],而且要約承諾應當以通知或行為的方式告知對方。僅違反披露義務的情況下,無從分析出要約和承諾的存在,更談不上將要約或承諾的意思送達對方。所以,僅憑違反披露義務就認定專利持有人和標準實施者之間存在默示許可合同關系,既不符合合同關系的法理邏輯,也不符合合同關系的生活邏輯。
有學者提出,此時之所以不能成立默示許可,是因為許可對價、范圍和具體內容無法確定,難以形成清晰的許可合同關系[16]。筆者認為這種考慮雖然不無道理,但尚不能達到影響合同關系成立的地步。除當事人特定這一基本要求外,合同關系的成立還要求就交易內容達成合意。學界公認,基于鼓勵交易的精神,合同成立所需要的合意,除非當事人有特別約定,只需要就主要條款達成合意即為滿足,無需就所有交易條件全部達成一致[17]。至于何謂主要條款,不同類型的合同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一般認為具備了當事人、標的和數量條款即為已足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1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是否成立存在爭議,人民法院能夠確定當事人名稱或者姓名、標的和數量的,一般應當認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對合同欠缺的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內容,當事人達不成協議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61條、第62條、第125條等有關規定予以確定。”,其他條款可以通過合同解釋的方法進行彌補。對專利默示許可合同而言,除了前文要求的當事人特定外,主要條款就是所許可的具體專利本身,至于許可對價、范圍、地域等內容并不屬于必備條款,這些條款雖為合同履行所必要,但是具有通過合同解釋的方法得以確定的可能。納入標準的專利就已經同時滿足了標的(哪項專利)和數量(就是這項專利)的要求,默示許可合同關系所需要的除主體之外的條款已經得到滿足。所以,將缺乏對默示許可合同具體內容的合意作為否定默示許可成立的理由,與法律規定和學界共識是相悖的。
(二)認定合同關系成立,將導致標準專利的“反向劫持”
“專利劫持”是專利制度負面效應的表現之一。“專利劫持”這一概念最早是由Mark A.Lemely教授和Carl Shapiro教授提出來的,他們認為所謂“專利劫持”是指專利權人以侵權訴訟和禁令救濟相威脅,通過協商從專利使用人處獲得高于基準的專利許可費率的行為[18]。這種過度收取專利權使用費的行為如同在含有專利技術的新產品上征稅,不但不利于反而是阻礙了創新[19]。標準化組織在標準制定過程中之所以要求披露專利信息,就在于避免專利權人利用標準的鎖定效應及其“潛水艇”專利⑩所謂“潛水艇”專利是指,在一些專利申請中,基于特定的目的,利用專利受理和審批的過程,控制專利公開或授權的時機的專利。,向標準實施者收取不合理的專利許可費,進行“專利劫持”。雖然采用標準專利組織制定的標準在理論上是“自愿”的,實際上市場的壓力在相當程度上導致強制性采用標準。一些標準,例如:802.11無線局域網標準的實施,即使只是產品中的一小部分,對產品的商業生存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標準的實施對于市場競爭而言是必要的,標準必要專利的持有人往往能夠從專利實施者中收取高于實際市場價值的許可費。這種技術增加價值與最終許可費之間的差距就是“專利劫持”的核心[20]。在現行專利體制下,專利權人擁有強制禁令,強制禁令的威脅可以使專利權人就遠遠超出專利權人實際經濟貢獻的專利費進行談判[21]。在一些專利密集型產業,“專利叢林”與禁令救濟的結合,還導致了許可費疊加效應,極大加重了專利使用人乃至整個行業的經濟負擔。“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可能借助專利權的排他獨占性和標準所形成的影響力疊加效應,利用市場支配地位優勢排除或限制競爭,對技術市場競爭秩序造成危害。”[22]毫無疑問,“專利劫持”行為應當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如果以阻卻“專利劫持”為由,簡單粗暴地對所有違反披露義務的專利持有人一起認定,構成對潛在標準實施者的默示許可,則可能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形成專利使用人(標準專利實施者)對專利權人的“反向劫持”。
所謂標準專利的“反向劫持”,是指標準實施者未經專利權人許可持續實施專利,而在必要專利權人要求協商時,又以許可條件無法達成一致為借口,采取拒絕協商、拒絕接受FRAND許可、提起虛假訴訟等手段,意圖以低于合理費率的價格獲得專利許可的行為[23]。僅因專利納入標準而認定默示許可成立,對專利權人來講最嚴重的后果莫過于排除禁令救濟。禁令救濟是專利保護的核心權利,是專利權人獲得專利收益的可靠保障,對于補償專利權人研發投資、鼓勵技術創新具有重要意義[24]。禁令救濟原則上僅適用于專利侵權訴訟,默示許可的成立即意味著在專利權人與專利使用人之間存在正當的許可合同關系,專利權人能夠行使的救濟權只能是損害賠償。損害賠償給專利使用人形成的訴訟壓力要遠遠小于禁令救濟,因為即使專利權人勝訴,法院判賠的往往也就是正常水平的許可費,甚至可能低于正常許可費率,使用人并不會因此受損。在季強、劉輝訴朝陽市興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專利侵權糾紛一案?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2007)遼民四知終字第126號民事判決書。中,最高人民法院復函認為,未披露專利信息的標準專利成立專利默示許可,標準實施者應當支付的許可使用費數額應當明顯低于正常的許可費率?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三他字第4號復函。。在專利權人起訴13.5萬元賠償額的情況下,遼寧省高院根據前述復函精神僅支持了4萬元。加之訴訟結果的不確定性,專利使用人在損害賠償訴訟中受到的壓力幾乎等同于雙方私下談判的正常壓力水平。“反向劫持”將會導致專利許可費率市場談判機制的失靈,抑制標準專利權人將先進技術納入標準乃至進行創新的積極性,最終損害社會公共福利[25]。
(三)我國走過的曲折實踐歷程證明,成立默示許可不可取
在標準專利的默示許可問題上,我國司法實踐走過了一段曲折的歷程。大體的情況是,在專利默示許可概念提出的早期,也就是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期間,人民法院傾向于認定標準專利成立默示許可,并不過問標準化組織是否要求過專利權人披露專利信息,甚至都不關心專利權人是否參與過標準的制定。前文述及的季強、劉輝訴朝陽市興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專利侵權糾紛一案,是我國標準專利成立默示許可的第一個案件,由于缺乏可適用的法律和先例,處理該案的遼寧省高院是在請示了最高人民法院之后才作出判決。在該案中,專利權人并未參與案涉標準的制定,但是僅憑其專利被標準化組織單方面納入標準這一事實,法院就判定默示許可成立,且權利人可得的許可費明顯低于正常水平。另一起案件是2009年的優凝公司訴河海公司等侵犯專利權糾紛案[26],該案被江蘇省高院列入2009年江蘇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例。在該案中,原告優凝公司擁有的案涉“擋土塊”發明專利被納入水利部“948”科技推廣項目,被告河海公司等在隸屬于“948”科技推廣項目項下的泰州市翻身河綜合整治工程中使用了原告專利,法院認定默示許可成立,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三他字第4號復函的精神判處了3萬元的使用費。與前一個案例不同的是,后一個案例中專利權人曾經參與了“948”科技推廣項目的制定和實施。但是這兩個案例中,標準制定組織均未提出專利披露要求,所以未披露專利不能歸咎于專利權人。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期間,人民法院審理標準專利案件的觀念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基本確定僅憑專利被納入標準這一個事實,不足以成立默示許可。這一時期有兩個標志性案件,一個是“張晶廷訴子牙河公司等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25號民事判決書。,另一個是“農大公司訴中西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終382號民事判決書。。前者確立了在已經披露專利信息的條件下不成立默示許可,后者確立了即使未披露專利信息仍不成立默示許可。這兩個案件均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可以視為形成了我國司法機關有關標準專利默示許可問題的最終裁判標準。前一個案件的審判過程頗為曲折。原告張晶廷的專利于2008年被納入河北省推薦性地方標準,并在標準文件的前言部分明確記載了需要識別的專利技術以及專利權人的聯系方式。被告子牙河公司等在未與原告進行任何接觸的情況下,以執行標準的名義實施了原告的專利技術,原告起訴被告專利侵權。石家莊市中院一審認為,案涉標準屬公開有償使用的技術,被告未經專利權人許可擅自使用,侵害了原告的專利權。被告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河北省高院二審認為,原告將其專利納入標準的行為,應認為許可他人在實施標準的同時實施該專利,被告的行為不構成專利侵權。原告不服二審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認為,在標準文件中已經披露了專利信息且被告能夠與原告取得聯系的情況下,被告未經許可擅自實施案涉專利的行為構成專利侵權。后一個案件中,原告農大公司的專利被納入推薦性國家農業行業標準,原告參與了該標準的制定,但是未披露其專利信息,被告中西公司以執行標準的名義實施了原告的專利,被告認為原告違反信息披露義務的行為導致其專利被默示許可,被告的行為不構成侵權。一、二審法院均駁回了原告對于默示許可的主張,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專利權人編制標準時未披露標準必要專利信息的,尚不足以構成標準必要專利默示許可的充分理由。
我國人民法院在標準專利默示許可問題上的演進思路非常清晰,即由最初的只要專利納入標準,無論專利權人是否參與、是否披露,均成立默示許可;到只要專利權人參與了技術標準的制定,無論是否披露了專利信息,均構成專利默示許可;再到專利權人參與技術標準制定,但是披露了專利信息的,不構成專利默示許可;最后到專利權人參與標準制定,即使未披露專利信息,仍不構成專利默示許可。上述四個案例分別代表了這四個發展階段。以上司法實踐歷程可謂“一波四折”,最終形成我國在專利默示許可問題上的裁判標準,即單純基于未披露專利信息這一個事實,不足以成立專利默示許可。誠如霍姆斯大法官所言,歷史研究之一頁,當抵邏輯分析之一卷?New York Trust Co.v.Eisner,256 U.S.345,349(1921).。在理論紛爭莫衷一是之時,傾心聽取司法實踐的教益,實為推動法律進步的不二選擇。
三、保守式規制策略:視使用人主觀心態區別對待
(一)反壟斷法規制無法解決違反披露義務問題
對于專利權人在專利標準化過程中違反披露義務的行為,學者們提出了多種解決方案,其中最常見的提議莫過于專利默示許可與反壟斷法規制[27]。前文已經述及,僅違反披露義務,并不符合專利默示許可的成立條件,所以默示許可這一條道路行不通。反壟斷法規制這條道路同樣行不通。反壟斷法的適用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規制對象必須在相關市場具有支配地位,二是規制對象濫用了該支配地位。正如德國法官在“華為訴中興案”中所指出的,擁有標準必要專利這一事實本身并不必然構成相關市場的支配地位,法院應當在事實基礎上對此進行個案判斷?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Press Release No 155/14,20 November 2014.。“反壟斷抗辯的軟肋在于,并不是所有的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都在相關市場擁有支配地位。因此,對于一部分可能不具有相關市場支配地位的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而言,反壟斷抗辯并不對他們適用[28]。”同時,即使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如果其肯遵循FRAND原則,也不構成對市場支配地位的濫用,從而也不適用反壟斷法規制。當然,如果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在違反披露義務后,又借助標準必要專利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則有可能違反反壟斷法,但此時反壟斷法所規制的也僅是其濫用標準必要專利的行為,而不是違反披露義務不當獲得標準專利的行為。換句話說,無論標準專利權人是否違反了披露義務,只要其濫用專利權的行為違反了反壟斷法,均可以且應當適用反壟斷法進行規制。所以,反壟斷法規制同樣不適于解決僅違反披露義務的問題。
(二)違反披露義務應當進行法律制裁
筆者認為,專利權人違反信息披露義務致使其專利被納入標準,試圖利用標準的“鎖定效應”和“網絡效應?“網絡效應”是指是指產品價值隨著購買這種產品及其兼容產品的消費者的數量增加而不斷增加。參見ECONOMIDES N.The economicsof network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96年第14卷,第2期。”獲得正常條件下難以獲得的專利收益,即使在事后發生的專利訴訟中其向標準實施者提出了FRAND許可條件,也不能視為是專利權的正當行使行為,應當對其進行相應的法律制裁。這是因為,其一,幾乎所有的標準制定組織都有對標準所涉專利進行披露的明確要求?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和國際電信聯盟(ITU)2005年制定的共同專利政策,標準化組織應盡量披露標準中涉及的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的全部信息;標準化組織應提請所有利益相關方注意標準中可能涉及的任何已知專利或待批專利,及時反饋給標準制定組織。三大組織在2007年發布的共同專利政策實施指南中進一步強調參與標準制定的各方從一開始就應提請標準制定組織注意任何已知的或可能的專利。,披露義務業已成為業界公認的行為準則,已經構成了一項習慣法,違反法律義務的行為當然應當受到法律的制裁。Mueller提出:“任何參與制定行業標準并隨后獲得該標準某些方面專利權的公司,至少必須披露可能與該標準相關的任何專利或未決專利申請的存在。”[29];其二,違反披露義務的行為,致使標準制定組織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喪失了及時尋找替代方案和對專利權進行處置的機會,導致了對專利技術的依賴以及被禁用后損失的擴大[30];其三,違反披露義務的行為多出于故意,通過損害標準實施者獲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意圖明顯,法律不能縱容惡意的存在,更不能助其實現;其四,《國家標準涉及專利的管理規定(暫行)》明確規定,違反披露義務的組織或個人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國家標準涉及專利的管理規定(暫行)》第5條規定:“在國家標準制修訂的任何階段,參與標準制修訂的組織或者個人應當盡早向相關全國專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或者歸口單位披露其擁有和知悉的必要專利,同時提供有關專利信息及相應證明材料,并對所提供證明材料的真實性負責。參與標準制定的組織或者個人未按要求披露其擁有的專利,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關于對違反披露義務專利權人的制裁方法,基于當下我國專利制度的實際,結合國外司法實踐中的經驗,可以劃分為保守式規制策略和激進式規制策略兩個階段梯次進行。
(三)現行專利法框架內的法律規制策略
所謂保守式規制策略,是指在不對現行專利法進行修改的條件下,在現行專利法所提供的制度框架內,對違反披露義務的專利權人的制裁方法。對專利權人進行制裁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維護標準專利使用人的利益,更是為了維護國家的標準實施秩序,因此同樣需要考慮使用人的主觀心態。具體來講,也就是要區分使用人為善意和惡意兩種情形分別做出處理。
1.使用人為惡意時的規制方法
如果使用人為惡意,也就是說使用人明知標準為他人專利所覆蓋而仍然擅自實施專利,或者使用人在實施專利時根本不知道該專利已經納入技術標準的事實,專利的標準化對使用人的實施行為并未產生實際影響,此時使用人擅自實施專利的行為應當認定為一般意義上的專利侵權行為,專利權人可以主張專利法給予的全部救濟權利,也就是其既可以主張損害賠償,又可以主張禁令救濟,甚至還可以主張懲罰性賠償。在前述農大公司訴中西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中,農大公司的專利技術被納入技術標準,但農大公司在參與標準制定過程中并未披露其專利信息,中西公司據此對其未經許可的實施行為提出了默示許可抗辯。最高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雖然農大公司在專利標準化過程中未披露其專利,但是中西公司對標準中存在農大公司的專利是明知的,在未與專利權人先行協商即直接實施的情況下,中西公司的主觀過錯較為明顯,遂判定中西公司停止侵權行為并賠償農大公司的經濟損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指出,即使被告所進行的是實施標準的行為,在被告明知專利權存在的情況下,專利權人仍可以主張禁令救濟和損害賠償。
2.使用人為善意時的規制方法
如果使用人為善意,也就是說使用人的實施行為是依據標準的行為且不知道該標準為他人專利所覆蓋,為了應對專利權人利用標準可能進行的“專利劫持”,此時僅應當對專利權人提供損害賠償救濟,不提供禁令救濟。在我國專利法上,在發生專利侵權的情況下,提供禁令救濟并不是必然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如果提供禁令救濟會造成當事人之間利益關系的重大失衡,人民法院在提供有效的損害賠償救濟的前提下,也可以不提供禁令救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產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5條規定:“充分發揮停止侵害的救濟作用,妥善適用停止侵害責任……如果停止有關行為會造成當事人之間的重大利益失衡,或者有悖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實際上無法執行,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進行利益衡量,不判決停止行為,而采取更充分的賠償或者經濟補償等替代性措施了斷糾紛。”。基于標準的開放性和公益性,在權利人違反披露義務且使用人不知道標準中存在專利的情況下,使用人依據標準的實施行為具有正當性,如果此時給權利人提供禁令救濟,必然造成權利人和使用人之間利益關系的重大失衡,所以依法不應當為權利人提供禁令救濟。“制定標準是為了推廣標準的適用,而非讓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處于壟斷地位,如果允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像一般專利權人那樣可以不加限制地提起禁令請求,而執法機關亦可以輕易對未經許可使用標準必要專利的實施者責以停止侵權責任,則相當于排除了對標準的適用,這與標準制定的目的背道而馳。”[31]但是我國現行法律并未規定此時可以免于承擔賠償責任,因此權利人仍有權獲得損害賠償救濟。
四、激進式規制策略:專利不可執行制度的引入
(一)現行專利制度無法有效解決違反披露義務問題
所謂激進式規制策略,是指通過修改現行專利法引入新制度的方式,構建與違反專利披露義務相適應的法律責任。違反披露義務的行為,構成了對標準制定組織和其他標準實施者的欺詐,是一種嚴重違反誠信的行為。權利人在此基礎上主張專利權,實為陷阱性行權行為,嚴重侵害了標準實施者的利益,構成對專利權的濫用。專利權濫用屬于民法上民事權利濫用的范疇,應當適用制止權利濫用的一般方法對其進行規制。在權利濫用的目的范圍內,否認權利濫用者的權利,或者不對其提供救濟,是規制權利濫用的一般方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總則編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第3款規定:“構成濫用民事權利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濫用行為不發生相應的法律效力。”。在現行專利法搭建的制度框架內,對于違反披露義務的專利權人,至多只能拒絕對其提供禁令救濟,但是尚沒有理據能夠否定其損害賠償請求。很多時候,違反披露義務的專利權人對標準專利的實施者雖然同時提出禁令救濟和損害賠償,但其真正目的并非禁止標準實施者實施其專利,而是意圖以禁令救濟為脅迫手段,在更大范圍內和更大程度上獲得賠償,因為在其參與標準制定過程中其已經預期到專利可能在更大范圍內被實施,這一點正是其所追求的,特別是在專利權人為專利非實施主體(Non-Practicing Entity,NPE)的情況下,這一點體現得尤其充分。“對NPE而言,禁令的目的不在于市場本身,而只是確保談判籌碼的手段。金錢賠償(無論是通過損害賠償還是禁令壓力下的和解)才是整個訴訟的目的。”[32]如果不能拒絕專利權人的損害賠償請求,即使不給予其禁令救濟,專利權人通過標準專利濫用專利權的目的也就達到了,這種做法顯然違反了民法上制止權利濫用的一般原理,實質上縱容了專利權濫用行為。故在現行專利法提供的制度框架內,無法圓滿解決違反披露義務的權利濫用問題,需要進行制度上的創新。
(二)標準制定組織自身難以解決違反披露義務問題
有觀點認為,可以通過標準制定組織來制止違反披露義務的行為。該觀點立論的基礎是:“專利權人的披露義務是基于標準化組織的知識產權政策而生,其法律屬性為基于合同而生的合同義務。”[33]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及其立論基礎均不能成立。首先,各標準制定組織雖然都制定了專利披露政策,但是對于拒不進行專利披露的行為也同樣都采取了“不干涉”政策[34],即使根據《國家標準涉及專利的管理規定(暫行)》的規定,也只是暫停實施和修訂所涉標準,而不對違反披露義務給標準實施者造成的損害進行任何處理。暫停實施和修訂標準并非總能做到,因為有時標準中的專利技術在市場上并無替代技術可以選用,或者有時所涉標準已經施行很長一段時間,標準本身已經成為了技術市場中的事實標準,并非通過法律措施可以清除。“然而,采用標準后,一旦企業已經致力于該標準,并對制造和銷售標準化產品進行了互補性資本的必要投資,此時轉換到另一種標準將不可行。”?這“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該行業在實施該(專利化)標準時,已經進行了投資,產品可能已經設計符合了該標準,而且工廠已經積極地生產該專利標準化的產品,這時,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些成本往往是‘沉沒成本’(無法收回的成本)。第二,對于兼容性的需求或要求會使轉換到不同標準的成本變得很昂貴(特別是對現有安裝的產品生產基地的逆向兼容)。第三,同樣,在使所有利益方轉換到一種替代標準時,往往會出現所有利益方的協調問題。例如,計算機制造商可能已經設計了具有符合現有標準的芯片的主板和電腦。那么轉換到不同的芯片設計時,將不僅需要芯片自身的改變,還需要主板和計算機的改變,進行協商改變的難度將使得從專利化標準進行轉換不切實際。”參見衛·蒂斯.技術秘密與知識產權的轉讓與許可——解讀當代世界的跨國企業。王玉茂,彭潔,李莎,等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年。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違反披露義務所引發的標準專利糾紛,并不是標準制定組織和專利權人之間的糾紛,而是專利權人和標準實施者之間的民事糾紛。對于該類糾紛,標準制定組織作為民間自治組織或法律授權的行政管理組織,并沒有法律上的主管權,最終還得通過司法機關進行解決。而司法機關解決該類糾紛主要適用專利法的規定,所以修改完善專利法的相關規定,也就成為了不可回避的主要應對手段。最后,披露義務不僅來自于專利權人與標準化組織之間的合同關系,更來自于國家標準化法律法規所規定的面向社會公眾的一般注意義務。違反該義務,未必給標準化組織造成實質性損害,但是一定會誤導以社會公眾面貌示人的標準實施者并給其造成實質性損害。違反披露義務的行為,損害了公平競爭,侵犯了社會公共利益[35]。故主要從標準實施者而非標準化組織的視角,對違反披露義務的行為進行規制,始符合生活邏輯。
(三)我國禁止專利權濫用制度的執行機制存在不足
我國2020年新修正的專利法增加了誠實信用原則和禁止專利權濫用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2020年)》第20條規定:“申請專利和行使專利權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濫用專利權損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濫用專利權,排除或者限制競爭,構成壟斷行為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處理。”,但是并沒有建立起相應的配套執行機制。專利法只是明確對構成壟斷行為的專利權濫用行為,按照《反壟斷法》進行處理,但是并未規定對于不構成壟斷行為的專利權濫用行為的處理方法。專利權濫用的概念比濫用專利權實施壟斷的概念大得多。濫用專利權實施壟斷行為的認定,要求專利權人在相關市場具有支配地位,濫用了該支配地位,并形成了反競爭效應。“要想證明存在專利濫用問題的專利權人同時也違反了反壟斷法,需要證明‘更多’:除了濫用的事實之外,還必須有證據顯示在相關市場上的影響力以及反競爭效應。”[36]一般意義上的專利權濫用行為并不符合壟斷行為的上述要求,因而無法通過《反壟斷法》進行規制。“專利濫用與反壟斷法是不同的,因此沒有必要為了證明專利濫用而確立行為對反壟斷法的違反。”[37]同時,即使針對濫用專利的壟斷行為,根據《反壟斷法》的規定,也只能對專利權人進行相應的行政處罰,無法在民事案件中否定專利權人的侵權請求權,同樣難以對違反披露義務的行為進行有效制止。故構建獨立于反壟斷法的專利權濫用法律責任制度,已經成為落實新修正的《專利法》第20條的規定,有效維護公共利益和專利使用人合法權益的不二選擇。
(四)不可執行是落實禁止專利權濫用制度的有效手段
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有關規制專利權濫用的立法比較成熟,司法實務經驗比較豐富,可以作為完善我國反專利濫用制度的借鑒。專利權濫用行為包括了一切超越專利法立法目的不正當行使專利權的行為,因而極為寬泛和多樣。“專利權濫用(抗辯)是一種無定性的法律原則[5]”,一般將其理解為“獨立于反壟斷法的限制專利權濫用的方法。”?B.Braun Med.v.Abbott Labs.,124 F.3d 1419,1426(Fed.Cir.1997).Chisum教授指出,在專利濫用領域,缺乏清楚及具有普遍性的理論來判斷什么樣的實踐行為才應當被視為專利權人對其法定專利權的妥善行使[38]。“盡管法院通常認為濫用法則關涉通過知識產權許可和其他安排取得專利權或版權‘范圍之外的’權利,但該法則缺乏一套用于判斷哪些行為應受譴責以及根據什么理由譴責的統一準則。”[39]Merges教授對此回應,由于專利權濫用是基于衡平法的原則,衡平的特性就是多少有些“混亂”,因此缺乏清楚的標準也不會令人感到意外[40]。雖然在美國專利法上專利權濫用的判定標準和邊界并不是特別清晰,但根據《美國專利法》第282條(b)款(1)項的規定,專利權濫用的法律后果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在權利人濫用意圖的范圍內,權利人的專利權不可執行。所謂專利權不可執行,指的是在特定條件下不向專利權人就其所指控的他人的專利侵權行為提供任何意義上的法律救濟,既不授予禁令,也不支持賠償。“根據有關的判例,如果被告能夠證明專利權濫用,專利權人將不能獲得法律救濟,直到專利權人停止相關的行為。而且,即使被告沒有受到濫用行為的傷害,也可以因此不承擔法律責任。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專利權濫用成了被告在專利侵權訴訟中經常提起的辯解。”[41]“第一,正如Morton Salt一案?Morton Salt v.G.S.Suppiger Co.314 U.S.488(1942).,專利權人的濫用過失使得他們無權主張損害賠償,也無權主張禁止令。第二,對專利權的濫用導致整個專利對侵權人失去強制執行力,即使在濫用和侵權行為之間沒有任何聯系也是如此。在濫用停止并且消除影響之前,專利權濫用會使專利侵權訴訟成為不可能。”[42]
(五)專利不可執行制度能夠融入我國民事法律體系
針對專利權濫用行為,引入專利不可執行制度,完全能夠融入我國的民法體系。專利權濫用屬于民事權利濫用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針對民事權利濫用行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總則編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第2款、第3款規定:“行為人以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權益為主要目的行使民事權利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構成濫用民事權利。構成濫用民事權利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濫用行為不發生相應的法律效力。”在標準專利權人違反披露義務從而構成專利權濫用的情況下,權利人的主要目的并非實現其專利的正當經濟價值,而是將專利作為劫持他人的工具,獲得遠超正常許可費的超額利潤,從而必將直接損害標準實施者利益,并會通過標準實施者的傳導間接損害社會公眾的利益。“承認私權之根據,乃在于私權系社會共同生活之向上及發展所不可或缺之要件,行使私權,絕未可忘卻私權之社會性格。本此理念,解釋‘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絕不能僅解為‘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或僅指損人不利己而言。若行使其權利之結果,自己雖獲有利益,惟他人亦受有損害,則應比較兩者之利益或害惡孰大,若自己所獲利益,多于他人之損害,即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反之,若自己行使權利之結果,自己雖不無利益,然對他人所造成之損害實甚于此,不管其對象為對造或其他多數人,均構成權利濫用。”[43]標準專利權人違反披露義務時,通過對標準實施者進行“專利劫持”所獲收益,一般會遠超標準實施者應當支付的許可費數額,主觀上損害他人目的明顯,客觀上所獲利益大于他人所受損害,構成權利濫用應屬無疑。剝奪權利濫用者的權利,或者使濫用權利者達不到所希望的法律后果,就是構成權利濫用行為的法律后果[44]。針對專利權濫用行為,引入專利不可執行制度,完全符合我國的民法理論邏輯,亦具有堅實的實定法基礎。相反,在構成專利權濫用的情況下,若仍然支持權利人的主張,甚或只支持其損害賠償的主張,將會違背我國民法的規定和民事法律邏輯。
(六)不可執行是標準專利違反披露義務的法律后果
2008年,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CAFC)判決的高通訴博通案?Qualcomm Incorporated v.Broadcom Corp.,548 F.3d 1004(Fed.Cir.2008).,是專利權人在專利標準化過程中違反披露義務,致使其專利被判決不可執行的一個典型案例。在該案中,法院認定高通通過欺詐標準制定組織JVT(Joint Video Team)的方式,致使其兩項專利被納入JVT制定的技術標準H.264中。博通根據H.264標準制造相關產品,高通遂起訴博通侵犯其專利權。CAFC最終判決高通的專利在實施H.264標準范圍內不可執行,駁回了其對博通的全部訴訟請求。早些時期由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處理的Dell案,代表了美國政府對違反披露義務的標準專利權人的基本立場。1991年,Dell公司獲得了一項有關VL-bus計算機總線方面的專利。1994年,Dell參加了由標準制定組織VESA?VESA(Video Electronics Standards Association,聲頻電子標準聯合會),是一個由美國主要硬件和軟件商組成的非營利性標準制定組織。主持的標準制定工作,標準提案中包含了Dell的VL-bus專利。VESA要求參與標準制定的公司申報標準提案中所涉及的專利,Dell公司的代表兩次書面保證:“據我所知,關于VL總線標準的提案并沒有侵犯Dell公司任何專利權。”該標準非常受市場歡迎,在標準發布后的8個月內,運用該標準生產的電腦的銷量就突破了140萬臺。隨后,Dell公司突然通知實施該標準的電腦制造商侵犯了其VL-bus專利,并要求支付專利使用費。各電腦制造商聯合向FTC提出仲裁請求。1996年6月,FTC認定Dell公司在標準制定過程中違反誠信原則,違反標準制定組織的內部規定性文件,未能在知識產權權利披露的前置階段披露有關的專利技術,卻在事后主張其自己知道的專利權,這種行為是對標準制定組織工作的誤導,構成專利權濫用,并最終以4∶1的裁決結果否決了Dell收取專利使用費的權利主張[45]。通過以上兩個案件可以看出,在美國專利法上標準專利權人違反披露義務的行為,構成專利權濫用,所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是其專利權不可執行。但是需要申明的是,專利不可執行遵循一事一議規則,并非一旦認定權利濫用專利在所有情形下均對世不可執行。例如,在前文提到的高通訴博通案中,一審法院以違反標準專利的披露義務為由,判決高通公司的案涉專利對世不可執行,但CAFC在二審中對此予以改判,僅判決高通公司的專利在執行標準的范圍內不可執行,這就大大縮小了高通公司的法律責任范圍[46]。
結 語
專利不可執行在美國專利法上是一項獨立的制度,是一種重要的侵權抗辯事由,它來源于衡平法上的“不潔之手”原則(doctrine of“unclean of hands”)。“不潔之手”原則要求原告在出庭之前,必須首先表明他不僅有一個良好的、值得稱贊的行動理由,而且他必須以干凈的雙手進入法庭?Keystone Driller Co.v.General Excavator Co.290 U.S.241-244(1933).。若其先前的行為違反了良心、善意或其他公平原則,那么,法院的大門將對他關閉,拒絕給予任何救濟。該原則被廣泛應用于涉及欺詐的民事案件[47]。違反披露義務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民事欺詐行為,顯然也違反了“不潔之手”原則,故其專利權不可執行。專利不可執行的原因不限于專利權濫用行為,還包括不正當申請行為?不正當申請行為抗辯是指,如果一項專利是通過對專利局作出不當行為獲得的,則法院應當拒絕執行該專利。、申請歷史懈怠?申請歷史懈怠是指,專利權人通過不合理地延長其在專利局的申請過程中所花費的時間,來不適當地延遲該專利的授權。等有違“不潔之手”原則的行為。專利不可執行制度調和了專利權保護與禁止權利濫用之間的緊張關系,有效平衡了專利權人和專利使用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我國2020年的《專利法》修正案引入了專利權濫用的概念,確立了制止專利權濫用的價值目標,但是未能建構起完整的配套制度體系,禁止專利權濫用制度未能真正落地實施。引入專利不可執行制度,不但能夠有效解決標準專利權人違反披露義務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還可以使專利法新引入的制止專利權濫用制度得到切實執行。
- 科技與法律的其它文章
- Calculation Rulesof the Baseand Multipleof Punitive Damage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 Do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Pilot Policy Promote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y?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 多源異構視域下基于區塊鏈的知識產權協同管理模式研究
- 地方科技立法中法律責任比較研究
- 數字經濟時代個人信息合理處理制度研究
- 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數額確定規則實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