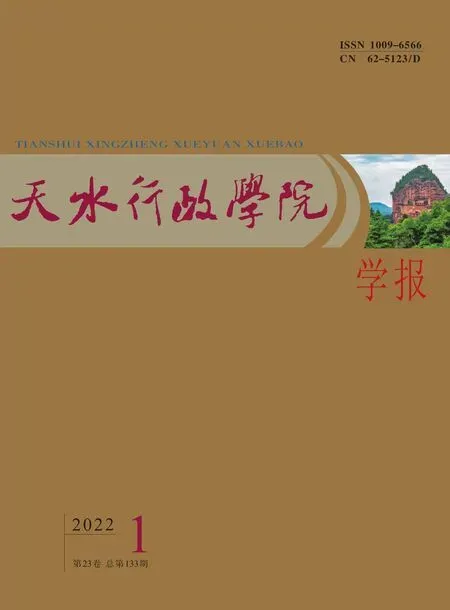多源流理論視角下三孩政策的議程設定分析
施清雯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上海 201620)
受20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背景下嚴格人口管控政策的影響,我國民眾的生育意愿減弱,生育率持續走低,出現了少子化、人口老齡化等問題。為了鼓勵生育,增加人口活力同時緩解老齡化,國家先后出臺了許多政策,放開生育管控。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正式出臺三孩政策,即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措施。三孩政策的政策之窗是如何打開、政策議程是如何被最終建立起來的過程值得我們探討,而金登的多源流理論模型闡述了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以及三者耦合、政策之窗開啟的過程,可以幫助研究政策議程設立。
一、文獻綜述
(一)生育政策研究現狀
國外關于人口及生育研究的代表理論包括馬爾薩斯人口論、近代社會學派、生物學派和數理學派人口理論、當代西方人口增長控制學說、當代西方生育經濟學說等。一般而言,立足梳理和分析本國生育政策的學者居多,沃爾夫斯特岡介紹了德國的人口生育政策,理查德·利特闡述了新加坡的人口生育政策的變化。也有學者從比較研究的視角研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生育政策,桑德拉·蘇亞雷斯基于經濟全球化的背景比較了愛爾蘭和新加坡的生育政策,認為生育政策由三個政治變量形成:主導黨鞏固、國家建設和利益集團政治。對于老齡化帶來的問題以及對人口生育政策的影響,日本學者Kojima H通過實證調研分析,闡述了間接生育政策和綜合家庭政策在提高生育率方面比人口政策更有效。此外,學者們也會將生育政策與難民政策、性別平等和社會保障等議題聯系起來,例如凱瑟琳·H·特尼斯和雷切爾·蘇利文·羅賓遜重點關注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的生育政策和難民政策;韓國學者宋多英從兩性平等角度評價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社會計劃和替代戰略,為韓國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性別平等低生育率政策的方向和詳細的替代方案;尼古拉斯·庫達契爾等人從社會保障改革角度討論了中國的人口生育政策。
國內學者對于人口生育政策的研究,可以分為三孩政策出臺前和出臺后。在三孩政策之前,學術界主要討論的大多是對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反思和探討二孩政策的影響。石智雷分析了計劃生育政策對我國家庭發展能力的影響,認為其限制了家庭生育選擇的權利并且改變了我國的家庭結構。徐俊由“單獨二孩”政策反思了計劃生育帶來的影響及我國為之付出的社會代價。石人炳和陳寧對我國生育政策的調整做出了評估,認為“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雖然從短期看有明顯的效果,但中長期而言還是無法滿足我國人口發展的需求。三孩政策出臺后,學術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其社會影響,以及闡述如何加強三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劉中一提出要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應該結合實際情況建立健全相應的實現機制。王軍和李向梅認為三孩政策下民眾生育意愿很可能繼續下行,主張需要盡早考慮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并擇機實行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張翼通過分析未來生育率變化趨勢,設計了短期防止生育率繼續下滑、中期維持并波動提升生育率、長期旨在建構生育友好型社會這三個制度紅利的釋放目標。
(二)研究述評
國內外學術界對于人口生育政策的文獻研究卷帙浩繁,從嚴格把控人口數量的計劃生育政策到現如今相對寬松的生育政策都做了詳盡的研究,然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這些研究中針對生育政策的文獻大多數是從整個國家的較為宏觀的角度出發的,但結合具體的地區、嵌入具體的社會文化環境情境的研究不多。其次針對生育政策實施后的影響的研究較多,即政策評估型的文獻占主體,而探討政策議程是如何被建立起來的研究較少。尤其是三孩政策出臺后,研究成果基本上無外乎是對其社會影響的評價,以及分析如何加強配套措施等,基本沒有對三孩政策的政策過程前端的研究。
本文運用多源流模型剖析三孩政策的議程設立過程的研究意義在于,一是由于多源流理論模型起源于西方,在我國學術界被用來剖析生育政策的非常有限。二是學術界研究人口生育政策多從經濟學、人口學的角度切入,用社會學和公共政策學等相關理論視角分析的研究很少。本文涉及了對政策出臺前的社會文化環境、政策背景、政治與經濟環境的描述和說明,嵌入多源流理論分析三孩政策的議程設立,彌補了學術界對生育政策的政策過程前端研究的不足。
二、多源流模型:政策議程的分析框架
1951年拉斯韋爾在《政策科學》一書中提出政策科學的概念后,公共政策分析慢慢進入到人們的視野。多源流模型是由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約翰·金登教授于1995年在其名為《議程、備選方案與公共政策》一書中提出的著名理論模型,該模型旨在回答一個社會問題為什么會被決策者關注、決策是如何被制定出來的,以及一項政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終結等一系列問題,對于政策過程的研究發展有著深刻的意義。
(一)理論淵源:對垃圾桶模型的修正
1972年邁克爾·科恩、詹姆斯·馬奇和約翰·奧爾森等人提出了“組織選擇的垃圾桶模型”,該模型假設:在組織化的無序狀態下,問題、解決方案、參與者和選擇機會四大源流獨立地流入組織結構。這個組織結構又受到凈能量承載量、進入結構、決策結構和能量分布四個變量的影響。因此時間段、決策方案數、源流經過四大變量的篩選、匯聚,最后產生決策結果。金登在西蒙的有限理性論斷的基礎上對該垃圾桶模型作了修正,將其運用在美國聯邦政府內部的政策出臺中,提出多源流理論模型。多源流模型雖然是建立在垃圾桶模型的基礎上的,卻將公共政策階段分析的觸角又伸向前一步,其表現為破解了垃圾桶模型“決策活動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這一模糊性命題,并將四源流變為三源流,即問題溪流、政策溪流和政治溪流,此外政策之窗對三源流的耦合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內涵闡釋:三源流與政策之窗
金登的多源流理論模型中的三源流包括問題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問題源流指的是對問題的發現和界定,包括積弊已久的社會問題和時事熱點、焦點事件等,用針對某一問題的各種數據、關鍵指標、符號、焦點事件、項目反饋等來反映問題的嚴重性。政策源流包括專家學者及其他相關人士提出的政策、方案、計劃等,“政策原湯”中漂浮著各種政策建議或政策主張,這些政策并不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取得公眾的關注和重視,需要不斷地討論、潤色、修改,并且由相關專業人士不斷地說服和軟化公眾或政策反對者。此外,政策建議也并非一成不變地存在于政策溪流之中,它們會隨著時局的變化相應地漂入或漂出,不契合時局的建議將漂出政策原湯,淡出人們的視野,相反,適應發展的新辦法也會漂入。政治源流包括國民情緒、政府或國會的更替、利益集團的壓力運動、選舉結果等。公民、國會、官員、利益集團等多元行動者在政治中都以各自的方式表達自身利益訴求,同時相互博弈,尋求政治妥協和利益平衡。
該模型中的問題流、政策流和政治流是相互獨立地運作,只有在某個關鍵時間節點才會發生例外,即政策之窗短暫地開啟。在此之際,公民、國會、官員、利益集團等精明的“政策企業家”們便會抓住機會,將三源流匯聚凝結,實現源流耦合,最終設立政策議程,實現政策變遷,如若不能成功抓住時機,政策之窗將會很快地關閉。因此,問題流、政策流和政治流的耦合具有隨機性、松散性、不確定性和動態性。綜上,如圖1所示,問題源流中的要素有數據與指標、焦點事件與信息反饋等,政策源流中各種政策建議經不斷討論、修改、完善,由相關專業人士說服和軟化外界公眾,政治源流中主要包含國民情緒、政府更迭、利益集團壓力等,三源流在政策之窗開啟之際被“政策企業家”匯聚,實現耦合,最終建立政策議程。

圖1 多源流分析架構(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三、三孩政策的背景介紹
回顧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發展歷程,大致經歷了獨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雙獨二孩”政策、“單獨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和三孩政策,如表1所示。

表1 我國生育政策發展變遷表(圖表來源:作者自繪)
(一)嚴格管控階段
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歷經了戰爭、饑荒和自然災害,人口數量急劇下降,然而在恢復國民經濟時期,勞動人口成為至關重要的因素,因此國家為了人丁興旺,鼓勵生育,導致人口大規模增多。全國人口的快速反彈導致了人口與當時經濟資源的不匹配,因此亟待出臺政策加以控制。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便開始全面地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作為我國當時的一項基本國策,計劃生育政策有著持續而深遠的影響。在計劃生育政策初期階段,我國實行的是嚴格的人口管控政策,具有強制性和不可違抗性。為了控制人口數量,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子女,此為“獨生子女政策”的開端。
(二)漸進調整階段
由于獨生子女政策在推行之后暴露出諸多弊端,如獨生子女家庭結構問題、失獨家庭問題,再如經濟發展困難的農村地區在“一孩”政策下缺少男性勞動力等問題,使得國家在對于困難農村家庭實施“一孩半”或“開口子”政策,即若第一胎為女孩,那么隔規定的年限之后可以申請生育二胎,但第一胎為男孩則不可以申請生育二胎。此外,獨生子女隨父姓還是隨母姓容易鬧得家庭不和諧,因此之后的政策松綁體現在實施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兩個孩子的政策,即“雙獨二孩”政策。在此鋪墊下,又啟動了“單獨二孩”政策,即夫妻雙方中只要有一個是獨生子女的家庭便可以申請生育第二個孩子,此為生育政策逐漸調整的階段。
(三)全面放開階段
國家為放松人口管控而實施的“單獨二孩”政策似乎并沒有受到公眾的廣泛響應,與此同時,社會上還出現了老齡化問題、人口紅利減退、性別比例失衡、人口結構逆自然化和生育意愿降低等問題。為了應對“單獨二孩”政策遇冷,進一步鼓勵生育,國家又提出了“全面二孩”政策,即只要是合法夫妻,不管是否是獨生子女,都有生育二孩的權利。此后,為了繼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國家又出臺三孩政策,即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孩子,標志著國家進一步放開生育管控,鼓勵國人生育。
四、多源流模型的嵌入分析
(一)問題源流:問題如何引發關注
多源流模型中的問題源流解釋了為什么有些問題可以引發政府或有關當局的關注,進而提上議事日程,而其他一些卻被忽視。結合三孩政策,放開三孩緣何在諸多紛繁復雜的社會問題中引發注意,其中有哪些積弊已久的難題,又有哪些指標可以反映問題的嚴重性,都值得研究與分析。
1.人口老齡化。對于老齡化社會的界定標準可以借鑒聯合國的觀點,若全社會人口中65周歲及以上的老年人比重超過7%,或者60周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超過10%,那么便步入了老齡化社會。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5周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的8.87%,顯然證明我國早已邁入老齡化國家。然而截至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5歲以上的人口數達190635280人,占總人口的13.5%(見表2),已經遠超老齡化指標,且老齡人口比重對比六普增長了近5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兩點:

表2 2020年年末人口數及其構成單位:人、%
其一,養老體系不堪重負。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和社會保障的日益健全,人們的平均壽命也更長。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我國參加養老保險人數已達43487.9萬人,離退人員參加養老保險人數為12310.4萬人。不僅養老金面臨壓力甚至虧空,養老機構和相關養老服務設施的供給也不堪重負,截至2019年年末,全國共有養老機構3.4萬個,養老服務床位761.4萬張。
其二,勞動力資源萎縮。根據國家統計局2021年的數據,2020年末我國在15-59歲之間的勞動年齡人口數為894376020人,占總人口數的63.35%(見表2),較2019年占比下降了0.65個百分比。由此可見,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數正在下降,揭示了我國勞動力資源正在萎縮,人口紅利正在消退,人口結構逆自然化,這將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沖擊,按照國家統計局的預測,可能不到2030年,我國勞動力將出現“負債”局面。
2.獨生子女家庭結構問題。獨生子女政策使得獨生子女家庭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家庭結構,然而這種家庭結構可能存在較大的風險。首先體現在獨生子女的性格和心理健康發展方面,他們也許會因父母的溺愛而性格軟弱、脾氣暴躁,心理健康也可能出現問題。其次便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失獨家庭問題,即獨生子女去世,夫妻不再生育,獨生子女政策使失獨家庭一生走不出陰霾。最后這種家庭結構的弊端表現在獨生子女成年后的養老與生活壓力上,正常情況下,一對夫妻要養育四個老人和一到兩個孩子,生活成本變高,生活壓力巨大,導致不敢生或不敢多生。
(二)政策源流:政策建議如何漂進漂出
三孩政策出臺前,圍繞這一問題的各種政策建議就不斷地涌現出來。政策源流的主導者通過提出政策方案決定了“政策原湯”的口味,即到底生育政策要往什么方向發展,公眾則是他們說服“軟化”的對象,專業人士需要不斷向外界輸出自己的政策觀點,說服大眾并取得支持。政策源流中的備選方案不是靜止的,即有沒有必要實行三孩政策等觀點會隨著時局變化適時地漂進或漂出決策者的視野,不同政策方案相互斡旋博弈,決策者和公眾也會在各種政策之間斟酌。
1.技術可行性和價值可接受性。政策方案的選擇歷程呈現出“思想在政策源流中四處漂浮的畫面”,是否兼具技術可行性和價值可接受性是政策建議能否繼續漂浮在政策源流中的關鍵。技術可行性從工具理性的視角出發,運用科學技術及先進的測量工具對一項生育政策下的生育成本、生育率、人口總量和結構、人口資源承載力和人口變動趨勢等變量進行評估,不具備技術可行性的政策建議將漂出政策源流。價值可接受性則從價值理性的角度出發探討政策的調整和實施可能帶來的倫理道德問題,如實行三孩政策是否遵循了以人為本的理念,保障了人們的生育自由權利,能夠緩解失獨家庭的痛苦等。因此,不同的政策方案在博弈的過程中,只有兼具技術可行性和價值可接受性才不容易被輕易淘汰,漂出“政策原湯”。
2.政策博弈與備選方案輸出。回顧三孩政策出臺前的一段時間,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在2018年兩會期間就提出議案,建議放開三胎政策,由于當時已經實行了兩年多的“全面二孩”政策,我國人口出生總量和出生率不升反降,因此他認為盡早出臺三孩政策才能使全國人口保持穩中有升。然而,有些專家不是很看好三孩政策,認為三孩政策意義并不大,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人口研究所的彭希哲教授就持有這樣的看法。事實上,許多學者也指出現今的住房、醫療和教育等生活成本不斷攀升,即使三胎政策不想生的還是不會生,一時間,關于是否要推行三胎政策的爭議很大。2020年10月至12月,恒大研究院的任澤平建議在“十四五”期間需盡快出臺三胎政策,理由是當前正處于第三波嬰兒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原本不想生的不會生,但放開三孩能讓想生的人生,也符合我國漸進式改革和增量化改革的內涵要求。雖然建議了許多次,但國家衛健委和計生委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是否要放開三胎政策。終于在2021年5月11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三孩政策才正式且快速地漂入決策者的視野。
(三)政治源流:政治環境有何變化
政治源流是多源流理論模型中政策議程設立的關鍵一環,流淌在政治溪流里的主要包括國民情緒、政府或國會的更迭、選舉結果等,這些要素構成政治氣候的變化,為三孩政策提上政策議程營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1.國內的政治氛圍。三孩政策出臺前夕,全國范圍內對于呼吁政策的國民情緒雖然不如“全面二孩”政策出臺前那樣高漲,但國內明顯形成了較為濃厚的鼓勵生育的氛圍。面對持續低迷的人口出生率,全國多地相繼出臺“催生”政策。自2018年起遼寧省便對生育二孩的家庭給予物質和其他方面的獎勵,湖北、新疆等地也紛紛出手,出臺積極的生育政策,完善配套設施如延長產假、生育補貼等,陜西省則明確表示,要適時全面放開計劃生育。雖然當時三孩政策還沒有正式出臺,但在某些程度上不少地區已經對生育三孩及三孩以上的家庭不再限制,比如生育三孩不再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一些社會補助、政策優惠、免費項目等,三孩家庭也同樣可以享有。全國范圍內的這些舉措為國內三孩政策的到來營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也是放開三孩的鋪墊。
2.執政黨的執政理念。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共產黨的意志和理念對于政策走向起指示性和決定性作用。2020年11月的“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明確了,要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增強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實際上,我國從“十三五”規劃中指出要“制定科學的人口發展戰略”開始,應對老齡化和改善人口戰略等問題就頻頻出現在各種政策建議中,體現出執政黨對人口問題和生育政策的充分重視。從獨生子女政策到放開二孩再到放開三孩,生育政策的轉變體現了執政黨以人為本和對人性的關懷。徹底放開三孩政策是對人們生育自由權的保障,是順從民意的表現,有利于實現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政府職能轉型,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并實現從統治型、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執政黨對于人口生育政策的執政理念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三孩政策的順利出臺,是三孩政策議程得以建立的至關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
(四)政策之窗開啟:三源流耦合實現
金登認為上述三源流是彼此獨立的,任意一個源流的形成和運作都不依賴另外兩個,然而只有在關鍵時刻,三條源流才能被政治企業家聚合到一起,此時政策之窗便會短暫地打開。若這時精明的政治企業家們能抓住時機,便可以順利促進政策議程的設立,若不能在短時間內把握政策之窗開啟的機會,議程就會被擱置,等待下一次政策之窗的開啟。
1.政治企業家的構成。三源流不會自動聚合,需要政治企業家們的推動才能實現,因此政治企業家在三源流的耦合和最終的政策議程設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他們的身份是不確定的,包括普通公民、民間意見領袖、人大代表、專家學者、政府智囊機構工作人員和國家領導人等。
首先是普通公民的參與,從全面二孩到放開三孩,公眾可以借助互聯網和新媒體表達自己的觀點,線上線下實現公民參與決策,影響政策決策的出臺。其次是人大代表和民間意見領袖,人大代表反映人民的呼聲,民間意見領袖往往也是民意的集中代表。再次是專家學者和政府工作人員,作為政治企業家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口學專家和政府智庫的工作人員是最為活躍的思想智慧源頭之一。最后是國家領導人發揮的關鍵性作用,領導人的政策傾向很大意義上促成了三孩政策議程的設定。
2.政策窗口的開啟。只有在關鍵時候當特定的“機會之窗”打開時,條件完備的三源流才能實現耦合,并且三條源流缺一不可,即“足夠嚴重的問題、成型的政策方案和適合的政治氛圍”這三條只要有一條不完備,就不能實現多源流的耦合。政策之窗包括問題窗口和政治窗口,因為機會窗口的開啟往往是因為緊迫的問題或是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其中問題窗口往往是不可預測的,政治窗口大部分是可預測的。
2021年5月11日,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喆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暴露了我國嚴重的老齡化問題和當今人口和生育方面的其他問題,一定意義上開啟了政策之窗的問題窗口。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了我國“十四五”時期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舉措匯報,審議了《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并指出,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此舉則是開啟了政策之窗的政治窗口。在問題窗口和政治窗口的雙重作用下,政策之窗被打開,三孩政策議程得以建立。
五、反思與討論
1.政策的過渡性。回顧我國生育政策的發展變化史,從計劃生育政策到三孩政策,通過總結規律我們不難發現,政策口子是越開越大的,國家對民眾的生育是越來越放寬的。事實上,無論是三孩還是二孩,政策要旨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只不過是不同時期在具體政策上的規定不同。我國推行漸進式改革和增量化發展,很好地體現在了生育政策的制定上,實施漸進式生育政策,逐步放開而并非一下對人口生育不加限制。因此,無論是二孩還是三孩政策,抑或是未來還可能會有的四孩、五孩政策,都并非生育政策的終點,多孩政策的出臺只是過渡性、階段性的,政策總是會向放開生育演化。
2.生育權的回歸。在探討多孩政策出臺后的政策影響時,研究者們通常會發現,即使不斷放開生育仍然收效甚微,沒有很好地達成理想中提高人口生育率的政策目標。為何在近些年不斷放開生育后我國的生育率仍然沒有顯著提高,為何出生人口數仍在下降,究其原因:其一,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的規模下降,生育年齡也有所推遲。其二,人們的婚育觀念改變,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已經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不少家庭選擇少生、優生。其三,新冠疫情打亂了人們的婚育計劃,疫情給年輕人的住房、就業、醫療、教育等都帶來了影響,不少人礙于疫情帶來的沖擊取消了婚育計劃。故在現今的經濟形勢和社會背景下,即便推行四孩、五孩政策,我國的人口出生率仍然應該是處于平穩的狀態,人口老齡化這一嚴重問題仍不會發生太大改變。
公民的生育權作為一項基本的人權是與生俱來的,是先于國家和法律發生的權利。過去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如獨生子女政策)雖然是結合當時社會背景制定的策略方針,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對公民生育權的剝奪。生育權既然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就應該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回歸民眾本身,民眾不應強制被規定應該或必須生育幾個孩子。與其一味地加以行政許可,不如徹底放開,不做限制。因此,應把生育權還給生育者,不再做行政許可,事實證明國家也正在朝這個方向前進,生育權利也正逐步地回歸正常家庭。我們期待隨著社會理性文明的發展和民眾素質的日益提高,人們將會有能力結合自身家庭情況合理評估生育幾孩,真正地實現生育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