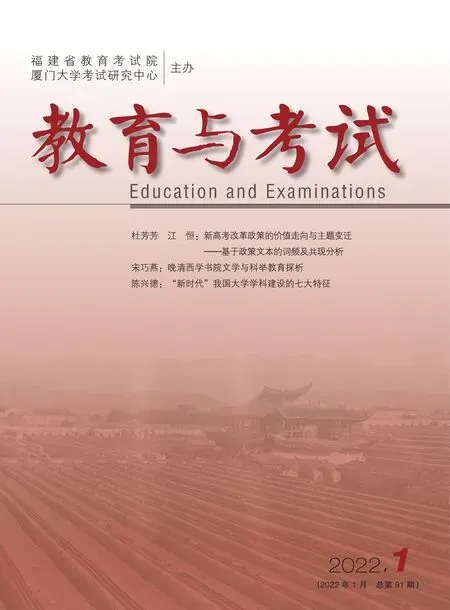晚清西學書院文學與科舉教育探析*
宋巧燕
晚清西學書院是以自然科學為主要教學內容的書院類型,辦學目的是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也就是西學。西學書院產生于西學東漸和洋務運動的時代背景之下,是有識之士為了挽救衰落的國勢、救亡圖存所做的努力。到了清末,傳統書院逐漸淪落為科舉的附庸,圍繞著科舉的指揮棒,重視詩賦和八股文教育。西學書院是對傳統書院普遍專注于詩賦、八股文教育的革新。
晚清西學書院著名的有上海格致書院、上海中西書院、杭州求是書院、武昌兩湖書院、陜甘涇陽味經書院、西安關中書院等。其中創辦最早的是上海格致書院,同治十二年(1873)由江蘇無錫徐壽和英國傅蘭雅(John Fryer)等開始捐資創辦,1876 年開始招生。在晚清的社會環境下,西學書院不可能完全超越國情和時代,只從事西學教育,中學仍是基礎和根本。如上海格致書院創建之初擬定的章程中,認為書院不但要備藏各種西學書籍和儀器,“又備中國經史子集,以期考古證今,開心益智,廣見博聞。”[1]上海中西書院,光緒七年(1881),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創建,自任院長,專課中西兩學,“意在中西并重”[2]。晚清西學書院文學教育依然受重視,與科舉仍然有著密切的關聯。
一、西學書院創建的文學與科舉教育批判背景
西學書院產生于西學東漸和洋務運動的時代背景之下,傳統書院普遍淪落為科舉的附庸,只圍繞著科舉進行詩賦與八股文教育,弊端重重,積習難返,批判的聲音非常清晰,改革的呼聲不絕于耳。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西學書院順應歷史潮流,應運而生。
晚清書院弊端很多,如很多書院山長只是掛名,而不到院,不和學生謀面,學生考課舞弊成風。《申報》1878 年8 月19 日發表《論書院弊藪》一文,批判蘇杭等地書院作弊成風,曰:“書院月課則有花紅膏火,以為獎勵之資,其所獲在利,而其初意則皆所以培養士子,振興文教。……蘇杭兩處則請托公行矣,山長之門生故舊每得優等矣,脂韋之流且鉆營謀刺競拜老師矣,甚至繳卷之時顯夾條子于其中,發案之前允抄閑本以呈覽,種種不公不一而足。”蘇杭,在清代是公認的人文淵藪之地,具有濃厚的學術文化氛圍,連這兩地的書院都舞弊成風,其他地方可想而知。《申報》1883 年10月2 日又發表《論書院流弊》一文,指出書院應課士子作弊謀利之風已不只是個別地區的現象,而是各地“莫不皆然”,“士子以區區書院膏獎而百計請托賄求,則是自隳其品行,名節由是棄,品行由是隳”。
書院到了晚清大多淪落為科舉考課類書院,而科舉時文、詩賦在晚清動蕩衰落、外強烈焰咄咄相逼的社會大勢下,因無經世致用之功而遭到批判和攻擊。很多有識之士呼吁改革書院教學內容,如葉爾昌《廢書院時文詩賦為有用之學議》中曰:
中國之取人才,在科目;其養人才也,在書院。科目以登進之,書院以肄習之,前明令甲特重時文,本朝因之益以詩賦,二百余年奉行惟謹,父詔子,師傳弟,從未有言其害者,何也?科目非時文、詩賦無以進身,書院非時文、詩賦不獲膏火。蓋餌其利,而忘其害也,久矣。
方今天下,日本橫于東,歐洲諸邦環伺于西,各挾其奇技異能與夫邦之利器,以爭衡于天下。而中國坐受其困,無一應變御敵之才,此坐時文、詩賦之病也!夫時文、詩賦小技也,昔之為此者,根柢六經,羽翼諸子,非無名臣大儒出其中,今之為此者,孔孟不知何道,程朱不知何學,惟日從事于咿唔占畢中,糟粕耳,皮毛耳,曷足貴哉!……
時文、詩賦有何建立?有何擔當?又安所得人才哉?……夫殺人者,只害一人,而時文詩賦,直害千萬人,一人受其害,猶含不白之冤,千萬人被其害,竟無解終身之惑。
中國所以自弱者在此,外人所以窺伺者亦在此。昔禹時洪水為害,周公時夷狄為害,春秋時亂臣賊子為害,戰國時楊墨為害,漢唐時佛老為害,今之時文詩賦不減五害也,不廢何待哉?[3]
歷史常常周期性地上演同樣的片段,一如明末清初,將明朝衰亡的原因歸罪于八股文,只是到了清末,多了明代科舉未用的詩賦而已。
葉爾昌對廢除時文詩賦后的書院教學內容進行了規劃,包括12 齋,即12 個方面的內容:宋學齋、掌故齋(即考據之學)、治事齋(政事之學)、時務齋(經濟之學)、天算齋(數理之學,兼以繪畫)、與志齋、西學齋、軍事齋、商務齋、律例齋、格物齋、制造齋12 類。詩賦等傳統文學教學內容被摒棄于設定的教學內容之外。
書院改革的呼聲一直未斷。光緒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撫胡聘之上《請變通書院章程折》,建議改革書院教學內容,逐漸減少科舉時文、詞章教學內容,不斷增加自然科學內容。奏折有曰:“查近日書院之弊,或空談講學,或溺志詞章,既皆無裨實用,其下者專摹帖括,注意膏獎,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宜將原設之額,大加裁汰。每月詩文等課,酌量并減。然后綜核經費,更定章程,延碩學通儒,為之教授,研究經義,以穹其理,博綜史事,以觀其變。由是參考時務,兼習算學,凡天文、地輿、農務、兵事,與夫一切有用之學,統歸格致之中,分門探討,務臻其奧。”[4]
書院改革的呼聲大都針對教學內容中的科舉時文和詩賦。西學書院的應運而生代表了晚清書院改革的時代文化潮流方向。而在西學書院任教的中方教師,身份值得探究,他們都接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并深有造詣,但都不以文學名世,在科途上皆不盡人意,愛好西學,并卓有成就。上海格致書院長時間主講者有徐壽、華蘅芳和王韜。徐壽、華蘅芳沒有科名,年少時就絕意科舉,王韜是秀才,鄉試未售后也絕意科舉。他們都有反科舉傾向。下面以王韜(1828-1897)的科舉批判為例。
接受過科舉教育的王韜,對科舉有猛烈的批判。不得科名就是不孝的思想,在清代很流行頑固,有友人給他寫信,勸他用心功名以盡孝。王韜回信說:“足下謂科名者,士子之進身,非得之不足為孝,以是為仆勸,其意不可為不厚,然仆聞有一時之孝,有百世之孝,吾人立天地間,縱不能造絕學,經緯當世,使天下欽為有用之才,亦當陶冶性靈,揚榷古今,傳其名以永世,若不問其心之所安,博取功名富貴,以為父母光寵者,烏足道也……況士各有志,仆不能強足下為古,猶足下不能強仆為今也。……于時文中求經濟,吾未見其可,足下勿挾尺寸之見,令人墮實而廢時,則幸甚。”[5]2他對朋友以科舉為重的愚見,反駁得很有分量,以科名盡孝是“一時之孝”,而從事自然科學研究是能經緯當世的“百世之孝”。
王韜猛烈批評了科舉時文選士的科舉制度,曰:“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趨益下,庸腐惡劣,不可向邇。乃猶以之取士,曰制科,歲取數千百貿然無知之人,而號之曰士。將來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變,則人才終不出。”[6]99“本朝試科以制藝,實沿明代舊習,遂使英賢杰士壯志消磨,皓首窮經,未蒙推選,不知湮沒幾何人品矣!”[5]1“今國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賢書,升之大廷,稱之曰進士,重之曰翰林,以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試者時文耳,非內圣外王之學也,非治國經野之道也,非強兵富民之略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于無用者,正坐此耳。乃累數百年而不悟,若以為天下之人才非此莫由進身,其謬亦甚矣。敗壞人才,斫喪人才,使天下無真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無不由此。”[7]44-45王韜對清代科舉制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八股文上,認為科舉時文選拔的都是無用的人才,不但不能選拔真正的人才,而且還是敗壞人才、毀滅人才的罪魁禍首,科舉制度不改革,就不能實現選拔真正人才的功能。
晚清西學書院產生于科舉和文學批判的時代教育背景之下,是走在時代前列的書院類型。
二、西學書院仍重視文學教育,沒有排除科舉教育
西學書院的課程特點是以西學為主要教學內容,但在晚清沒有突變的文化環境下,中學內容仍是根本,考課制度的確立意味著西學書院從形式到內容都難以擺脫傳統書院的影響。考課時策論文受到重視,關注時事和時務,對學生的文學基本功有較嚴格的要求,文學水平是閱卷時衡量評判的重要標準。而小說等傳統書院堅決排斥的文學作品,也進入了可閱讀書目之中。而科舉也沒有絕對地排除在教育教學之外。
上海格致書院考課制度的確立,意味著西學的教學模式中實實在在地融進了傳統書院科舉與文學教育的訓練方式。1885 年王韜任上海格致書院山長,直到去世(1897 年),這12 年是格致書院最為興盛的時期,王韜在辦學諸多方面進行了改革,吸取了傳統書院的考課制度就是重要的一項。格致書院最終沿用了清代書院的考課制度,采用征文比賽的形式獎勵課試優秀的肄業生。考課的課題大多屬于策論文,而考課的形式被認為與科舉有密切關系。傅蘭雅說:“(中國)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幾乎全部是做文章,因此,這門藝術傳承了幾個世紀,在文體、選詞和組織各方面已經達到了完美的境界,這是在西方從未有過的。為了使西方知識受到知識分子的歡迎,必須很好地利用現有的民族特色。因此,可以說做文章是一種能促進上層中國人對外國實用技術進行讀、想、寫的最有效的方法。藉此可以實現格致書院的主要目的。”[8]17以“做文章”為主體內容的考課制度,傅蘭雅認為是科舉應試的重要訓練手段,格致書院藉此可以更有效地實現西學的教育目標。學者熊月之對此評價最為精辟,可謂一語中的。他說,“作文著論,這對中國士子來說,屬科舉考試一路,駕輕就熟”,而格致書院實行考課,“就將中國科舉考試的外殼,與西方科學技術的內核,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科學普及方式”[8]17。格致書院的西學教育最終還是順應國情,利用了科舉考試訓練中“作文著論”的舊瓶,裝進了西學的新酒,關注的是有關國計民生的社會歷史問題。1897 年,王韜病逝,傅蘭雅說:“由于王韜先生的病逝,有獎征文競賽不如從前那么富有生氣了。”[7]165格致書院考課被傅蘭雅稱作“有獎征文競賽”,考課內容與形式,終究沒有脫離傳統之“文”與科舉考試的范疇。
上海格致書院教學內容以各科自然科學為主,而考課中比較傾向于策論文的寫作,直面各種社會歷史問題,涉及有關國計民生的時務、經濟、科學、歷史等各個方面,要求提出對策和應對措施,以期經世致用。時務題如:中國創設海軍議;中國近日講求富強之術當以何者為先論;中國創行鐵路利弊論;輪船電報二事應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論;海軍、軍艦與鐵甲船塢問題;如何有效地禁止鴉片;等等。時務題中比較關注經濟問題,如中國近年絲茶貿易問題;收回被洋人所奪工商利權問題;水旱災荒平時如何預備、臨事如何補救論;等等。[9]373-375
考課答題需要提出自我觀點,可以各盡所言,沒有標準答案,正反方觀點都允許。但畢竟學生們缺乏資深的閱歷,闡述救亡圖存的治國大道目的還在于更新觀念,擴展眼界,開拓思維,所以課卷評閱中比較注重對文字表述和行文的評判。熊月之對格致書院課藝批閱有這樣的描述:“從現存的課藝來看,王韜、傅蘭雅以及各位命題、閱卷人,對課藝采取的是只加評論、眉批、不予改動的方式;對課藝等第的評定,只問其是否言之成理、自成一說,不問其觀點是否合乎閱卷人本人的見解。我們在課藝的評語和眉批中,隨處可以見到他們對學生意見的反駁、對修辭文法的批評。這種只批不改的存真態度,使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學生課藝的真實面目。”[9]363-364論述要“言之成理、自成一說”,課藝評閱中隨處可見“對修辭文法的批評”,這其實是中國古代作文寫作的基本訓練要求,也是科舉考試的基本功。
西學書院的中方教師在科舉考試中普遍不擅長八股文寫作,但他們的傳統學術素養都非常深厚,擅長西學可能抑制了他們后來的中學發展,但他們是在積淀深厚的經史子集學養基礎之上,取得了豐厚的西學成就。以王韜為例。王韜父親是塾師,母親出自書香門第,受到良好的啟蒙教育和家庭教育。王韜回憶說:“老民母固知大體,四五歲時,字義都由母氏口授,夏夜納涼,率為述古人節烈事,老民聽至艱苦處,輒哭失聲,因是八九歲即通說部。”“少承庭訓,自九歲迄成童,畢讀群經,旁涉諸史,維說無不該貫,一生學業悉基于此。”[6]386“一生學業悉基于此”,西學的根基也在其中。王韜傳統學術頗有所成,有《春秋左氏傳集釋》60 卷、《皇清經解校勘記》24 卷、《毛詩集釋》30 卷,還有《周易注釋》《禮記集釋》等,都是有關傳統儒家經典的研究成果。
建于光緒七年(1881)的上海中西書院,辦學之初就設定中西學兼課。光緒十七年(1891)林樂知所訂《中西書院規條》中這樣一條:“本書院每逢禮拜三課期,或作詩文,或作論,或作尺牘,各盡所長。”“習西學以達時務,尤宜兼習中學以博科名,科名既成,西學因之出色。而諸生務各恪守。”[10]可見,傳統“詩文”“論”“尺牘”等文學樣式仍在書院教學范圍之列,并且特別強調“尤宜兼習中學以博科名”,學習中學的目的竟然是為了博取科名,認為科舉成功,西學因之出色。可見中西書院西學、中學、科舉三者兼容并蓄,處于社會變革時期的西學書院并不能擺脫傳統文學與科舉的影響。
浙江求是書院仍然重視中學和文學教育。光緒二十三年(1897)當時的杭州知府林啟發布《招考求是書院學生示》,明確招生對象是“無論舉貢生監,年在三十以內,無嗜好,無習氣,自愿住院學習者”。[11]2159招生對象主要還是奔走在科途中的士子。浙江求是書院學生選擇標準有“文理通暢”一條,要求學生有一定的文學功底。學習課程以自然科學和英文為主,英文有翻譯課,常翻譯書籍報章,也要求學生學習漢文。《求是書院章程》有課程規定:“學生漢文宜加溫習,時務尤當留心。每日晚間及休沐之日,不定功課,應自瀏覽經史古文,并中外各種報紙,各隨性情所近,志趣所向,講求一切有用之書,將心得之處,撰為日記,至少以一百余字為率。”考課要求:“以講求實際為主,每月朔日課西學,是為月課,由教習分別等第;每月望日考漢文,或經義,或史論,或時務策,不定篇數,是為加課,由總辦分別等第。每年冬間,由撫憲督同總辦、監院、教習通校各藝,分別等第,是為會課。”[11]226中學課程主要是自學,鼓勵學生閱讀“中外各種報紙”,關注時事;中學考試仍沒有離開傳統的經史,不過關注的仍是時務。
據錢均夫(錢學森父親)《求是書院之創設與其學風及學生活動情形》中所回憶的教學情景,中文課程仍是重要內容,曰:“當時之課程遠無今日之完備。國、英、數為必修課,學生專心于國文者最多。”“國文不是由教授直講,而由學生自行研閱,疑則發問,教師解答。”“學生必須日作札記,每晚呈繳,由教師批改。”[11]2163和傳統書院的教學方法非常一致,學生自學為主,有日課的札記。所聘請的國文教師多是德高望重、學養深厚的博學之士,如光緒十五年(1889)聘請的中學主講是著名的學者宋恕(字燕生、平子)。文中如是記載:
宋先生學問德望為海內冠,讀書能過目不忘,并謂不獨盡閱中國書籍,即大藏經典,亦皆過目。年事雖高,而思想甚新,著有《宋平子卑議》,學生有詢以既有卑議,則必有高議,能假閱否。師謂有之,然斯時尚不許爾輩假閱也。并曾游說李鴻章、張之洞等,欲為國事有所畫策,不為所采,退為主講。某次,見一學生方閱《紅樓夢》,問其閱至何處,答云已至某某回,隨命其背誦《芙蓉誄》,生不能對,宋先生即自始而終背誦之,一字不亂,并告誡同學曰:“爾輩讀書,遇有佳文,須熟記之,則他日行文,方有進境。”又一次,詢一生時讀《經世文編》,問其每日閱幾本,答曰十余篇。師喟然曰:“如此則全書正續兩編共有四十八冊,若干年后,始能閱完,中國書籍即以全書所載者,浩如煙海,爾輩何時方能讀畢。”有某生轉問師日必須閱讀若干,乃答曰日必三四本,且抽取若干精讀之文而指講之,一篇不亂。其記憶力之堅強也如此。故宋先生在校未到一年,學生受益甚多,而校風頓變。師所教學,純為啟蒙式教育,非斤斤于占畢者所可比擬也。[11]2163-2164
宋恕是具有非常濃厚個性色彩的博學學者,在求是書院教學中教導學生的仍是傳統的讀書門徑,精讀硬背,深入體悟,廣涉博覽。宋恕在書院教學中能夠關注并指導學者閱讀《紅樓夢》等小說,難能可貴。傳統書院中鄙視為“誨淫”之作的小說在求是書院中得到了重視和認可。所以說,晚清西學書院不但重視傳統的文學教育,而且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
其他如陜甘涇陽味經書院、西安關中書院、湖北武昌兩湖書院、上海求志書院等都有意識、有目的地提出和實施了西學教育,但中學仍是根本,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西學書院類型。這些從事了西學教育的書院,當然不可能完全超越時代,擺脫文學和科舉教育的影響。如西安關中書院,建于明代,歷史悠久,是標準的傳統書院類型。陜甘涇陽味經書院創立于同治十二年(1873),學政許振祎籌集民間資本建成,是得到官方認可的書院類型,教學中特設時務齋。劉光蕡《陜甘味經書院志》“經始第一”中對課程有這樣的設置:“其設課也,則合制藝、論策、經解、詩賦、法戒錄,分課一一為之。”[12]2制藝和詩賦是重要的教學內容。《陜甘味經書院志》中有“諸生題名”,乃登第士子名錄。其中“教法第五下”在學習內容中特別強調了“四書”,亦有研讀八股文的學習要求:“一讀時文(既作時文,不可不讀時文,然一切坊閑卑靡之編,與闈中腐濫之作,則斷不可讀。)”[12]18接著文中較詳細地介紹了八股文練習技巧。
湖北武昌兩湖書院,光緒十六年(1890)張之洞創建,茶商捐資,中西學并課,西學中重視算學和兵學,中學仍重視文學和科舉。光緒十七年正月初一日(1891.2.9)張之洞《咨南北學院調兩湖書院肄業生并單》中對課程有明確記載:“課士之法,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算學、經濟學六門,延請分教六人,專門訓課。諸生愿執何業,各隨才性所近,能兼者聽。”[11]2168傳統的經史文學仍是首選課程。《張文襄公年譜》卷3 亦載:“院課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可兼習并另設算學、經濟。”課程設置和選擇還是明顯偏重中學。雖然教學中沒有針對性的科舉教學內容,但突出的科舉成就是津津樂道的話題,“十九年鄉試,肄業生中式者二十三人”。[13]張之洞對于有意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可謂照顧有加,《咨南北學院調兩湖書院肄業生并單》中有曰:“其愿習時文者,北省諸生俱準送入江漢書院應課,無須另行甄別。”“本年適值鄉試,南省入院肄業諸生,本部堂自當于場前先期派撥輪船送歸。”[11]2168-2169張之洞光緒二十三年(1897)《新定兩湖書院學規課程》其中一條規則:“除鄉試外,不準給假,如有必須應科歲兩考者,勿庸來院。”[14]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受到優待,書院中的學生大都是奔走在科途上的舉子。
由上可知,晚清西學書院仍非常重視文學教育,也沒有完全擺脫科舉教育的影響,還吸取利用了傳統書院考課的教學模式和方法。
三、晚清西學書院是清末科舉變革的前奏和先驅
在晚清內憂外患的困境中,倡導洋務運動的李鴻章、丁日昌等不斷提出了科舉中加試西學的建議,在科舉文武科中加設藝科實科的奏折不斷呈送給高層統治者,但科舉變革的道路不會是一番坦途。光緒十年(1884)鄭觀應《盛世危言》卷1《考試》中提出,在科舉文武科之外,為專攻西學的士子,特設藝科,但他也認為,“恐未必能與正科并重”。[15]光緒十六年(1890)湯震《湯氏危言》卷1《考試》中,建議科舉考試“并經義子史古學為一場,時務為一場,洋務為一場,場以三藝為率,隨試官之意為先后場,不預為之限”。[16]在科舉考試中加設西學制科的設想不斷被提出,如“潘衍桐請開藝科,交閣部會議”,但客觀情況卻是“試官無其人也,舉子不及額也,統維全局窒礙良多。禮部調停其間,改藝科為算科,以二十名中一名為額,行之數載,每歲大比,數皆不及廿人,文具空存,竟同旒贅。”[17]
經過了甲午戰爭的慘敗,西方列強的咄咄相逼,庚子事變后清代科舉制度終于迎來了質變的改革,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在各級科舉考試中廢除八股文和試帖詩。改革后的科舉考試內容和程式為:
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二篇、五經義一篇。考官評卷合校三場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場。生童歲科兩考仍先試經古一場,專試中國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策論。正場試四書義五經義各一篇。考試差庶吉士散館均用論一篇,策一道,進士朝考論疏,殿試策問,均以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命題。以上一切考試均不準用八股文程式。策論均應切實敷陳,不得仍前空衍剽竊。[18]
考試內容首重中國政治史事和各國政治藝學,考試文體主要是論、策、疏等應用文體。而這樣的考試內容和文體是晚清西學書院教育的主體。可以說,晚清西學書院是走在時代改革前列的書院類型,它們的辦學方向代表了科舉考試改革的時代發展潮流。
其實,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榜眼馮桂芬(1809-1874)就建議改革科舉考試制度,他設計的考試內容是:“宜以經解為第一場,經學為主,凡考據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學、算學附焉。經學宜先漢而后宋,無他,宋空而漢實,宋易而漢難也。以策論為第二場,史學為主。凡考據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學為第三場,散文、駢體文、賦、各體詩各一首。”[19]這套科舉內容設計非常有見地有水平,內容全面,但輕重緩急分得很清楚,契合中國傳統文化本原和現實需要。經學是儒家思想的載體,不該廢除,漢宋學相比,就該先漢后宋,漢學講求實事求是,踏實求真,用這樣的態度治國、治家、治學、治身,當然是值得信賴的。里面有西學內容,及策論和史學,可以說馮桂芬遠遠走在了時代的前列。馮桂芬乃改良主義先驅,1863 年在上海設廣方言館,培養西學人才,最早表達了洋務運動“中體西用”的指導思想。后來上海格致書院、中西書院的創建,當然受到了馮桂芬上海廣方言館的前驅導向影響,廣方言館的西學教習有格致書院創辦者傅蘭雅,中西書院創辦者林樂知。可惜,清王朝的教育改革和科舉改革都如此得滯后。中國從來就不缺乏具有前瞻性的精英人士,不缺乏匡扶社稷、興國安邦的志士能人,只是高層統治者的昏庸無能和制度文化層面的諸多弊端,重重疊疊,礙手礙腳,使他們難以施展治國平天下的才能。而晚清西學書院的創辦,雖然數量不多,但總算讓馮桂芬科舉改革理想在書院中開花結果,有所收獲。
科舉改革后鄉會試等各級考試中出現了很多的時務策論題,有的還涉及西學,如光緒二十八年(1902)壬寅補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鄉試題,各省有關國計民生的時務題,如湖北省有題曰:“富強基于興學,應比較中西學派性情風尚之異同,參互損益,以定教育之宗旨論。”“強國之道,財政為先。試取泰西理財之法,參以中國情勢,通盤籌畫,分別其緩急利病之宜以濬利源而裨國計論。”湖南省試題有曰:“理財論。”陜西省試題有曰:“勸農桑慎選舉論。”[20]
而這樣的時務策論題,是格致書院等西學書院教學中一直實踐的常規教學內容。由《格致書院課藝》來看,書院學生對西學非常熟悉,有學者有相關評價:“從刊出的答卷可以看出,那時的不少學生,對西書相當熟悉,其西學素養,決不在人們所熟知的后來成名的康有為等人之下。”[9]367而廢除八股文后的科舉考試加入了西學內容,因不明西學內容而鬧出了很多笑話,可以看出當時教育文化中西學知識的嚴重缺失。科舉考試和后來的學堂考試不止一個考官出過《項羽拿破侖論》一題,當然有很多學生不知“拿破侖”為何,所以出現了很多跑題的答卷。有一考生作了篇如下文章,雖然跑了題,倒是很精彩:
夫項羽乃拔山蓋地之雄,豈有一破輪而不能拿乎?非不能也,勢不必也!
彼破輪為何物?其大幾許?其高若干?縱或擋道,烏騅且揚蹄,項王即可安然而過焉,何需下馬將其移開,而后再前,豈非多此一舉!退萬步而言,欲將其去之以利行軍,然則彼一破侖,百數斤而已,令一二士卒足以勝任矣;而何勞項羽主帥之尊,躬自動手?于情于理無乃不可乎?基于上述,余固以為:項羽不必拿破輪也!
為文至此,本當收筆,然意猶未盡,硯有余墨,卷有余紙,如鯁在喉,一吐為快。故不揣冒昧,斗膽向命題先生進獻數言:以“項羽拿破侖論”為題,其造詣立意,新則新矣!然于遣詞煉字,似略欠工,何哉?蓋用“拿破輪”三字者也,“拿”系白話;“破”文言當曰:“敝”;至若“侖”與“輪”互無通假——余揣度再三,方悟先生之意,乃敵軍為項軍所破,其輪與車體分離,安然不止余“侖”也——費解,費解!
統觀此題,文白夾雜,先生雖為用心良苦,然實屬似通非通,愚生不敏,未敢敬頌高明也! 打油詩一首,幸先生垂聽:欣然應試入場來,考題離奇復怪哉。但愿細流能容海,勿拋不才孫山外!①
由這篇不能審題的答卷,可以對比看出西學書院在晚清教育史中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晚清科舉改革造成了考試文體和內容新舊銜接的斷層,這時候西學書院的課藝成為了科舉考試的模仿對象,新的場屋秘訣,新科利器。晚清李伯元《文明小史》第24 回有用時務題考核捐納官員的故事描寫,不但被考核官員不會答題目,就連考官也不會出題目,所出題目從《格致書院課藝》中直接抄來,裝神弄鬼改了幾個字形而已,有題目“問的是礦務,偏偏那個‘礦’字照著周禮古寫”,七十一本考卷,有三十多本是白卷,其余的都是文理不通,不知所云的。而通關節作弊考第一名的金颎,從出題老師處不但得到了題目,而且連答案一并得到了,就是格致書院課藝中的現成的五、六篇文章。這些非常糟糕的考卷,考官的批語非常有意思,給作弊名列第一的金颎的批語是“應有盡有,應無盡無”八個字。還有批語是:
又看底下有的批:“兩個黃鵬鳴翠柳,文境似之。”姬公看了,卻不懂得,說:“這本據兄弟看來,頗有些不通的去處,為什么倒批他好呢?”王總教道:“晚生這個批語,原是說他不通。那兩個黃鵬大柳樹陰中對談,咱們正聽不出他說的是些什么。”[21]
晚清《格致書院課藝》成了科場新的秘本,可見當時的西學書院辦學效果突出明顯。可惜,這樣的日子沒過多久,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極端地廢除了科舉制度。光緒二十七年(1901)伴隨著科舉八股文被廢除的,還有正在超高速發展中的書院,光緒三十一年(1905)科舉制正式廢除,這一切都注定清王朝離滅亡的終點已經不遠。
在晚清文學與科舉批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西學書院,終究不能完全擺脫文學與科舉的重要影響。
注釋:
①轉引自今古傳奇.1994(2).另外舒蕪.項羽拿破侖論.吳小如.《項羽拿破侖論》及其他.(文匯讀書周報[N]1994年4 月30 日)亦有相關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