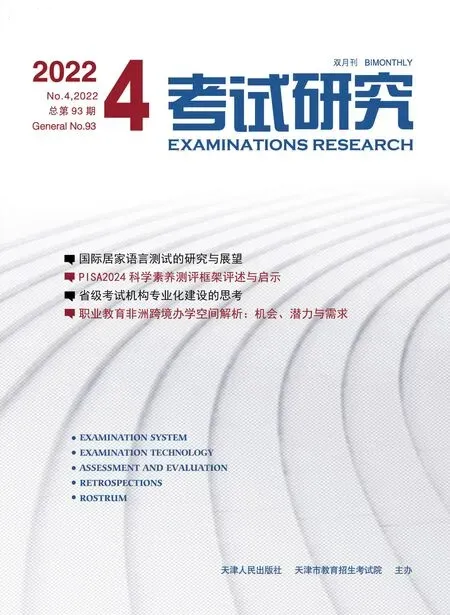遼金高麗科舉比較考述
解洪興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在唐宋時期日臻完善,其改善社會流動、維護政治穩定、促進文化繁榮的成效斐然。這一開放競爭機制不斷向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及鄰國輻射。西夏與大理雖有科舉,可惜史料珍稀難窺全豹,科舉發展蔚然成風的是地處東北亞的遼、金與高麗。這幾個政權的開基始祖,無論是耶律阿保機、完顏阿骨打,還是王建,均以武立國,后繼者卻不約而同地開科取士以興文治,其文化視野及政治胸懷殊為可觀,但若具體落實到為用為體的預期及其因時制宜的實踐動態上終究參差不齊。高麗王朝后期受到駙馬國①自忠烈王以后,歷代成年的高麗王都要迎娶元朝公主為王妃,元朝公主在高麗國有至高威望和權力,所生男子立為世子,世子入元宿衛,娶公主即位后受元朝任命為征東行省丞相并冊封為高麗王,多次以駙馬國國王名義覲見元朝皇帝,高麗國奉元正朔,在辮發、胡服、謚號等儀式方面內地化。及征東行省②1287年元朝在高麗國設置征東行省作為元朝統轄高麗國的首腦機構,以高麗王為行省長官,在高麗國王都設有官署衙門,與高麗政權的官僚機構分署辦公,行省官員在名義上是由元朝任命,執行元朝的旨意,征東行省具有羈縻特點,統轄機制等與元朝內地行省有所不同,高麗國始終保持很強的獨立性。等政治影響,其科舉也成為元朝科舉的鄉試[1]27-30。因此,筆者認為10-13世紀東北亞遼、金、高麗的科舉更具可比性。
一、遼金高麗科舉的繼承性比較
無論是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還是王氏高麗,就其在政權建立后對科舉制的引進而言,在東北亞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但三者科舉的繼承性仍有較具體的差異。
第一,遼、金、高麗引入科舉的時間早晚不同。公元976 年遼景宗下詔恢復南京禮部貢院,距遼朝建立已經整整六十年。遼圣宗統和六年(公元988年)正式開始科舉取士,只有高舉一人及第。高麗太祖興建學校為科舉奠定了基礎,公元958 年高麗光宗采納翰林學士雙冀建議在境內開科取士,距高麗建國不過四十年。金太宗在戎馬倥傯的天會元年(公元1123 年)即詔命科舉[2]1134,《渾源劉氏世德碑》載有天會二年(1124 年)[3]金進士姓名,距金建國尚不足十年。
就引入科舉的時間階段而言,金朝最早,其次高麗,遼最晚。高麗與契丹建國時間大致相當,引入科舉卻早于后者,說明農業文化的高麗對于科舉認同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明顯超過游牧文化立國的遼朝。后起女真政權所以汲汲開科取士與其由不足20萬戶[4]到400萬戶[5]的急速擴張“意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2]1134的直接需要有關。在剛剛占領的遼、宋地區,各路軍事統帥被授予科舉的權限甚至空白的告身,錄取后就地授官。據《褚先生墓碣》[6]1254載,天會四年(公元1127年)真定府策試73人除了褚先生本人均被錄取。
第二,遼、金、高麗科舉取法模式不同。遼朝前期科舉繼承唐制。從統和六年(公元988 年)到開泰二年(公元1013 年)遼圣宗開科20 次,幾乎每年一次,頻次雖與唐相仿,但一共取進士101人,最多一次23人,最少僅1人,平均一次僅5人,規模卻遠不及唐朝。圣宗開泰三年(公元1014 年)至道宗清寧元年(公元1055年)開科14次,相當于3年一次,共取進士649人,最多時為72人,最少時為31人[7],平均一次超45 人,說明自圣宗后期科舉開始參仿宋制。遼后期雖間或出現殿試,但據高福順先生考證僅有7次[8],說明對宋制的吸收遠未達到常制程度。據《寧鑒墓志》,乾統十年(公元1100年)尚有明經登第者[9],說明遼末仍有舊唐科目。金代科舉兼采眾長,金初甚至為了兼顧占領區遼、宋不同的科舉傳統實行“南北選”[2]1134。律科、制科襲于遼,進士分詞賦、經義則引自宋,金章宗甚至仿行宋代恩科[2]1147-1148。高麗繼承唐制,常舉科目高度雷同。制述相當于唐代進士,律、書、算相當于唐代明法、明書、明算,明經、三禮、三傳與唐名實俱同。州縣的“貢士”、中央各學校的“生徒”相當于唐代的“鄉貢”“生徒”。考前要提交家狀以備審核,考中也要舉行放榜儀式[1]126-127。
二、遼金高麗科舉的創新性比較
高麗科舉雖仿唐制,但也多有因地制宜的變通。唐代制舉在朝鮮半島始終沒有出現,常舉設置了極富朝鮮半島文化特色的醫科、卜科、地理科,這與遼明令禁止醫卜[10]參與科舉截然不同,崇信佛教的高麗君主甚至創設過僧科[11]。高麗科舉基本上是兩級制,即相當于鄉試的“界首試”和“禮部試”。高麗禮曹相當于掌科舉的禮部,但實際主持考試的是國子監。相對較晚的恩賜科及糊名等新環節顯然受宋制影響,一度取法北宋三舍法設立“七齋”[1]22,公元1102年(高麗肅宗七年)專門為來高麗的宋文人設立別賜科。高麗科舉不定期舉行,雖然高麗宣宗一度下詔三年一試,但未真正實行,有時一年一試,有時兩年一試,甚至隨時視情況考試[1]126。高麗科舉在武臣當權前的錄取數量亦無定額,從三四十人到幾人不等[12]。高麗現職官吏可以應舉,非遼朝有限的制舉所能相比,應視為高麗科舉特色。高麗太祖“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殊方異土,人性各異,不必茍同”[13]的祖訓得到后嗣忠實恪守。
遼初科舉局限于南京道,統和六年之前找不到一例幽云地區以外之漢人應舉者[14]。國子學中的契丹貴族子弟不得參加科舉,世選是契丹貴族子弟的特權,漢族大姓亦可以依靠恩蔭躋身仕宦,科舉并不被遼代早期社會看重。圣宗、興宗、道宗幾代皇帝連續倡興儒教,均曾御試進士,禮遇一再水漲船高,成于元末的《遼史》雖然無《選舉志》,但《禮志》詳細記載了進士登科禮儀。《契丹國志》載及第報喜儀式隆重熱烈,“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及第者直接授官,第一人授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的高官[15]。科舉對遼后期政權輻射越來越顯著,南樞密院官僚幾乎都是進士出身[14]。宗室后裔耶律蒲魯因擅舉進士導致興宗怒鞭其父,但還是被重用為親信近臣牌印郎君,沖破禁令本身就有象征意義。天祚帝天慶五年(公元1115 年)耶律大石舉進士,科舉已對各民族開放。遼朝多次制舉,以貢明經、舉賢良等搜求人才,進士及第者和低級官吏均可參選,與其牽強地歸于唐制的繼承,民族政權成長中的開放性[16]則更引人入勝。
相對于遼與高麗,金朝科舉最具創新性。金朝進士劉渭《重修府學教養碑》載曰,“我國家應天順民,雖馬上得天下,然列圣繼承,一道相授,以開設學校為急務,以愛養人才為家法,以策論、詞賦、經義為摧賢之首”[6]1194。若以開放公平論,這雖有溢美,也并非過于失實。金朝官學生總額超過6000 人[17],《金史·食貨志》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3 年)全國1878謀克①謀克是金代女真社會最基本組織,由最初的圍獵編制發展為軍事組織,首領常由部長或族長一人擔任,完顏阿骨打定300戶為謀克,10謀克為猛安,遷居中原各地后變革為地方行政組織,具有行政、生產與軍事合一的特點,謀克相當于縣,但地位高于縣。,以每謀克2 人入學計,女真官學生超過3000人。金朝110 年開科41 次,取士6150 人,平均每科150 人[18],遠遠超過遼。據元好問所輯《寄庵先生墓碑》,李平父[19]749世醫為業而登詞賦進士第,巫醫不得應舉的禁令已經突破。以金章宗明昌年間(公元1190 年~1196 年)為例,進士籍貫可考者覆蓋全國19路中的15路[20]47,進士出身可考者家世從宰執到平民的分布呈遞增狀態,證明了科舉取士階層的廣泛性[20]74-75。
海陵王以后形成鄉試、府試、會試、殿試的四級制,府試則為金朝新創,朝廷派要員主考,于公壓縮了地方官上下其手的舞弊空間,于私免去大批落第舉子赴京趕考的奔波之苦。金世宗大定年間(公元1161 年~1189 年)設大興、大定、大同、開封、東平、京兆六處府試,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 年)新增遼陽、平陽、益都,承安四年(公元1199 年)又增太原,十處府試遍布要津,遠至胡里改、蒲與等路及各招討司的邊疆士子均可以就近參加府試。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 年)詔免形同虛設的鄉試后,府試事實上替換為三級考試中的鄉試,成為元明清各省鄉試的藍本。
大定十一年(公元1171 年),金世宗創設以女真字為程文的女真進士科,這是少數民族科舉制的首創。女真進士科考試內容從較早的每場500 字以上策一道,循序漸進地增加了詩賦、試論,以策論進士著稱。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 年),章宗繼位后“詔許諸人試策論進士舉”,即將女真進士科向漢族和女真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士子開放,同時對其程式進一步規范:“以詩、策合格為中選,而以論定其名次。”[2]1142由此不難看出,經過近二十年的培育,金朝統治者對女真進士科已經非常自信,并無保守封閉的狹隘民族主義。據都興智統計,有確切記載的女真進士62 人中,官至三品者50 人,任宰執者16 人。章宗朝13 名女真宰相有3 人是女真進士,宣宗至金末女真宰相出身進士的有12名[21]。《金史·忠義傳》以身殉國女真義士43 人中進士出身者多達17 人。后世蒙古進士榜與八旗科舉不過步其后塵而已,成效則難望其項背。
金代科舉考紀整肅之嚴厲遠過唐、宋、遼與高麗。考場設“至公樓”,主考官登樓監考,無論哪一級考試均以目不識丁的軍人巡場,殿試時甚至一名考生配置一兵。考生搜身甚至達到“解發袒衣,索及耳鼻”的地步,如此苛待本應禮遇的士子,令統治者倍感尷尬,“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2]1147。考生一有舞弊即重罰,主考若有徇私決以沙袋[22]。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對考生提出更高的要求,擴展考試內容與難度:“以《六經》《十七史》《孝經》《論語》《孟子》及《荀》《揚》《老子》內出題,皆命于題下注其本傳。”[2]1136-1137從海陵王、世宗到章宗,金代科舉漸入佳境,三品以上高級官員中進士的比例一路攀升到60%[23]。據元好問所輯錄《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 年)登科60人中除官至宰相的數人外,官至刺史、節度使者過半,被譽為“龍虎榜”[19]725。金代碑銘體現科舉深入人心:“入仕者惟舉選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19]877-878
三、結語
10 到13 世紀處于東北亞核心的遼、金、高麗在科舉領域共性較多,進士科最受重視,進士及第備受榮寵,民族政權不約而同因科舉而文治,但就縱向抑或共時的對比而言,不均衡性表現得復雜而明顯。相對于金初借才異代較為迫切不太介意借鑒的文化對象外,高麗與遼均對唐制更為認同。二者對于共時發展的宋制需要一個從認知到認同的過程,后來蘇軾在遼境和朝鮮半島的聲名鵲起不難佐證這一點。實力雄勁的遼朝面對相對文弱的宋朝,在文化自信上肯定與傳統四夷對天朝的敬畏完全不同。朝鮮半島自新羅時代即有慕唐之風,新羅士子在唐以賓貢登科多達幾十人[24],高麗將早期契丹或女真政權視為夷狄,宋朝守內虛外不勤遠略,對外政治聯系與文化交流相對不熱心,文化借鑒前提的共情認同又非短期所能快速培養起來的。
遼、金、高麗無論對外借鑒的傾向性還是個性文化差異,應聯系到其各自對于科舉為用還是為體的預期設計及動態調整上。統治者開科取士均出于維護王權統治的需要,遼如是,金如是,力圖削弱豪族以強化權力的高麗亦如是。前兩者在科舉推進文治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中漸漸從為用求實升華到為體求化的高度,海陵王、金世宗在提振科舉爭取儒臣鞏固封建皇權上非常主動,文治水平更高的金章宗對于科舉更為熱情,甚至體貼地安排考生沐浴更衣。受科舉催化的遼金后期社會彬彬儒化,不約而同地呈現華夷同風的氣象。科舉是滲透上層建筑的文化建樹,一如文治的遼金難以抗衡后起武力的凌厲攻勢,高麗早期興文治以強王權的科舉在后來的武臣專權下陷入委頓[1]25-56。亦如遼金科舉會被元明清接力延續一樣,朝鮮半島的科舉也會在高麗王朝之后的朝鮮李朝重煥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