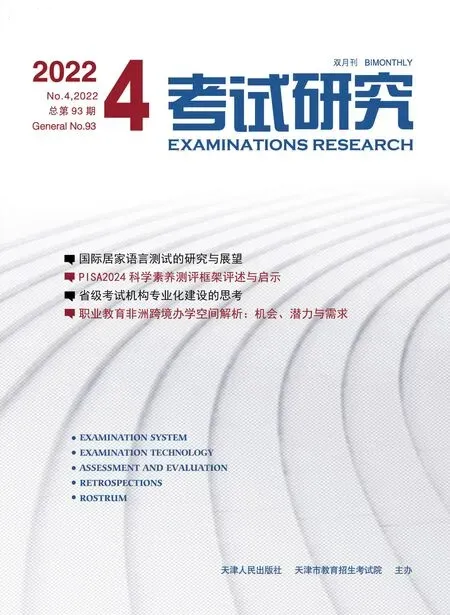科舉至公若權衡:讀程偉《清代河南鄉試研究》有感
馮用軍
科舉考試制度是中國古代及其儒家文化圈附屬國分類分層選拔文武官員的銓選制度,也是中國古代運行1300 余年(隋大業元年即公元605 年創立至清光緒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 年遽廢)的“國家掄才大典”。科舉考試運行正常的時候(唐宋元明清),基本是中國國家統一富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強烈的時期;運行異常的時候(五代十國、遼金西夏),基本上是中國國家動蕩分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薄弱的時期。由此可見,科舉考試制度對古代中國維護國家統一、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有重大影響,1905 年科舉遽廢也成為壓垮清政府走向歷史終結的“最后一根稻草”。
鄉試是科舉考試系統中競爭最激烈的一級考試,是最能反映科舉考試制度公平公正公開與否的關鍵“砝碼”。鄉試,唐宋時稱為“鄉貢”“解(jiè)試”,是由各地州府主持、皇帝欽派的主考官主考、地方學正(全稱“提督學政”或“督學使者”,也稱學政、學臺、學院、學憲、學道、學使、提學,或俗稱“大宗師”)監考的考試。明、清兩代定為每三年考一次,在各省省府(包括京畿)舉行。凡本省生員與監生、蔭生、官生、貢生等,經科考、歲科、錄遺合格者,均可應試。逢子、午、卯、酉年為正科,遇慶典加科為恩科,考期均在八月,故又稱“秋闈”(與會試的“春闈”相對)。中試者稱為“舉人”,第一名稱“解元”,第二名稱為“亞元”,第三、四、五名稱為“經魁”,第六名稱為“亞魁”。凡中試者正常情況下都可參加次年在京師舉行的會試。
鄉試是五等七級科舉考試承上啟下最關鍵的一環考試(童生試—縣試、府試、院試,取中者為秀才,縣府院案首多人,三試皆第一者稱“小三元”;科考、鄉試,取中者為舉人,第一名稱“解元”;會試,取中者為貢士,第一名稱“會元”;殿試,取中者為進士,第一名稱“狀元”,鄉、會、殿三試皆第一者稱“三元及第”;復試、朝考,按考試名次并結合殿試、復試成績名次授官,第一名稱“朝元”)。清代吳敬梓所著《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舉》一節充分說明了鄉試中“秀才”與“舉人”的“魚龍之變”——上可攻“進士”、退可守“大挑”。宋代以降,會試、殿試基本不黜落,童生和秀才雖然享有一定的“優待”,如童生獲得秀才功名后,可以享有免除徭役田稅兵役、見官不跪、遇罪不輕易處罰(先奪去功名后才能審訊)、出門游學免費糧米膏火和擔任私塾教師等權利,但原則上獲得高級功名的舉人才真正獲得了選官的資格,一只腳已經踏入官場——“頭頂知縣,腳踏教官”,即使當不成官也能改善經濟待遇、提高社會地位、成為地方士紳、平等會見知縣等,正常情況下明顯比秀才的綜合待遇要高很多、發展空間要大得多、政治前途要光明得多,這也是孔乙己落第后“慘死”、范進中舉后“發瘋”的重要原因。
“天地之中,豫見河南”,河南省是逐鹿中原文化的發祥地,是中國最后一科鄉試、會試的舉辦地。自從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秋各省舉行丁酉科鄉試、二十四年(1898 年)舉行戊戌科會試之后,科舉考試制度的命運同清政府的命運一樣——強弩之末、衰廢崩潰、回光返照。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秋庚子科鄉試因義和團事件而作罷。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廢止八股文改試經世致用的新學并補行庚子恩科鄉試,僅在云南、甘肅、貴州、廣西、廣東舉行,順天、江南等12 直省則于二十八年(1902 年)補行庚子恩科、辛丑正科并科鄉試。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由于八國聯軍入侵破,破壞了順天貢院和禮部貢院等科舉考試場所,導致全國各地舉人無法“進京趕考”,于是清政府下令借闈河南開封貢院(舊址今河南大學校內)“補行”辛丑恩科、壬寅正科并科會試,五月舉行殿試錄取進士315 名,閏五月舉行了空前絕后的經濟特科考試及復試,8月又舉行癸卯恩科鄉試(順天鄉試亦借闈河南開封貢院,其它各省貢院按章同步舉行)。光緒三十年(1904年),為慶賀慈禧太后七旬生日,清政府將本是正科的會試和殿試改為恩科,3月仍借闈河南開封貢院舉行甲辰恩科會試;5月放榜,中舉者276 名,會元譚延闿;7 月舉行殿試,273 名貢士參加,狀元劉春霖。1905 年,清政府兩宮發布上諭“廢科舉興學堂”,河南省成為中國最后一科鄉試、最后一科會試的舉辦地,運行1300 年的科舉制度在“豫”劃上句號,在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后成為“絕響”。
程偉,2012 年9 月進入劉海峰教授門下攻讀教育史專業“科舉學研究”方向博士學位,他的博士選題為“清代河南鄉試研究”。2016 年9 月,程偉的博士學位論文獲評為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分會每屆只評出中國教育史、外國教育史優秀博士論文各一篇,獲評殊為不易。2020 年3 月,程偉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清代河南鄉試研究》(57.5 萬字,以下簡稱“程著”)列入劉海峰教授主編的“科舉學研究叢書”,由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2021 年12 月,程著獲評為天津市第十七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當時以中級職稱申報并獲評省部級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甚為難得。以上從多個側面證明了該書是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較大社會反響的優秀科舉學專題著作。作為“科舉地理學”標志性成果之一的《清代河南鄉試研究》,可以說是目前海內外首部系統研究清代河南鄉試的專門性論著,對山東、廣東、河南、福建、河北、江西、貴州、湖南、湖北等其他直省鄉試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閱完全篇,細細品來,該書四個特點躍然紙上:
一是比較系統完善。鄉試是科舉考試系統中考生來源最復雜、組織運行難度最大、作弊與反作弊斗爭最激烈、程序儀節最多樣、淘汰率最高、科場條例最完備的子系統。程著以清代河南鄉試為獨特研究對象,充分運用了錢學森院士提出的“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M-S 法)”,綜合利用歷史、比較、文獻、計量等具體研究方法,將清代河南鄉試系統分解為鄉試制度體系與活動中的場期與配額、規程與儀節、經費與供應、考官與執事官、解元和舉人的地域分布等子模塊,對這些子模塊的關鍵性要素作了系列專題研究,最后獲得了系統性分析結果,可以輕松讓讀者對清代河南鄉試系統“一目了然”。例如對河南鄉試供應情況的分析,不僅系統分析了闈中人員(監臨院、主考、內監試、外簾四所官員、外簾四所書吏等)飲食的供應情況,具體到主食、副食、蔬菜、肉類、調料、煙酒茶的名稱和數量都列得一清二楚,而且系統分析了闈中人員的用具供應情況。在劉海峰教授給程著寫的序中,“系統性”也被反復提及,如“對清代河南鄉試錄和相關檔案盡力搜尋,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按照鄉試實施的時間順序,以考生為中心,分考生入闈前、考生入闈及考試期間、考生三場完竣出闈后三個階段,對清代河南鄉試實施前后的規程與儀節作了系統探討”等。可以說,類似的系統性論述和專項全要素統計是其他鄉試研究論文或著作所不具備的。
二是比較客觀公允。研究歷史,有幾分史料說幾分話,有一分史料就只說一分話。不少歷史文化制度研究者,由于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修養,在研究過程中容易陷入對自己所立身的學科的特定研究對象的某種“美化”和“輝格化”,對其不足或弊端往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有意忽視或無意得見)。如在科舉研究中就有類似的極端情況,即偏重對科舉“投牒自進,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客觀公平、“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促進階層流動等“贊賞有加”,而對科舉舞弊、科舉冒籍、八股文扼殺創新、館閣體書法僵化等“一筆帶過”。實際上,作為專業的科舉學研究者,對科舉歷史人物、事件、活動、思想、文化、制度等,應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刻意貶低。持論中和、評述公允,才是歷史文化研究的應有態度和科學方法論。所以,當代社會的科舉專業研究者對千年科舉的“蓋棺定論”、為科舉“平反”和“正名”等均在學理之中,但為科舉考試制度“美名”則是不可取的。科舉不能“死而復生”。1903 年光緒癸卯科河南鄉試監臨官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卷二中形容科舉“功令本極嚴肅,人心先存敬畏”。程著秉持了“科舉至公”的精神理念,著書立說前心中先存了對作者、讀者、編輯、出版社等的“敬畏之心”,所以在論述河南鄉試的整個過程中,都盡力依據珍貴的科舉文獻史料做出相對客觀判斷,給出中立公允結論,如利用《甲午科河南鄉試儀節》《豫省文闈供給章程》對鄉試儀節、文闈供給的邏輯論述,幾近先秦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形容“東家之子”的“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深諳中庸之道,可謂恰如其分。
三是比較扎實細致。以史為鑒、論從史出、以論帶史、史論結合是歷史文化制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邏輯進路。優秀的歷史文化制度研究就是擺事實、講道理,事實要清、細(遵循實事求是原則),道理要順、和(遵循邏輯自洽原則),即通過事實論證(例證)、道理論證(引證)、對比論證(喻證)讓人相信歷史、文化和制度,樹立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傅斯年說,做歷史文化考古研究,采集證據既要如李白《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也要“動手動腳找東西”,極盡搜羅之能事,勿使有遺漏也。程著利用千方百計搜集到的兩份其他省所無的珍貴科舉文獻,不僅對清代河南鄉試的各個子系統進行了扎實分析,而且還對鄉試經費、貢院物資供應等進行了可視圖化和定量細化,文字與圖表結合相得益彰,可謂內容穎異、構思別致,僅相關統計表格和量化圖示就數以十計。如主考官辦公場所陳設器具表,就詳細列出了玻璃燈(四盞)、鏡屏(一座)、花瓶(一個)、座鐘(一架)、掛鐘(一架)、掛鏡(一面)、文具盤(一個)、粗帽架(二對)、細帽架(三對)、紅彩綢(三掛)、帶套宮燈(四對)、桂花(兩盆)、金桔(兩盆)、柚子(兩盆)、佛手(兩盆)、各樣花草(一池)、中堂(一軸)、畫屏(四扇)、對子(兩幅)、橫披(一張)、直條(兩軸)、小屏(四扇)、官銜紗燈(一對)、雙席天棚(一座)、竹堂簾(一掛)、門簾(一掛)、窗簾(十一掛)等器具的名稱和數量,絕對是下了苦功、用了心思。書后還專列八份附錄,“附錄一”到“附錄六”詳細統計了河南鄉試歷科首場試題、部分科次五經義試題、歷朝舉人分府州縣統計、歷科主考官、河南地名古今對照、舉人題名錄等信息,堪稱斷代科舉史、科舉地理學、科舉計量學等稀見的量化分析樣本,其特殊性、完整性、稀缺性特別具有史實、史料、史論、史觀、史學價值,值得其他學者做后期研究。
四是比較通俗易懂。宋朝詩僧釋惠洪的《冷齋夜話》卷一載:“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于鄙俚。”彭乘撰宋代文言軼事小說《墨客揮犀》亦有載。白居易的詩歌通俗易懂、簡約直白,如他作為新科進士參加曲江賜宴后到“雁塔題名”的詩——“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所以流傳甚廣、婦孺皆知。歷史文化制度研究,特別是一些專題史研究成果,往往佶屈聱牙、晦澀難懂,所以多“曲高和寡”,結果基本是“束之高閣”,不為百姓所識。眾所周知,以科舉考試制度為獨特研究對象的新科舉學,雖然已經從20 世紀的中國式“險學”蝶變為21 世紀的國際性“顯學”,但它與敦煌學、甲骨學、紅學等新國學專學一樣,仍歸于“冷門絕學”。鄉試雖然是新科舉學研究一大宗,但在整個科學界特別是哲學社會科學界、人文社會科學界,仍屬于“小眾學問”。新科舉學系列研究成果要從“陽春白雪”變成“下里巴人”,即成為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大眾學問”,必須走王艮、艾思奇、易中天等人的“平民路線”。《清代河南鄉試研究》從優秀“博士論文”歷經五年修訂成為優秀“學術著作”的過程,既是框架結構和體例布局上的扁平化,也是新科舉學研究從精英化走向大眾化的過程。程著非常注重語法規訓和章句推敲,行文風格上盡量夾敘夾議,義理辭章上盡量通俗易懂,遣詞造句上盡量雅俗共賞,段落考據上盡量短小精悍,既是一本研究區域科舉學的學術專著,可“藏之名山”,也是一本普及區域科舉地理的科普之書,可“納于大麓”。
當然,“人無完人,金無赤足”,程著仍有值得繼續提升和深度優化的地方,如:“鄉試供應奢華化”等部分觀點還有待商榷和辨析,鄉試經費等部分論據還有待充實和完善,參與鄉試工作的各種官員還要分門別類論述,影響舉人地域分布的社會文化環境還要進行專題分析,明代河南解元和舉人地域分布的狀況略顯突兀,對清代河南開封貢院舉行的最后一科中國鄉試、會試等未進行專題研究等。但瑕不掩瑜,程著總體是“有分量和水平”的,例應書評欣然推介。
老子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做學問猶如“淘沙金”,需要有舍有得、述而不作,就像唐代詩人劉禹錫《浪淘沙》所言“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劉海峰教授在《科舉學導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自序中寫道:“做學問會日日精進,科舉學也會漸漸成長。相信再過幾十年之后,或者在一百年之后,科舉學必將進入一個更為壯闊的境界。”做學問猶如“下圍棋”,需要有進有退、日積月累,恰如南宋詩人陸游《冬夜讀書示子聿》詩曰“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道德經》又云:“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定以取天下。”做學問猶如“隆中對”,需要沉潛于心、長期耕耘,好似宋代詞人柳永《蝶戀花·佇倚危樓風細細》詞云“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古往今來,著書立說都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科舉是古代中國的“國之大者”,“立足”天津大學多年的程偉博士已憑《清代河南鄉試研究》一書在科舉學界“立言”,希望他能繼續以鄉試研究為新起點,發自內心地“知之、好之、喜之、樂之”;繼續在學問中沉浸醲郁、含英咀華,嚴謹治學、日新月異,體驗“人生得法,猶度二世”;繼續在學界行走而不忘“一陰一陽是為道”的初心使命,學高為師、立德樹人,堅信“海到無邊天作岸,山登絕頂我為峰”;繼續在新科舉學學科建設、新高考改革、高校社科刊物評價等熱門學問上做出新的學術貢獻,努力從“學術新人”躍升為國內外科舉學界的“學術大咖”,從而助力新科舉學進入交叉學科建設的“更為壯闊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