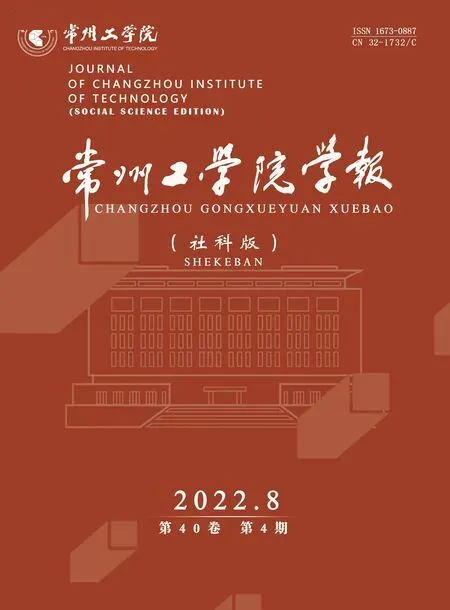燈火闌珊處的古典詩傳統
——20世紀30年代“晚唐詩熱”對現代詩創作的啟發
吳俊辰
(南寧師范大學文學院,廣西 南寧 530299)
于20世紀30年代掀起的“晚唐詩熱”,是廢名、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現代派詩人在對現代詩發展道路的探索中,自發向傳統回眸并對傳統“再發現”的過程。時隔90多年,在“現代詩”這一體裁的邊界已經越來越模糊的今日,反思20世紀30年代的現代派前輩詩人們對傳統詩學的重釋,重新發掘古典詩歌傳統以啟發現代詩歌創作,以中國傳統文化哺育中國現代文化,對現代詩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一、 晚唐詩熱的發生
在五四后的新詩探索初期,胡適選擇了“明白易懂”作為白話詩的美學標準,他認為:“看不懂而必須注解的詩,都不是好詩,只是笨謎而已。今日用活的語言作詩,若還叫人看不懂,應該責備自己的技術太笨。”[1]而在向傳統追根溯源時,胡適也將一向以明白易懂而著稱的“元白”詩風作為源頭,并將以綺靡、隱僻、唯美為特征的“溫李”詩風斥為“妖孽詩”。但隨著更多詩人投身新詩寫作并探尋新的發展方向,不同的聲音也越來越多。早在20世紀20年代,針對胡適“明白易懂”的美學標準,周作人就已經提出了質疑:“一切作品都象是一個玻璃球,晶瑩透澈得太厲害了,沒有一點兒朦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種余香與回味。”[2]在30年代,以廢名為代表的現代派詩人們則不約而同地提及對晚唐詩的喜愛。如廢名就曾于北大講授新詩時說過,“現在有幾位新詩人都喜歡李商隱的詩”[3]37。何其芳也表示自己曾“蠱惑于那種憔悴的紅顏上的嫵媚”[4]。
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晚唐詩熱”固然是對胡適“明白易懂”的美學標準的質疑,但更多的則是廢名、林庚、何其芳等現代派詩人對所謂“滄海月明”“玉露凋傷”的古典綺麗的傳統詩美的沉醉,這種對“含蓄幽深”之美的肯定既展現了他們與新詩萌芽初期的標準所不同的美學追求,也探索了一條處于“回歸傳統詩學”與“投身西方理論”之間的道路——對古典詩傳統進行重新闡釋,并以古典美為養分為新詩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現代詩并不代表著和古典相背離,白話詩也正如梁實秋所批評的那樣應該以“詩”為關注對象而非僅僅追求“白話”,白話雖天然帶有“明白清楚”的特點,但這特點并非詩的必要的質素,如果因為追求白話而忽略甚至放棄了詩美,詩就會失去與其他文體的界限。同樣,如果因只追求現代而刻意背離古典,空守著傳統的文化瑰寶而不知善用,無疑也會拖累現代詩發展的腳步。
“晚唐詩熱”的發生,既是詩人對古典詩美天然的親近,也是詩歌探索道路中對傳統詩學自覺的重新發掘。雖然其目的是以晚唐詩歌“綺麗幽深”的特征來抗辯胡適的白話新詩理論,但敢于向傳統回眸并從古典詩歌中汲取養分,已經顯示了廢名、林庚、卞之琳、何其芳等現代派詩人廣闊的眼界和從容的氣度。當然,“晚唐詩熱”的發生從歷史背景來看具有其必然性。
首先,從文學的發展規律來看,平白易懂與晦澀幽美本就在歷史上輪流占據主導位置,雖然新詩在萌芽階段以“白話”為重心,但隨著白話文學整體的發展及完善,其本身對藝術性的要求會自然拔高,當早期白話新詩在創作方法上所作的簡單處理無法營造詩歌所需要的詩意時,詩人們便會自覺找尋能讓新詩蛻變的道路,他們自發地“進入對于傳統具有現代性眼光的選擇與觀照的自覺,對于西方現代派詩歌與中國傳統詩歌之間藝術聯系的溝通與對話的努力”[5]。而晚唐詩之所以會受到現代派詩人們的青睞,其本身所包含的詩歌所必需的優秀質素是最核心的原因,唐朝作為詩歌盛世,即便是末期,這一時期的作品在詩這一體裁上的完成度和藝術性都是頂尖的,并且由于晚唐詩風所帶有的含蓄幽深之美既能揭露出早期白話詩過于樸素的缺陷,也具備使人回味無窮的深厚文化底蘊,完美符合現代派詩人們對詩歌這一體裁的理想,所以才將晚唐詩作為古典詩學的代表,從中提取優秀質素來對白話新詩進行完善。
其次,任何一種文學思潮的流變都與其特定的社會背景有關。與大氣磅礴的盛唐詩歌不同,晚唐的詩人們受當時動蕩的時局影響,詩歌作品中往往透露出沉郁幽怨的氣質,這些作品大多精致華美且含蓄晦澀、余韻幽絕且婉約綺麗,其主要特征為詞句艷麗、意境綺靡、情感綿長。而30年代的詩人們同樣身處革命與戰亂之中,“晚唐詩熱”的主力軍們同樣面臨理想與志向被現實所壓迫的困境,與晚唐大多數詩人的選擇相似,他們的作品同樣“回避、疏離社會政治,在大學里,在文壇中,在將求學問與藝術中安頓身心,尋找出路”[6]。類似的生存困境與相投的志趣使詩人們自發地熱愛著晚唐詩,并產生了希望參考其創作對新詩發展進行指導的想法。
最后,30年代的詩人們,所接受的大多是古典詩學教育,從小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其在審美志趣上天然帶有古典特征,這便使他們在新詩的創作中自覺地向傳統文學回眸,希望尋得能為新詩的完善起到作用的古典素材。而晚唐詩歌在辭藻與技巧上精美綺麗,正能彌補白話新詩在當時因過于直白樸素所導致的詩意的缺失,情感上晚唐詩纏綿悱惻,也正迎合了現代派詩人們的創作目的,所以選擇晚唐詩歌作為新詩創作的指導對象,絕非是詩人偶然的偏愛,而是多種因素結合下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但現代詩作為一種文體,發展至今也仍處于不成熟的狀態,應對包括“晚唐詩熱”在內的新詩百年來所做的探索和嘗試進一步沉淀,并深入反思,為新詩創作的進一步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讓新詩能在新的時代中綻放出不遜于傳統古典詩歌的光輝。
二、 繼承和融合之外的另一種思路
在對傳統進行回眸時,我們難免面臨著如何處理現代詩與古典詩的關系的問題。現代詩之于古典詩究竟是傳承的關系,抑或是中國的古典蘊藉與西方理論相融合的結果?誠然,“融合”可以理解為現代詩發展過程中對西方理論進行學習的必然過程,如呂進就曾評價戴望舒“融合了中國古詩(尤其是晚唐五代)的優秀傳統和法國象征派(尤其是后期象征派)的技法”[7],羅振亞也曾提出現代詩人們的創作“是雙管齊下,踏著東方與西方文化的兩條鐵軌,在古老民族的歷史積淀與法國象征詩的交匯處進行古典與現代的成功嫁接的”[8]。然而新詩絕非固化地以“古典詩歌內容”填充于“西方詩論框架”,而是同時將中西的詩學理論作為營養源,試圖作出蘊涵著中國古今文化特質的現代詩歌,既能“不以為新詩是舊詩的進步,新詩也只是一種詩”[9],亦須“新于中國固有的詩,也要新于西方固有的詩”[10]。
可“融合論”的觀念放在今日卻略顯陳腐,中國古典詩歌當中諸如“溫李”、姜夔等人的創作與西方象征主義詩歌歷來便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同質性的存在恰恰表示二者無須融合。例如西方詩、古典詩和現代詩三者之間都具有類似的“象征”手法,但卻并不能武斷地認為現代詩的“象征”手法是古典詩與西方詩融合的結果。
雖然不同的詩人們根據個人的審美取向與人生志趣,有的沉醉于古典的詩美,如何其芳希望找到“重新燃燒的字”[4],林庚則表示“我們要借鑒的不是文言詩的陣地,而應該是它的藝術性,比如它的飛躍性呀,交織性呀,各種形象的相互交織等等”[11]。有的則投入外國詩歌理論的懷抱,如施蜇存、曹葆華等人。但毋庸置疑的是,現代詩從古典詩歌與西方理論中都汲取了力量,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文學史序列中的一員,絕非“融合”便可簡單概括。在處理古典詩傳統與西方詩論的關系時,我們還需以一種更加審慎的態度,以避免落入呆板的形式主義的窠臼。
“融合”雖然不夠妥帖,“繼承”卻也過于機械。白話新詩不論形式還是內容都和古典詩迥然不同,雖然詩人們在新詩創立初期對古典詩進行了刻意的疏離以劃清界限,但經過近10年的曲折發展,到30年代“晚唐詩熱”的發生,可以說詩人們已經在重新發現并探究古典詩的寶庫,而寶藏的使用方式則是多元的。就如艾略特所說,“如果傳統的方式僅限于盲目的或膽怯的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傳統’自然是不足稱道了……傳統是具有廣泛得多的意義的東西。它不是繼承得到的”[12]。當我們回眸古典詩傳統,所想到的不應是“回歸”或者“繼承”,而應是一種“繁衍”或“發展”,我們不能否認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下現代詩與古典詩的承續性,但更不能因為兩者在時間空間上的關聯就將他們直接以時序聯結。
羅小鳳的《古典詩傳統的再發現——1930年代新詩的一種傾向》認為現代詩對古典詩傳統是一個“再發現”的過程,這種“再發現”是指詩人們對傳統詩歌內容的重新利用,在總結古典詩傳統的優秀質素的基礎上對新詩進行的“糾偏與歸位”。她將“古典詩傳統的優秀質素”歸納為“詩的內容”“詩的感覺”“想象”“詩語魅力”和“韻律與節奏”5個方面,囊括了從表層的語言及技巧到深層的內容與詩意等維度,但這種質素上的挖掘與使用和詩人自身的文學底蘊牢牢掛鉤,這種表述使現代詩與古典詩的復雜羈絆幾乎成為了詩人的個人志趣。現代詩與古典詩傳統理應有著更內在的深層次聯系,前文所提到的“繁衍”與“發展”也許正是另一種思路——同樣作為“詩”的體裁而存在,現代詩與古典詩有其內在貫連的內核,這種內核決定了“詩”能否成為詩,決定了中國現代詩與“中國古典詩”一脈相承的“中國韻味”,并且在時代的變遷中不斷適應及磨合。一方面像羅小鳳所言依靠詩人的發現摸索著詩歌新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能不因詩人的關注與否而潛移默化地影響全體中國詩人,這也是為何即使在沒有主動向古典回望的詩人的作品中,我們也時常能看到一些古典的質素存在。“繁衍”既代表了一種基因鏈的繼承與延續,也蘊含著動態性的適應和改變,象征了“詩”這一體裁內在靈魂的活力,同時也能彰顯“詩”作為一個族群在磨礪中壯大的發展性和海納百川的包容性。
但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晚唐詩熱”的發生存在一個必要的基礎條件,即當時的新詩創作主力們接受的大都是傳統的古典詩學教育,他們從小浸淫于傳統詩歌的熏陶之中,有著豐厚的古典文學底蘊,會自然將經由傳統教育而培養出的審美理念、詩學觀念、人生志趣融入詩歌創作當中。這其中雖然少不了詩人對新詩的創作方法自發性的探索,但若非其自身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底蘊,對古典的回眸也難免會面臨“無米之炊”的窘境。卞之琳曾自言“喜翻閱家中所藏的詞章一類書籍”[13]。廢名也曾說過“中國詩詞,我喜愛甚多,不可遍舉”[14]。“晚唐詩熱”這一現象雖以晚唐為中心,但實際上將整個傳統文學都作為了可以取經的寶庫,這些現代派詩人們舉晚唐為代表提出了審美的多元化,從而打斷了由胡適標舉而壟斷的“明白易懂”之詩風。在從古典詩中汲取營養時,用現代性的眼光去考察晚唐詩歌,也能將當中的隱僻、晦澀與法國的象征派相聯系,從而對詩歌創作有所啟發,再從內容、感覺、語言、技巧等多個角度對現代詩進行全面的打磨,嘗試探索出一條中國所獨有而不同于外國的現代詩道路。
綜上所述,新詩只不過是詩歌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對時代進行必要適應的結果,雖然從其創立來看受到了諸多外來因素的影響,但無論是它的出現還是其發展,都依然是中國文學演變進程的一部分。現代派詩人對“晚唐詩風”的推舉,也是現代詩發展的必然過程。但時至今日,已經鮮少有人如30年代的現代派詩人那般有著豐厚的古典文學底蘊,面對古典詩傳統逐漸從現代詩中銷聲匿跡的情況,詩人亟須向古典進行一次全新的回眸,這不僅是對古典詩與現代詩關系的重新審視,更是讓中國的現代詩變得更加“中國”的必然要求。
三、 如何參考晚唐詩熱的經驗為現代詩重設框架
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詩就如黑格爾的歷史螺旋發展論那般不斷在“晦澀含蓄”與“明白易懂”之間徘徊,經歷了最初期胡適的白話詩學主張,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的“晚唐詩熱”重提“含蓄幽深”之美,50年代末的新民歌運動則又重新把清楚明白放到了第一要義,80年代的朦朧派詩人也像30年代的現代派詩人那樣舉起“朦朧美”的大旗向“明白易懂”的詩學宣戰,現代詩不斷在中國各時期的歷史背景下改造著自身適應著發展。
現如今“第三代詩人”重新撿起平白如話的語言,將反崇高、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的內容作為表達中心,詩歌又重新走向了胡適的“明白易懂”的路子。同時,“詩”借助移動互聯網而泛濫成災,這個時代的詩已經從胡適時期的“白話詩”進一步變為“口語詩”,更有無數不足以稱為詩的內容,將“現代詩”的界限無限放寬,幾乎已經找不到詩之所以能稱之為詩的標準。“薛蟠體”“梨花體”“口水詩”等將“淺白”發展到極端的“詩”大行其道,并且扭曲地將“淺白”與“粗鄙”“低俗”相掛鉤,背離了詩本應具有的美感,這不能不說是“現代詩”的悲哀。
30年代的現代派詩人是新詩出現后第一批向“明白易懂”的詩風提出有力質疑的群體,也是第一批在回眸古典詩傳統上作出卓有成效探索的詩人。要對現今諸多“非詩”亂象進行糾偏,不妨借鑒“晚唐詩熱”的經驗,重拾古典詩傳統中能為現代詩發展提供方向的優秀質素,厘清現代詩作為“詩”所應有的邊界,并力求作出“更新,而且更是中國的了”[15]的現代詩。
現代詩在創立之初,為了與古典詩相區別而打破了各個方面的框架,既突破了古詩“溫柔敦厚,哀而不怨”的特點,也不重古典詩詞的平仄格律和韻腳,語言上則全面使用白話而放棄文言。但與古典詩相區分并不意味著要將“詩味”全然放棄,胡適的詩歌缺少“新技巧”和“新意象”,這正是深厚的古典詩文化底蘊所擅長的。
以30年代現代派詩人所闡述的內容為參考,關于如何作出區別于古典詩歌同時具有“詩”的特征的現代詩,框架大致有以下3點:第一,有內涵。詩應該寫詩的內容,并且包含詩的感覺。第二,有韻律。詩應該具有不同于散文與小說或其他文學體裁的韻律,并關注詩歌的音樂性。第三,有美感。不論是語言美、意象美或是意境美,現代詩應是審美性的,對美有著必然的需求。以上3點并非要像古典詩那般給現代詩設定一個固有的框架,讓現代詩失去其重要的“自由性”,而是為了確立現代詩作為“詩”而存在的必要的質素,使詩可以不再被當成“分行的散文”。
首先需要辨明的是,詩歌的“內涵”與其語言是明白易懂的或是晦澀含蓄的并無矛盾,為了晦澀而晦澀的詩一樣會缺乏內涵,而明白易懂的語言也同樣可以意蘊悠長。胡適所主張的白話新詩將內涵拋之度外,而“內涵”既是廢名口中的“詩的內容”,也是林庚與卞之琳、何其芳等詩人關注的“詩的感覺”。從內容的角度來說,“新詩要別于舊詩而能成立,一定要這個內容是詩的,其文字則要是散文的”[16]。在廢名的理解中,古典詩有很多作品用“詩的文字”表現了“散文的內容”,這些作品只因為創作于古典詩所固有的格律和體式中所以才能作為詩而存在。而在現代詩中,由于沒有了明確的語言與形式上的框架束縛,所以必須要著重突出詩的內容。“只要我們有了這個詩的內容,我們就可以大膽的寫我們新詩,不受一切的束縛。”[3]37廢名將舊詩與新詩相互對比,對內容和文字進行了跨越性的思考,“詩的內容”代表的是由感性的想象和意象構成的內容,比如晚唐詩中的“云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而“散文的內容”則側重理性的敘述與說理,譬如“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種“二分法”的區分方式只是方便理解,實際創作中則更為復雜。廢名所說的“詩的內容”的含義并不局限于文本,作為他的詩學的核心理念,“詩的內容”囊括了詩意、感覺、情緒、風格等諸多形而上的內容,前文所述的“內涵”也更多地指向這個多元層面。這些不易把握的方面被廢名、林庚等人論述為“詩的感覺”,他們要求新詩在創作中要保持充沛而飽滿的詩意,能夠專注于這種感覺的塑造而非耽于外在的敘述與描寫,這其實依然在描述一種詩的本質,這種本質決定能否成為詩。這種“詩的感覺”表達的是一種審美的興味,就像廢名用李商隱的《錦瑟》一詩舉例,“我們想推求這首詩的意思,那是沒有什么趣味的。我只是感覺‘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這兩句寫得美”。何其芳也說過,“對于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他的表現”,對于詩他則“縱然表達著意思但我欣賞的卻是姿態”[4]。可以看出,林庚與何其芳都更看重詩所表現的那種美的感覺,這種感覺的觸發讓他們得到審美的享受,故而他們在自己的創作中也貫徹了這種詩學理念。何其芳的《月下》一詩著重于塑造月下那凄清的意境,用紛繁的意象含蓄地表現思念之情,情感與意象渾然一體,他以自己的方式傳達出“詩的感覺”。林庚的《夜》《破曉》等詩也是如此,將感覺的表達放在了首位。
其次是現代詩必須要有詩的韻律。詩與歌的同源與分流不必贅述,但二者確實依然保持著一些內在的共性。詩的“音樂性”作為其固有屬性,至少包含了三重含義:一是語言層面,由物理性質帶來的,類似于古典詩平仄與格律的語言音樂性;二是樂曲層面的,像我國古代的“詞”和“樂府”這些體裁外在的音樂所包含的樂曲音樂性;三是一種“語言表現本身的音樂性”,展現意象內在的律動,“詩是一種語言的藝術,話語的某些組合可以產生別的組合所不能產生的,我們名之為‘詩意’的情感”[17]。而現代詩所必備的,應是這第三種“語言表現本身的音樂性”,它并不脫離語言,所以依然可以用“韻律”一詞來表述。林庚是30年代現代派詩人中致力于新詩韻律探索的典型代表,他所提出的“自然詩”概念就是對“自由詩”過于散漫而缺失音樂性的糾偏:“如宇宙無言而含有了一切,也便如宇宙之均勻的,從容的,有一個自然的,諧和的形體;于是詩乃漸漸的在其間自己產生了一個普遍的形式;這并非人為的。”[18]現代詩固然是由一代代詩人努力探索而得到了發展,但其自身也存在著規律,林庚便主張不要越俎代庖地為現代詩安排一個固定的格式,應讓現代詩自己去找“合適的瓶子”,詩人能做的就是“努力于自由詩”,“則全新的詩歌語言中自會產生出新的韻律來”。林庚也始終致力于此,他稱《春野》為自己的第一首自然詩,并試驗了多種定行齊言的詩體,可惜他的“新格律”卻又囿于字數、押韻等語言層面的音樂性,變得不“自然”了。“語言表現本身的音樂性”應當是對情感、意象、語言三者進行藝術性的安排,達到一種自然和諧的狀態,既追求語音上的流動悅耳,也追求形象上的天然無雕琢;既讓讀者感受詩整體的自然,也使作者的情感得到流露。這并非是給現代詩配上枷鎖并要求詩人“戴著腳銬跳舞”,而是希望現代詩擁有真正自然的韻律,出現“妙手偶得之”的天成佳作。
最后,現代詩作為文藝作品,其內容應該具有審美性,這份審美性可以來自語言的錘煉,也可以來自意象的組合,可以來自動人的情感,也可以來自發人深省的哲思。現代詩所包含的美感需要詩人學古人那般精心打磨詩藝,雕琢文字,如何其芳曾言自己墜入了那空幻光影里的“文字魔障”,“喜歡那種錘煉,那種色彩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4]。這種古典詩傳統基因自然地繼承到了何其芳的創作當中,他將自己的詩集命名為《刻意集》,表示自己要將這份古已有之的“刻意”承載下來,致力于找到詩中那“重新燃燒的字”。
語言是現代詩的基礎,除了語言的雕琢,表達上的技巧更需要詩人的玲瓏心思。對于重點關注晚唐詩的現代派詩人們,他們所發現的技巧就是“象征”。晚唐詩的含蓄蘊藉來源于晚唐詩人對直抒胸臆的拒絕,他們會用自己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安排傳神的意象,以意象來表現自己。譬如溫庭筠極富盛名的“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這兩句詩字字列錦,被前人評價為“意象具足”。廢名曾說李商隱是“借典故馳騁他的幻想”[19],并依舊援引了《錦瑟》來舉例,詩中的兩個典故相互聯系,所依靠的也是詩人非凡的想象力與十足的創造力,古典詩傳統中對典故的使用造就的“互文性”美感,不僅讓詩歌富含了悠長的韻味,更將濃厚的民族性蘊藏于其中。
“互文性”在法國符號學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符號學》一書中被定義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20]。而這種中國古典詩傳統與20世紀西方提出的理論遙相呼應的情況其實并不鮮見,“李商隱詩兼具象征性語言、超現實意象與意識流技巧;而吳文英詞則包含了晦澀的時空跳接與豐富的感性修辭”[21]。朱光潛也說“李義山和許多晚唐詩人的作品在技巧上很類似西方的象征主義,都是選擇幾個很精妙的意象出來,以喚起讀者多方面的聯想”[22]。
四、結語
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戰爭使詩人們無法再偏安一隅靜心鉆研詩歌的發展,家國的動蕩密切關聯著所有人的命運,以綺靡之風著稱的“晚唐詩”難以在這樣的年代為人們帶來力量,只能為詩人保留一方心靈的凈土。戰爭年代現代詩更傾向于以描寫現實及振奮人心為主要作用,直到戰爭結束后,詩人們才繼續以自身對詩歌的理解尋求文學的進一步發展,依據自身在“晚唐詩熱”時代所表述的觀念繼續進行相關的研究。但白話文學在這百年間的發展日新月異,改革開放之后,大眾的審美趣味更是隨著國內外不同文學觀念的交匯而產生新的變化,從朦朧派的崛起到先鋒派的探索,詩歌總是在不斷探索與創新的道路上前進著,新生代的詩人們大多成長于白話文語境,而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社會普遍推崇舶來文化,所以后來的現代詩普遍求新求變,有意識地追求“詩歌精神的現代化重鑄”,這便使發生于30年代的“晚唐詩熱”幾乎成為滄海遺珠,被遺漏在現代詩的發展史之中。
自現代詩誕生以來已經過了100余年,這百余年里一代代詩人不斷探索著現代詩的發展道路,才將現代詩推進到今天的模樣。重提“晚唐詩熱”并不代表現代詩必須以其為模板進行復古的創作,現代詩向來以“自由”著稱,有著無限的可能性與多元化的審美性,但詩作為文學作品中最為獨特的體裁,有必要以自身獨有的藝術特征與其他文學體式區分開來,這需要詩人在創作中時刻保持“自律”,在接受新時代文明成果的同時不忘回首把握住古典詩歌的蘊藉,幫助現代詩得到進一步成長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