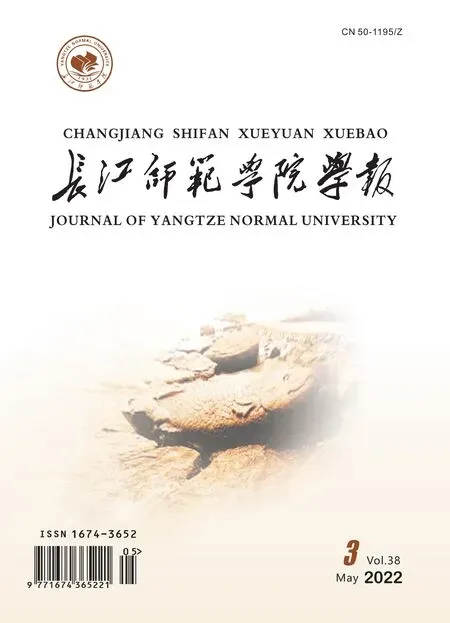前秦民族政策與統一政權建構研究
安仕博
(青海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青海西寧 810007)
一、引言
民族關系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石,而民族政策則是民族關系處理的重要途徑。民族政策的推行關系著民族地區的和諧穩定,也關系著國家統一的歷史命運。中華民族是中國境內各民族共同創造和形成的民族共同體,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要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苻氏前秦是十六國中最有希望完成南北統一的民族政權。但淝水之戰的失利促使其政權土崩瓦解,統一進程終止。這有其軍事戰略的關聯,也與前秦實行的民族政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二、前秦民族政策簡述
“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1]統一話語情境下,上天命之統御九州的天子享有獨一的地位,這也蘊含著“中央王朝正朔的唯一性[2]”這一潛在的政治命題。因而對于氐族苻氏而言,締造政權的統一也是其渴求的政治理想。前秦君主苻堅枉顧氐漢官僚的勸諫,堅持南伐東晉的國策也是在為重塑統一而努力。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政治格局,苻秦君主面對非氐民族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項民族政策。
(一)徙豪酋雜夷于關中以鎮撫他族
氐族是人數寡少的民族群體,面對人數龐雜、分布遼闊的非氐族群,氐族統治者選擇遷徙其部落民眾以求鎮壓撫慰促使太平。
永興二年(357),苻堅在平定并州二張父子反叛后,徙張氏部眾達三千戶至長安地區。建元元年(365),苻堅以堅甲銳兵摧服匈奴曹轂的反叛以后,再“徙其酋豪六千余戶于長安”[3]2889。本年九月,苻堅又徙涼州部民“豪右七千余戶于關中”[4],建元六年(369),秦滅燕后,亦遷徙除慕容暐外四萬戶的鮮卑王公大臣和部落酋民于長安,同時“徙關東豪杰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3]2898”。于攻滅前涼的376年,前秦再次遷徙其豪右赫族十萬多戶到長安一帶[5]。
這一施策的考量,一方面是以京畿地緣的輻射度和政權核心的影響力監督控馭各少數民族部落,避免其生發異心、為禍一方或圖謀反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更便利地實施對其上層首領的安撫策略。其根本出發點是徙舊民于新地以人地分割、兩兩不識,以求得統治之效。但這種遷徙之策“仍在原有酋帥的統領下,維持著軍營組織”[6],部落內部賴以生存的組織基礎并沒有根本改變,遷徙部眾只是空間范圍內由邊地至中樞的機械移動,并無融合氐與他族關系的考量。這為前秦政權的瓦解埋下了隱患。
(二)恩寵漢官以崇儒修教進達六合
魏晉以降中原呈現南北分峙格局,永嘉后衣冠漢族紛紛南往,但黃河以北地區仍然存在占據主體地位的漢民族,寓居北方的士人也時常參與北方政權中,士人群體以推行“仁政”和“王道”為政治訴求。這與苻堅“懷遠以德”的施策愿望以及“混同六合”的鴻鵠理想不謀而合。同時,苻堅也深知氐族少而寡且散布四方、漢族多而眾并局部聚攏的民族分布格局,如果不能穩妥處理氐漢之間的關系,“其統治在關中地區就無法得到確立”[7]。在這種際遇下,氐族君王與漢族官僚之間形成了契合的政治聯系,君臣上下互動影響,前秦政權也呈現出明顯的漢化趨勢。
苻堅高度重視儒家教化。《晉書》記載其八歲即延請儒師學習,且愛好儒家尋文摘句的學問。即位后,他更是敦促儒家教化,其治下也一度形成“英儒畢集”的氣象[8]15。其倡導儒學、廣設庠序以申張儒者之義。在丞相東海公苻法為苻堅奉茍太后之意而除之后則更是“禮神祗、課農桑、立學校……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9]411。苻堅還選擇“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本人更對儒生表現出親和態度,常“與博士講論”,幾乎達到每月必去一次的程度[10]。這種與儒生談經論道的頻率是歷代君主不能比的,蔣福亞稱贊苻堅這種做法“在中國歷史上的明君圣主中也屬顯見[11]”。同時,苻堅也在朝堂之上強調面對學儒而有通者或者秉行忠孝仁義以致清廉正直的人,要“旌表之[9]416”。由此,苻堅重視儒學教化可見一斑。
除推崇儒家思想文化外,苻堅也在朝堂內部重用漢族士人官僚,面對王猛、呂婆樓等王佐之才,苻堅甚為禮遇并“以(之)為股肱羽翼”[9]410。他與王猛之間圣主賢臣的關系也是歷代儒家士大夫傳誦的美談。苻堅還任用漢人鄧羌為御史以監控百官僚屬。對于漢族官員王攸進言的充盈儒家君臣父子之義的十略方針[9]420,苻堅也一并接納,并任用王攸為諫議大夫。這種重用程度除了下旨百僚,見猛如其親臨般給予漢官以政治優渥,還體現在當漢官王猛與氐族豪酋樊世出現矛盾糾葛時,苻堅即命在西廄中處死樊世,并不顧及同族血脈之親。這無疑是在向前秦各級官員傳遞苻堅重視漢族官僚并支持其主張的態度。苻堅拉攏漢官兼崇儒修教的政策是在謀求邊地氐族與中原漢族在思想文化上的契合,以儒家思想為凝聚紐帶整合氐漢之間的血脈關聯,以求共同締結統一格局。
(三)恩撫貴族以借威信懷戎進而倡導王化
面對羌與鮮卑等族首領和勛貴,苻堅亦給予其政治優待和個人倚重,以德撫之、以信攏之,使其達到心向氐秦的效果,并有意識地向他們“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3]2912。
這種民族施策集中體現在鮮卑首領慕容垂身上,苻堅對慕容垂禮之、愛之、親之、信之,其禮遇程度比漢官王猛更勝一籌。苻堅在官位爵級上賜予慕容垂以冠軍將軍、賓徒侯并親往迎接慕容垂的歸順,為表誠心苻堅還握著他的手,論與其共同圖取天下。這種信賴發展到后期,即使氐漢官僚多次勸誡苻堅,雖號賓侯、萬里列地也不能滿足其沖天之志,警告苻堅不要因小恩信而失去天下時也不改變初衷。甚至在王猛與慕容垂心生嫌隙時,苻堅也選擇站在慕容垂一邊,而對于其弟苻融“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來”[9]436的切切囑托也只是指責苻融未知德行而置之不理,其輕重選擇可見一斑。
對待同為非本族的羌族首領姚萇,苻堅也是信任至極,恩賜予他從不輕授旁人的“龍驤”之稱,并且將“山南之事”一體交給他全權處理[8]4。即便有旁人小心提醒苻堅,苻堅也緘默不言,不予回應,更不改變自己的決定。
這種威信懷戎政策一度發展到即使這些首領擁眾為亂且危害統治,苻堅也不加以處罰的地步。史載云中護軍賈雍以雷霆手段懲戒作亂的部落首領以求定邊河時,苻堅卻以“朕方以恩信懷戎狄”[3]2887的說辭阻止了賈雍的行為,同時釋放了作亂的首領們,再次走上了對他們倡導王化之政的理想路線。同樣,面對二張父子的叛亂,苻堅赦免其罪的同時以武賁中郎將和右將軍之職授予二人,對待東海公苻陽和丞相王猛之子王皮叛亂[9]459也是如此。
這種政策促使剛剛統一的前秦政權快速進入穩定的發展時期,避免了次生動蕩。同時,這種政策也在苻堅積極倡導下消除了氐族君主和其他少數民族首領之間的心理隔膜,為凝聚氐族與鮮卑羌族等對氐秦政權的向心力做出了努力,也達到了一定的效果,淝水之戰后慕容垂一度表示不愿再興舊朝,勸其子“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3]3079的事件即為明證。
三、前秦民族政策分析
前秦君主苻堅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統一政權的政治建構,面對疆域內的諸多民族采取了一系列民族政策。這些政策的實施維系著前秦政權的穩定和王朝的一統,但也有無可避免的弊端,這種弊端也促使前秦注定無法實現“混同六合”的政治理想。
(一)徙民關中:強以懾服,弱則離叛
從民族遷徙具體實踐的視角來觀察,前秦有別于此前歷代政權的徙民策略,苻秦采取的不是遷徙民眾于邊陲以實邊疆的做法,而是選擇徙民于政治中樞。關中地區是氐羌民族的發源地,也是氐族前秦的統治中心,苻堅主導的每一次民族遷徙最后的定居地都是關中。這自然是為了利用京畿地區的便利條件以管控鮮卑等族部眾,也確實發揮了維護前秦政治穩定和政權統一的作用。但這種政策的推行有一個潛在的政治前提,即前秦是穩定堅固的政治實體,同時處于權力中心地位的氐民族也是具有統管四方能力的。這一潛在的政治前提為苻融所見,針對叛復降之的匈奴左賢王的數萬部眾,苻堅也想遷移他們到關中核心地帶,但這一做法卻為苻融以若居塞內,倘見氐族之弱,必縱兵抄掠郡縣,“為北邊之害”[3]2887的理由加以勸阻。苻融看到了如果前秦失去了強壓震懾,氐民族內部出現分化呈現衰弱之氣時,素懷二心的羌和鮮卑等族,就會利用“布諸畿甸”的便利位置威脅關中,京師長安首當其沖的不利局面。這種局面對于前秦來說是有亡國之危的。如果再輔之以因政權內部“優待異族貴族與打壓本族豪強之間的政治失衡”[12]而釀成的民族矛盾,那么前秦統治的終結也許只在頃刻之間。
(二)籠漢崇儒:氐族本位,局促上層
苻堅面對北方漢民族群體采取了帶有漢化色彩的籠絡漢官和重儒修教的民族政策。這個政策的推行吸納了境內漢族官僚進入前秦中央,遂使漢氐聯合共秉國政,中原士人的碩族豪姓也都為之凝聚,令占主體地位的漢民族與氐族之間的隔閡和差異相對縮小,進而打造了“一個政治上較為穩定的小康局面”[13]191。
深入考量前秦的這種“漢化”策略就可以看出,盡管苻堅采取了敦促儒家教化和重用漢族官僚的措施,但局限于身體力行地學習和自我推崇儒學,并未見苻堅將儒家之道義推廣到前秦官僚隊伍和部眾黎庶中,修尚儒學似乎只是上層之事,是“肉食者謀之”。而對于漢官,他自始至終都局限于聽其策、用其人,而未必行其主張、使其為事,落實政令推行還是要依靠本族酋首去完成。在遇到事關政權命運之戰或做重大決策時苻堅選擇的是斥散百僚,言“吾當與汝決之”[3]2912選擇和本族將領協商,做出終極決策,不聽從漢族官員的意見,王佐之才王猛的臨終告誡也拋之九霄云外。可見,前秦統治者身上以氐族為本位民族的意識和觀念依舊存在。同時,前秦政權中躋身上層的只是漢族士人群體,他們“僅占全國人口很少的一部分”,而對廣大漢族民眾仍然采取一種“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5]。在這種政策的推行下漢氐之間的矛盾非但沒有消除,反而急劇加大了。
(三)恩撫懷戎:以恩易忠,難服其心
從歷史長時段來看,恩撫貴族以懷戎的政策從根本上是對石氏后趙政權民族鎮壓政策的一種反叛,革除了以往政權不斷激化民族之間矛盾的政策性弊病,苻秦選擇對民族首領施予恩惠并加以撫慰。這降低了部落酋首因不滿統治而制造反叛對抗行為的概率,緩和了氐秦與諸民族首領之間的矛盾,維護了前秦的統治秩序。
這種政策雖然有利于維系前秦統治,但是它同樣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前秦君主優待這些民族首領并給予崇高的禮遇,但始終未能撲滅他們反叛的火苗。這種政策僅僅依靠安撫手段拉攏鮮卑等族首領和勛貴,把他們對于前秦的擁護寄希望于“感恩戴德”的做法不過是西周時期天子與諸侯之間“恩惠換忠誠”原則在十六國環境下的再次呈現。這種政策的弊病也早為苻融“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來”[9]436的主張所見。苻堅費盡心力愛護和寵信這些首領,希冀他們能成為前秦政權的磐石之宗,但因始終不能收服其心而徒勞無功。淝水之戰失利后,苻堅昔日極度寵信的慕容垂盡管開始并不想圖謀自立,但在其弟慕容德的反復勸說下也開始著手建立政權。
四、前秦民族政策失當與統一政權建構隕滅根源
綜上所述,盡管前秦針對統治疆域內的各民族所采取的民族政策有利于緩和民族矛盾、化解民族沖突,但從長遠來看,該政策有天然弊端。同時,前秦政權自身也是一個多民族架構而成的“不穩固的、暫時的聯合體”[14],因而很難持之有效地維護北方統一的局面。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戰促成前秦政權統一南北失敗的緣由雖然有“驟勝而驕故”[10]的因素,但不過是軍事戰略失策掩蓋下民族政策施行的嚴重局限所釀成的后果。綜合對前秦民族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民族政策的失當與統一政權建構理想隕滅之間存在著三種根源。
(一)日久之弊,卒至分化
前秦政權的形成是與武力征服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針對被征服地區之部落和民眾所實施的遷徙之策也是以強大的軍事征服為重要保障的,而且這種遷徙也與前秦每一次平叛活動緊密相關。這就促成了前秦遷徙豪酋雜夷至關中的政策與始皇徙民以備胡和魏武遷徙烏桓的做法別無二致,前已有之、今又為之,承襲日久遂致弊病叢生。拉攏漢官重用漢族官僚的做法也是早在后趙時期便已延續下來的,后趙統治者石勒就曾經將漢族官僚張賓“引為謀主”。而凸顯漢化的崇儒修教之策也是“文化與教育仍繼承中華傳統,而少有變更”[15]58。整體觀察前秦民族政策,它始終沒有擺脫“中國古代民族治理過程中呈現出的武力高壓威懾與恩撫懷柔兩大特點”[16]。
因此,從政策本身的創新性角度來看,前秦實質上的創新活力尤其不足,它充其量是前代王朝民族政策和治理思想的一種簡單延續。歷代民族政策推行的經驗已經證明,一味依靠武力遷徙部眾以圖控制卻不加以內部整合是無法形成向心力的,一味拉攏漢族上層群體代表也很難真正獲得士族群體對政權的擁護。缺乏創造性活力的政策因其施行日久弊病叢生,前秦不加創新地延續這些民族政策是把其釀成民族群體分化的弊病承繼下來。
(二)有限受益,傾心難獲
前秦立足于疆域內各民族雜居的現實情況,針對不同民族實體采取了一整套加強治理的民族政策,這些政策無一例外地將著眼點放置在各民族和各部落的上層貴族集團,受益者也是這部分人群。
徙民政策對氐族統治管理有利,重儒式的崇儒修教政策對吸引漢族中的士大夫群體更有效,恩撫懷戎從其對象上來看也主要針對鮮卑等民族首領。對于各部落民眾,前秦既沒有任何措施加以招撫,也沒有行之有效的舉措直接管理。既無頂層構建的政治施策,又無底層的制度規束,其恩撫之策實質也是一種以部落首領為媒介所實行的間接統治。這種統治釀成氐族上層與他族底層民眾的溝通為各部落首領所隔,進而天然地制造出統治集團與被統治群體之間無可調和的隔閡。
隔閡久而不解就會生發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加之前秦統治者對主體漢族希冀東晉北伐,以求南北統一的愿望認識不清[15]60,遂促使“這些政策不僅不利于消除民族矛盾,有效地控制被統治的民族,反而加劇了民族矛盾”[17],如此前秦統治便無法安固。何況鮮卑等族與氐族之間的矛盾與隔閡更被這種“夷狄應和”的氣象粉飾起來,前秦失去了調節和消除這些民族矛盾的可能性,其最終命運就可知。
(三)儒法悖論,消解合力
苻秦君主振興學校、力辦太學并以儒家古圣賢王自居,敦導儒家王道之政。從頂層建構而言,前秦在致力于推行儒家“仁政”的治國模式,但化歸到政令施行,其執行者卻不是“仁政”模式的倡導者。
常被苻堅稱譽為諸葛孔明的士族王猛,更像是主張嚴苛峻法以刑治天下的法家思想繼承者。王猛任始平縣令時因當地盜賊趨利為亂、豪門大族依權勢而行,遂“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9]491并鞭笞官吏以整肅縣紀;也曾與御史中丞鄧羌誅殺二十余王公豪強來整治朝綱,即使是身為京兆尹的苻氏親族,王猛也在未曾奏報苻堅的情況下予以擊殺,同時曝尸于市,以為告誡,一度令“百僚震肅,豪右屏氣”[3]2887。王猛為政舉措的嚴酷性連身為君主的苻堅都不禁慨嘆“何其酷也”!
由此可見,苻堅傾心任用的王猛等人根本不是儒家思想的信仰者和倡導者,他們為政只是在導行刑罰。苻堅一心追求“追蹤唐、虞,懷遠以德”的儒家王道式治國理想,力倡儒者之政,但落實到政策執行者卻不是力主儒家思想的士大夫。王猛、鄧羗的政治理念與苻堅的治國理想形成了一種錯位的對反關系,這種對反關系在苻堅勸導王猛為政以德化為先與王猛反駁苻堅亂世當用重典[9]491的說辭中得到體現。這就見證了君臣治國思想取向上的不同。君臣之間人為制造了統治階層意識形態的儒法二元悖論。如果說統一問題是指國家之間或政權之間,或其內部在政治上的一致性從而結合為統一整體而言[18],那么前秦統治集團在法家還是儒家的治國思想選擇上,集團內部都是極度不統一的。在這種境遇下,不僅消解了前秦君臣的政治合力,也促成了儒家士族群體對前秦政權名儒實法本質的厭惡,進而撕裂了漢族儒家士人與前秦政權的內在關聯,破壞了氐族與漢族士人通過苻堅重儒修教策略所建立起來的薄弱凝聚力。前秦統治集團內部已然分化,淝水之戰以前秦軍力之盛而未能完成南北合一進而締結統一政權的政治理想,反而促就“風聲鶴唳、不戰自潰的局面”[13]192也就很好地得到了解釋。但這一過程并非簡單的是“由于前秦不斷征服進而激化民族矛盾的結果”[19]。
五、結語
前秦統一北方的歷史尤為短暫,其所推行的民族政策也不過轉瞬即逝,但前秦政權民族政策推行的歷史卻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鏡鑒。前秦所推行的徙豪酋雜夷于關中以鎮撫他族、崇儒修教兼籠絡漢官以混六合和恩撫民族首領,借威信以懷戎進而倡導王化的三項民族政策天然存在著“強則畏服,弱則為叛”,氐族本位、受惠上層和以恩惠換忠誠難以收服其心的弊端。這些弊端在前秦繼承久已生弊的政策和未獲得政權底層民眾支持以及統治集團內部儒法治國理想二元背反的影響下,使前秦既未夯實統治基礎,也失去了漢人士族群體和鮮卑等其他民族的支持,最終消解了前秦統一政權建構的內在凝聚力,促使苻堅“混同六合”理想隕滅,前秦統一南北的希望化為泡影。前秦政權民族政策推行的利弊得失也為今天處理民族關系、實施民族政策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