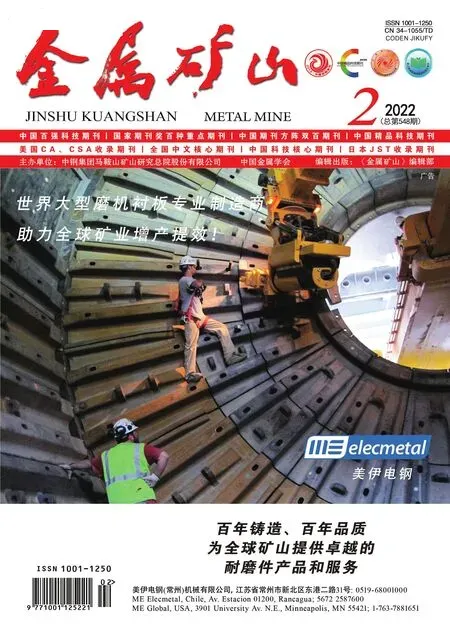西南地區某礦產集采區土壤重金屬遷移規律及生態風險評價
史帥航 白甲林 余 洋
(1.中國航空器材集團有限公司,北京 101312;2.中化地質礦山總局地質研究院,北京 100101;3.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北京 100081;4.自然資源部礦山生態效應與系統修復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1;5.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測繪工程學院,北京 100083)
礦產資源是人類生存、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其在勘察、開采、選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引發區域性生態擾動、景觀損毀以及地質破壞[1-8]。其中,作為礦山生態修復與環境治理難以攻克的技術問題之一,礦區土壤重金屬超標一直備受國內外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9-19]。近年來,隨著“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等生態文明建設理念的不斷完善,系統全面地開展礦山生態修復與環境治理日趨成為業內共識[20-27]。本研究以西南地區某礦產集采區典型礦區為例,通過對礦區及其周邊流域內土壤樣品進行采集測試,合理簡述相關土壤重金屬遷移規律,系統評價潛在生態風險,嘗試實現對礦區及其周邊土壤重金屬超標追根溯源,以期為當地生態保護修復、生態環境治理提供科學有效參考。
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四川省西南邊緣的橫斷山脈東段,屬于高山峽谷氣候,年內干濕季節分明,降雨集中。礦產資源開發產生的尾礦堆、廢渣堆充斥著區內溝道,加之受地形高差影響,廢渣隨地表水體發生遷移,極易誘發下游土壤重金屬生態風險。基于上述討論,本次研究重點選取礦產集采區內Ⅰ號鉛鋅礦區、Ⅱ號鉛鋅礦區、Ⅲ號磷礦區和Ⅳ號磷礦區進行土壤樣品采集,其中,Ⅰ號鉛鋅礦區、Ⅱ號鉛鋅礦區位于X河支溝內,Ⅲ號磷礦區、Ⅳ號磷礦區位于Y河支溝內,均為長江上游金沙江水系。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樣品采集:根據野外調查結果和現場實際情況,沿X河支溝和Y河支溝、從上游至下游均勻布設采樣點位。其中,Ⅰ號鉛鋅礦采集土壤樣品8個,Ⅱ號鉛鋅礦采集土壤樣品9個,Ⅲ號磷礦采集土壤樣品13個,Ⅳ號磷礦采集土壤樣品9個,如圖1所示。另外,在礦產集采區西北部設置研究比對樣品(CK)。

圖1 研究區及采樣點分布Fig.1 Distributions of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sites
在土壤樣品測試方面,由四川省某工程技術測試中心按照有關技術規程[28-29]開展測試,根據測試報告遴選出相關指標作為研究的數據來源;在綜合評價方面,采用單因子指數法和內梅羅綜合污染指數法進行土壤重金屬狀況評價;采用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進行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評價。
3 結果與分析
3.1 礦區土壤重金屬含量分析
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法分別對各礦區土壤樣品重金屬含量進行分析。統計發現,4個礦區土壤樣品中鉛、鋅、鎘和砷等重金屬含量均存在較大差異,離散程度大(如表1所示)。其中,Ⅰ號鉛鋅礦區土壤樣品重金屬含量變異系數偏大,可能源于土壤樣品布設點位較為分散。

表1 礦區土壤重金屬含量統計分析結果Table 1 Statistical analyses of heavy metal content in soil of mining area
基于統計結果對礦區土壤樣品重金屬含量作進一步分析。分析認為:一方面,在礦產資源開采、洗選、冶煉過程中,大量粉塵通過大氣干濕沉降直接進入土壤;另一方面,堆積于地表的原礦石、尾礦等經淋溶、風化等自然作用將重金屬等物質帶入土壤,從而引發礦區土壤重金屬含量超標[30-46]。
3.2 礦區土壤重金屬遷移規律
3.2.1 Ⅰ號鉛鋅礦區
由圖2可知,Ⅰ號鉛鋅礦區土壤樣品各重金屬含量均大于對照樣品;從X河支流上游至下游,土壤樣品重金屬鉛、鋅、鎘含量呈現雙峰變化趨勢、砷含量呈現單峰變化趨勢。其中,在Ⅰ號鉛鋅礦區廢渣堆下游(T02、T03)和某礦業洗選廠下游(T07)處鉛、鋅、鎘含量較高,T07處砷含量最高。分析認為:礦產資源開采、洗選活動與礦區土壤樣品重金屬含量超標可能存在正相關;礦區土壤樣品各重金屬含量變化趨勢相似,說明土壤樣品中重金屬鉛、鋅、鎘超標與砷超標可能存在相關性[33-34]。


圖2 X河Ⅰ號鉛鋅礦區土壤重金屬含量Fig.2 Variations in soil heavy metal contents in Pb-Zn Mining Ⅰ of X River
3.2.2 Ⅱ號鉛鋅礦區
由圖3可知,Ⅱ號鉛鋅礦區土壤樣品各重金屬含量大于對照樣本比例超過88%;從X河支流上游至下游,土壤樣品鉛、鋅、鎘、砷含量呈現不規則的波浪形變化趨勢。其中,礦區固體廢棄物堆附近土壤樣品(T14、T16、T17)重金屬含量相對較高,河流交匯處(T13、T15)重金屬含量相對較低。分析認為:礦產資源開采過程中產生的固體廢棄物可能存在重金屬含量超標;河流交匯處水量增大可能會稀釋河流底泥中的重金屬含量。


圖3 X河Ⅱ號鉛鋅礦區土壤重金屬含量Fig.3 Variations in soil heavy metal contents in Pb-Zn Mining Ⅱ of River X
3.2.3 Ⅲ號磷礦區
由圖4可知,Ⅲ號磷礦區土壤樣品各重金屬含量大于對照樣本比例超過69%;從Y河Ⅲ號磷礦區支溝上游至下游,土壤樣品各重金屬含量呈現不規律的波浪形變化趨勢。其中,采礦活動產生的尾礦、固體廢棄物堆附近(T24)鉛、鋅含量相對較高,選礦活動產生的廢渣附近(T18、T20)鎘、砷含量相對較高。分析認為:采礦活動、選礦活動產生的固體廢棄物中不同類型重金屬含量可能存在差異。


圖4 Y河Ⅲ號磷礦區土壤重金屬含量Fig.4 Variations in soil heavy metal contents in P Mining Ⅲ of River Y
3.2.4 Ⅳ號磷礦區
由圖5可知,Ⅳ號磷礦區土壤樣品各重金屬含量大于對照樣本比例超過55%;Y河Ⅳ號磷礦區支溝上游至下游,土壤樣品鉛、鋅、鎘含量呈現不規律的波浪形變化趨勢,砷含量呈現單峰變化趨勢。其中,開采活動產生的固體廢棄物堆附近(T36)重金屬含量相對較高。分析認為:開采活動產生的固體廢棄物可能存在重金屬含量超標。


圖5 Y河Ⅳ號磷礦區土壤重金屬含量隨流域上游至下游變化規律Fig.5 Variations in soil heavy metal contents in P Mining Ⅳ of River Y
3.3 礦區土壤樣品重金屬含量評價
因各礦區礦產資源類型、開采時間以及礦石洗選工藝不同,導致4個礦區土壤各重金屬單因子污染指數和礦區內梅羅綜合污染指數存在明顯差異,如表2所示。

表2 礦區土壤樣品重金屬污染評價結果Table 2 Evaluation results of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mining area
對比發現,鉛鋅礦區土壤樣品鉛、鋅、鎘單因子污染指數均高于磷礦區,表明鉛鋅礦區土壤樣品以鉛、鋅、鎘含量超標為主;磷礦區土壤樣品砷單因子污染指數總體高于鉛鋅礦區,表明磷礦區土壤樣品以砷含量超標為主。
3.4 礦區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分析
因各礦區土壤樣品中重金屬濃度不同,導致4個礦區土壤各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指數、礦區生態風險綜合指數存在明顯差異,由表3所示。

表3 礦區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分析Table 3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analysis of heavy metals in soil of mining area
對比發現,鉛鋅礦區土壤鉛、鋅、鎘的潛在生態風險指數均大于磷礦區,磷礦區土壤砷的潛在生態風險指數高于鉛鋅礦區,表明鉛鋅礦區土壤鉛、鋅、鎘的潛在生態風險大于磷礦區,土壤砷的潛在生態風險則呈現磷礦區大于鉛鋅礦區。
4 結 論
通過分析西南地區某礦產集采區4個礦區土壤樣品重金屬含量及其隨流域遷移規律,分析研究區內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得出以下結論:礦產集采區中鉛鋅礦區、磷礦區土壤樣品重金屬超標類型不同;研究區土壤樣品重金屬含量從上游到下游的遷移規律變化,可能與礦產資源開采方式、洗選方式、礦區固體廢棄物分布、地表徑流強度等因素存在相關性;研究區土壤樣品重金屬含量超標排序依次為Ⅰ號鉛鋅礦區、Ⅲ號磷礦區、Ⅳ號磷礦區、Ⅱ號鉛鋅礦區;研究區生態風險排序依次為Ⅰ號鉛鋅礦區、Ⅱ號鉛鋅礦區、Ⅲ號磷礦區和Ⅳ號磷礦區。
基于上述研究與討論,建議進一步加強長江上游金沙江流域內礦產資源開發引起土壤重金屬含量變化的相關研究,重點關注不同類型礦產資源開發對土壤重金屬含量擾動的作用機理,有效厘清礦產資源開發方式、洗選工藝對土壤重金屬含量影響的核心環節,深入挖掘礦產資源集中開采區土壤重金屬含量變化的內在關聯,持續探索礦產集采區土壤重金屬遷移規律的演化特征,不斷提升長江上中游重要流域礦產資源開發生態風險評價水平,繼而為科學推進礦產資源集采區“綠色礦山”建設、礦山生態保護修復等相關工作提供更加有效的數據來源、科學的理論支撐、詳實的研究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