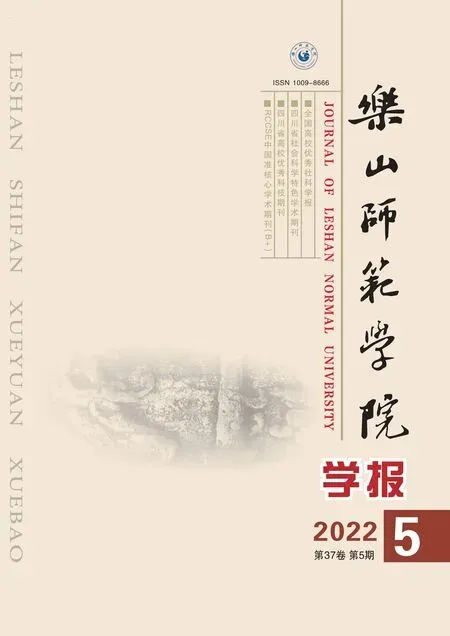孔子對話教學與兒童哲學教育會通的辯證
——與高振宇先生商榷
湯廣全
(龍巖學院 師范教育學院,福建 龍巖 634012)
一、問題的提出
兒童哲學(philosophy for children)是國內習慣譯法,實際是兒童哲學教育[1],本文擬用后者。兒童哲學教育不是源于本土,主要源自美國,偏于李普曼(Matthew Lipman)的風格,即在中小學乃至幼兒園對學生進行哲學教育,以故事、繪本、游戲等符合兒童身心發展特點的方式展開的思維探索活動。在兒童哲學教育中國化的過程中,必然牽涉到傳統文化精粹如何與外來的兒童哲學教育進行交流與會通問題。孔子,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奠基者,他的對話教學飽含豐富的哲學思想,澤被后世,影響卓著。如何對孔子對話教學與兒童哲學教育進行創造性的會通,是一個不易繞開的話題。高振宇先生在其大作《孔子對話教學視野下兒童哲學探究團體的重構與創新》(以下簡稱“高文”)進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讀與闡釋,即孔子的對話教學秉持“無知”、強調獨立思考、重視相互學習,預示它與基于蘇格拉底對話法的兒童哲學教育存在相通之處,據此可重構和創新探究團體的目標、取向和策略,進而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兒童哲學教育話語奠定堅實的基礎。[2]論者的闡釋,即“孔子的對話教學在‘無知’精神的秉持、對主動與獨立思考的強調、對相互學習的重視”是否確當,與基于蘇格拉底對話法的兒童哲學教育存在多大程度的相通之處,他的對話教學之于兒童哲學教育探究團體中國化的貢獻在于“從關注認知到兼顧情感和審美”、“從‘思維技能’轉向‘哲學智慧’”、“從訴諸定義走向訴諸情境”是否準確、完整,這些不僅需要反思,而且需要“清思”。
二、孔子對話教學中的“無知”
蘇格拉底的名言是:我知道自己無知。正是操守這樣的“無知”,蘇格拉底才不斷追尋真理,不斷對自身與他(她)人知識的有限、常識的悖謬及神圣事物的不完滿等保持思維的警覺。這是其對話教學法的前提與基礎,也是兒童哲學教育展開的前提性條件。高文認為,與蘇格拉底一樣,孔子對話教學中的“無知”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其一,《論語·衛靈公》中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能夠證明孔子與蘇格拉底的“無知”在本質上是一樣的。論者認為,這里的“道”近于客觀真理。只言片語,不知推斷的依據何在,論者并未明示,讀者不明就里。繼而,高文認為,《論語·述而》中的“若圣與仁,則無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兒已矣”句證明:孔子一方面對自己的局限保持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又不斷保持開放的心態,持續求“道”。但是,論者忘了,《論語》中的孔子沒有言說標準,缺失對基本概念的嚴格界定,甚至“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如何證明其持續求的“道”一以貫之。同樣是在《論語·述而》中,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里的孔子形象與高文所呈現的孔子形象截然不同,換了個人似的。也是在《論語·述而》中,孔子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中孔子諸如此類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話語不在少數。也就是說,高文摘引《論語》中的只言片語不足以證明孔子始終懷抱與堅守“無知”的精神,至多只能說,孔子時而堅守“無知”,但多數情況下,孔子并不是這樣。
其二,孔子對非經驗事物始終保持“不知”“不言說”的姿態。高文用了《論語》中的三處話來證明此點:一是“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二是“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三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與“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而且,論者還引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的話,對孔子論及有關生死、自然及世界秩序時,贊揚孔子的回答“保持開放”,而非“故弄玄虛”。即便如此,《論語》中孔子的相關言說仍然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如前文提及的“天生德于予”句中的“天”就是非經驗事物,但孔子恰恰就在“言說”。再如,“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這里的“天”也不是非經驗物,偏偏孔子又在言說。同樣是在《論語·子罕》中,“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這里的“鳳鳥”是傳說中的神鳥,而“圖”是指傳說中的卦圖,二者同樣是非經驗物,孔子仍在“言說”。
也就是說,孔子與蘇格拉底在“不知”“不言說”等方面存在著程度上甚至本質上的不同:首先,二者的“不知”程度不同。孔子的“不知”是偶爾的、不經常的,頻次上遠遠少于他慣常的“教師爺”姿態;蘇格拉底的“不知”是常態的、精神性的習慣。其次,二者對待神圣事物的態度也不盡相同。孔子盡管時而“不知”、“不言說”,但又不時地反其道而行之,更主要的是“在他的學說中給予祖先之道、給予傳統以首要地位”。[3]與之相反,蘇格拉底“不僅不相信一些傳統的諸神故事,而且認為神圣的存在不依賴于諸神”。[4]即蘇格拉底的“不知”、“存疑”、追尋、探究是相當徹底的。
因此,高文認為孔子對話教學中“始終”堅守“不知”“不言說”的姿態是不準確的,他的“不知”是非常有限的,在論證上也是不嚴密的。
三、孔子對話教學中的主動與獨立思考
蘇格拉底認為,人的知識與真理是先天的,只是由于人的肉身及其欲望、情感等因素的干擾或“遮蔽”而無從呈現。教育者的使命在于幫助學習者“解蔽”,在于“喚醒”受教育者,在于引導學習者把自身內在的知識與智慧“顯現”出來,也可理解為: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進行獨立思考。
高文認為,“孔子非常強調學生學習的自主性”,例證有三:其一,“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論語·顏淵》);其二,“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其三,“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第一例是孔子與顏淵在對話中說的。而顏淵聽后就說:“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大意是說:我顏淵即使不才,也要按先生所說的話執行。也就是說,這個對話不是真正意義上對話,即沒有探討、存疑、好奇及追問,而是學生向老師“討教”,“請教”;孔子好為人師,誨人不倦,他發話后,學生照單全收。第二例、第三例“對話”連真實對話的形式都沒有,只是孔子的獨白、斷語、結論,沒有對話的具體情境。繼而,高文還舉兩例“鞏固”其前期“論證”成果:其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其二,“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這里的兩例雖表達了孔子對主動性思考的強調,但仍與前文二、三例一樣,即都是孔子個人的“自言自語”,連對話的情境都沒有。
繼而,高文指出,孔子“師徒之間的對話也往往是由學生的主動提問而啟動”的。問題是,“主動”并不必然意味著相當于蘇格拉底對話法中常態化的嘲諷、助產、歸納、定義,并非近于平等的對話乃至存疑、挑戰等。事實上,《論語》中這種由學生主動提問而開啟的對話往往多是學生“請教”先生,而非真正意義上兒童哲學教育中的平等探討。正如學者指出的那樣:與《論語》中孔子“答疑解惑”的形象迥異,蘇格拉底在對話中多以提問者的形象出現,他的對手才是問題的闡釋者與回答者;而全部對話的中心恰恰是提問者,而非回答者。[5]
最后,高文總結性地提出,《論語》中的對話,學生質疑孔子、與孔子爭辯的情境“時有存在”。首先,“時有存在”具體何指。是三五次,還是幾十次,抑或上百次。也就是說,“質疑”、“爭辯”是否是孔子對話教學中常態化的境遇。顯然,《論語》中的對話情境多數不具有這樣的精神風貌,即孔子并非總是與學生處于一種平等關系,這使得他的道德教育只是一種回應教育,在本質上與對話之間存在差距。[6]進而言之,《論語》中的孔子實質不是一位“對話者”,而是一位“訓話者”。[7]其次,這種“質疑”“爭辯”不具有持續性。也就是說,在蘇格拉底對話教學法中,每場“質疑”“爭辯”往往持續三五個、十幾個甚至更長的回合。而孔子對話教學中的“質疑”“爭辯”通常只有二三個回合的“你來我往”,就會戛然而止,不具有持續性。蘇格拉底對話教學法卻迥然不同,而是持續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將相互交流思想作為對抗自我蒙蔽的防護措施介紹給學生”。[8]
總之,孔子對話教學中彌散的“主動”精神與“獨立思考”姿態是非常有限的,至少不具有常態化的特征。
四、孔子對話教學中的“相互學習”
一般傳統教學中,教者與學者至少在知識的擁有量上不是對等的,話語權因此而有高下之別,往往意味著學者向教者“請益”,教者“居高臨下”地“施教”。而蘇格拉底教學法及其衍變而成的兒童哲學教育則強調師生的平等、相互學習、“教學相長”。
高文認為,《論語》中的孔子對話教學不僅是師生間的相互學習,還要教師本人“好學”,此外還要學、思結合。對于《論語》來說,無論是師生間的相互學習,還是教師本人的“好學”,抑或學習與思考相結合,都偏重知識的學習、
記憶或理解,甚至是為學習而學習。這就涉及孔子的教學“思想”只關乎經驗性的知識,而缺失“統一性”的關聯與提煉,不能為學習者“提供任何特定的、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而蘇格拉底不只是一位“事實性知識的傳授者”,還是一位通過方法使得其門徒身上潛在的“更高”真理得以誕生的“助產士”。[9]也就是說,孔子師徒之間的對話重視“格物致知”,偏于“實踐探究”;注重培養學生“舉一反三”的演繹能力,并直接告訴學生結論或答案,指向學生的具體“操作行為”。而蘇格拉底對話教學法則充斥“反問詰難”,側重發掘學生的潛能,強調思辨,培養學生的抽象邏輯思維能力;突出“由三而一”,即由具體到抽象、特殊到一般,著重培養學生由歸納而綜合的邏輯推理能力。[10]前者偏于安德森(Anderson)等人的記憶、理解等相對較低層次的思維,后者偏于安德森等人的應用、分析、評價、創造等高階思維層次。[11]
進而言之,蘇格拉底的對話教學法,重要的不是最終結論,而是問題、回答、質疑及發現的交流與互動。[12]而《論語》中孔子對話教學多數情況下追求的是結果、結論,甚至是強加的標準答案,不具有真正的對話所指向的持續的質疑與追問姿態。因此,后者對話教學中的“相互學習”“好學”“學思結合”很大程度上不具有蘇格拉底對話教學法的真精神,即“充分地展現我們所固有的提出問題、虛心學習、挑戰自我和堅持真理的能力”。[13]
五、孔子對話教學之于兒童哲學教育探究團體中國化的貢獻
在兒童哲學教育中,探究團體的構建是一種重要的組織形式,它既符合兒童哲學教育的教學形式,又有利于兒童哲學教育內容的推進與深化,也有利于兒童哲學教育中的協同與合作。高文認為,在兒童哲學教育探究團體的重構與創新方面,孔子對話教學的貢獻有三:
第一,探究團體的取向:從關注認知到兼顧情感和審美。
高文認為,無論李普曼,還是在奧斯卡·博尼菲(Oscar Brenifier)的兒童哲學教育實踐中,兒童的情感都沒有得到足夠關注,甚至被視為干擾;而《論語》中的孔子突出“詩教”“樂教”,值得國內兒童哲學教育實踐的借鑒,即應嘗試利用我國詩歌、音樂、戲劇、美術及其他藝術品,使兒童擁有開展美學探究的機會,以便在獲得審美體驗的同時充分享受哲學探究的樂趣。這里的問題有三:一是“認知”與情感、審美并非截然對立,而是相互滲透的。也就是說,無論是蘇格拉底的對話教學法,還是當下的兒童哲學教育實踐,“認知”并非就必然排斥情感、價值觀。狹義而言,“認知”是借思維活動認識、了解。[14]廣義來說,按安德森(Anderson)等人的理解,“認知”既包括記憶、理解等較低層次的思維,也包括應用、分析、評價、創造等高階思維活動。而應用、分析、評價、創造等就不可避免地滲透著情感、價值觀等因素。實質上,思想交鋒愈激烈,對話形式愈搖曳多姿。[15]二是“詩教”“樂教”如果脫離了認知中的理解、分析與評價、創造,必然充斥純粹的文藝性,固然充滿想象力,但因缺失邏輯與理性而飄忽不定、游移不定,乃至高妙玄遠而無持守,不能“接地氣”,最終因過于失范而難有進步,或原地打轉而無實質性提升。三是真、善、美是連為一體的。真是基礎;缺失了真,善、美,形式上再高大上,也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無法長成實體性的“參天大樹”,甚至是空中樓閣。
第二,探究團體的目標:從“思維技能”轉向“哲學智慧”。
高文認為,西方的兒童哲學教育實踐偏重邏輯思維、批判性思維的培養,止于“技”“器”,只是一類“表層”的目標,而《論語》中孔子對話教學追求的是深層次的“道”,是一種智慧教育、精神教育、啟蒙教育。這里的問題有四:首先,《論語》中的“道”具體何指。高文引《論語·里仁》中的“朝聞道,夕死可矣”句與《論語·述而》中的“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句證明孔子追求的是哲學智慧。前文已述,《論語》中的孔子沒言說標準,缺失對基本概念的嚴格界定。上面兩處的“道”具體何指,我們并不清楚;同時,上面兩處的“論語”也不是教學對話情境中出現的,而是夫子自道。《論語》中有關這樣的“道”還有不少,比如:“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論語·公冶長》)“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其次,“思維技能”是否與“智慧教育”兩不相干,還是彼此交融或者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它們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只是嚴格區分的表層與深層、器與道的關系?高文并未明確地向讀者論證二者之間的邏輯聯系。再次,不能機械地割裂思維技能與智慧教育之間的有機聯系。即便有思維技能與哲學智慧高下之別,也難以割裂二者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內在邏輯聯系。也就是說,思維技能是哲學智慧的詞中應有之義,而不是彼此隔閡、相互絕緣。最后,兒童哲學教育旨在幫助中小學生合乎邏輯地思考問題,發表意見,作出合適的評價,聆聽他(她)人不同的觀點和意見。[16]實際上,李普曼的兒童哲學教育能夠有效促進學生邏輯推理能力的發展。[17]而邏輯思維這個被論者稱之為“技”“器”的“表層”目標恰恰是新時代孜孜以求的核心素養,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基礎學科目錄中,邏輯位居第二;由世界500 多名教育家列出的16 項最重要的教育指標中,“發展學生邏輯思維能力”也排在第二。[18]
第三,探究團體的策略:從訴諸定義走向訴諸情境。
高文認為,蘇格拉底對話教學法中只側重基本概念本質性定義的探討,而“參與者本人的個性、經驗、學識是隱藏或逐漸退場的”。與之相對,《論語》中孔子的對話教學則突出概念的“與生活、對話和個人語境緊密相連的多元答案”。這里的問題有三:其一,概念的界定“訴諸定義”與“訴諸情境”,并非截然對立。也就是說,概念的界定是非常復雜的,“訴諸定義”與“訴諸情境”并不矛盾。廣義、狹義也好,日常用語、學術用語也罷,抑或是本義、引申義、衍義,無不與概念界定的具體情境相關,都需要參與者的具體“在場”,哪里會是其個性、經驗、學識的“退隱”?其二,概念明確是哲學探討的基石。創造性對話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培養孩子們的概念性理解能力。[19]如果概念含糊或變動不居,就必然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模棱兩可境地,也就無法逼近“真理”或真相。也就是說,無論概念具有多少可能性的“含義”,它在任何特定的具體語境下,總有一個相對明確的界定,即它對對話雙方都是相對清晰的,否則真正的對話必將無從展開。其三,單純的“訴諸情境”易陷入“無可無不可”的玄妙境地,只會離真理或真相越來越遠,而不是相反。正因為缺失言說標準,偏于“訴諸情境”,所以《論語》中的孔子未能提出一個系統的哲學。[20]也就是說,孔子哲學的顯著特征就是對人及其實踐生活的世俗關懷,而不能形成邏輯學、倫理學及形而上學那樣完整的體系。[21]
六、結語
作為一位影響深遠的思想家,《論語》中孔子對話教學不能說完全沒有高文所說的“無知”、“主動與獨立思考”及“相互學習”的因子,但就具體的《論語》文本而言,三者的存在是非常有限的,無法比肩蘇格拉底。至于高文在其論述的第三部分,借兒童哲學教育探究團體的重構與創新,禮贊孔子的貢獻時,突出其具有探究團體目標中的“哲學智慧”、價值取向中的“兼顧情感與審美”、對話策略中的“訴諸情境”,而疏于“思維技能”“關注認知”“訴諸定義”。這些都不符合辯證法,即人為地把“哲學智慧”與“思維技能”“關注認知”與“兼顧情感與審美”“訴諸情境”與“訴諸定義”機械地割裂開來。因為“心靈的各種能力不能單獨培養,而是要與其他的聯系起來進行”。[22]而且,蘇格拉底對話教學法不是教人以知識,而是使人歷經對話過程,讓雙方的思想在對話中碰撞、呈現,乃至產生共鳴。[23]如果我們不尊重事實,草率比附,甚至刻意溢美、拔高孔子的形象,不僅有損、玷污孔子的一世英名,而且也從根本上違背孔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的實事求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