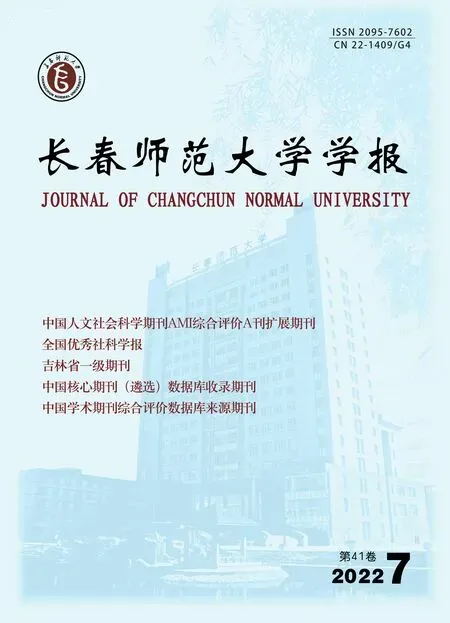《浮生六記》英文譯介研究
——基于翻譯動機視角
許宗瑞,胡小兵
(1.上海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上海 201620;2.安徽農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浮生六記》是我國清代文人沈復所著的一部自傳體筆記,自清嘉慶年間問世以來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堪稱中國古典文學寶庫中的一件珍品和中國封建社會的一部百科全書。據考證,該書著于1808年左右,于1877年刊行,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俞平伯等人的大力推動下開始受到關注,并被譯成外文。目前,全球已有上千家圖書館收藏《浮生六計》英譯本。“對于這樣一部作品,無論是在文學批評上,還是在翻譯研究上,都有特別的價值。”[1]
一、《浮生六記》及其英文譯介研究
自《浮生六記》被發現以來,一代又一代專家學者圍繞作者沈復的生平事跡、與其他文學經典的比較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持續、廣泛、深入的探討。《浮生六記》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主要在于作品本身達到的藝術高度和蘊含的文學價值。俞平伯在《重刊〈浮生六記〉序》中對其評論道:“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露明瑩的顏色;只見精微,不見制作精微的痕跡。”[2]98陳寅恪則將《浮生六記》概括為“例外創作”:“吾國文學,自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間關系,而于正式男女關系如夫婦者,尤少涉及。蓋閨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鹽之瑣屑,大抵不列載于篇章,惟以籠統之詞,概括言之而已。此后來沈三白《浮生六記》之閨房記樂,所以為例外創作,然其時代已距今較近矣。”[3]99誠如兩位學者所言,《浮生六記》以渾然天成的特質和注重表現日常生活和真情實感的細膩描摹,開創了第一人稱抒情小說的美學范式,樹立了一種新的中國文學文體類型。因此,它不僅感染了一大批中國讀者,也吸引了不少海外人士。
《浮生六記》的首部譯本出自林語堂。該譯本為英譯本,于1935年推出。此后,這部作品陸續被譯成日語、捷克語、意大利語、馬來語、瑞典語、法語、韓語、俄語、希伯來語、西班牙語、丹麥語、荷蘭語、德語等十余個語種,譯著多達二十多部。其中,譯介次數最多、影響最大的當屬英譯。除1935年林語堂譯本之外,英譯本還有1960年英國譯者Shirley M. Black譯本,1983年美國譯者Leonard Pratt和我國臺灣譯者Chiang Su-hui的合譯本,以及2011年加拿大譯者Graham Sanders譯本,共計四部。
文軍、鄧春在評述國內《浮生六記》英譯研究取得的階段性成果時指出,相關研究可分為總括性述評、譯者研究、翻譯策略研究、譯本對比研究、文化視角的研究、文學視角的研究、語言學視角的研究七大方面[4]。但是,翻譯動機研究一直未得到充分關注。翻譯動機研究雖然在譯者研究中有所涉及,但基本針對林語堂一人。梁林歆、許明武在回顧和展望國內外《浮生六記》英譯研究時也指出,過往研究存在切入視角有待開拓、研究對象比較單一等問題[5]。許鈞曾強調,在影響翻譯具體活動的所有因素中,最活躍且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是翻譯的主體因素,尤其是翻譯動機和翻譯觀念6]。鑒于此,本研究將聚焦《浮生六記》四英譯本譯者不同的翻譯動機或翻譯追求,以及由此產生的翻譯影響。
二、林語堂:為“中國文學上最可愛的女人”樹碑立傳
1935年《天下》月刊創刊號第1卷第1期上,林語堂發表了《浮生六記》第一章“閨房記樂”的英文譯文,譯文中還附有他用英文撰寫的譯者序。之后,該刊第2、3、4期繼續推出了第二至第四章的譯文。1936年林語堂又將《浮生六記》以英漢對照的形式在《西風》月刊創刊號第1期連載,連載至1939年第29期完成,且同年該英漢對照版由上海西風社出版。1938年美國紐約莊臺出版公司出版了林語堂的TheImportanceofLiving(《生活的藝術》),其中以四頁篇幅展現了《浮生六記》中的女主人公陳蕓對自然的熱愛。1939年該出版社又出版了林語堂的MyCountryandMyPeople(《吾國與吾民》)一書,其中以三頁篇幅引用《浮生六記》中的片段,展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人的生活。1942年林語堂將《浮生六記》英譯本匯編入TheWisdomofChinaandIndia一書,由紐約蘭登書屋(Random House)出版。1962年香港華文出版社推出《浮生六記》中英對照譯本注釋版,此后我國兩岸三地陸續推出了近十個版本的林語堂《浮生六記》英譯本。
近百年來《浮生六記》之所以屢屢獲得譯介,得到海內外讀者的廣泛關注,林語堂可謂功不可沒,尤其是他對這部作品的推崇,對女主人公陳蕓的贊美。他在譯者序中寫下的第一句,一直被很多學者廣為引用:“蕓,我想,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one of the loveliest women in Chinese literature)”[7]17。在這篇序言中,林語堂用了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贊美陳蕓,贊美她賢達、馴良、天真、癡情,為她樹碑立傳。他希望通過自己的譯筆,讓世人知道她的故事,“以流傳她的芳名”。林語堂坦言,在主人公陳蕓和沈復的簡樸生活中他仿佛看到“中國處世哲學的精華在兩位恰巧成為夫婦的生平上表現出來”[7]17。盡管他們遭遇接二連三的不幸和悲劇,但他們胸懷曠達、淡泊名利、與世無爭的人生態度深深感染了林語堂。這種強烈的翻譯動機影響了一批又一批海內外讀者,如1938年將《浮生六記》譯介到日本的伊藤春夫。除譯介工作外,伊藤春夫還于1943年在《江蘇日報》上分五期發表“談浮生六記:中國文學中最可愛之女性”一文。這是日本人較早發表的關于《浮生六記》的研究文章[8]92,僅根據文章題目就不難判斷伊藤春夫深受林語堂的影響。再如澳大利亞當代作家Nicholas Jose(尼古拉斯·周思),他以《浮生六記》為基礎,利用作品提供的想象空間創作了愛情小說TheRedThread(《紅線》)。小說使沈復和陳蕓轉生,讓這對前世恩愛夫妻歷經磨難和坎坷后再續前緣,演繹出一段凄婉動人的愛情故事。Jose坦言,其改編完全基于自己對原文的翻譯和林語堂1935至1936年間的譯本[9]。此外,我國學者關于《浮生六記》的討論還衍生出了專門的“陳蕓形象研究”。陳蕓形象所凝聚的文化底蘊,使得《浮生六計》獲得了永久的藝術魅力[10]。所有這些,都以林語堂為起點。
三、Shirley M. Black:再現“一段至悲的悲劇人生”
繼林語堂后,Shirley M. Black翻譯的ChaptersfromaFloatingLife:TheAutobiographyofaChinesePainter是《浮生六記》的第二個英譯本,由牛津大學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Shirley是英國漢學家和中國文學翻譯家,中文名馬士李,出版有RainbowSkirtsandFeatherJackets:TwentyChinesePoems(《霓裳羽衣:中國古詩英譯20首》)等譯著。與林語堂為陳蕓樹碑立傳不同,Shirley譯介《浮生六記》的主要動機是再現“一段至悲的悲劇人生”(a life essentially tragic)[11]xii。在譯文前的作品簡介中,她雖然也提及小說蘊含的浪漫、懷舊、溫馨等情調與特質,但反復強調沈復、陳蕓夫婦的“悲劇”和“不幸”,使用了諸如“out of place”“pressures”“destroyed”“misfortune”“miserable”“poverty”“failed”“died”“cheated”等詞語。正是出于這一翻譯動機,Shirley在翻譯時將與作品悲劇主題無關的一些章節進行刪減,對原文中一些讓讀者在敘事順序方面感到困惑的部分進行重組。對此她這樣解釋道:“在翻譯這部傳記時,我首先盡我所能再現作品的細膩情感,以及其中的悲傷、激情、快樂,這在我看來就是沈復原著中的最突出的特質……第四記中很多部分我省去未譯,比如游覽廟宇名勝等處,它們基本大同小異,而且對于這些廟宇名勝不太熟悉的讀者而言并沒有多大意義。同時,也省略了原文中與文學評論、養花種草有關的一些部分,因為涉及專業知識,對讀者吸取力不大。再者,我還對一些章節按照時間順序進行了重組,以減少讀者的困惑。”[11]xiii
針對這種翻譯理念和處理方式,國內外學者褒貶不一。國內翻譯家劉士聰認為,“(Shirley)超出了語言層面的形式‘對應’,她實際是‘翻譯’加‘創作’。所謂‘翻譯’,指她的翻譯以原文內容為依據,這當然是生產譯文的基礎;所謂“創作”,因為她要把原文‘微妙情感氛圍’和‘漢字的確切意思’譯出來,就需擺脫原文句法和行文方式的束縛,因而常有增譯,常有變通。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遵從英語表達習慣和行文方式進行的獨立創作。”[12]美國漢學家Cyril Birch(白之)在1972年編撰出版的AnthologyofChineseLiterature(《中國文學選集》)中選用了Shirley《浮生六記》譯本,并在一篇針對該譯本的書評中對Shirley的“省譯”行為表示理解[13]。不過,也有學者明確反對,認為“Shirley女士的譯筆可謂專橫,不僅任意刪減,還任意調整。硬是將李白(第13頁)和杜甫(第14頁)的詩歌插入至一段文學討論中;第12頁中的一段似乎純粹是捏造……如果這是《浮生六記》首譯倒還情有可原,具有一定價值,但實際上林語堂之前已譯出了全本。”[14]總體而言,Shirley譯本是幾部英譯本中爭議最多、最大的一部。
四、Leonard Pratt 和Chiang Su-hui:奉上“一份有價值的中國社會檔案”
《浮生六記》第三個英譯本由美國人Leonard Pratt(白倫)和我國臺灣學者Chiang Su-hui(江素惠)合譯。該譯本作為企鵝經典叢書(Penguin Classics)之一,由企鵝出版社1983年出版,后來又入選我國《大中華文庫》(LibraryofChineseClassics),由譯林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關于翻譯該書的緣起,譯林出版社的責任編輯許冬平這樣描述道:Pratt指出,當初在閱讀臺灣版林譯雙語本時發現了幾個問題,一是有些地方翻譯不夠準確,沒有完全反映中文原意;二是許多需要加注的地方,林譯本注解闕如;三是有幾處可能因為中文原文較難翻譯,結果并未譯出;四是譯文語言風格不太一致,文中有些文字像莎士比亞時代英語,有的如19世紀美國小說或20世紀20年代的俚語[15]。從Pratt的表述中不難看出,他們之所以翻譯《浮生六記》,主要由于林語堂譯本語言的準確性和地道性問題。但如果細讀Pratt和Chiang譯本前的作品簡介,則會發現兩人譯介的目的主要是為西方讀者奉上“一份珍貴的中國社會檔案”(a valuable social document)[16]9。在他們看來,這份檔案比較“別具一格”(unique):“盡管《浮生六記》是圍繞沈復和妻子蕓的愛情故事,但是是中國傳統社會里的一段愛情故事——夫妻之愛與丈夫狎妓、妻子替夫尋妾等共存并生,相互交織。”[16]9
因此,在譯文前的作品簡介中,“社會”是Pratt和Chiang筆下的關鍵詞,讀者讀到的是有關當時中國妓女、衙門、幕友(俗稱師爺)的大段介紹。將作品的文學性置于次要位置,凸顯其歷史檔案價值或文獻價值,是兩位譯者的用力所在。這也是一直以來不少海外漢學家、翻譯家譯介中國文學時的普遍做法。很多海外讀者原本就對中國文學知之甚少,譯者如果偏離軌道,廣大讀者容易隨之誤入歧途,作品也最終淪落為社會歷史檔案或文獻資料,與文學無關或者關聯較少。美國作家Celeste Heiter在評論Pratt和Chiang譯本時,較為認同《浮生六記》的文學魅力,但同時也指出,書中有些章節令讀者困惑,如“閑情記趣”一章開始十頁的敘述完全圍繞盆栽、插花、居家裝飾等瑣事[17]。再如Carlos Ottery的評論:該作品結構不同尋常,各記之間常有重疊,一些關鍵事情反復提及,但又切換視角,這種分層敘事讓人霧里看花,故事發展的關鍵轉折又經常從天而降……另一讓人費解之處在于,作者沈復敘事的可靠性問題,他并不意在將自己描繪成一成功人士或者孝子良夫,也不希望謀求讀者的同情。[18]雖然Pratt和Chiang譯本是四譯本中唯一入選企鵝經典叢書和我國《大中華文庫》的譯本,但產生的影響可謂喜憂參半,這與兩人的翻譯追求不無關聯。
五、Graham Sanders:擦亮“這塊中國敘事文學的瑰寶”
《浮生六記》第四個英譯本為加拿大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者、漢學家Graham Sanders(中文名孫廣仁)所譯,書名譯為SixRecordsofaLifeAdrift,由美國Hackett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與林語堂譯本、Shirley譯本、Pratt和Chiang譯本相比,Sanders譯本的作品簡介部分最長。Sanders譯本最鮮明的地方在于,希望擦亮(“擦亮”為筆者所加)“這塊中國敘事文學的瑰寶”(this gem of Chinese narrative)[19]viii。顯然,在重視和追求譯本的文學價值方面,Sanders可比肩林語堂。Sanders認為,《浮生六記》因其獨特的敘事手法,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特殊存在,雖然各章節間時間有所重疊,但展現了不同主題[19]viii。他還指出,沈復以詩歌、散記、官史所采用的簡潔的文學語言進行書寫,而非明清時期流行的長篇小說、戲劇慣用的冗長的口語敘事,能較快進入詩性、抒情的敘事模式,描摹自我內心感受、與他人的愛恨情仇以及自然世界之美[19]viii。不僅如此,Sanders在簡介中還提醒讀者,在閱讀時注意容易產生誤解之處。譬如,陳蕓喜愛憨園很可能是為取悅丈夫,作品的多層拼貼結構與人類記憶本身的樣態極為相似,表現出選擇性、前后矛盾、循環往復、情緒化等特點。
Sanders在一次訪談中曾坦言,翻譯這部作品時自己一直努力保留沈復原文中流暢、抒情、率真的特質[20]。他對原文的深刻理解、對其價值底蘊的執著追求和深入闡釋,令《浮生六記》在海外獲得了較好反響。美國漢學家Michael Gibbs Hill(韓嵩文)對Sanders譯本大為褒獎,認為Sanders為學生、教師和學者奉上了一部全新且權威的譯本,再現了沈復古雅飄逸的文筆,讓人領略到作者的書寫風格和古文散記的意蘊[21]。加拿大中國文學研究專家Milena Dole?elová-Velingerová指出,這部讓中國讀者癡迷一個多世紀的經典,最終在Sanders的努力下才以應有的英文樣貌展現在世人面前,其翻譯融入了對原著語言、風格、結構的深刻理解[22]。美國英語文學研究學者Joe Sample認為,與其他三個譯本相比,Sanders譯本最為豐富、最為全面,完全可以作為性別研究、世界文學、比較文學以及創意寫作等課程讀本[23]。
六、結語
許鈞認為:“翻譯動機可以是多種多樣的。確實,它可以是政治的,文化的,也可以是藝術的。它可以是強大而明確的,也可以是微弱而隱約的。應該承認,任何一種翻譯活動,都受到一定的動機所驅動,都為著一定的目的去進行。”[6]《浮生六記》四英譯本譯者不同的翻譯動機或翻譯追求,不僅體現了譯者本人對作品的不同理解、對自己譯介活動的不同期待,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英語世界廣大讀者甚至專家學者對《浮生六記》的閱讀實踐,影響了他們的閱讀感受和對作品的接受。展望未來,關于翻譯動機與翻譯影響間關系的研究還需進一步加強,考察作品及相應譯本、譯者的范圍還要進一步擴大,如此可為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整體在海外的譯介傳播梳理出更為清晰的路徑,為今后深入推進中國文學“走出去”工作提供參考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