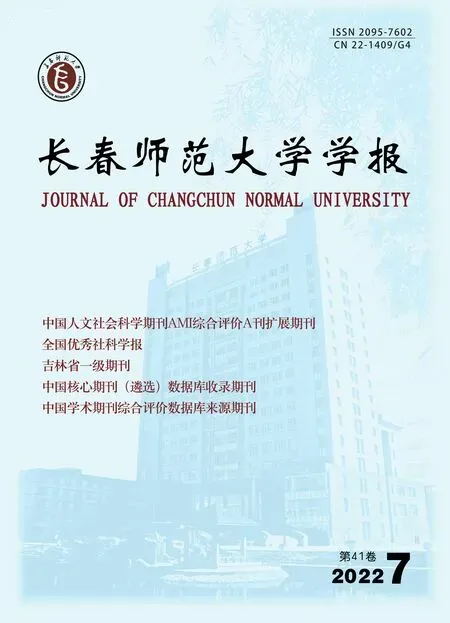“黃禍”語境下的傅滿洲角色塑造:一個關(guān)于刻板印象與陳規(guī)定型的迷思
黃瓊慧,陳 礦
(1.廣州華商學(xué)院,廣東 廣州 511399;2.成都大學(xué)中國-東盟藝術(shù)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0106)
20世紀上半葉,英國作家薩克斯·洛默(Sax Rohmer)在他的一系列小說中塑造了一個虛構(gòu)的華裔反派人物——傅滿洲博士(Dr. Fu Manchu)。近百年以來,這個角色在電影、電視、廣播、連環(huán)畫中都有廣泛的亮相,并已然成為邪惡的科學(xué)怪人與犯罪天才的角色原型,甚至連他的標志性胡須也成為一個別致的能指。
傅滿洲的形象在小說及其后各種媒介形式的改編作品中都有鮮明體現(xiàn)。他最具代表性的外貌特征在于狹長細窄、末端逐漸變尖并一直下垂到下巴的胡須,甚至牛津詞典都將“Fu Manchu mustache”一詞收錄在內(nèi),足以見得這一特征強烈的標出性。《陰險的傅滿洲博士》(TheInsidiousDr.FuManchu)中曾有這樣一段描述:“想象有這樣的一個人吧:身形高挑瘦削,束肩斂息,宛若一只饑腸轆轆的老貓;撒旦般的臉龐上有著莎翁式的眉宇……他神機妙算,坐擁著空前絕后的技術(shù)資源……想象一下這個可怕的存在,你腦海中便會浮現(xiàn)出傅滿洲博士的形象,‘黃禍’的概念便也化身為一個具象的人物。”[1]
本文致力于探討傅滿洲的角色塑造背后存在的社會性根源,即由刻板印象催生出的“黃禍”觀念;通過梳理“黃禍”這一隱喻的思想脈絡(luò),進一步審視傅滿洲及其他西方文藝作品中的華人形象創(chuàng)作由此受到的影響;并指出“黃禍”的種族主義恐慌在當下并未消散,呼吁文藝創(chuàng)作應(yīng)避免陳規(guī)定型的負面傾向。
一、概觀“黃禍”:從色彩隱喻到種族主義論調(diào)
“黃禍”(Yellow Peril),常常也被稱為“黃色恐怖”(Yellow Terror)或“黃色幽靈”(Yellow Spectre),是一個充斥著種族主義思想的色彩隱喻,也是殖民主義仇外心理的一個組成部分,即黃皮膚的東亞人被認為是西方世界的生存威脅。羅斯洛普·斯托達德(Lothrop Stoddard)在其論著《反對白人世界霸權(quán)的顏色浪潮》(TheRisingTideofColorAgainstWhiteWorld-Supremacy)中指出,作為一種對威脅的心理文化感知,作為仇外心理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這種基于臆想的東方“黃禍”恐懼是模糊的,它更多針對的是種族而非國家,是來源于對西方世界對岸的一群無名的黃種人的不祥恐懼;“黃禍”的意識形態(tài)將東亞人與“類人猿、矮子、原始人、瘋子和具有特異功能的人”等意象并置。[2]
據(jù)學(xué)者考證,這種偏見起源于公元前499年古希臘與波斯帝國之間的戰(zhàn)爭,在這場戰(zhàn)爭中出現(xiàn)了對東方有色人種的文化表征。幾個世紀以后,西方帝國主義的地理擴張進一步將東亞納入“黃禍”的范疇。[3]從詞源看,在19世紀末,來自沙皇俄國的社會學(xué)家雅克·諾維科夫(Jacques Novikow)在其論文《黃禍》(LePérilJaune)中首創(chuàng)了這個術(shù)語。從社會動員實踐來看,德意志皇帝凱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利用“黃禍”這樣的種族主義論調(diào)鼓勵歐洲各帝國入侵、征服與殖民當時的清朝。他甚至將1904年爆發(fā)的日俄戰(zhàn)爭中亞洲取得的勝利描述為對白人社會的種族主義威脅,并將清朝和日本的關(guān)系誤判為征服與奴役西方世界的聯(lián)盟。[4]
基于“黃禍”的各種政治實踐,種族主義政治家不斷呼吁白人之間形成某種程度上的種族團結(jié)。為了解決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當代社會不同領(lǐng)域爆發(fā)的突出問題,他們號召白人團結(jié)起來,以對抗來自亞洲的威脅。盡管他們利用各種手段在軍事上擊潰了反殖民主義的義和團運動,但是在西方世界,白人對當時東亞國家產(chǎn)生的民族主義的恐懼逐步上升為一種文化性恐懼,即黃種人試圖侵略和征服表征著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
漢學(xué)家梁永輝(Wing-Fai Leung)認為,“黃禍”這一概念及由此衍生出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融合了西方文明對性的焦慮、對異族威脅的恐懼,以及某種斯賓格勒式的信念,即所謂‘西方的沒落’,其終將被東方超越并奴役。”[5]吉娜·馬切蒂(Gina Marchetti)則認為,“‘黃禍’結(jié)合了對外來文化的種族主義恐懼、性焦慮,以及對西方將被東方不可抗拒的黑暗神秘力量壓倒和包圍的深信不疑”[6]。從國際形勢來看,鑒于日本日益崛起的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傾向,西方將日本人納入“黃禍”的指涉范圍當中。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作家們開始將所謂“黃禍文學(xué)”發(fā)展成為一種以種族主義為主題的敘事小說,并在故事中引入了殖民冒險、種族戰(zhàn)爭和科幻等元素。
西方文明存在的性焦慮是探討“黃禍”時不容忽視的一點。格式塔心理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奧地利哲學(xué)家克里斯蒂安·馮·厄棱費爾(Christian von Ehrenfels)認為,西方與東方正處在達爾文式的種族斗爭中,雙方爭奪世界霸權(quán),而黃種人正越來越接近于獲勝。他甚至指出,一夫一妻制在法律上阻礙了白人至上主義在全世界的發(fā)展,因為它將基因優(yōu)越的白人男性限制為只有一名女性的孩子的父親;而在當時東亞社會風(fēng)行的一夫多妻制中,黃種人似乎具有更大的生育優(yōu)勢,因為他們允許一個基因優(yōu)越的東亞男性與許多女性繁殖后代。
歷史學(xué)家克勞斯·特威里特(Klaus Theweleit)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研究,認為厄棱費爾將他對性的不安全感投射到“黃禍”的種族主義當中,而不像通常所謂“反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神話那般,后者是一種在德國社會中更為常見的偏見。同樣,特威里特認為,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歐洲的右翼雇傭軍組織“自由兵團”(Freikorps)的宣傳中也常常出現(xiàn)致命的水意象,猶太人和共產(chǎn)主義者對右翼歐洲人的世界觀構(gòu)成了政治和文化上的雙重威脅。“自由兵團”在心理上缺乏安全感,癡迷于男子氣概,并且急著想證明堅強的男性氣質(zhì)。他們使用水的負面意象反映出其對女性身體柔軟、情欲、愛、親密關(guān)系和人類依賴感的恐懼——這些元素在心理上威脅著他們,使他們顯得不那么男性沙文主義化。[7]
二、演繹“黃禍”:傅滿洲角色塑造背后的現(xiàn)實錯覺關(guān)聯(lián)
在西方殖民冒險小說中,“黃禍”是一個常見的主題,其中極具代表性的反派人物是由薩克斯·洛默創(chuàng)作的傅滿洲博士。傅滿洲是一個邪惡的華裔黑幫分子,他想征服世界,盡管他的計劃不斷地被英國警察和紳士間諜丹尼斯·內(nèi)蘭·史密斯爵士(Sir Denis Nayland Smith)及其助手佩特里博士(Dr. Petrie)挫敗。傅滿洲通常被描述為一個詭秘莫測的惡棍,因為他其實很少出現(xiàn)在舞臺上,而總是派他的爪牙為他犯罪。例如在《陰險的傅滿洲博士》里,傅滿洲往往派遣一位曼妙的女郎到案發(fā)現(xiàn)場幫他確認受害者是否已經(jīng)斃命。
在虛構(gòu)的故事當中,傅滿洲是“四藩集團”(Si-Fan)的頭目。這是一個國際犯罪組織,是一個從“東方最黑暗的地方”招募黨羽的泛亞謀殺團伙,有無數(shù)來自中國、緬甸、馬來亞和印度的暴徒愿意執(zhí)行傅滿洲的任何命令。小說中反復(fù)出現(xiàn)傅滿洲派遣刺客(通常是華人或印度人)去謀殺的情節(jié)。在冒險過程中,內(nèi)蘭·史密斯和佩特里博士往往被意圖傷害他們的有色外國人包圍。這無疑是對斯賓格勒式文化形態(tài)史觀,或者說是“東方侵入西方”的比喻。傅滿洲的出現(xiàn),使得華人被描繪成西方文化語境下的肇事者和威脅者。正因如此,“傅滿洲”這一角色在一些人看來成為“黃禍”的典型代表;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傅滿洲成為西方對華人的看法里最臭名昭著的化身,也成了當代“黃禍”題材創(chuàng)作中其他反面角色的標桿:這些反面角色身上往往具有與西方殖民主義時期對東亞人群的仇外意識形態(tài)相一致的特征。
在社會心理學(xué)中,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對某一特定類別的人的過度概括的信念。[8]有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可以建立在一種認知機制的基礎(chǔ)上,這種認知機制被稱為“錯覺關(guān)聯(lián)”(illusory correlation),是對兩個事件之間關(guān)系的一種錯誤推斷。如果兩個統(tǒng)計上罕見的事件同時發(fā)生,觀察者會高估這些事件同時發(fā)生的頻率;罕見的、不頻繁的事件是獨特和突出的,當它們成對出現(xiàn)時,會變得更加明顯;顯著性的提高導(dǎo)致更多的關(guān)注和更有效的編碼,這加強了事件相關(guān)的信念。在談到如何開始創(chuàng)作“傅滿洲”這一角色時,薩克斯·洛默聲稱自己對中國文化其實并沒有任何先入之見;據(jù)說當他對著占卜板求卦“對白種人而言,危機在何處”的時候,占卜板給出的答案是“C-H-I-N-A-M-A-N”——這或許是巧合,或許是心理暗示指引的下意識動作,他由此開始創(chuàng)作傅滿洲系列。然而巧合的是,在他創(chuàng)作這一角色的時候,正是“黃禍”觀念在北美社會傳播開來的時期。西方人曾擔(dān)心華人會通過埋頭苦干以更快的速度從大學(xué)畢業(yè),在白人主導(dǎo)的社會里爭奪資源;與此同時他們也極易沾染毒癮,讓社會陷入歇斯底里的境地。[9]洛默在與妻子合著的傳記《邪惡大師》(MasterofVillainy)中,對其被指將亞裔人妖魔化作出了回應(yīng):“當然,并非所有居住在萊姆豪斯的華人都是罪犯,但其中確實有許多人是因為最為緊迫的原因離開時自己的國家。這些人除了違法犯罪以外,并不知道如何謀生,于是乎,他們從中國帶來了他們的罪行。”洛默的論點是,他將傅滿洲和其他對“黃禍”的解讀,建立在他擔(dān)任萊姆豪斯當?shù)赜浾邥r接觸到的與華人有關(guān)系的犯罪案例的基礎(chǔ)之上。社會心理學(xué)家丹尼爾·卡茨(Daniel Katz)和肯尼斯·布拉里(Kenneth Braly)認為,當人們對一個群體產(chǎn)生情感反應(yīng),并將現(xiàn)實特征歸于該群體的成員,然后評估這些特征時,陳規(guī)定型會導(dǎo)致種族偏見。[10]有學(xué)者認為,作為反映“黃禍”的典型反派人物,傅滿洲這一角色的塑造來自洛默自身對異族擴張和侵犯的非理性恐懼。
即使少數(shù)群體和多數(shù)群體的行為或特征所占比例相同,錯覺關(guān)聯(lián)也會導(dǎo)致人們將罕見的行為或特征錯誤地歸為少數(shù)群體成員,而非多數(shù)群體。在傅滿洲系列作品里,我們看到創(chuàng)作者將威權(quán)主義、犯罪和性焦慮等廣泛存在于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強加在華裔角色身上。在洛默去世以后,他的傳記作者及前助理凱·范·阿什(Cay Van Ash)成為接手創(chuàng)作該系列的作家。據(jù)他的描述,“傅滿洲”其實是一個榮譽稱號,指的是“好戰(zhàn)的滿族人”(the warlike Manchu)。范·阿什推測,傅滿洲是滿清皇室的一員,在義和團運動中站錯了隊,支持了失敗的一方。在系列早期作品中,“四藩”是一個針對西方帝國主義進行暗殺行動的同盟組織,而傅滿洲是這個組織的一個特工。在后來的作品里,傅滿洲逐漸獲得了對“四藩”的控制權(quán),在他的領(lǐng)導(dǎo)下,“四藩”也從一個純粹扎根于華人的同盟會日益躍升為一個國際組織。除了試圖接管世界和恢復(fù)中華民族的古老榮耀之外,它還試圖擊潰法西斯獨裁者并組織共產(chǎn)主義的傳播。傅滿洲深知,這兩者會是他統(tǒng)治世界計劃的主要障礙。“四藩”這個名稱讓人容易想起中國古代的“四方”概念,即對中國邊區(qū)文化較低各族之泛稱。《禮記·王制》記載:“東曰夷,西曰戎,南曰蠻,北曰狄。”四境極遠之地,本來就充滿一種對異族的神秘想象。“四藩”的運作資金主要來源于各種犯罪活動,尤其是毒品貿(mào)易和對“白奴”的人口販運業(yè)務(wù)。傅滿洲通過服用長生不老藥,使自己已經(jīng)相當長的壽命繼續(xù)獲得延長,他甚至花了數(shù)十載的實踐不斷調(diào)配和完善這一配方。《奇怪的死亡之王:薩克斯·洛默的惡魔世界》(LordofStrangeDeaths:theFiendishWorldofSaxRohmer)一書批評洛默公然將傅滿洲塑造成一個極端的種族主義者。書中提到:“這些極其荒謬的作品,散發(fā)著瘋狂的異國情調(diào),實際上遠沒有它們最初看起來的那么兩極,那么黑白分明,甚至是‘黑黃分明’。”[11]1932年上映的電影《傅滿洲的面具》(TheMaskofFuManchu)反映出白人在“黃禍”意識形態(tài)面前折射出的性焦慮,例如傅滿洲在率領(lǐng)他的亞裔團伙時發(fā)號施令:“殺死白人,并擄走他們的女人!”在《傅滿洲的面具》中,父女之間的亂倫關(guān)系也是電影敘事反復(fù)出現(xiàn)的主題,尤其是傅滿洲和女兒之間的曖昧關(guān)系,這樣的情節(jié)設(shè)置被指影射黃種人社會里的戀童癖等非自然性欲。
刻板印象常常被認為是共享的(shared)。一個解釋是,它們是一個“共同環(huán)境”(common environment)的結(jié)果,這個環(huán)境刺激人們以同樣的方式作出反應(yīng)。[12]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研究表明,人們在描述不同的種族和民族群體時彼此非常相似,盡管這些人對他們所描述的群體沒有個人經(jīng)驗。[10]作為一個虛構(gòu)的民族主義者和犯罪首腦,傅滿洲引發(fā)了無數(shù)關(guān)于種族和“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爭議。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在1932年發(fā)行了改編自《傅滿洲的面具》的電影,當時的中國駐美大使館便對這部電影提出了抗議。在這部電影里,傅滿洲以一個惡棍的姿態(tài)吩咐他身邊聚集在一起的亞洲人(包括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必須“殺死白人并擄走他們的女人”。由共和電影公司(Republic Pictures)出品的改編電影《傅滿洲的鼓》(DrumsofFuManchu)在1940年上映之后,美國國務(wù)院要求該公司停止拍攝以傅滿洲為主角的電影,因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是美國的盟友。在美國參戰(zhàn)之后,與洛默合作的雙日出版社(Doubleday)拒絕出版傅滿洲系列小說的新作品。與此同時,英國廣播公司(BBC)和百老匯的投資者也取消了對傅滿洲系列的廣播劇與舞臺劇的創(chuàng)作提議。1972年,有電影院宣布重映《傅滿洲的面具》,但這一舉動遭到了日裔美國公民聯(lián)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的抗議,該聯(lián)盟稱這部電影“是對亞裔美國人的冒犯與貶低”[13]。有鑒于這場抗議活動帶來的波動,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決定取消對《傅滿洲復(fù)仇記》(TheVengeanceofFuManchu)的播送。洛杉磯的KTLA電視臺最初也有這樣的考量,然而最終還是決定播放《傅滿洲的新娘》(TheBridesofFuManchu),并在“聲明”中說:“這部電影作為虛構(gòu)的娛樂類節(jié)目,無意對任何種族、信仰或民族血統(tǒng)進行負面的反映。”[14]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之后,受傅滿洲啟發(fā)的邪惡刻板角色又一次日益成為挖苦諷刺的對象。“著名的中國竹薩克斯演奏家”弗雷德·傅滿洲(Fred Fu Manchu),是20世紀50年代的英國廣播喜劇《呆子秀》(TheGoonShow)中多次出演的角色。1955年,他甚至有了專屬劇集《弗萊德·傅滿洲的可怕復(fù)仇》(TheTerribleRevengeofFredFuManchu),還在《中國故事》(ChinaStory)、《黑夜堡壘的圍攻》(TheSiegeofFortNight)和《失落的皇帝》(TheLostEmperor)等劇集中客串出演“東方紋身師弗萊德·傅滿洲博士”一角。
由“黃禍”推導(dǎo)的種族刻板印象,是20世紀初俗文學(xué)中存在的普遍現(xiàn)象。傅滿洲系列作品出現(xiàn)后,又誕生了一些借鑒前者對“黃禍”的隱喻而創(chuàng)作的作品,例如由H·歐文·漢考克(H. Irving Hancock)創(chuàng)作的反派人物李朔(Li Shoon)于1916年第一次出現(xiàn)在《偵探故事》(DetectiveStory)雜志的《李朔的禁令》(UnderTheBanofLiShoon)和《李朔的致命任務(wù)》(LiShoon’sMission)這兩篇連載小說上。從肢體來看,李朔是一個又高又胖的男人,有著“渾圓的、滿月一般的黃臉蛋”,在“凹陷的眼睛”上方長著“鼓鼓的眉毛”;而就人格來說,李朔是“邪惡與智慧的驚人結(jié)合”,這讓他“對所有邪惡的事物都感到驚奇”,并有著“撒旦般狡猾的神奇”。基于對李朔的創(chuàng)作,1937年DC漫畫出版公司(DC Comics)又創(chuàng)作了《青龍》(ChingLung)這個作品。又如《閃電戈登》(FlashGordon)里的“無情的大明帝”(Emperor Ming the Merciless),也被認為是對傅滿洲系列作品的模仿。有學(xué)者稱之為“未來的黃禍”,將這位邪惡的虛構(gòu)帝王描述為“泛光的禿頂下是一對斜眼,長著彎彎的眉毛,留著尖尖的指甲,穿著奇特的東方華服”[15]。另一部漫畫《巴克·羅杰斯》(BuckRogers)描述了蒙古紅軍(Mongol Reds)在未來的25世紀征服了美國。20世紀50年代晚期,阿特拉斯漫畫公司(tlas Comics),也就是后來人們耳熟能詳?shù)穆荆瑒?chuàng)作了《黃爪》(YellowClaw),這被認為是對傅滿洲系列作品的仿制。不過這也是一個以亞裔對抗亞裔的作品,作品中的反派角色最終被其中的英雄人物——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亞裔特工吉米·吳(Jimmy Woo)擊敗。這對外界可能存在的種族主義懷疑而言是一種抵消,也是一種平衡。
三、反芻“黃禍”:對刻板印象引發(fā)文化癥候的省視與提防
無可否認,“黃禍”是一個典型的種族主義隱喻。在19世紀,極端種族主義者聲稱,黃色人種是對白色人種的威脅,并將吞噬歐“西方文明社會”(Western civilized society)。當時,“黃禍”是一種普遍的焦慮和恐懼,也是一些統(tǒng)治者用來攻擊東方的一個理由。20世紀初,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利用這一點鼓吹歐洲帝國對中國的入侵、征服和殖民化。人們被社會化后會接受同樣的刻板印象。一些學(xué)者認為,刻板印象通常是幼兒時期在父母、老師、同齡人和媒體的影響下形成的。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公眾輿論》(PublicOpinion)中反映了刻板印象的內(nèi)容依賴社會價值觀的觀點,即如果刻板印象是由社會價值觀定義的,那么刻板印象只會隨著社會價值觀的變化而變化。[16]
19世紀70年代,“黃禍”引起了美國社會的焦慮。由于害怕在經(jīng)濟衰退期間失業(yè),加州工人將亞洲移民歸入“骯臟的黃色群體”。一些美國人認為,從事低收入工作的勤勞的亞洲工人的出現(xiàn)對他們的生計構(gòu)成了威脅。這種厭惡導(dǎo)致了1882年的《排華法案》(ChineseExclusionAct),該法案不僅禁止華人成為美國公民,還牽涉到一些已經(jīng)擁有合法居留權(quán)的人。當時,著名記者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說過,“華人不文明、不潔、骯臟”,具有“淫蕩、肉欲的個性”[17]。這些負面特征也成為當時一些美國人心目中對華人的刻板印象。
平權(quán)運動逐漸削弱了美國人對亞洲人赤裸裸的歧視,取而代之的是對亞洲人(尤其是華人)正在侵蝕白人或西方文明霸權(quán)的更深恐懼,這可以被美國高等教育界證實。在1933年出版的小說《傅滿洲的新娘》中,傅滿洲聲稱自己擁有四所西方大學(xué)授予的博士學(xué)位。在1959年出版的小說《皇帝傅滿洲》(EmperorFuManchu)里,他透露自己曾就讀于海德堡大學(xué)、索邦大學(xué)和愛丁堡大學(xué)。而在《傅滿洲的面具》這部電影中,傅滿洲自豪地夸耀道:“我是愛丁堡大學(xué)的哲學(xué)博士、基督學(xué)院的法學(xué)博士和哈佛大學(xué)的醫(yī)學(xué)博士。我的朋友們出于禮貌,直接稱呼我為‘博士’。”在作品中,佩特里博士與傅滿洲博士第一次相遇是在1911年,那時佩特里博士認為傅滿洲已經(jīng)年過古稀,因此可以推斷,傅滿洲在19世紀60年代或70年代開始在西方攻讀他的第一個博士學(xué)位。無論如今亞裔身上裝點的是時尚領(lǐng)域還是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頭銜,抑或其他彰顯成功的標識,他們?nèi)匀缓茈y成為所謂主體性的“自我”,而被視為西方后殖民理論中的“他者”(the other)。2019年6月,有報道指出,哈佛大學(xué)在積極性、善意、勇氣和受尊重程度等人格特質(zhì)方面一直對亞裔申請人打出低于其他族裔申請人的評分。[18]這表明即使亞洲精英有能力進入美國常春藤盟校,他們的“優(yōu)秀”反而會成為對既得利益白人的威脅,從而遭到拒絕。“模范少數(shù)族裔”(model minority)一詞既否定了個人付出的努力,又貶低了其他種族。這個詞乍聽之下像是恭維,實則不然,因為對成功的期望本身就是一個問題。認為亞洲人有優(yōu)勢的想法源于白人社會對其將“被接管”的恐懼:這是一個被重新包裝的新“黃禍”。
刻板印象的觀念是我們社會中的嚴重問題,它可能產(chǎn)生的不利影響包括:越來越多毫無根據(jù)的偏見使得人們不愿重新思考自己的態(tài)度和行為,因此某些被陳規(guī)定型的人會被阻止在其活動領(lǐng)域中取得成功。不同的學(xué)科對刻板印象形成的原因給出了不同解釋:心理學(xué)家可能關(guān)注個體與群體的經(jīng)歷,以及群體的溝通模式和群體間的沖突;社會學(xué)家可能關(guān)注社會結(jié)構(gòu)中不同群體之間的關(guān)系,他們認為刻板印象本身是沖突且糟糕的,它是人們精神和情感發(fā)展不足的體現(xiàn)。一旦刻板印象形成,有兩個主要因素可以解釋它們的持久性。第一,圖式(schema)加工處理的認知效應(yīng),當一個群體的成員如人們期望的那樣行動時,這種行動證實甚至強化了現(xiàn)有的刻板印象;第二,偏見使得反對刻板印象的邏輯論據(jù)在對抗情感反應(yīng)的力量時無效。[19]由于種族、性別或性取向限制了人們的行為方式,陳規(guī)定型觀念的負面形象會讓人憎恨少數(shù)群體,甚至導(dǎo)致仇恨犯罪。
從社會現(xiàn)實再回過頭來看傅滿洲引發(fā)的文化癥候,我們發(fā)現(xiàn)文藝創(chuàng)作一方面觀照著時代與社會,另一方面對現(xiàn)實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幸的是,許多文藝創(chuàng)作將現(xiàn)實扭曲,提供了一種將世界淺顯地分為好與壞、善與惡、忠與奸的呈現(xiàn)方式。20世紀至今,以歐美為強勢主導(dǎo)的文化產(chǎn)業(yè)中的亞洲人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刻板印象和代表性不足的困擾。從歷史上看,假若亞洲人不曾被塑造成刻板化形象,那么他們似乎像是從未被賦予任何角色,也更容易被相應(yīng)文化產(chǎn)業(yè)的受眾及更廣泛的社會大眾忽視。亞洲人在文化產(chǎn)業(yè)中的邊緣化角色,對他們在社會中被如何看待產(chǎn)生了破壞性影響。
文藝創(chuàng)作及承載它們的媒介對敘事題材和形式的影響從來都不是完全透明的,這種影響尤其體現(xiàn)在傅滿洲這樣的“系列人物”的制作中。在這種背景下,媒介不僅充當敘事平臺,而且憑借自身的力量成為自我反思的對象,體現(xiàn)出不斷變化的敘事功能。從傅滿洲的案例出發(fā),在亞洲人尤其是華人的媒介形象呈現(xiàn)的問題上,我們還需要進行更細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