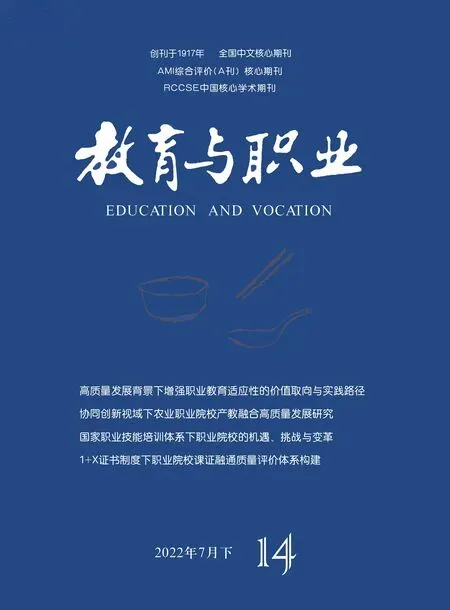張謇社會治理思想與黃炎培農村改進思想的比較及啟示
唐千千 唐勇
清末民初,隨著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受西方實用主義思潮影響,實業教育開始在我國興起。張謇、黃炎培都秉承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理想,分別基于社會治理思想和農村改進思想進行實踐探索,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追溯我國教育家在職業教育服務鄉村建設方面的實踐探索歷程,對職業教育更好地服務鄉村振興戰略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經驗借鑒價值。
一、社會治理思想與農村改進思想的緣起
(一)社會治理思想的緣起
1.歷史驅動下的實業教育救國實踐。甲午戰爭失敗后,帝國主義加緊對我國的經濟侵略,使我國民族工商業發展舉步維艱。在此背景下,張謇與其他民族工商業者提出了“實業救國”的主張,認為國家處于危亡之際,人民生活日益艱難,富國圖強迫在眉睫。當務之急,唯有重視實業,發展教育,除此別無他法。他進而提出“父教育,母實業”“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①。為實現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理想,1895年,張謇在南通創辦大生紗廠,并先后創建企業60多家、各類學校370余所,開啟了在南通長達30年的地方治理實踐。
2.國外考察影響下的地方自治構想。張謇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也堅定了實施地方治理的信心,其間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變法平議》中萌生地方自治思想。早在1901年張謇所著的《變法平議》中已有地方自治的設想。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影響,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發展變革、各項政治制度的實施,若要老百姓擁護,“權衡樞紐,必在議會”②。他在《變法平議》中提出府縣議會制,寄望于鄉紳通過地方府縣議會,達到“釋民教之爭”“通上下之情”,這是最初的地方自治思想。第二階段:赴日本考察過程中構思了城市自治思想。1903年,張謇赴日本考察,其間參觀了20多個城市,對日本明治維新后的政治制度、城市治理以及城市交通、市政建設等方面作了詳細了解。他看重士大夫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指出“士大夫生于民間,而不遠于君相,然則消息其間,非士大夫之責而誰責哉?”③他還對中西方歷史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中國古代的地方治理主要是“官治”;而現代西方受專制政治少,所以在地方“別乎官治而言自治”④,甚贊“日本維新,先規道路之制,有國道焉,有縣道焉,有市鄉之道焉”⑤。訪日后,他的城市建設與社會發展理念逐漸形成,地方自治藍圖逐步勾畫。
(二)農村改進思想的緣起
1.歷史背景驅動下的農村改進實踐。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中國民族工業逐漸走向衰弱,農村更是一片凋敝。為解決農村問題,一批愛國知識分子開始關注農村發展,一場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應運而生。在這一背景下,黃炎培和他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開啟了農村改進的教育實踐。
2.國內教育考察后的農村改進構想。黃炎培早在民國初期就開始關注農村民生疾苦,其農村改進思想也在考察民生的過程中歷經四個發展階段漸成體系。第一,初步思考階段。1914年2月,黃炎培在考察浙江、江西、安徽三省的教育及社會狀況后又北上山東、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對農村凋敝、民不聊生的疾苦有了深刻了解,并將兩次考察見聞寫成《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第一集、第二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通過這兩次國內考察,黃炎培從實用主義教育觀出發,開始思考農村教育問題。第二,專門調查階段。1917年5月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后,黃炎培便開始對農村教育進行專門調查。是年11月,他親赴江陰、南通、蘇州考察農業教育,其間參觀了張謇創辦的南通農校。他特別肯定了農校因地制宜、根據當地需要設置課程的做法,也肯定了農校與當地農民實際生活的密切聯系。這表明黃炎培在主張因地制宜辦農村教育的同時,開始關注農村社會治理問題。第三,切實探討階段。1920年,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農業教育研究會”,開展對農村教育的專門研究,并廣泛開展相關合作,與中華農學會、中華教育改進社共同擬定推廣農村教育的方案,制訂農村教育計劃,舉辦全國農業討論會。討論會認為“農業之衰敗有江河日下之勢”,如果不奮力改變,國家經濟就“永無活動與發展之希望”⑥。與此同時,中華職業教育社接受一些省的委托,為其規劃農村職業教育,并開展了大量的農村調查。第四,形成體系階段。1925年8月,黃炎培為山西省籌劃職業教育,正式提出了“劃區試辦鄉村職業”計劃,這是他第一次比較全面、系統地思考農村改進方略。是年底,他提出了“大職業教育主義”,并把農村改進作為大職業教育的具體實踐。1926年,他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正式創辦徐公橋鄉村改進區,拉開了農村改進試驗的大幕。
不難看出,張謇的社會治理思想與黃炎培的農村改進思想誕生的歷史背景不同。張謇的社會治理思想萌發于清末民初,當時社會經歷了中日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以及辛亥革命,一大批仁人志士寄望于通過振興實業來實現救亡圖存的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民族工商業開始萌芽并迅速發展,正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張謇開始了地方治理試驗。黃炎培的農村改進思想則誕生于在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此時我國民族工業開始衰微,社會建設重心開始移向農村,鄉村建設運動開始興起,到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已成燎原之勢。在這一社會背景下,黃炎培及他所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開始了農村改進試驗。雖然兩位所處的歷史背景有所不同,但都基于愛國這一出發點,在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這一點上殊途同歸。
二、教育在社會治理與農村改進中的作用比較
(一)教育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及實踐
1.地方自治思想產生的動因。地方自治原本是西方的一種地方政治體制,隨著清末立憲運動的開展得以在我國傳播。張謇是立憲的積極倡導者,也是地方治理最早的探索者和實踐者。1909年,清政府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強調“地方自治為立憲之根本,城鎮鄉又為自治之初基”⑦,把地方自治作為立憲之本。但是,清政府的地方自治失去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只是地方紳士與中央政府分權的代名詞。張謇在政治上屢屢受挫后,決心經營鄉里,獨自走一條地方自治之路,“志在求一縣之自治”⑧。他指出:“今人民痛苦極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頑固如此;求援于社會,社會腐敗如彼。然則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豈有他哉。”⑨
2.地方自治的內容體系。清政府強調“地方自治”是“輔佐官治”,地方官員有權組成城鎮鄉議事會、董事會,并有權撤銷自治職員。張謇主張的地方自治希望憲法能充分保障“民治”,“進我人民參與政權之地,而使之共負國家之責任”;“民治無非是在政府無力承擔發展地方事務的條件下,渴望政府給予地方較大的自主權,從而最大限度地激發地方士紳建設地方的責任感和積極性,全面推進地方建設事業”⑩。從地方自治的內容看,張謇以南通作為區域自治試驗區,認為地方自治是救國治本之道,國家的強盛靠自治,而自治最重要的內容是實業教育并輔之以慈善。所以,舉辦實業、教育、慈善等地方建設事業,是張謇地方自治思想的主要內容,也是其地方自治規劃中的三大支柱。張謇闡述三者的關系是:“以為舉事必先智,啟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達,乃先實業;實業、教育既相資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11]先實業后教育的思想,體現了他作為儒家知識分子“富而教之”的思想。
(二)教育在農村改進中的作用及實踐
1.農村改進的理論基礎。黃炎培的大職業教育主義觀主張職業教育要與廣闊的社會生活聯系起來,若不與整個社會、各行各業結合起來,就“不能發達職業教育”[12]。他主張職業學校要和一切教育界、職業界溝通、聯絡,提倡職業教育要“參加全社會的運動”,融入整個的社會生活。基于這一認識,他把發展農村教育視為實現大職業教育的重要途徑,并提出職業教育要“為大多數平民謀幸福”,要“決心腳踏實地、用極辟實的工夫去做”[13]。他還指出,職業教育要努力和勞動界聯絡,根據農村老百姓的需要傳授相應知識,以此來改善他們的生活。正是以大職業教育為理論基礎,黃炎培帶領中華職業教育社同仁在農村開展了“富教結合”的農村改進試驗區工作,提出“富教合一”“劃區施教,先富后教,綜合改進”。在實踐中黃炎培發現,當時農村最根本的病癥是一個“窮”字,要治“窮”病,就“要使它富……隨富隨教,即富即教”“先富之,后教之”[14]。他的這種改進理論打破了學校與社會隔絕的傳統模式,將農村改進事業推向高潮。
2.農村改進教育的實踐探索。農村改進試驗之初,黃炎培提出要“特別注重農村教育,一時雖不能推及各地,但擬就交通便宜之地擇一區或數區,實施改進農民生活,漸及各地”[15]。1926年6月,黃炎培和楊衛玉赴昆山調查,最終確定以昆山徐公橋作為農村改進試驗區,并擬定了《改進農村生活事業大綱》。大綱規定其任務有“散布改良種子”“改進小學教育,推行義務教育”“施行職業指導”“籌設通俗圖書館及演講所”“實行衛生運動”“提倡修治道路”“增加娛樂機會”[16]等。自徐公橋試驗區之后,中華職業教育社又先后設立了鎮江黃墟農村改進試驗區、吳縣善人橋改進區、滬郊農村改進區等,同時還設立推廣新農具的推行所等。據不完全統計,1926—1935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的農村改進機構近30個,特別是推廣新農具的區域幾乎遍及全國。
張謇和黃炎培開展的教育實踐,都基于對民生的關注,都是為了解決民生疾苦問題。張謇看到“人民痛苦極矣”,靠政府、社會無法救人民于水火,才投身于地方自治,希望通過自治而自救。“自治之本,在實業教育”“舍注重實業教育外,更無急要之計劃”[17]。他辦教育的出發點是“探究國民他日生計之關系”“教育以普及為本,普及以生計為先”[18]。黃炎培實施農村改進,也著眼于人民生計,認為“根本上解決生計問題,厥為教育”[19]。為解決人民生計問題,黃炎培提出了“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在地方自治思想和農村改進思想的具體實施步驟上,張謇主張實業為先,并贊同“孔子‘富而教之’之義”,認為辦實業必須先“開啟民智”,而“啟民智必由教育”。辦教育需要經濟支撐,只有先辦實業,然后才有財力發展教育,此乃“實業教育既相資有成”[20]。張謇“富而教之”的理念與黃炎培農村改進思想中主張的“先富后教”理念是一致的。
張謇的社會治理思想以南通為試驗區,實行“區域自治”,著眼于市政建設及社會公益事業等并大量舉辦實業;黃炎培的農村改進思想則“劃區施教”,因地制宜劃成若干區域進行試驗,著眼于農民的具體生計問題,其實施內容包括產業調整、種子改良、土地改良、新農具推廣等,通過施教實現“鄉村自治”。雖然兩者的著眼點不同,實施范圍不同,但都強調發揮教育的作用和功能,從而提高民眾素質,改善民眾生計,改變社會面貌。
三、教育在社會治理與農村改進中的成就及影響
(一)教育在南通社會治理中的成就及影響
張謇經營南通近30年,以“教育與實業迭相為用”,在城鎮、交通、水利建設及社會公益慈善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特別是圍繞城市建設發展實業和教育,精心布局,細心打造。
1.城鎮建設方面。張謇在南通城鄉建設上圍繞南通舊城政治行政及商業中心,在周邊方圓6~7千米范圍進行一市三鎮的布局,從整體上看,區域功能分工明確,城鄉交錯嵌合,形成了相對科學合理的空間布局。
2.交通建設方面。張謇考察日本,看到“日本維新,先規道路之制,有國道焉,有縣道焉,有市鄉之道焉”[21]。他說:“地方實業教育,官廳之民政軍政,機紐全在交通。”[22]張謇所規劃的一市三鎮區域,其間修筑公路連接,并從美國購買10輛公共汽車進行運營,成為我國近現代史上最早運營的公路。
3.水利建設方面。張謇先后擔任全國水利總裁、導淮水利督辦、治運督辦等,從事治淮水利事業20余年,其間引進西方近代水利工程方法,制訂科學的治淮水利方案,加強南通全境水利建設,創立了我國近現代史上第一所專門培養現代水利工程技術人才的高等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為我國培養了最早的一批水利工程技術人才。
4.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方面。除了交通、水利等建設之外,張謇還在南通城市的東西南北中區域各建公園一座。他說:“實業教育,勞苦事也;公園則逸而樂;償勞以逸,償苦以樂……以少少人之勞苦,成多人之逸樂。”[23]在張謇看來,地方自治主要解決“教”和“養”兩大問題,而“養”主要依靠慈善公益事業。南通建立了諸如養老院、育嬰堂、殘廢院、盲啞學校等系列“社會公益慈善事業”[24],初步展示了現代化城市的特性。
在20世紀初的中國,南通社會治理成績顯著,成為聞名一時的“模范縣”,“是中國人在完全沒有外國人幫助的情況下自行建設的一個很有意義的典范城市”[25]。
(二)教育在農村改進中的成就及影響
黃炎培所進行的農村改進試驗,主要表現為普及農村文化教育、改進農村風俗習慣、推廣農業技術等。黃炎培在《改進農村生活事業大綱》中明確提出的任務包括“改進小學教育,推行義務教育”“推行平民教育”“施行職業指導”“籌設通俗圖書館及演講所”“實行衛生運動”“勸導戒除煙賭”“增加娛樂機會”[26]等,實現“使學校無不用之材,社會無不學之業,國無不教之民,民無不樂之生”[27]的目標。以徐公橋實驗區為例,在試驗期,廣泛開展農村各種改進事項,包括推行新農具、試驗優良種子、舉辦農產展覽、建立信用和消費合作社、修建小學、開辦民眾夜校、整理村政、設立民眾公園、成立公共醫診所等。經過6年努力,徐公橋試驗區實現了“沒有失業的游民,沒有竊物的小偷,也沒有沿街乞討的乞丐。區內盜賊不興,煙賭絕跡,人民安居樂業”,是“純潔的太平之鄉”,是“小小一塊凈土”[28]。
張謇的地方自治思想和黃炎培的鄉村治理思想都是從教育入手,以喚起民眾的自覺為出發點,在20世紀初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們的不同在于:其一,在實施對象上,張謇著眼于城市建設,其設計規劃的南通市成為未來城市建設的樣板;黃炎培則著眼于農村發展,其創辦的農村改進試驗區為我國農村的發展提供了示范。其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張謇重在發展實業和實業教育;黃炎培則在發展農村文化教育的基礎上,更多提倡改良種子、推廣新農具、發展建設新農場。兩位先賢雖然探索的路徑和方式有所不同,但殊途同歸,都體現了希望通過教育來啟發民眾思想進而改變社會面貌、實現社會變革的理念。
四、社會治理思想和農村改進思想對當前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啟示
張謇、黃炎培都是我國近現代職業教育的開拓者、奠基人,他們同在江蘇進行了教育救國的實踐探索,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對今天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重視農業農村教育,培養適用人才
2019年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提出職業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也明確指出“鄉村振興,關鍵在人”,提出要“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撐”[29]。這些均強調了教育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性,與張謇重視教育、啟發民智、主張“富而教之”的思想是一致的。張謇注重農村產業的發展,目的是“沒有飯吃的人,要他有飯吃,生活困苦的,使能夠逐漸提高”[30]。他尤其關注農業,認為“民生之本農為本”[31],認為立國之本不在兵、不在商,“在乎工與農,而農為尤要”[32]。他在言及地方自治中的實業教育時認為,教育是改造社會的主要手段,“一國之強,基于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達,乃先實業”,即所謂“富而教之”[33]。黃炎培認為,職業教育對個人來說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對社會來說則是促進各項事業的發展。他認為我國的主體是農村,大部分人口在農村,因此,發展教育、普及教育的重點也應放在農村,“學校十之八九當屬于鄉村,即其所設施十之八九,當為適于鄉村生活之教育”[34]。他還指出,“我國向以農業立國……今組織此會,即可討論農業教育如何改進,農事試驗用如何之科學方法以促成之”[35],強調了鄉村教育對鄉村改良的重要性。
以教育為手段,以發展實業、產業,改善人們的生活為目標,是張謇和黃炎培共同的社會改造理念。這對于當前服務鄉村振興、促進農業農村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借鑒價值。在職業教育服務鄉村振興的過程中,也應以培養農村人才、發展農村產業為重點,充分發揮職業教育的功能,為農村培養更多懂技術、懂管理、會經營的本土人才,從而為農村農業的發展打下堅實的人才基礎。
(二)加強農村文化建設,創新鄉土文化
張謇把鄉村文化公益事業作為地方自治的重要內容,不僅創建了若干體育場,還先后創建了博物苑、圖書館、伶人學會、更俗劇場以及若干公園。在文化建設中,他特別注重戲劇改良,認為“改良社會措手之處,以戲劇為近”[36],強調“戲劇不僅繁榮實業,抑且補助教育之不足”[37]。張謇在南通地方自治中對文化建設的重視,為我們今天開展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的鄉村文化建設提供了典范。
黃炎培在農村改進教育實驗中也把建設文化公益事業作為重要的著力點。他在昆山徐公橋試驗區從事農村改進實驗時特別提出“籌設通俗圖書館及講演所”“實行衛生運動”“增加娛樂機會”等,“以徐公橋為用力集中點,略分精力,協助確有能力之機關,進行改良農村生活事業”[38]。黃炎培在農村改進中注重文化公益事業建設,啟發我們在實施鄉村產業振興、發展教育事業的同時,要高度重視鄉村文化公益事業的發展。
張謇、黃炎培發展鄉村文化公益事業的實踐,啟示我們在服務鄉村振興中要注重農村文化事業建設,把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鄉村文化事業的發展中,通過建設鄉村文化廣場、文化禮堂、鄉村戲臺、非遺文化傳承場所、鄉村博物館等,開展農村文化宣傳、展覽、文娛會演等活動,豐富鄉村文化;要繼承和弘揚優秀文化傳統,移風易俗,創新鄉土文化,建設美麗鄉村。
(三)堅持劃區施教,因地制宜實施
就地方自治而言,張謇認為沒有必要羨慕外來新奇的自治理念,關鍵要適合國情和民情。他說要“不慕于外之新且異,不強人以就我,不貶我以就人”[39],在地方自治中要“國無大,一家無小,視吾力所能,大不足矜,小不足餒”[40]。他要求學校做到“學必期于用,用必適于地”,“在江蘇南通講教育,先要想什么是南通所需要的,什么是適合南通的”[41],為因地制宜開展鄉村振興提供了很好的樣板。
黃炎培也提倡因地制宜,強調社會需要什么人才,就辦什么學校。他說辦農村學校,要利用一區域所擁有的資源,投入人力、財力。他特別強調農村學校一定要與當地實際情況相結合,使學校成為當地職業教育最重要的機關。在農村改進中,他主張教育要與農業融為一體;教育一方面要解決農民的生計問題,另一方面要發展農村產業。他強調,在農村學校,無論是教學形式、課程設置,還是教學時間、地點安排,都要根據農民的實際情況確定。農村改進只要從農村實際出發,順應農村的需要,就能得到農民的擁護,“只需把有利的事實給人們看,不怕人家不照辦”[42]。這些觀念都啟發我們實施鄉村振興一定要因地制宜,不可一刀切。
張謇、黃炎培在鄉村教育中因地制宜、按需施教的做法,啟示我們在實施職業教育服務鄉村振興中,要堅持從實際出發,把鄉村教育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結合起來、與當地文化及風土人情結合起來,從農民的實際需要出發,分區分類開展職業教育與培訓,采取多層次、多形式、多種類的教育與培訓,不搞齊步走、一刀切,為農民提供內容豐富、靈活多樣又適合實際需要的職業教育。
五、結語
綜上所述,張謇和黃炎培在20世紀初都進行了教育救國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張謇認為教育是救國的根本,極力主張廢科舉,辦新式學校。他在南通興辦實業,廣開學堂,希望通過教育提高國民整體素質以彌補早期洋務運動之不足,實現強國富民的目的。黃炎培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了大職業教育觀,并借助農村改進實驗區來踐行大職業教育,在農村積極推行小學教育改革,實行義務教育,開展平民職業教育,施行職業指導。從徐公橋試驗區開始,通過劃區施教,建立了一系列農村改進試驗區,以此解決平民的生計問題,實現“為大多數平民謀幸福”的理想。張謇和黃炎培的教育救國實踐與探索,雖然所處的歷史環境不同,其思想基礎和核心內容也有所差異,但都重視教育,希望借此啟發民智、改善社會面貌、改革社會治理體系,對于當前實施的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當前實施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應當高度重視農村教育,培養農業技術人才,發展農村文化,打造特有的鄉土文化,同時堅持劃區施教,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開展農業農村農民教育,創新發展鄉村農耕文化。只有這樣,才能走出一條特色鮮明、行之有效的鄉村振興之路。
[注釋]
①曹從坡,楊桐,向榮,等.張謇全集:第6卷[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480.
②曹從坡,楊桐,向榮,等.張謇全集:第1卷[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53.
③⑦⑩[21][24][25][37]虞和平.張謇——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前驅[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491,79,78-79,512,517,509,294.
④⑤⑧⑨[11][17][20][22][23][32][33][36][39][40]曹從坡,楊桐,向榮,等.張謇全集:第4卷[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467-468,398,147,439,91,468,398,411-413,427,468,291-292,468,490,13.
⑥崔軍偉.試析民國時期中華職業教育社向農村改進事業的轉向[J].蘭州學刊,2010(7):204.
[12][16][26][34]謝長法.教育家黃炎培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162,174,174,134-136.
[13][15][27]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446,426-427,182.
[14]許瑞泉.黃炎培農村改進理論與晏陽初鄉村教育思想之比較[J].科技信息,2006(7):205.
[18]羌建,馬萬明.張謇與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及實踐之比較研究[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6):140.
[19]尚丁.黃炎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1.
[28]胡均偉,王智.梁漱溟和黃炎培鄉村教育思想比較研究[J].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4):14.
[29]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EB/OL].(2021-02-23)[2022-04-10].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3/content_5588496.htm.
[30]劉厚生.張謇傳記[M].上海:上海書店,1985:252.
[31]曹從坡,楊桐,向榮,等.張謇全集:第3卷[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801.
[35]黃炎培.記山東之三大盛會[N].申報,1922-07-09(10).
[38]黃炎培.改進農村生活社之董事會[N].申報,1927-01-11(8).
[41]千江月.張謇傳——近代中國實業第一人[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21:274.
[42]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教育文選:第2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