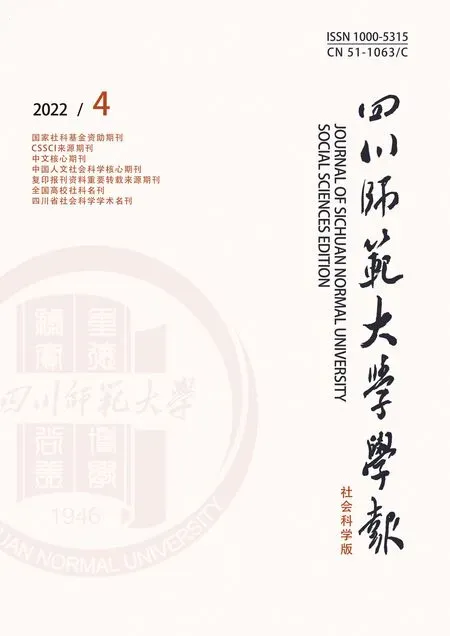《文心雕龍》“文體訛濫”說探原
陳貝 高林廣
《文心雕龍·序志》言:“而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1)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726頁。按:后引《文心雕龍》文句皆本此書,標點依現代用法,略有改動;如非必要,不引校語。劉勰舉“文體訛濫”作為對江左文風的基本判斷,不僅總結了“訛濫”的主要表現,也分析了其產生的社會文化根源,更重要的是,劉勰還臚列了療治其弊的創作原則、藝術手法及文辭運用等。所謂訛濫之“文體”,并非單指文章的體類或形式,也非普通意義上的體裁、體貌一類,而是兼有體統范式、體貌風神、體裁風格等眾多內容。因此,“文體訛濫”說實際上包涵和反映了劉勰“雅潤準的”的本末觀、“為情造文”的情辭觀、“銜華佩實”的文辭觀、“蔚風嚴骨”的風骨觀、“資故酌新”的通變觀等,是一個完整、嚴密的系統理論。“正本矯訛”是劉勰的立論基礎與文論精髓,也是釋解《文心雕龍》最為關鍵的一環。
一 明其體統,識其本然:劉勰對“文體”的體認
“文體”一詞,在《文心雕龍》中屢有出現,如《宗經》“文能宗經,體有六義”,《風骨》“洞曉情變,曲昭文體”,《序志》“去圣久遠,文體解散”等(2)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23、514、726頁。。劉勰持廣義文體觀,此中之“文體”并非單指體式或體類。《文心雕龍》中的“體”或“文體”,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含義和指向。前賢對此有所總結,如,范文瀾將《文心雕龍》二十一篇文體論歸為文類、文筆類、筆類三部分(3)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4-5頁。;羅宗強曾指出,《文心雕龍》之“文體”,兼有“體裁”、“體貌”之意(4)羅宗強《劉勰文體論識微(續篇)》,羅宗強《讀文心雕龍手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68-170頁。;羅根澤又以“體派”論《文心雕龍》之文體(5)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81-183頁。;徐復觀則以為,劉勰所指之體乃“體貌”、“體要”、“體制”之體(6)徐復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1頁。;郭紹虞則論為“風格或體制”(7)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42頁。;詹福瑞認為,“‘體’既是體裁,亦指體制、體統”(8)詹福瑞《怎樣讀〈文心雕龍〉》,《中華讀書報》2017年3月1日,第8版。。可見,《文心雕龍》中的“文體”指向確乎異常復雜,各家釋解亦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就其所針對的“訛濫”文風而言,本文認為,劉勰的文體論主要以“體統”、“體貌”、“體裁”為基本致思路徑,這是窺測其“文體訛濫”說的關鍵所在。
(一)體統之正與體制之要
“體”是中國古代文論中最為復雜的概念之一。《文心雕龍》的“文體”首先是指以道為本然的文章“體統”、“體制”,同時也體現傳統儒學規范萬物秩序的思想和理念,是為文之大局和肇始,也是彌倫群言的基礎和依憑。紀昀評劉勰《原道》云:“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眾流。”(9)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4頁。紀昀之論,揭示了劉勰“尊體”的根源在于統體之道。六朝時期文道離間,舍本逐末,直接表現為文體流變而至“訛濫”。文道分離必然有傷體之正統,影響到體的規范性和表現力,道亦不能一以貫之。因而,尊體、變體成為了《文心雕龍》討論的重點。
體統,即體之統合。《附會》言:
夫畫者謹發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銳精細巧,必疏體統。(10)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51頁。
劉勰認為,文章若專意于細節描繪,必然會疏離于體統之外。文體的語言結構“呈現自我合目的統一完整性”(11)龔鵬程《劉勰的文體論》,《關東學刊》2020年第4期,第33頁。,“合目的”即是對文章道統的內在要求。凡是“合目的”的文章,就是“正體”,不“合目的”者,則為“訛濫之體”。“正體”如四言詩,以垂示儒家典誥之訓為目的。《明詩》云: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12)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7頁。
傳統上以四言為詩之“正體”,因此,劉勰強調以典雅溫潤為根本;五言詩,劉勰以為是“流調”,主張以清新華麗為主宗。所謂“正體”,亦謂“本體”,即指合乎文類基本要求規范的體式或風格,更接近“合道”之體統。四言以《詩經》為代表,自然有其典雅溫潤之遺風;五言雖主清麗而為變體,但劉勰并不反對運用此體,他認為,如果能做到“神理共契”,即作家的神志符合自然之規律,則不為訛濫。
訛體,是與正體相對的范式,如《頌贊》云:“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這里所言“訛體”,就如“義(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13)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158頁。,指違背某一特定文體基本要求的體式或風格。陳思王曹植所作的《皇太子生頌》和陸機所作的《漢高祖功臣頌》都有連綴鋪陳的特點,并不符合“頌”體原本應有的典懿清鑠的文辭特點,因此,劉勰目為“訛體”。此論意在說明,文辭(如“頌”)為道之有形之體,是無形之道的寄寓和依托。立言行事要符合儒家法度,文章寫作要以正制訛,合于傳統規范,合于圣賢制定的綱常倫理,這樣才能實現文體的純正與典范。
體,亦謂體制之體,是附著情志、事義、文辭的結構楷式。《附會》云:
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后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14)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50頁。
劉勰以人喻文,以人體喻文體,認為思想感情為文章之精神,事義為骨骼,辭采為肌膚,語言音調為聲氣。顯然,情志、事義、辭采和宮商四者是構成文章“體制”的關鍵要素。詹锳謂“體制”“包括體裁及其在情志、事義、辭采、宮商等方面的規格要求,也包括風格”(15)詹锳《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3頁。。縱觀劉勰各篇論述可知,其文體觀緊扣文辭觀、風骨觀,強調了文辭、風骨的整體關聯性,文辭、風骨是糾正文體訛變的內在動力。因而,作者只有尊崇法度并加以實現,方能標舉文章的風清骨峻。
《文心雕龍》“文體”之“體”亦是“體要”之“體”。徐復觀解釋“體要”之體:“系以事義為主之文章而來。”(16)徐復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第30頁。徐氏的釋解指向了觀點、事義。他認為,相對于楚辭系統的感情傳統,體要之“體”則代表著以《詩經》為傳統的“事義”系統;以“華侈”與“典雅”為例,凡是與體貌(精神風格)不相符契的體要(觀點事義)都是累贅。但從《文心雕龍》文體論的整體風貌而言,筆者認為,“體要”只是合于要點的文體。在“體制”、“體統”面前,體貌、體要的意涵都顯單薄,并不能涵蓋劉勰“文體”論的本來意蘊。要言之,體要并不能涵蓋體制。
劉勰認為,為文之道,只有遵循圣人經典的楷式,才能使得文章成為表里渾融的整體。《宗經》篇總結《春秋》的辭體特征是明白曉暢,“此圣人之疏致,表里之異體者也”(17)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22頁。。反之,“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18)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726頁。。離開圣人意旨,文與體相離散,遂不成體統了。
依此,判斷文體是否清峻宏深,可以將“體統”作為致思路徑去評判其是否是沿著圣人體制去彌綸全篇的;否則,文體將遂鞶帨訛濫。
(二)體貌本原與辭共體并
在《文心雕龍》中,“體”又是文之氣結所在,是作家體性在文章中呈現出的通體形貌,即“體貌”。“體貌”首先出現在《原道》篇:“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效。”(19)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3頁。此所謂“獻體”、“呈貌”,即龍馬出河,神龜負文而出,啟發圣人伏羲繼天而王,始創八卦。在這里,劉勰“體”、“貌”對舉,揭示了上古圣人觀天象而為文的特點,呈現了中國早期文體的肇始和發端情形。這里的“體貌”,既非單指情感,也不僅僅喻指文類,而是對初始文章產出和演化的通體形容。
羅宗強對《文心雕龍》文體論的體認,亦是由“體貌”出發的。他認為,《文心雕龍》之“體貌”包涵動靜兩態:體性為靜,如《體性》篇“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體勢為動,如《定勢》篇“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20)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06、531頁。。羅先生臚列了劉勰對于作家作品體貌特色評論的諸多文料,著眼于“文章之情思事義與文采”,“義、理、情、志”,“文辭之表現特色”,“狀作品或作家之創作體貌”(21)羅宗強《讀文心雕龍手記》,第168-170頁。等方面予以總結和討論。筆者認為,其論更貼近劉勰文章體式論的本意。
《文心雕龍》有關體貌、形貌的指陳,往往是與內容體式、情感風格等合而論之的。實際上,這也正揭示了體貌的綜合性、融通性特點。如,《風骨》篇講:“情與氣偕,辭共體并。”(22)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14頁。黃侃發微曰:“明氣不能自顯,情顯則氣具其中,骨不能獨章,辭章則骨在其中也。”(23)黃侃《黃侃講文心雕龍》,河海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10頁。情之于氣,必如辭之于體;情淺乃無氣之征,辭肥則是無骨之征。再如,《才略》中提到“解散辭體”:“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閑情,并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24)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701頁。陸侃如、牟世金解釋說:“這里所說的‘解散’,即指玄風而言;‘辭體’即‘辭趣一揆’的玄現文辭。解散:分散,沖淡。”(25)劉勰著,陸侃如、牟世金譯注《文心雕龍譯注》,齊魯書社2009年版,第615頁。周勛初的解析是:“解散辭體:指沖擊其時風行的玄風。縹渺浮音:言玄言詩的虛浮之氣仍存。”(26)周勛初《文心雕龍解析》,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767頁。體,是文辭之附著;那么,“解散”中的“辭”與“體”的語法關系就應當是并列關系,并非“辭之體”,而是“辭與體”。這樣,在邏輯肌理上,劉勰把文(辭)與體分而論之,也就把能夠體現圣人意旨的內容和所運用的恰當的文章體制分而論之。這體現了劉勰對玄風內容和形式之間錯位的不滿,揭示了歷史和現實、經典和訛體之間的矛盾。
當然,貫穿文章體貌的不僅僅是形式和內容的協調,更為核心的是作家群體的心性在作品中的集體體現。徐復觀論《文心雕龍》之文體,一方面強調了文體是語言、思想情感、風格的集合統一;另一方面又極言體貌與性情的關系,力陳體貌、體要不稱之弊,稱“‘輕靡’始于晉世,而‘新奇’始于謝靈運,然此皆系沿楚辭之‘麗’的系統而衍變出的”(27)徐復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第43-44頁。。的確,從字源上看,“體”的本意是“身體”,這就和作家的才性學習、性情秉性有著密切的關系。《禮記·大學》:“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28)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631頁。正道出了心與體之間的關系。由此可證,文心與文體之間有著必然聯系。《說文解字·骨部》:“體(體),總十二屬也。”(29)許慎撰、徐鉉校《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86頁。言人身體的各部分總稱“體”。文章辭體之流也稱“體”,如此,由身體、肢體而至文體,正顯示了中國傳統文論的人文化傾向,也是中國文論的探本之論。自古以來,“體”與“心”就是相依相對的概念,《周禮·春官》賈公彥疏:“統之于心名為體。”(30)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1622頁。劉勰《樂府》篇亦云:“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31)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102頁。在劉勰看來,聲詩即是心體,世風日下造成的心體動搖,會表現在體貌不正上。
《風骨》云:“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32)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13頁。其意在說明:辭情須有氣力,猶形體須有骨骸,正是文體實實在在地支撐著文辭。此中之“體”,顯然由人之形體演變成為包含辭、情等眾多因素的綜合體。如果意脈不通暢,則文章通體了無生氣。在《情采》篇,劉勰又強調:“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33)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38頁。此論又包含有文章寫作要按照情辭的需要而隨類賦體的含義。可見,在劉勰之論中,無論是命意還是文辭,都深及人的性情,強調了道統之下文心的具體呈現。如果說“命意”為道,“文體”則為“器”。其中“文”、“體”、“心”三者,既相對獨立,又意脈相連、互為支撐,正所謂“一物攜二,莫不解體”(34)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56頁。,也即一物不統合,則全盤解體。
(三)隨類賦體與體要成辭
體,從狹義上講,是“體裁”之體,偏指文章之楷式辭藻、體派風格。體裁與風格是《文心雕龍》文體論的核心要義,也是現代學者對文體的普泛看法。吳承學認為:“從《明文(詩)》到《書記》二十篇,分別闡明了各種文體的歷史發展和基本要求,其中包括風格要求。……《定勢》篇中集中討論文章體裁與風格的關系。”(35)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330頁。學界也多舉《宗經》篇“體之六義”來說明“體”的體裁風格之義,該篇云: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36)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23頁。
“體之六義”的具體內容是:感情真摯而不虛假,文風清新而不駁雜,敘事真實而不荒誕,義理正確而不歪曲,文體精約而不繁蕪,文辭華麗而不過分。這里的“體”,既是指體裁樣式,又指辭藻風格。與徐復觀以“神”為統領的文體論相對,龔鵬程比照“形/神關系”,以為“文體論,所討論的就是這有關形的知識”,并稱文體指示“辭采、聲調、序事述情之能力、章句對偶”等形式問題(37)龔鵬程《劉勰的文體論》,《關東學刊》2020年第4期,第31-32頁。。筆者認為,這更貼近劉勰對于“辭體”范疇的論述:“是以子政論文,必征于圣,稚圭勸學,必宗于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38)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16頁。也就是說,文體之“體”的核心在于辭體,徐復觀所講的“體要”也正由此而發。
文章的體裁不同,則風格各異。在《體性》篇中,劉勰舉出八體:
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39)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05頁。
這里,不僅涉及風格典雅的“正體”,而且涉及風格繁縟的“訛體”。《體性》篇說:“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40)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05頁。劉勰以為,無論是什么樣的文體風格,都是以文辭為根葉支撐并充裕其中的。文辭既包括言,又包涵意,因而,文體風格是“內容和形式”的統合(41)詹锳《文心雕龍義證》,第1021頁。。
“體”作為體裁的用法,在《文心雕龍》中亦比較常見。如《諧隱》:“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42)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270頁。這里的“本體”,指諧隱之辭原本的體類楷式。劉勰崇尚雅正之體,而訛體的出現,只因人們濫用舊的體裁。相對于詩、騷等雅正之體而言,滑稽的體裁相對鄙俚庸俗,只能供人一時之笑,容易出現過于隱晦的弊病。
如果從創作論角度來看狹義的文體,作家的體派風格的確規定了體裁形制。因而所謂體裁,當然也是就“體派”而言,即體現在作家群體的心性表現。“體裁”更強調文章的外部形態和整體感,“體派”則強調文章的思想和意志。劉勰也曾針對不同體派的文體加以精密的分析,《體性》云:
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43)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05頁。
在具體創作中,作家根據具體情境,以才情控馭體類,作品則被隨類賦體。體派繁縟者、追求新奇者、體氣輕靡者,就會流于“訛濫”。
綜上所述,“體”和“文”一樣,在《文心雕龍》中的含義是比較寬泛的,并不僅僅限于“體裁”一義,而是具有多層次的指向。廣義上的“體”,既囊括體統、體制、體勢、體性,還指向體裁、辭體、體派等,而狹義上的“體”則僅僅指楷式與體類。筆者認為,就“文體訛濫”說而言,“體統”、“體貌”、“體裁”是其基本旨意,厘清這一點,對于了解劉勰的六朝文學觀至為重要。“體統”牽涉文章道體大義,“體貌”反映情志心性,“體裁”著眼文章楷式類型,三者層次清晰,邏輯嚴密,內涵豐富生動而又充滿活力。可以說,中國古代“體”之道統、賦形、雅正等論,在《文心雕龍》這里都得到了空前的強化。
二 離經逐末,乖道訛新:《文心雕龍》“訛濫”說的具體指向
所謂“文體訛濫”之“訛”,即訛誤、錯謬;“濫”,意謂不合禮義。賈誼《新書·道術》有云:“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44)賈誼撰,閻振益、鐘夏校注《新書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04頁。劉勰對于訛濫的乖謬失實及其現實危害,也多從文體層次予以解剖和辨析。散見于《宗經》、《明詩》、《通變》、《定勢》、《序志》等篇中的有關論述,對六朝和江左的“訛濫”之風進行了具體的指陳和分析,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概而論之,劉勰所指“訛濫”主要有以下數端。
(一)背離經典,追新逐奇
辭體辭意是否能夠擺脫庸近,是判斷文體演進是否訛濫的關鍵。針對文體的訛變,《宗經》提出“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45)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23頁。,意欲通過宗經來規范文章的體制,通過酌取經典中的雅正語言,來豐富文章的意旨和表達。《通變》篇云:
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46)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20頁。
他指出,宋初文章的基本特征是“訛而新”。所謂“訛而新”,主要指文章意旨、體式和辭藻取向上的新變及其所造成的訛亂。劉勰認為,從黃唐到劉宋,文體由質而訛,這是由于“競今疏古,風味氣衰”所致。“競今疏古”,是就對待經典和古人優秀文化遺產的態度而言的。下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近附而遠疏”之論,都是就這一傾向而言的。近者,即宋及江左;遠者,即《詩》、《書》經典與漢初文制。“風味氣衰”顯然是對宋初文風卑弱、缺乏氣骨的概括。劉咸炘評曰:“魏、晉崇尚玄風,專取淡逸,間出綺采。總歸輕易,故曰淺而綺。士衡矜重,故卓爾于當時。宋時大謝及顏,以雕琢為工,氣息愈薄而尖新百出,故曰訛而新。彥和所慨于當時在味薄氣衰,主矜重,不主輕靡,固是卓識。”(47)劉咸炘《〈文心雕龍〉闡說》,劉咸炘《推十書》(增補全本)戊集第2冊,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965頁。所論頗能切中肯綮。“競今疏古”與“風味氣衰”是劉宋文壇的基本趣尚和整體風貌,二者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正是由于江左體派負氣適變,才造成文辭謹細而衰敗。
但是,“訛而新”并非一定會走向“濫”,新變是推動文學發展的動力,只要“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48)蕭統《文選序》,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頁。,變革和創新都是必要且合適的。劉勰以為,齊梁文風之所以“訛濫”,關鍵在于沒有合理承續經典之精神和風范。劉勰雖然稱宋初文章“訛而新”,但是總體認為它距離經典文章的體裁楷式還不是很遠,只是追新逐奇的開始,所以,還沒有達到“訛濫”的地步。陸侃如、牟世金說:“商周以后繼續發展的趨勢,仍是華麗的程度一代一代逐漸遞增,以致發展到宋初的‘訛而新’。既然說‘九代詠歌’都合于‘文則’,這一總的趨勢,也當然在內。”(49)劉勰著,陸侃如、牟世金譯注《文心雕龍譯注》,第67頁。也就是說,文章創作只要是符合文則,就能夠通其變,進而保持正確的發展方向。
劉勰認為,“追新逐奇”之弊不僅表現在文體之總觀上,同時也表現在對具體語言和文字的運用上。《練字》篇云:
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圣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50)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25頁。
衛人把《晉史》之“己亥渡河”錯改為“三豕渡河”,愛好奇異的心理在古今都是一致的。史書中殘缺的文字,圣人們極為慎重,如果能夠依照字義運用,拋棄愛奇之弊,那就可以與之矯正文字了。由此可見,破解“追新逐奇”的方法,就是要和圣人一樣慎重推敲文字背后實在的意義。周振甫注云:“于是棄同即異,穿鑿旁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51)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7I-172頁。在文辭上立說奇險,造成史實的虛構,才是訛濫的本源。《物色》又云:
《詩》《騷》所標,并據要害,故后進銳筆,怯于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于適要,則雖舊彌新矣。(52)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94頁。
文體訛濫的局面是由于人們一味追逐新奇造成的。劉勰以為,這是不足取的。要對照經典,抓住要害,借用經典的辭體,循借其事義并加以融會貫通。這樣,即便承襲前人之法,也可以推出新意。
(二)“極貌寫物”,“文貴形似”
作家在文章創作中,如為文造情,則結言端直;為情造文,則文體訛濫。情和氣是文體定勢之源,《定勢》曰:“勢流不返,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53)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31頁。要避免文章體貌的駁雜和泛濫,作家就要控馭情術。《明詩》開篇講“詩者,持也”(54)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5頁。,劉勰以詩歌為例,認為文學是規范人的情性的。推而廣之,當作家以任何一種文體形式書寫喜怒哀懼等感情的時候,都應當有所節制,不能膚淺,更不能濫情。
李白《古風》其一:“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55)《李白全集編年箋注》卷9,安旗等箋注,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885頁。劉勰《宗經》篇所提出的“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淫”(56)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23頁。的創作主張,主要是針對極貌寫物、綺麗追新的齊梁詩風而言的。《明詩》篇云: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57)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7頁。
宋初文體訛變,老莊流行過后,山水詩漸次興盛。但此時的山水之作講求駢儷對偶,奇突警策,極盡情辭,追新逐奇。劉勰認為,這是文體訛濫的又一具體表現。對于晉宋以來文采繁縟、風骨不存的文壇狀況,有識之士多有不滿和抨擊。劉勰“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的創作主張,體現了當時及后世文人“發乎情、止乎禮義”(58)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67頁。的主流價值追求。《物色》又謂: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鉆貌草木之中。……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59)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94頁。
劉宋以來的文學創作,注重對景物形貌的逼真描繪,重形似而不重神似。尤其重要的是,缺乏真摯情感,風味不存。在劉勰看來,這就是訛濫。劉勰所指陳的主要是謝靈運等人的山水詩創作。《詩源辯體》稱:“晉宋間謝靈運輩,縱情丘壑,動逾旬朔,人相尚以為高,乃其心則未嘗無累者。”(60)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卷7,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頁。謝靈運的作品著眼山水丘壑的形似,以至于累及內心,不能神似,缺少神韻,正是《物色》所舉“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之末度。劉勰以為,景物雖千變萬化,但作者在遣詞造句上應注重簡練,只有實現“文約”,才能“體約”。這樣,才可以避免形似、泛濫的流弊。《明詩》又言: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61)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6-67頁。
建安時期是五言詩蓬勃發展的時期,在述懷敘事上,絕不追求細密的技巧;在遣辭寫景上,只以清楚明白為貴。這是正面的例子。與此相悖的“纖密之巧”、“驅辭逐貌”,當然就是訛濫。《明詩》評《古詩十九首》云:“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62)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6頁。劉勰以古為訓,樹立了創作文體的標準:在“造懷指事”上,只有風骨充盈,“直而不野,婉轉附物”,“為情者要約而寫真”(63)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38頁。,才能達到切情而不泛濫的目的。
(三)“詩雜仙心”,“率多浮淺”
劉勰結合具體作家、具體作品及文壇趣尚,對玄言、玄風的有傷體統多所批評。東晉南朝玄言詩大盛,這類詩往往以莊、老玄勝之談寓之于詩,因其缺乏準的,主體情感容易流逸消散。空泛而不切實際是玄言泛濫的又一體現,何晏、王弼等人雖以儒家經義雜糅老莊思想談玄論道,與五經等儒家經典漸行漸遠,體統盡失,終究脫不了膚淺。《明詩》言: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64)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7頁。
正始年間(公元240-249年)的玄言詩,多出于道家思想。劉勰認為,以何晏為代表的詩大多是浮淺之作,只有嵇康、阮籍之作清峻遙深,可圈可點,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玄學與禪學的合流,使得玄言詩削弱了言意二元中“言”的力量,這有悖于文體的基本特質,故郭預衡指出:“以玄學入詩,本來就是意落言筌,有悖于玄學對物道關系、言意關系的根本認識。所以,玄言詩既是對建安以來文學自覺的反動,也是對老莊與玄學本質的反動。”(65)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簡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頁。玄學與詩的結合,對詩旨和玄學本身都是有害的,也是有傷體統的。劉勰早就深諳“詩雜仙心”的弊端,《明詩》言:
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66)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7頁。
東晉王謝貴族、袁宏、孫綽等沉溺于談玄論道,在世事艱難的政治環境下,文人們普遍嘲笑徇務之志,表露玄淡之風,這與劉勰《序志》以篇制“拔萃出類”、“騰聲飛實”(67)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725頁。的文學主張相悖。所以,在劉勰看來,這也正是文體訛濫的表現。關于玄言、玄風,鐘嶸《詩品序》也有過尖銳批評:“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于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眾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68)鐘嶸《詩品序》,王叔岷《鐘嶸詩品箋證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646-649頁。在《時序》中,面對時代興替與文體流易,劉勰也發表了類似的感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余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69)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75頁。劉勰指出,晉尚清談,延及江左;雖時勢艱難,文辭卻寫得平靜寬緩,詩文創作皆以老莊為旨歸。晉宋文章的這種變化是受到了時代的感染,其中,玄風是導致文體流變的主要原因。文體既大,而義不周密;辭雖引長,而聲不通利,這都是為文之大忌。正如《文鏡秘府論》所云:“體大義疏,辭引聲滯,緩之致焉。”(70)﹝日﹞遍照金剛《論文意》,遍照金剛撰、盧盛江校箋《文鏡秘府論校箋》,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433頁。文心道統發生了變化,體貌亦隨之訛變,文氣也就隨之膚淺緩滯。
劉勰《論說》篇中略論玄學的變遷及旨歸,并再次指斥了玄言之弊:“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于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途矣。……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71)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327頁。曹魏年間,何晏之徒開始大肆談玄論道,于是文壇上出現了“惟玄是務”的清談風氣。劉勰指出,玄言有“徒銳偏解,莫詣正理”之失,難以達到義直尚實的至高境界。劉勰通過批評玄言詩指責晉人歸玄思、尚黃老的傾向,進而表達了自己對文章功用和文章風格的獨特認識。
齊梁文學之失,人所共識。蕭子顯《南齊書·賈淵傳論》云:“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72)蕭子顯《南齊書》卷52,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908頁。這段文字對齊梁文學之失多有總結,其中“疏慢闡緩”、“頓失清采”、“操調險急”、“雕藻淫艷”種種,《文心雕龍》也有過不少類似指陳。可見,對江左文風之弊的認識,各家趨于一致。對于這樣的文體訛變,劉勰多從思想淵源和學術背景方面考察其存在的必然性,與蕭子顯相比,其批評態度和批評方法也更為辯證。
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務春華,少秋實。“文體訛濫”說的提出,提醒當時的“才穎之士”矯正偽體,改變浮淺文風,以經典為楷式。這使得劉勰“原道”、“宗經”的文學觀念具有更強的現實針對性。
三 雅潤準的,“昭體曉變”:《文心雕龍》“文體訛濫”說的意義和價值
“文體訛濫”是《文心雕龍》論文的出發點和現實基礎,有關“文體訛濫”的歸納和辨析直觀地體現了劉勰對歸正文體、極其心實、圓熟風骨、資故酌新等方面的具體要求,更與其本末觀、情辭觀、風骨觀和通變觀等緊密相連、環環相扣。訂正文體訛濫,垂示典誥之訓,“執正馭奇”、正本去訛,正是劉勰論文的意旨所在。
(一)標舉了“準的雅潤”的文章規范
劉勰辨別和衡量“文體訛濫”的重要依據是文學創作是否符合經典規范,同樣,其糾正時弊的理論武庫依然是經典。《征圣》篇認為:“稚圭勸學,必宗于經。”(73)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16頁。只有尊崇憲章典誥,才能矯訛翻淺,使文章趨于端直。《通變》言:
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檃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74)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20頁。
劉勰通過對時文的批評,提醒當時的人們,要矯正訛濫的文風,必須歸正文體,以經典為準的,以雅潤為標準。《明詩》言:“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75)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65頁。“無邪”之論出于經典,《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76)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346頁。劉勰以“詩”為經典體式,持人之行,使之不墜,這體現了他秉持儒家溫柔敦厚、中正平和精神的論詩傾向。相比之下,追新逐巧、日競雕華,顯然有悖于中和精神,這就是訛濫。
文體訛濫的實質是有違圣人之道,糾正的方法是“熔鈞六經”。劉勰認為,只有經典才能書寫天地,曉解民生,流傳千古。《序志》云: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77)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726頁。
只有追溯經典,確乎正式,文章才能發揮其彰顯君臣功業、曉明國家軍政大事的現實功能。劉勰因經典以致用,以憲章典誥為文體之本,反對舍本逐末。這些觀念對于糾正齊梁文壇有失道統之弊,具有切實的現實意義。
(二)強調了“極其心實”的創作要求
從劉勰“文體訛濫”的有關論述可見其對“為文之用心”的重視。其“文體論”不僅關涉到文章體式和規范,更強調了情感對于文章寫作的關鍵意義,也即情感不能訛濫。這為作家表達情感樹立了極其心實、體周事核的準則,深刻影響到了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
在對訛變的界定和評判中,劉勰表現出了對文體流變中“怪而不辭”、“未極心實”等傾向的擔憂,認為作者只有隱心結文、為情造文,才能避免采濫寡情。以哀辭為例,其《哀吊》言:
及后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云”,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仿佛乎漢武也。至于蘇慎、張升,并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其心實。(78)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239-240頁。
“不辭”,周勛初釋為“文辭不妥”(79)周勛初《文心雕龍解析》,第209頁。。劉勰稱,崔瑗所作哀辭“始變前式”,詹锳解釋為:“‘前式’,指哀辭最初的體式用途。哀辭原只用于夭折者,后不盡限于幼年。”(80)詹锳《文心雕龍義證》,第469頁。《詩經》中的《黃鳥》哀悼三個優秀青年為秦穆公殉葬而夭折,情感表達委婉得體;到了漢代,哀辭開始改變了以前的體式,開始寫鬼門仙境,還以五言結尾,體現了道家思想對人們的影響。在劉勰看來,哀辭的體變,帶來的是“怪而不辭”、“仙而不哀”,影響了哀傷情感的表達,違背了哀吊一體原有的基本規范。張升、蘇慎(順)之作,雖然表現出了他們的情思和文采,卻未能充分反映出其內心深處的真實情感。
這充分說明,劉勰意識到了文體是情志的反映,如果文體變而失其正、變而為“體奢”,就會失去真實情感。《哀吊》篇中,劉勰對潘岳的舊體之作多有稱頌,主要也是基于潘岳之作情感上的凄婉真摯:“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81)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240頁。然而,劉勰對一些哀體之作的“體奢”卻表達了不滿:
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為辭,則雖麗不哀。(82)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240頁。
依照劉勰的總結,哀文變體之失主要有二:首先,內容上由原來的為童殤夭折而作,變化為“為不幸暴死之人而作”,擴大了適用對象;其次,形式上,改變了原有紆緩的四言句式。四言義直而文婉,五言雖麗而不哀,“卒章五言”之式打破了含義純正、言辭委婉的審美范式。其又云:“而后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83)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38頁。可見,其文體論與情辭是緊密聯系的。正是“采濫忽真”的情辭論直接導致了南朝后期違背真情、內容空泛的文體面貌。
劉勰通過選文定篇和對具體創作情形的評判,表明自己對文體創作的基本要求,進而樹立了文體創作的規范:只有文體慎變,情志才能得到很好的表達。同樣,只有情感真實,文體才能更加合宜。
(三)樹立了“風清骨峻”的美學風范
“文體訛濫”論的意義還在于,力避跨略舊規、馳騖新作的創作傾向,標舉確乎正式、結言端直的文體趨向,進而樹立了自然而文、風清骨峻的美學風范。
自然而文是《文心雕龍》用以糾正當時文風的重要標的。《原道》云:“至于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锽。”(84)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1頁。大抵山水之作,以自然為宗,但如果矯揉造作,“爭價一字之奇”,就有違自然之道。紀昀評曰:“齊梁文藻,日競雕華,標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85)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4頁。劉勰標舉“自然之道”、“自然之趣”、“自然之勢”(86)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1、530、530頁。,用來反對當時浮靡和矯揉造作的文風。在他看來,遵循銜華佩實的自然之道,是破除背離經典、追新逐奇的良方。所以,紀昀稱劉勰最重要的旨歸,即是要通過標舉自然來“原道”,來洞曉情變、依義棄奇。正如詹福瑞所云:“在六朝重文采辭藻的風氣下,劉勰提出這樣的情采理論,自有其糾正訛濫文風的意義。”(87)詹福瑞《〈文心雕龍〉創作理論生成的基礎》,《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第9頁。
劉勰一再細分“情、骨、辭、氣”之間的關系,認為文章之和樂精妙、篇體和諧,是因為文辭、風骨與文體交相呼應。《風骨》言:“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88)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13頁。文辭、風骨是融為一體的,文辭依賴于“骨”,猶如人體必有軀干;情思中包含了“風”,就像形體中包蘊著血氣一樣。風骨是糾正文章體性訛變的內在動力,也是歸正文體的具體體現。如果說,這里的“體”是形式和構架,那么“辭”還不能算作完全意義上的文章形式,“辭”只能是比“體”更微小的形式單元,是反映文意和風骨的載體。風辭未煉,則骨采未圓;骨采未圓,則危敗體骸。《風骨》云:
《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于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89)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14頁。
針對訛濫之風,劉勰援用了《周書》中開出的治世良方,即要“辭尚體要”、“確乎正式”,反對好高騖遠,跨越舊規。劉勰認為,防止和拯救“文濫”的重要方法是,要文辭體現要義,鮮明剛健;以經典為范式,確立正確、合適的文章體式,不能急功近利,取巧文意,一蹴而就。依靠寫作之術的正確傳遞和合理繼承,文章才能風骨清峻,篇體光華。因此,劉勰的“文體觀”合縱文辭、風骨而言明要義,即文辭要想端直,風骨必須圓熟。依此,他倡導作家要根據各種體類的演變,追求“功以學成,才力居中”(90)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06頁。,通過自我修養,成就作家群體捐俗趨雅、風清骨峻之整體品格。
(四)提供了“昭體曉變”的矯訛良方
劉勰“文體訛濫”之論,為其通變說作了堅實鋪墊,意在托出昭體、曉變的矯訛良方,即文體是要變,但過猶不及;只有曉變昭體、資故酌新,才能“矯訛翻淺,望今制奇”。《風骨》篇曰:“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91)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14頁。劉勰認為,要熔鑄經典,一方面要“昭體”,即清楚辨識文體,這是對正確、規范運用文體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曉變”,即是通曉文情變化,這是其通變觀的反映。文體沿革遵循自身發展的規律,文章才能篇體光華。兩者完滿結合,才是成就優良文風的關鍵。在這里,劉勰為作家提供了具體的寫作指導,即一部成功作品的創作,從橫向來說離不開辨識文體,這是對作家空間結構能力的要求;從縱向來看,又離不開通曉文情,這是對作家把握時代潮流的要求。作家只有張弛有度、望今制奇,才能參古定法、熔鑄經典。
文體有常,通變無方,要使文道持續發展,必須在“有常”和“無方”之間尋求科學的通變之術。其《通變》篇言: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途,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92)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19頁。
劉勰認為,作品的體裁是一定的,但寫作變化卻是無窮的。如詩歌、辭賦、書札、奏記等,名稱和寫作的道理都前后相承,這說明體裁、體類是一定的;至于文辭的氣勢和感染力,唯有推陳出新才能永久流傳。所以,在實際寫作中,作家必須借鑒成功的歷史經驗,酌取新的文辭聲律,并有所創新和發展。這樣,就能在文壇馳騁自如、左右逢源。
通變是文體發展的動力,正確的“通變觀”是矯正文體訛濫之良方。作家只有外通文情變化,詳辨文體規范,內修才性學識,才能避免文體訛濫、空結奇字,所成文體風格才能剛健有力。
綜上,為糾正“文體訛濫”之弊,劉勰《文心雕龍》立足于“大文體”的視野,在概括和總結文風之失的同時,也提出了救失補闕、療正時弊的具體方法和路徑,進而清晰地表露了垂示典誥之訓、正本矯訛的文體主張。既能敏銳地發現問題,又能完美地解決問題,這是劉勰的杰出之處,也是《文心雕龍》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