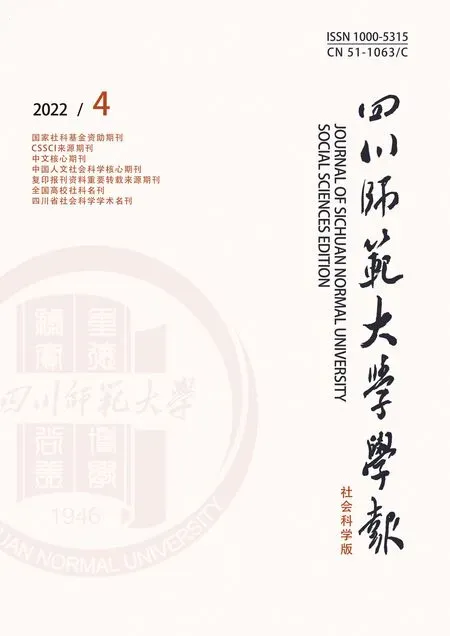論雅克·朗西埃的時間錯位詩學
何健毓 馬元龍
在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將美學與政治內在而非外在地關聯起來,指出二者的一致性,最為著名的即英國的伊格爾頓與法國的朗西埃。前者在《審美意識形態》(TheIdeologyoftheAesthetic, 1990)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學根本就是一種政治,西方現代美學史就是一部意識形態斗爭史;后者則在其《感性的分配:美學與政治》(LePartagedusensible:Esthétiqueetpolitique, 2000)等一系列著作中,剖析政治的基本策略的美學性質。尤為關鍵者,朗西埃獨辟蹊徑,將“時間”維度納入審美政治之思,不僅為審美政治打開了嶄新的境域,而且開啟了探討時間問題的新視角。
朗西埃曾明確表示:“時間作為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一種分配形式:對這個‘美學’主題的考察一直是我整個研究的核心。”(1)Jacques Rancière, “From Politics to Aesthetics?,” Paragraph 28, no. 1 (March 2005): 23.在此朗西埃不僅表明他將時間作為美學的核心,而且彰顯了他的時間之思絕不是一種純粹的哲學思考。故馬克·羅布森說:“朗西埃的工作一直都與時間有關,即使這并不意味著他的思想可以或應該被抽象為關于時間本身的哲學。”(2)Mark Robson, “Jacques Rancière and Time : le temps d’après,” Paragraph 38, no. 3 (November 2015) : 309.“歷史”因其與時間的密切關聯成為朗西埃審美政治中的關鍵一環,但朗西埃介入歷史絕非因為歷史事件一般意義上的時間性,他關注的是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歷史這種關于時間的話語如何能成為一門科學?在他看來,答案在于歷史書寫采取了一種“詩學”機制。歷史敘事中的“時代錯誤”(anachronisme),由于集中突顯了歷史詩學的運作機制等核心問題而備受矚目。通過解構“時代錯誤”,朗西埃提出了具有激進政治內涵的“時間錯位”(anachronie),指向歷史敘事中的真理與民主。雖然近年來漢語學界研究朗西埃審美政治思想的成果日益豐碩(3)自2012年起國內開始較多地關注朗西埃的審美政治思想,成果頗豐,代表作有:蔣洪生《雅克·朗西埃的藝術體制和當代政治藝術觀》,《文藝理論研究》2012年第2期,第97-106頁;李三達《走向審美的政治——論朗西埃審美平等理論的兩個維度》,《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第103-108頁;饒靜《民主之疾:朗西埃的書寫政治學解讀》,《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第137-144頁;等等。,但時間問題緣何在朗西埃的思想中舉足輕重?歷史書寫為何要采取一種詩學機制?時間錯位為何在審美政治中具有積極意義?以及所謂時間錯位究竟為何?所有這些問題的討論至今仍有待深入。
一 以時間為核心的審美政治
自古以來便不乏對時間問題的哲學探討,朗西埃時間觀的獨特之處在于,他以感性分配為基石,一方面吸收了康德哲學中時空表象的“先天”性質,另一方面又從實踐活動出發,為時間注入了指向平等的審美政治意涵。為了理解這一點,必須首先澄清作為朗西埃思想體系基石的“感性分配”(partage du sensible)理論。
“感性分配”是朗西埃創造的重要概念,具有靈活的多義性。首先,關于“分配”(partager)這個動詞,它一方面指共同分享某物;另一方面,分享的前提意味著被劃分,納入的同時也意味著排除,分割或分配是該動詞的第二層含義。其次,分配的對象“le sensible”在英文中亦有雙重含義,一是指可感知的、可感受的,二是意味合理的、理智的。所以感性分配不僅是對感覺的劃分,更是對合法性的劃分,且劃分絕非局限于外部結構,它還內化于人們感知萬物的方式中。正是在感性分享的共有性與分配的區別性的相互接觸中,蘊含著消解劃分的等級性的動力與可能。因此,與其說朗西埃關注的是某一領域,不如說他關注的是在分配和分享的接觸中動態生成的分界。朗西埃的工作便是檢驗這些界線,而檢驗的起點是美學的。正是在此基礎上,朗西埃發展出了他獨特的審美政治思想。在他看來,美學和政治不僅不外在地二元對立,而且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審美行為:“它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混雜的;政治有其美學,美學有其政治。”(4)Jacques Ranciè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ed. and trans. Gabriel Rockhill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58.朗西埃認為,美學維度內在于任何激進的解放政治中,這一斷言被齊澤克看作朗西埃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之一(5)Slavoj ?i?ek, “The Lesson of Rancière,” in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72.。
美學和政治之所以能夠對等或同一,與朗西埃對政治和美學的獨特理解有關。政治通常被我們看作達成集體的集結或共識的程序、對權力和角色的分配,以及使這些分配正當化的策略。但朗西埃認為這種看法是對政治的簡化,在《歧義》中他將這種分配和正當化的體系命名為“治安”(la police):“治安在本質上是一種通常而言隱蔽的法律,它定義了一部分人享有或沒有份額。但要界定這一點,必須首先界定可感知者的配置,總有一方會被納入此配置之中。因此治安首先是各種機構的秩序,這一秩序決定了行為方式、存在方式和言說方式的分配,并確保借助名稱將那些機構指派到特定的地方和分配特定的任務;它是可見者和可說者的秩序,確保了一種特定的活動是可見的,而另一種則不可見,確保了這種言語被理解為話語,而另一種則被當作噪音。”(6)Jacques Ranciè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 Julie Ro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29.由此生成的“治安秩序”(police order)即社會等級秩序,它多層次、流動地區分有資格和沒資格參與共同體事務的人,決定人們在社會中的位置。這不只是表面上社會地位的高低之分,它更深層地指向某群人是否可以被理解,因為被治安秩序排除在外的人變得不可見和不可知。
由此出發,朗西埃用“政治”(la politique)一詞來表示反對既有治安秩序的活動:“政治就是與感知配置決裂的一切事情,正是借助此配置,團體與成員或不享有成為團體或成員之份額者被一個預設定義,根據定義,那些無份額者的部分在此配置中沒有位置。這種決裂彰顯在一系列行動中,這些行動重塑了界定了團體、成員或無份額者的那個空間。將一個實體從它被指定的位置移開或改變一個位置的目的地的一切活動都是政治活動。它使本不該被看見的東西變得可見,使人們在原本只有噪音的地方聽見了話語,使曾經只被當作噪音的聲音被理解為話語。”(7)Jacques Rancière, Disagreement, 29-30.所以政治是對既有配置的破壞,使原本不可見、不可聞的事物彰顯出來,變得可以被感知。正是在這一點上,政治和美學相聯結。朗西埃所談論的美學,絕非關于藝術的品味,或一般意義上的藝術理論和學科,他指出,“美學可以在康德的意義上被理解——或許被福柯重新審查——作為一種先天形式系統,它決定著什么東西可以將自身呈現給感覺經驗”(8)Jacques Ranciè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8.。美學劃分出了時間和空間、可見和不可見、言語和噪音的界線,而這正是政治關注的中心問題。可見朗西埃的審美政治本質上即感性的分配問題。
那么被分配的感性以何種方式呈現又如何得以可能?是時間和空間,為感性分配的實現提供了場所和中介。如朗西埃所言,“審美首先是一個時間和空間的問題”(9)Jacques Rancière, “From Politics to Aesthetics?,” 13.。他明確表示,他的美學工作“旨在重構通常藉以把握現當代藝術實踐的時間范疇”(10)Jacques Rancière, “From Politics to Aesthetics?,” 19.,因為在他看來,既有的時間范疇阻礙了我們理解現當代藝術的轉型及其與政治的關系;他關于政治的討論,“旨在打破解放的政治和任何單向的歷史或‘宏大敘事’之間所謂的聯結一致”(11)Jacques Rancière, “From Politics to Aesthetics?,” 19.,以此表明并不存在所謂的政治終結。在此朗西埃將時間處理為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的構型方式、對公共和個人份額的分配方式:“空間和時間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容器或空洞的方向構建的,而是作為一種劃分生物的方式。”(12)Jacques Rancière, Peter Engelman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trans. Wieland Hob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67.正如海德格爾所昭示,“時間”本質上與“呈現”或“在場”一致,具有時間性就意味著被呈現/在場/存在,反之則不存在(13)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修訂譯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426-427頁。。
朗西埃早在他的博士論文《無產者之夜》(LaNuitdesprolétaires, 1981)中,便將工人運動的誕生重述為一場美學運動——一種重新配置無產者所處時間和空間劃分的嘗試,并揭示出“工人解放的核心是審美革命,審美革命的核心是時間問題”(14)Jacques Rancière, “From Politics to Aesthetics?,” 14.。理解這一點可追溯至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否定一個人可以同時從事兩件工作:“為了把大家的鞋子做好,我們不讓鞋匠去當農夫,或織工,或瓦工。同樣,我們選拔其他的人,按其天賦安排職業,棄其所短,用其所長,讓他們集中畢生精力專搞一門,精益求精,不失時機。”(15)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6頁。柏拉圖根據人不同的“金屬”屬性,即所謂“天資”,來分配時間份額,進而決定其身體和精神的存在方式:鋼鐵一族的手工業者是進行生產和繁衍生息的白天勞作的人,除了從事自己的活計外,他們“沒有”時間參與任何額外的事務;而另一批休閑和熬夜的人,即黃金一族,只有他們有時間關注共同體的事務,他們是城邦的最高委員會。這一本質上為了維護既有等級秩序的構想之核心,正是時間的分配問題。朗西埃指出,“說他們(鋼鐵一族)‘缺乏時間’,實際上就是將禁止把他們寫進可感經驗的形式自然化。一旦當那些‘沒有’時間的人花費必要的時間作為公共空間里的一員站出來,證明他們的嘴里確實能發出能夠評論公共事務的言語,且這種言語絕不能被還原為僅僅表示痛苦的聲音,這時政治便發生了。這種對位置和身份的分配與再分配,對空間和時間、可見和不可見、噪音和言語的劃分與再劃分,構成了我所說的感性分配”(16)Jacques Rancière, 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Steven Corcor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24-25.。當那些除了做自己的活計“沒有時間”做其他事情的人,在本應用于恢復勞動體力的夜晚,從事額外的審美活動,以此證明他們能夠參與共同的世界,并質疑時間分割下的不可能性時,便是時間錯位和政治發生之時。
因此,要想打破既有等級秩序和重塑身份認同,時間成為這場革命的關鍵突破口,時間錯位則是實現突破的有效策略。在《時代錯誤概念和歷史學家的真理》(“Le concept d’anachronisme et la vérité de l’historien” , 1996)中,朗西埃明確提出具有積極意義的“時間錯位”,這首先建立在他對既有的“時代錯誤”概念的解構之上。
二 時代錯誤的罪與贖
法國年鑒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在《16世紀的無信仰問題:拉伯雷的宗教》(LeProblèmedel’incroyanceauXVIesiècle:lareligiondeRabelais, 1942)中,將“時代錯誤”視為歷史敘事中最不可饒恕的罪惡(17)Lucien Febvre, 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Religion of Rabelais, trans. Beatrice Gottlieb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5.。何以如此?朗西埃認為與該詞的前綴“ana-”有關:這一前綴不僅指時間軸上水平的前置位移,而且暗示“自下而上”的垂直運動。朗西埃由此指出:“時代錯誤不是時間秩序的水平問題,而是在存在者的等級制度中時間秩序的垂直問題。它是在‘一個人以其份額得到了什么’的意義上的時間劃分問題。這個問題關心的是,在把時間與高于時間之物,即人們通常所說的永恒,聯系起來的垂直秩序中,時間在其劃分中具有了何種真理。”(18)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trans. Noel Fitzpatrick and Tim Stott, InPrint 3, iss. 1 (June 2015): 23.可見時代錯誤絕非歷史編撰中的技術性問題,而是與現實政治緊密相關的美學問題。
時代錯誤不是歷史元素被錯誤地從一個時期“植入”另一個時期,而是其被錯誤地從一個時代“逐出”這個時代,其中包含了兩種時間運動。一種是敘事時間前置的水平位移,如確證的編年時代與無法確定時期的傳說時代的接合。但時代錯誤之所以不可饒恕,尤其指向第二種更為本質的時間運動,即違反等級秩序的垂直錯位。時代錯誤并非日期(date)的混亂,而是時代(epoch)的混淆。一個時代并不僅僅是連續的歷史時間中一段簡單的切割,而是由特定的真理體制所標識。朗西埃認為年鑒學派推崇的時代真理與永恒時間緊密相連——“永恒”部署真理,使真理顯現于流變的時間經驗中。所以他指出:“編年時間依靠一種無編年順序的時間:一種純粹的現在(a pure present)或永恒。”(19)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24.一如柏拉圖在《蒂邁歐篇》中所言,時間是永恒者的流動形象。由此,日常經驗的流變時間,與凌駕其上的唯一而不變、連接真理的永恒時間相接,在結構上形成每個時代特有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式真理體制。因此對年鑒學派而言,看似僅是擾亂了編年時間水平次序的時代錯誤,實則是歸屬于另一真理體制的時間對特定時代真理體制的入侵,進而擾亂了既有的穩固的自上而下的等級秩序。此即時代錯誤于歷史的編年時間而言最不可饒恕且致命之處。該擾亂是由位于下層的流變時間所致,并由此觸及了位于頂端、象征真理的永恒時間,這便是朗西埃所謂垂直錯位的原意。
然而,朗西埃賦予這一概念和模式的政治意涵更為重要。那些“入侵”的異質時間,象征處于社會底層的“異端”,它們遭到被入侵時代之主導真理體制的驅逐和抹除。但這些“錯誤”的異端,通過時間錯位,從底層自下而上地挑戰等級秩序——當他們花費時間去從事按原有分配并不屬于自己時間份額內的政治或審美事務,以此證明自身蘊含的豐富可能性時,正是以人人各司其職為核心的時間秩序發生錯位之時,并由此質疑和動搖了與時間分配秩序相聯的等級秩序。可見,時間的垂直錯位包含三層意涵,它不只是對歷史書寫中的“時代錯誤”抽象、靜態的概括,而且象征了“失聲”的底層人民追求平等、挑戰等級的政治斗爭,更是實現斗爭的自下而上的重要反抗策略。因此,致力于建構事實和真理的歷史學家,之所以不能容忍時代錯誤,不是因為它只是歷史編年中的技術失誤,而是因為它在更為根本的維度觸犯了真理秩序,亦即既有感性分配體制下的等級秩序。對此,歷史學家采取了詩學的方式來救贖這一不可饒恕的罪行。
朗西埃描繪了兩種典型的尋求時代與真理同一的詩學機制。第一種是以因果秩序取代事件發生的簡單先后順序。古希臘著名史學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最早將歷史學家的任務規定為撰寫一個有意義的有機整體世界,而非僅僅簡單地鋪陳分散、孤立的事件,并提出了普世史說(20)易寧《波利比烏斯的普世史觀念》,《史學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6頁。。普世史觀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強調歷史的有機整體性;二是“實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即認為盡管歷史的具體內容瞬息萬變,但始終有一個不變的主題貫穿其中。朗西埃的敏銳之處在于,他認為波氏的普世史觀回應了亞里士多德。后者在《詩學》中作出了哲學高于詩歌、詩歌高于歷史的等級劃分,依據是詩歌比歷史更具哲學性。朗西埃則進一步揭示出詩歌與歷史的深層差異與關聯。他指出,“歷史是個別的(kath’hekaston)、‘一個接一個’的領域,它告訴我們這里只是存在一件接一件的事。至于詩歌,它是綜合的、普遍的(katholon)(‘關于整體的’)領域,它把行動置于一個單一的、鉸接式的總體(totality)之下”(21)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25.。這一差異造成的重要后果是,以真實性為基礎的歷史,通過摹仿詩歌的總體性能力,即運用文學手段來提升自己話語的真理地位,亦即波氏采用的手段。由此可見,在這種救贖時代錯誤的方式里,是必然性或逼真(verisimilitude)的詩學邏輯,以及顯示神圣真理的目的論邏輯,支撐著歷史的真理體制的建構。
第二種救贖方式與時代錯誤的核心問題緊密相聯,它不同于第一種方式依循因果秩序將歷史敘述為一系列顯現天意的必然事件,而是將時間建構為一個總體,摹仿或替代永恒的時間,成為這一總體內所有歷史對象都要遵循的內在原則。年鑒學派是采取這一方式的代表。“(年鑒學派)告訴我們:要使歷史成為一門科學,亦即為了讓它獲得某種永恒的東西,它的時代必須盡可能地與永恒相似”(22)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34.。換言之,要讓歷史編撰成為不容置疑的真實,因其真實而永恒。何以可能呢?年鑒學派的答案是:“時間要得到救贖,就必須要有一個純粹的現在,必須要有一個讓諸歷史主體共同存在的原則。歷史主體必須‘類似于’他們的時代,即必須類似于他們的共同存在”(23)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34.。這意味著,歷史主體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必須與其生活的時代一致,就歷史編撰而言,意味著歷史書寫借助敘述,將事件或人物呈現于“現在”,從而讓其存在。因為年鑒學派認為,時代的基本原則是共時性而非連續性,存在者是與其時代而非與其父母相似,其行為方式無不根據時代的要求進行。朗西埃指出:“這第二種方式是歷史的科學性的現代定義的核心。正因如此,歷史將時代錯誤問題作為不可饒恕的罪惡置于歷史的中心,因為它違抗了在時間之中和作為時間的永恒的存在。”(24)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26.
這一詩學機制尤其體現在費弗爾關于拉伯雷的宗教信仰問題的討論中。該問題起源于,阿貝爾·勒弗朗(Abel Lefranc)認為在拉伯雷式的戲仿下,隱藏著拉伯雷反基督的無神論思想,但費弗爾認為勒弗朗的這一論斷犯了最嚴重和荒謬的時代錯誤,并指出拉伯雷并不擁有包含這種可能性的時間。朗西埃認為,費弗爾通過運用“謀篇布局”(dispositio)和“言說風格”(elocutio)這兩種詩學程序,來證明拉伯雷不可能無信仰。
首先,謀篇布局指置入了“時代錯誤”的元素。朗西埃強調,“這種‘時代錯誤’,指該元素不屬于或不符合它所置身的位置”(25)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40.。判斷標準取決于判斷者所處時代的逼真或真實性原則。如在費弗爾的時代,描述一個生活在16世紀的人無信仰,顯然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利用這一真實性及其缺席的詩學邏輯,費弗爾證明拉伯雷無信仰這一無法考據的問題是時代錯誤的。其次,言說風格關涉一系列的語法程序,朗西埃指出費弗爾在論述中部署了一個“超現在時”(more-than-present)的時間系統,“這個系統由一種時間——直陳式現在時——甚至由一種類時間(quasi-time)、去時間性(detemporalised)的時間專橫地控制著,這種時間使該系統本質化,使之類似于永恒和時間的缺席”(26)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43.。當費弗爾敘述在拉伯雷的時代,一個死者拒絕基督教的葬禮或拉伯雷無信仰是不可能的時候,一個簡單的“不可能”,壓制了所有的時間和動詞標記,塑造出拉伯雷的時代是如何即刻限定了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存在方式。這一“非時間性”(non-time)達到頂峰的詩學程序,模糊了本維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對歷史敘事(récit historique)和話語(discours)的區分(27)本維尼斯特區分到,歷史敘事是預設說話主體缺席、用過去時對過去事件的表述,話語是預設了說話主體及其對話者,以現在時、將來時和完成時為基本時態的表述。參見:本維尼斯特《普通語言學問題》(選譯本),王東亮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70-271頁。,消除了字詞和時間的非真理性。費弗爾借此實現了流變經驗與一般規則在敘述上的同一,證明了違背真理體制的不可能性。
因此,要成為年鑒學派的書寫對象,主體必須信仰其所處時代的信仰。朗西埃將其描述為“信仰之于真理,正如生成之于本質”(28)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36.,這里的“信仰”只不過是歷史主體與其時代相似的標記,歷史學家通過將這種相似,即仿造的永恒強加于人來保證真理。朗西埃指出,這在雙重意義上保留了《理想國》中時間的區分功能(29)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39.。一是時間對真理的摹仿,意味著主體不能成為除了被規定的自身之外的任何角色,這對應著柏拉圖一人只干一事的要求。二是時間對知者與無知者的區分,朗西埃認為,一個人所信仰的,正是他所不了解的,這意味著歷史主體被置于對自己時代的無知之中;但作為知道這一“純粹的當下”意涵的歷史學家,卻凌駕于這一“當下”之上,歷史學家在保留歷史主體與其時代的相似性時,卻消除了前者與無知的同一性。因此,這一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之城,是以柏拉圖等級鮮明的哲學城邦為藍本,歷史學家苦心經營的真理,實則基于深刻的不平等。
三 裂隙中的“異端”
歷史科學讓歷史存在服從于時代要求和修辭學的做法,引發了歷史否定主義的挑釁。但朗西埃指出,真正不合法和應當被否定的,不是歷史本身,而是歷史科學提出的時代錯誤概念,因為“這一概念的核心,是讓存在服從于可能性,這種服從是反歷史的”(30)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45.。朗西埃提出,歷史本身就是由“時代錯誤”構成,歷史恰恰存在于當人們不與他們的時代相似、違反將他們固定在某一位置的時間線的裂隙之中,而非線性的真理進程中。所以根本不存在要被救贖的時代錯誤,正是這種將時間的“錯位”看作“錯誤”的觀念需要被解構。這意味著,除了要將歷史從可能性的游戲中解救出來,將時間從共存原則中解放出來,更要為時代錯誤概念注入新的內涵。因此,朗西埃提出了具有積極意義的“時間錯位”:“那些與時代相悖的事件、觀念和意指等,它們使意義以逃離任何同時代性、任何與時代‘自身’相同一的方式流通和傳播。這種時間錯位可以是脫離了‘它自身的’時間的一個字詞、一個事件或一種符號序列,通過這種方式,它們被賦予了一種定義完全原始的方向點的能力,一種從一條時間線跳躍至另一條的能力。正是因為有這些方向點、這些跳躍和這些聯系,才存在‘創造’歷史的力量。這種時間線的多樣性,甚至在‘同一種’時間中包含的多重時間感知,正是歷史活動的條件。”(31)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47.
在朗西埃看來,作為“異端”被隱藏的無產者(proletarian)是時間錯位的同義詞:“無產者是‘斷裂’的另一個名字,它意味著工人與‘他們的’時代間的相似性的斷裂,和白天勞作、夜晚休息這一普通的時間循環的斷裂,于柏拉圖而言,正是這一時間循環阻止了工人們去從事他們應做之事以外的任何活動。”(32)Jacques Ranciè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46.無產者一詞來源于表示種族和血統的拉丁語“proles”,指那些除了維持生存和繁衍外什么都不做的人,他們在城市中不擁有姓名、身份或任何象征地位。在此,無產者即被治安秩序消除了身份的人:“無產者既不是體力工人,也不是勞動階級。他們是一類未被計算的人,僅存在于他們被計算為不被計算的人的宣言中。”(33)Jacques Rancière, Disagreement, 38.無產者與他者的身份間的間隔,暴露了治安秩序分配的不平等。同時,異端(heresy)的本義即分離(separation),被視為異端的無產者要做的,正是從被假定的習性中出離,是工人與強加其上、不斷循環的工作時間的決裂,“他們將民主的主體設立在其無限的裂隙和相互論爭中,使其歷史脫離了從屬的保證,置身于結合的不確定性中”(34)Jacques Rancière, The Names of History: On the Poetics of Knowledge, trans. Hassan Mele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94.。正是在這種時間錯位中,歷史從與連續體的決裂中被不斷創造。因此,被年鑒學派等歷史學家排斥的異端,恰是朗西埃認為真正應當被書寫的歷史對象。他推崇的歷史是“在其中每個人的知覺和感覺都被捕捉到的新的織物。歷史的時間不只是偉大的集體命運的時間,它是在其中任何人和事都能創造和見證歷史的時間”(35)Jacques Rancière, Figures of History, trans. Julie Ros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69.。這一由對世界的新感知定義的時代即朗西埃所說的藝術的審美體制,在其中藝術的無序性和民主的任意性取代了等級體系,無名的人民進入了言說者的世界,那些被傳統歷史書寫抹去的“異端”的聲音重新響起,歷史的新主體——人民從中誕生。
除了對歷史書寫具有重要意義,無產者的審美實踐更展示了時間錯位詩學的實踐可能和解放潛能。白天辛苦勞作后,夜晚繼續思考和寫作的青年馬拉美便是一個充分展現了夜晚、“自殺”、思想和詩歌的同一性的“闖入者”形象。馬拉美年輕時的書信,記述了他那些白天被迫按要求工作后,夜晚從睡眠中擠出時間寫詩的工作日。他將這種拒斥晝夜分割的行為稱為“自殺”,“自殺是時間/勞動/貨幣之間等價關系的斷裂,是連接生命繁衍和等價物交換的節點的斷裂”(36)雅克·朗西埃《文學的政治》,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頁。。它象征著一種更加本質的“自殺”,即“工人的軀體從某個時代走出來,從某種生存方式、行動方式和說話方式中脫離出來,而這些方式是再生產的人們所固有的屬性”(37)雅克·朗西埃《文學的政治》,第130-131頁。。朗西埃類比到,如果將工人機械重復的勞作,看作以勞動換取貨幣的等價交換這樣一種經濟學的橫向秩序,那么闖入者通過額外的寫作實踐,創造了另一種不能被貨幣衡量、屬于詩歌的象征經濟的縱向秩序(38)雅克·朗西埃《文學的政治》,第119頁。。后者不僅造成了橫向的經濟結構的斷裂,而且在時間的垂直錯位中擾亂了既有的感性分配秩序和等級關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朗西埃認為時間是審美革命和工人解放的核心。因此時間錯位不只是連續性的簡單中斷,而是將異質性的斷裂嵌入資本主義生產同質的線性時間中,使一條時間線擁有與其他時間線連接起來的可能,亦即創造歷史的可能。
由此可見,無產者打破既有的時間秩序,并非僅僅為了掙得更多懶散的休息(rest)時間,而是為了獲取屬于自由人的閑暇(leisure)。前者只是工作中消耗能量的兩個時刻的分離,后者卻是屬于不需要以工作謀生的人的時間,它指向的不是怠惰而是思考的特權。閑暇時間的力量,一如工匠家庭出身的盧梭在自傳中所呈現的:“我只有在這一天當中孤獨沉思的時候,才能夠充分表現我自己和屬于我自己;我獨自一人思考,心無旁騖,毫無阻礙,敢于說我真正成了大自然希望我成為的那種人。”(39)盧梭《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夢》,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1頁。這種美妙的享受,不只是因為無產者超脫了本來的位置,更因在這些時刻中,在最本質的感覺體驗上,人的利欲和層級被消解。因此朗西埃指出:“底層人的幸福并不在于征服社會,而是存在于什么都不做中,是就在此時此地,取消社會等級的屏障和面對這些屏障的痛苦,是在純粹感受的平等中,在可感性時刻不被計算的共享中。”(40)Jacques Rancière, Aisthesis: Scenes from the Aesthetic Regime of Art, trans. Zakir Paul (New York: Verso, 2013), 52.可見獲取閑暇時間的背后是一場踐行平等的革命,因為不論處于何種位置的人,都平等地擁有這種感性能力。如同席勒在審美王國中看到了人在感覺上的平等,可以塑造出一種全新的自由——在這里“一切東西,甚至供使用的工具,都是自由的公民,他同最高貴者具有平等的權利”(41)席勒《審美教育書簡》,馮至、范大燦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頁。。又如康德所揭示的共通感原則:“這條原則只通過情感而不通過概念,卻可能普遍有效地規定什么是令人喜歡的、什么是令人討厭的。”(42)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頁。在這種不需借助概念的普遍性中,朗西埃看到了聯合仍分化的各階層的可能,而在時間錯位的裂隙中去獲取閑暇是實現這一切的基本前提。
四 結語
如果說朗西埃眼中的年鑒學派推崇歷史應嚴格受制于同時代性,與黑格爾認為特定歷史中的所有社會成分都只能表達該歷史時期的本質有相似之處,那么朗西埃對歷史的認識則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相仿,后者堅持認為,總有某些人或事可以超越特定的歷史階段。當朗西埃指出時代錯誤不只是在水平維度上,更是在垂直維度上發生,并與真理和永恒問題直接相關時,意味著時代錯誤不是一種技術性失誤,而是內在于所有歷史編撰中不可逃避的本體論性的“錯誤”,因為歷史編撰不可避免地要進行感性分配,即有所選擇。因而并不存在所謂的時代錯誤,時間錯位正是歷史的本色。問題不在于歷史學家是否創造了文學,而在于他創造了何種文學。
毋庸諱言,朗西埃這種以時間錯位為核心的審美政治過于激進,但這種在實踐上具有明顯烏托邦色彩的革命方案并非朗西埃獨有,而是20世紀下半葉左翼政治從政治經濟領域走向文化領域、在總體斗爭策略上從強硬走向疲軟的表現。盡管如此,這一以感性分配為樞紐、以紛爭性為核心特征的時間錯位觀,仍然是理解朗西埃思想的關鍵。同時在這個“996”甚至“007”工作制大行其道的時代,重新討論作為生存方式的時間格外具有現實意義。24/7(43)即一天24小時,一星期7天的縮寫,意即全天候提供服務。式的體制正試圖剝奪人們最后的睡眠時間。盡管如喬納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認為正因睡眠時間無法被資本收編,所以睡眠蘊含著抵抗資本主義的力量(44)喬納森·克拉里《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許多、沈清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頁。,但事實是,現代人的睡眠時間日益短缺(45)王俊秀、張衍、劉洋洋等《中國睡眠研究報告(202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第4頁。,除了因大幅延長的工時外,還因越來越多的人在超時工作后選擇“報復性熬夜”,在本已短暫且應用于休息以恢復工作體力的夜晚按個人意愿進行額外的休閑活動,以此補償被劫掠的時間。表面上看,報復性熬夜是個人為了獲取掌控時間的自由感,但究其根本,這一傾向于打斷經濟再生產鏈條的行為,正是時間垂直維度的突顯,即個體通過占有額外的時間份額來表達對既有存在方式的反抗。正如朗西埃所強調,“時間在連續的水平軸上的表達依賴于垂直軸,后者區分了在時間中的存在方式、擁有或沒有時間的方式。在垂直軸上,時間不是一種持續,而是一個位置”(46)Jacques Rancière, “Anachronism and the Conflict of Times,” Diacritics 48, no. 2 (2020): 113.。他認為我們只有把時間的這兩個維度結合起來,才能避免掉進歷史時間的連續性的陷阱,并指出“這就是解放:改變一個人占據時間的方式”(47)Jacques Rancière, “Anachronism and the Conflict of Times,” 122.。所以時間錯位所包含的反抗壓制時間的觀念和策略,為我們反思當下人們對時間新的知覺體驗、構建新的感知共同體等問題提供了積極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