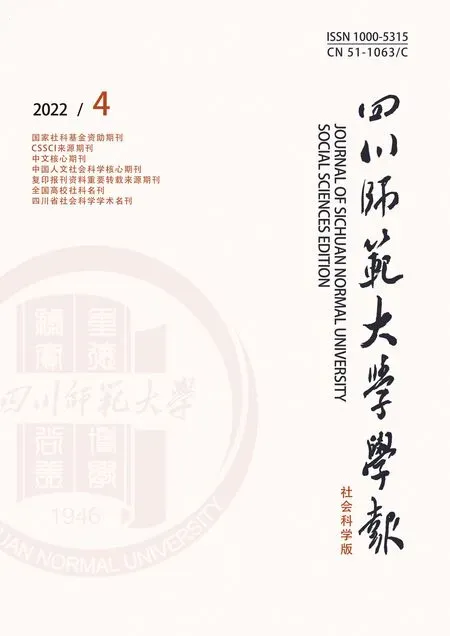北宋元符青唐之役新探
——以朝廷與將帥的交流溝通為中心
王化雨
元符(1098-1100)時期,宋軍對青唐政權(quán)發(fā)動了進(jìn)攻,僅用數(shù)月即將之吞并,然而不久之后,當(dāng)?shù)夭柯浼娂姳﹦樱仁顾诬姺艞壛俗约旱膭倮麑崱U茏诔耐剡吇顒釉诖艘壑羞_(dá)到業(yè)績頂峰,亦在此役后黯然結(jié)束。對于這場戰(zhàn)役,學(xué)界已有論述,但分析得相對簡略(1)關(guān)于哲宗朝的青唐之役,可參見:吳天墀《唃廝啰與河湟吐蕃》,《吳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262頁;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后期對夏戰(zhàn)爭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168頁;羅家祥《北宋晚期的政局演變與武將命運——以王厚軍事活動為例》,《學(xué)術(shù)研究》2011年第11期,第98-106頁;祝啟源著、趙秀英整理《青唐盛衰:唃廝啰政權(quán)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137頁;李華瑞《宋夏關(guān)系史》,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313頁。。尤其是戰(zhàn)役中前線將帥與中樞決策者之間的交流互動,目前還缺少細(xì)致研究。這使我們難以對此次戰(zhàn)役中宋方的決策制定、執(zhí)行過程形成透徹認(rèn)識,不利于我們理解此次宋方的成敗得失。筆者特撰此文,以期能有所發(fā)明。
一 招降納叛
11世紀(jì)初,吐蕃貴族唃廝啰建立了一個以青唐城(今青海西寧)為政治中心的政權(quán)。哲宗親政后,宋軍在西北開邊,青唐進(jìn)入宋人的視野。元符二年(1099)四月,熙河路經(jīng)略使孫路奏請在鄰近青唐要地邈川(今青海樂都)的斫龍筑城(2)曾布《曾公遺錄》,程郁點校,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卷7,第91頁。。四月乙未,兩府同進(jìn)呈孫路章奏云:“夔(宰相章惇)力欲成之,余(知樞密院事曾布)與同列皆以為不可,曰:‘如此,青唐必驚疑生事,西夏未了,又生一敵國。’余因為上言:‘臣自有邊事以來,嘗以謂但得北虜及青唐不警,則西事可了,若一方小警,則無所措手足,青唐一動,則熙河應(yīng)接不暇,何暇經(jīng)營青南、冷牟以通涇原也?今事已垂成,可惜壞了。’上云:‘如此且已’。遂進(jìn)呈訖。”(3)曾布《曾公遺錄》卷7,第91頁。但孫路的動議卻遭到了否決。
章惇之所以力主進(jìn)筑斫龍,與當(dāng)時他在朝中的處境有關(guān)。任宰相后,章惇與知樞密院事曾布一直存在矛盾。元符二年初,他與尚書左丞蔡卞的沖突也趨于白熱化(4)楊小敏《蔡京、蔡卞與北宋晚期政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1頁。。加之其性格強橫,朝中士大夫“眾怨歸之”(5)曾布《曾公遺錄》卷7,第94頁。,故他一時面臨政敵環(huán)伺的不利局面。紹圣以降,章惇一直以經(jīng)營“邊事”為自己的政治資本。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記載,最初章惇主要致力于對西夏作戰(zhàn),多次倡議應(yīng)吞并西夏,然而在元符二年初,哲宗決定采納曾布之見,在奪取天都山后結(jié)束對西夏的進(jìn)攻(6)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卷505,元符二年正月丁卯,第12044頁。,這給章惇造成了不小的打擊。在進(jìn)呈孫路奏議的前一天,章惇曾“留身乞退”(7)曾布《曾公遺錄》卷7,第91頁。,其主要目的應(yīng)是借此表達(dá)對政敵的不滿,并試探哲宗的意旨。但用此非常之策,亦見他所承受的壓力之大。重壓之下,章惇須立即設(shè)法鞏固權(quán)位。在對西夏作戰(zhàn)行將結(jié)束之際,章惇要再借“邊事”來強化權(quán)力,須馬上開辟新戰(zhàn)場,這是他積極推動青唐之役的根本原因。
哲宗、曾布等人否決孫路之議,一方面緣自他們對章惇的戒惕,另一方面,元符二年四月北宋對西夏的進(jìn)攻正進(jìn)行到關(guān)鍵階段。時宋廷命熙河、涇原兩路集中力量,在青南訥心、東冷牟、南牟會等地筑城,以求占據(jù)戰(zhàn)略要地天都山。此時最高決策集團的大部分成員自不愿節(jié)外生枝,在青唐方向分散力量。可以說,孫路之議被否決,既與他上奏的時機不當(dāng)有關(guān),也折射出中樞內(nèi)部在開邊一事上存在的分歧。
此后不久,青唐出現(xiàn)了內(nèi)斗。君主瞎征和唃廝啰侄曾孫溪巴溫等爭權(quán),諸部落首領(lǐng)各懷異心,“篯羅結(jié)逃奔河州,見知河州、洮西安撫王贍,言瞎征為欽氈等所制,其國必亡,吐蕃可承亂取也。贍方坐白草原增級冒賞奪官,冀以功贖過,密畫取吐蕃策,遣其客黃亨詣京師白宰相章惇。惇納之,下其事熙河蘭會經(jīng)略使孫路計議,路嘗欲取青唐,先建請于喀羅(即斫龍)川口作橋筑城,繼西賊與吐蕃相通道,朝廷猶難之,及是遂言青唐必可取,即大發(fā)府庫招來羌人”(8)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07,元符二年三月,第12092頁。。
《長編》將青唐之役的醞釀,完全歸結(jié)于王贍“以功贖過”的私心作祟,失之偏頗。在“密畫取吐蕃策”之時,王贍不可能對當(dāng)?shù)匦蝿莸纫蛩厝珶o考慮。據(jù)陳均記載,王瞻是在與熙河路經(jīng)略司屬官王厚商議后,乃“同畫策”(9)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25,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614頁。,可見他并非師心自用。然由他繞開主帥孫路,直接與宰相聯(lián)絡(luò)的舉動看,他確有貪功冒進(jìn)之心。這難免會影響其所畫之策的可靠性。此外,孫路對王瞻的“越級”做法,必心存芥蒂;王瞻在獲得宰相支持后,又不免會輕視孫路。此后,將帥失和,實源于此。
還應(yīng)注意,王瞻獲知青唐內(nèi)亂,卻未用公文向朝廷報告,而是以私密方式告知章惇。章惇、孫路在知曉情況后,亦未呈報朝廷,而是私下聯(lián)絡(luò),經(jīng)營青唐事務(wù)。他們之所以如此,應(yīng)是擔(dān)心自己的意見會被其他決策者所否定,畢竟此前宋廷剛剛駁回了孫路的提議。正因如此,一些重要信息未能及時被朝廷獲知,例如“溪巴溫初亦求助于漢,而贍、路輩不能深知其謀,亦不詳以情狀上聞”,結(jié)果“巴溫既得志,亦不復(fù)求助”(10)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1,元符二年六月己亥,第12173頁。。宰相與邊臣的“暗箱操作”,為此后的事態(tài)發(fā)展埋下了隱患。
五月二十三日,王瞻始將青唐事上奏,稱瞎征很可能被溪巴溫推翻,邊斯波結(jié)等當(dāng)?shù)厥最I(lǐng)紛紛請求內(nèi)附,他“乞朝廷速取青唐,今時不可失”(11)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1,元符二年六月己亥,第12172頁。。如前所述,宋廷之前不愿意對青唐用兵,主要是擔(dān)憂會影響對西夏進(jìn)攻。到五月上旬,宋軍在天都山一線進(jìn)筑的城寨陸續(xù)完工;五月中旬,宋廷曲赦晉秦,宣布對西夏拓邊告一段落(12)《曾公遺錄》卷7,第109頁。。結(jié)束對西夏進(jìn)攻,意味著宋廷可以挪出部分資源,用于對付青唐。此時奏請對青唐用兵,獲得批準(zhǔn)的可能性較大。王贍選擇此時上奏,顯然是吸取了孫路之前的經(jīng)驗教訓(xùn)。
王贍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據(jù)《長編》記載,六月,宰輔進(jìn)呈王贍章奏,“朝廷以前次溪巴溫不求助于漢,邊臣不能知曲折,失不以聞,今既得志,遂不復(fù)來。方阿里骨之篡,嘗加封爵,而溪巴溫之立,初無以助之,又納其叛人,恐溪巴溫必怨。然不納,則河南一帶部落未肯附溪巴溫,不乘時撫而有之,將失機會。乃詔孫路依詳近降朝旨,精加措置施行,無令遷延,有失機會”(13)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1,元符二年六月己亥,第12172頁。。宋廷決定介入青唐。
按《長編》所載,宋廷“詔孫路依詳近降朝旨,精加措置施行,無令遷延,有失機會”,似乎在青唐事宜上的態(tài)度變得十分積極。但此前,其并未下達(dá)過關(guān)于青唐的指揮,此時如何能要求孫路“依詳近降朝旨”?在小注中,李燾稱上述說法源自《實錄》六月二十六日的記載,他懷疑該記載當(dāng)“移八月末”(14)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1,元符二年六月己亥條小注,第12172頁。。《曾公遺錄》則記,六月二十六日,宋廷并未討論青唐事宜,宰輔進(jìn)呈王贍奏狀是在六月十一日;而當(dāng)日的商議結(jié)果,只是“令孫路子細(xì)斟酌敵情,相度收接”(15)《曾公遺錄》卷7,第121頁。。這一說法,應(yīng)與史實相符。“子細(xì)斟酌敵情,相度收接”云云,表明此時宋廷雖決定介入青唐,但仍秉持著較為謹(jǐn)慎的態(tài)度,目的只是招撫河南一帶部落,以鞏固熙河路的側(cè)翼安全,開疆拓土尚不在計劃之內(nèi)。此后,曾布稱宋方最初曾對青唐諸部首領(lǐng)承諾“一丘一隴地不要他底”(16)《曾公遺錄》卷8,第145頁。,即為證明。之所以如此,主要還是因為宋廷不愿再耗費太多財物,畢竟之前的對西夏進(jìn)攻已令朝廷財政捉襟見肘了。也應(yīng)指出,宋廷的態(tài)度雖審慎,但詔令內(nèi)容卻并不很明確,“斟酌敵情,相度收接”之語事實上賦予了孫路等邊臣一定的自主空間,也折射出宋廷對相關(guān)信息的掌控不充分。章惇、孫路等人的暗箱操作,確實讓他們在博弈中獲得了些許優(yōu)勢。
總之,元符青唐之役并非宋廷經(jīng)過認(rèn)真籌劃后實施的軍事行動。相反,對于是否應(yīng)對青唐用兵,宋廷一度持消極態(tài)度。最后,其之所以決定介入青唐內(nèi)亂,宰相章惇的影響力固不容忽視,但更多的還是受孫路、王贍等邊臣的推動。此外,無論中樞,抑或邊臣,在處置青唐事務(wù)時,都含有某些軍事之外的考量,并因此采用了一些信息操控的手段。在此役中,中樞與邊臣的關(guān)系,一開始即顯得比其他戰(zhàn)役更為微妙。
二 臨陣換帥
六月以降,孫路、王瞻接連奏稱有吐蕃首領(lǐng)投附宋方,但二人屢次上奏“并不及溪巴溫一字”(17)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3,元符二年七月壬子,第12193頁。,從而引起了曾布等宰輔的警覺,故而欲“詰路所以應(yīng)接措置溪巴溫情狀”。章惇“封孫路數(shù)書,乃密與夔議云:‘溪哥城乃積石軍,欲除溪巴溫為閤門使、知積石軍。欲自邈川直趨青唐,欲建為州,而以他人領(lǐng)之。’”章、孫吞并青唐的圖謀,至此得到公開,宰相與將帥私相聯(lián)絡(luò)的舉動,也被公之于眾。曾布認(rèn)為孫路的提議不當(dāng),遂面奏哲宗:“孫路累奏河南邈川部族歸漢,而不及溪巴溫一字,不知路何以處之?臣欲如此問孫路,而章惇以為未可。路欲除溪巴溫官,處之積石軍,而建青唐為州,以他人領(lǐng)之,臣恐未可。兼此事只是路與惇私書往還議論如此,臣等皆不預(yù)聞。路既不奏朝廷,又不申樞密院,在臣為失職,不得不論。”哲宗問:“如何?”執(zhí)政皆“唯唯”,許將稱:“問他如何應(yīng)接措置,莫也不妨。”章惇以“事未定,未可詰問”為由,表示反對。曾布反駁曰:“事定而后詰問,則已后時,雖令改正,亦已費力,此事大,乞裁處。”哲宗亦曰:“此大事,不可忽。”曾布補充道:“臣今來所問,只是問他如何應(yīng)接措置,亦別無擾他經(jīng)畫處。”章惇稱:“如此則須添一將來字,云見今如何應(yīng)接,將來如何措置。”最終宋廷采納曾布、章惇意見,降詔詢問孫路(18)《曾公遺錄》卷7,第132-134頁。。
在這次討論中,哲宗和大多數(shù)宰輔對應(yīng)否在青唐方向采取進(jìn)一步行動,依然比較慎重。“詰問”孫路,既是為了解情況,也是提醒他不可冒進(jìn)。不過,宋廷雖下詔詰問,措辭卻相對溫和,沒有給孫路設(shè)太多限制。這既與章惇對孫路的庇護有關(guān),也是出于不阻擾孫路“經(jīng)畫”的目的。對邊臣言行的包容,折射出宋廷在處理邊事時所具有的靈活性,也表明朝廷在信息掌控上的劣勢,使之不得不對邊臣做出一定讓步。
對孫路“既不奏朝廷,又不申樞密院”,唯以私書聯(lián)絡(luò)章惇的做法,曾布等比較不滿,但宋廷亦未予以批駁否定。之所以如此,除了私書的私密特性有助于邊臣暢所欲言外,還應(yīng)與宋廷在收集邊情時面臨的兩難處境有關(guān)。一方面,信息缺失將導(dǎo)致朝廷失去對邊臣和軍務(wù)的掌控,這是其絕難接受的;另一方面,若邊臣將大量信息寫成公文上報,則朝廷勢必要負(fù)起決斷之責(zé),而朝堂與邊陲之間的遙遠(yuǎn)距離,意味著君相對前方軍務(wù)的“遙控”指揮很難不出紕漏。在這樣的情況下,允許邊臣不用公文,唯以私書將邊情告知宰相,既可保證中樞不至完全不了解邊情,又可利用私書的私密屬性令某些朝廷難以處理的信息不進(jìn)入正式?jīng)Q策議程,從而減輕朝廷的責(zé)任。此后,哲宗等表示,之所以默許孫、章私書往還,是因為青唐事“經(jīng)畫未定”,言下之意即是不想由朝廷來負(fù)經(jīng)畫之責(zé)。當(dāng)然,宋廷對私書往還的縱容,難免會影響到體制內(nèi)的信息溝通,只不過此時這一弊端尚未顯現(xiàn)。
十余日后,章惇又向同僚出示孫路書信:“且留溪巴溫以持瞎征,若捐數(shù)十萬縑,招巴溫新附之眾歸漢,則巴溫一孤雛爾。”曾布稱:“孫路欲逐溪巴溫,而奪青唐為州郡,則布死不敢從也。”哲宗及其余宰輔亦認(rèn)為須約束孫路,遂降詔孫路:“依累降朝旨,應(yīng)所招納河南邈川等處愿投漢部族首領(lǐng),更切體度審情,務(wù)先以恩信撫納,毋專以兵迫脅。并合措置應(yīng)接溪巴溫等,務(wù)為邊鄙經(jīng)久安便之利,不得過有所圖,別生邊患。其所得城寨內(nèi)合只以心白向漢,有力量首領(lǐng)坐住把守,或系要害,須合差兵馬戍守之處,子細(xì)審度經(jīng)久利害,務(wù)從簡便,無令廣有增費財用兵力。”(19)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3,元符二年七月己巳,第12204-12205頁。
相比于上一份詰問詔書,這封詔書的措辭嚴(yán)厲得多,明確否定了孫路“逐溪巴溫,而奪青唐為州郡”的計劃,對他設(shè)了種種限制。孫路一味主張激進(jìn)之策,勢必會加劇朝廷不滿。此外,在商議青唐問題前一天,哲宗、曾布發(fā)現(xiàn)孫路在修建會州關(guān)城事上,也如處置青唐事那樣不申奏朝廷,只以私書告知章惇。哲宗極為惱怒,稱:“如此事何故不奏?青唐事,尚云經(jīng)畫未定未敢奏,此不奏何也?”(20)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3,元符二年七月戊辰,第12204頁。這也是朝廷態(tài)度變化的誘因。如前述,宋廷有時對邊臣不用公文,唯以私書與宰輔溝通的行為會予以涵容,但這種容忍是出于規(guī)避責(zé)任的考量,是有限度的。私書所涉之事是否“經(jīng)畫未定”,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宋廷容忍與否。然宋廷的上述想法不可能明確地宣示于眾。這使得遠(yuǎn)在千里之外的邊臣,容易感受到朝廷對自己的包容,卻很難探明后者心中的底線,在使用私書時不免會愈發(fā)膽大,最終觸怒朝廷。可以說,宋廷對孫路的態(tài)度變化,顯現(xiàn)出中樞與邊臣之間溝通互動的復(fù)雜曲折。
熙河路與朝廷的關(guān)系漸趨緊張之際,其內(nèi)部矛盾也逐漸變得尖銳。七月丙寅,王贍帥軍渡河,斬殺了密戩等當(dāng)?shù)厥最I(lǐng),攻克了邈川城,“即日以捷書聞。孫路怒贍徑上捷書,不復(fù)由帥府,諂間自此作矣”(21)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3,元符二年七月丙寅,第12202頁。。王贍之所以“徑上捷書,不復(fù)由帥府”,除了與他急于表功有關(guān)外,還有兩個原因:其一,他之前通過私密溝通,獲得了章惇的支持;其二,五月以降,他就曾有過繞開主帥直接上奏的舉動,且得到了朝廷的默許。而孫路之所以惱怒,則不全因王贍不將自己放在眼中。之前宋軍所獲城堡,均為當(dāng)?shù)厝酥鲃荧I(xiàn)納,出兵奪取邈川,意味著宋軍的舉動已不限于收接降人,而是有升級為開邊之勢,這有悖朝廷所定基調(diào)。王贍驟然將這一行動上奏,極可能令身為主帥的自己陷入被動。此時宋廷尚未直接介入到將帥之爭中,但其態(tài)度已然影響到了將帥雙方。
八月壬申,兩府同呈王贍捷報(22)《曾公遺錄》卷7,第141頁。。數(shù)日后,兩府同呈孫路章奏,“王贍收復(fù)邈川,乞建為湟水軍”。曾布認(rèn)為:“才得邈川一處,便乞建軍,恐將來乞創(chuàng)置郡縣不一,非朝廷累降約束,令于邊防經(jīng)久簡便可行及不得增廣邊費之意。此請未可從。”章惇“力欲從之”,其余宰輔“皆依違無定論”。哲宗認(rèn)為:“恐亦須有合置州軍處。”蔡卞表示同意。曾布則再次以財力不足為由,表示反對。經(jīng)過一番激烈爭辯,曾布建議:“當(dāng)俟一切撫定河南邈川之后,然后據(jù)地理緊慢,畫一措置。甚處系最要害,合建置州軍,甚處系以次,合差兵將人馬戍守,甚處只令本處首領(lǐng)心知向漢,有力量者守把坐住。俟奏到朝廷,折衷乃可定。”這一看法得到哲宗、蔡卞的認(rèn)同,最終“詔孫路詳累降約束指揮施行”(23)《曾公遺錄》卷8,第144-145頁。。
這次討論的結(jié)果,與之前差別不大。但從過程看,哲宗等雖沒有接受“建邈川為湟水軍”的建議,對王贍舉兵攻克邈川這一不符合“累降約束指揮”中“毋專以兵迫脅”、“不得過有所圖”之意的舉動卻未批駁,予以默認(rèn)。又,哲宗、蔡卞等人之前不同意“奪青唐為州郡”,此時卻開始考慮將青唐土地建置為州郡。為何他們的態(tài)度會發(fā)生如此變化?
首先應(yīng)看到,哲宗其實素有開疆拓土的意愿。之前態(tài)度謹(jǐn)慎,主要是顧忌對青唐用兵會影響對西夏作戰(zhàn),并加大財政負(fù)擔(dān)。此時對西夏拓邊已經(jīng)結(jié)束,孫路、王贍接連獲得若干城寨,又顯得頗為輕松,似未付出太大代價。哲宗的進(jìn)取之心,難免悄然復(fù)萌,這又不免影響到蔡卞等其余宰輔。
其次,從之前的奏對來看,宋廷最初判斷溪巴溫應(yīng)能順利成為青唐新主,故選擇謹(jǐn)慎行事,以期后者登位后能與之保持友好關(guān)系。但部落首領(lǐng)接連降宋,顯示溪巴溫似乎并不為當(dāng)?shù)厝擞H附。就在進(jìn)呈孫路建邈川為湟水軍之奏的前一天,兩府“同呈熙河五狀,奏接納西番次第,仍云:‘溪巴溫未見其能得與不得青唐,未可應(yīng)接,徐觀其事勢,隨宜措置次。’”(24)《曾公遺錄》卷8,第144頁。對此,曾布認(rèn)為是“夔意”(25)《曾公遺錄》卷8,第144頁。,然他也拿不出證據(jù)來加以否定。若溪巴溫確無法掌控青唐,宋方自有必要考慮轉(zhuǎn)換策略。
再次,元符時期,宋廷以“紹述”神宗、反對元祐為國是。熙豐開邊、元祐棄地,對青唐問題的立場很容易被上升到“政治正確”的高度。堅決反對孫路、王贍主張的曾布,在丁丑日的討論中,便因被章惇指責(zé)為 “非先朝而是元祐”(26)《曾公遺錄》卷8,第145頁。,而不得不做出退讓。王贍的舉動,雖違背“已降約束”,但在“紹述”的語境下,朝廷卻不易對其加以否定。
攻克邈川后,孫路令王愍為都統(tǒng)制,王贍為同統(tǒng)制,削奪了王贍的兵權(quán)。《長編》認(rèn)為,孫路鉗制王贍,是出于嫉恨(27)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丙戌條下小注,第12219頁。。《宋史》則稱當(dāng)時王贍急于進(jìn)軍青唐,而孫路想“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暫緩進(jìn)軍(28)脫脫等《宋史》卷350,《王贍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070頁。。孫抑制王,是緣自策略分歧。結(jié)合史實看,攻克邈川后,孫路確實趨于保守。第一,他將兵權(quán)移交王愍后,又?jǐn)y王愍返回了熙州(29)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丙戌條,第12217頁。。可知他暫無繼續(xù)進(jìn)取之意,否則斷不會讓主將離開前沿。第二,孫路《墓志》稱,他在攻克邈川后,下令“焚省章棧道”(30)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丙戌條下小注,第12219頁。。省章峽是邈川前往青唐的要道,截斷此道,固然可以“絕青唐之援”(31)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丙戌條下小注,第12219頁。,但也增大了宋軍向前推進(jìn)的難度。這也說明孫路此時只想保住既有成果,沒有立即擴大戰(zhàn)果的打算。如此一來,他勢必與一心向前推進(jìn)的王贍發(fā)生更激烈碰撞。
同為青唐之役的推動者,王贍、孫路為何在取得重大進(jìn)展之際忽然產(chǎn)生歧見?兩人的性格、心態(tài)固然有差異,但也應(yīng)看到,宋軍介入青唐內(nèi)亂后,朝廷下達(dá)的若干詔令指揮均秉持著謹(jǐn)慎基調(diào),對孫路的激進(jìn)主張還曾明確予以駁斥,然對于王贍攻克邈川之舉卻又未予處分。這很容易令人對朝廷的真實想法形成相異解讀,進(jìn)而造成策略分歧。可以說,是邊臣的舉動導(dǎo)致朝廷的態(tài)度趨于曖昧,而朝廷的曖昧態(tài)度又刺激了邊臣群體內(nèi)部業(yè)已存在的矛盾。雙方的互動,逐漸偏離了良性軌道。
八月初,事態(tài)又有變化。青唐門戶宗哥城(今青海平安)首領(lǐng)舍欽腳求內(nèi)附,王贍派王詠率五十騎入宗哥,同時向?qū)O路求援。孫路反令王贍離開邈川,前往河州(今甘肅臨夏)督糧;王贍申訴于朝廷,將帥之爭白熱化(32)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丙戌,第12217頁。。在向朝廷進(jìn)言時,王贍“怨孫路不專委己,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欲以中路”(33)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壬子,第12243頁。。按,元符二年七八月間,宋軍看似推進(jìn)順利,實則危機暗伏。攻取邈川時,即發(fā)生過當(dāng)?shù)厥最I(lǐng)“背盟拒旅”(34)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3,元符二年八月丙寅,第12219頁。之事。王詠入宗哥時,更一度因“諸羌連接作亂”,而不得不“登子城樓,去其梯以自固”,幸得高永年救援,方逃過一劫(35)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丙戌,第12218頁。。上述事件,表明番部并非真心臣服。宋軍要奪取青唐,未必會很輕松。高永年即指出,必須“重兵以臨之,厚賂以結(jié)之,恩威并行乃可也,不然事必不濟”(36)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4,元符二年八月壬辰,第12227頁。。王贍身在前沿,不可能全不知曉這些情況,但此時他為了在政爭中壓倒主帥,只得上報不實信息,以騙取朝廷的支持。
收到王贍申訴后,八月丙戌,兩府“同呈王贍申:‘經(jīng)略司句追河州,宗哥首領(lǐng)方乞歸漢,已遣使臣部五十余騎往據(jù)宗哥城,而經(jīng)略不肯應(yīng)副兵馬,恐溪巴溫旦夕入青唐。’遂得旨,孫路知西京,胡宗回帥熙河”(37)《曾公遺錄》卷8,第149頁。。臨陣換帥實為兵家大忌,因部將申訴而撤換主帥,則有可能造成部將跋扈。對于這些隱患,宋廷不會全無認(rèn)識。曾布記,在此事上,章惇曾“數(shù)與余爭論”,直到進(jìn)呈王贍申狀的前一天,還“議罷孫路熙帥,未果”(38)《曾公遺錄》卷8,第149頁。。可見,宋廷做出這一決定并不輕松。宋廷決定換帥,一方面與其對孫路積累的不滿有關(guān),另一方面則是出于要迅速奪取青唐的考量。“青唐不煩大兵可下”之說固然不確切,但朝廷遠(yuǎn)在千里之外,對當(dāng)?shù)夭柯洹氨趁司苈谩钡燃?xì)節(jié)并無了解。相反,從當(dāng)時的形勢看,在拿下宗哥城后,宋軍距青唐城便只有一步之遙,確有機會搶在溪巴溫之前攻占青唐。而宗哥首領(lǐng)降宋,似乎再次印證了溪巴溫不被當(dāng)?shù)厝擞H附。在這樣的情況下,素有開邊之志的哲宗、章惇,自然希望能盡快收功;之前一直謹(jǐn)慎的曾布、蔡卞等,也無由繼續(xù)堅持持重主張。可以說,隨著宗哥城歸降,宋廷已放棄之前的穩(wěn)健策略,轉(zhuǎn)而謀求吞并青唐。撤換孫路,重用王贍,正是其政策轉(zhuǎn)變的表現(xiàn)。
以后見之明視之,宋廷的策略調(diào)整得相當(dāng)倉促。哲宗的不成熟,章惇等宰輔的急功近利,都是造成這一決斷的重要原因。也應(yīng)看到,此前宋廷秉持的穩(wěn)健策略,本身就不是建立在對青唐情況的全面了解之上的。缺乏信息支撐,既有策略的根基本來就比較脆弱,自然容易遭到更改。又,此前對西夏拓邊的戰(zhàn)績,也在無形中影響著北宋君相。對西夏連戰(zhàn)獲勝,證明宋軍戰(zhàn)力很強,決策者難免因此輕視蕞爾青唐。另一方面,受制于客觀條件,北宋最終未能將西夏吞并,又不免令哲宗、章惇等心存遺憾。青唐內(nèi)亂,恰為他們創(chuàng)造了失之桑榆、收之東隅的機會。正因如此,決策者一看到某些有利跡象,就不顧其他,匆忙改弦更張。不料,此后青唐給宋軍造成的困難,遠(yuǎn)勝西夏。
三 吞并青唐
八月中旬前后,青唐局勢更加復(fù)雜。瞎征在篯羅結(jié)等人的威脅下朝不保夕,于八月癸巳前往宗哥降宋(39)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4,元符二年八月癸巳,第12227頁。。篯羅結(jié)等最初聯(lián)絡(luò)王贍,只是想借宋人之勢逼走瞎征。目的達(dá)到后,他們“不欲屬漢”,奉迎溪巴溫次子隴拶為青唐新主(40)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丁酉,第12232頁。。青唐各部亦聚集人馬(41)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2頁。,欲與宋軍一決雌雄。在這樣的情況下,要以“輕兵”取青唐幾無勝算。即令動用“重兵”,在當(dāng)?shù)厣礁呗冯U、補給困難的條件制約下,失敗的風(fēng)險也不小。因此,王贍產(chǎn)生了放棄之念。然礙于之前的承諾,此時他無法向朝廷明言,無奈之下運用了一些手段。
首先,申奏當(dāng)?shù)厥最I(lǐng)之所以奉迎隴拶,是因為孫路強令自己去河州,耽誤了十余日,致使人情“復(fù)中變”(42)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1頁。。宋廷當(dāng)時對孫路正深感厭惡,立即認(rèn)可了王贍的這一說法,哲宗、章惇、曾布等均認(rèn)為孫路“須重貶”(43)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3頁。。
諉過孫路后,王贍“力言羌情叵測,非重兵不可”(44)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3頁。。從此后,熙河大軍匯集宗哥,王贍依然“久駐宗哥城,遲疑不進(jìn)”,并對胡宗回言“青唐未可取之”(45)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3頁。,可見他并非真想率領(lǐng)大軍直取青唐。如前述,宋廷不希望因?qū)η嗵朴帽黾迂斦?fù)擔(dān)。對此,王贍心知肚明。他在攻訐孫路時,倡言“青唐可不煩大兵取”,即是利用此想法。此時討要援兵,依然是利用這一點,只不過目的已經(jīng)變?yōu)橄M⒅y而退,不再要求自己前進(jìn)。
據(jù)《長編》載,宋廷在獲悉隴拶入青唐之后,“章惇白上,促遣苗履、康謂、李澄選兵馬同王贍入取青唐。曾布以為宜降指揮,令多方招來隴拶,侯其不聽命,加兵未晚。惇從之,乃依此行下”(46)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2頁。。看來,宋廷對于動用重兵,確實心存猶豫。但過了不久,宋廷還是令剛剛完成會州進(jìn)筑任務(wù)的熙河大軍開赴宗哥(47)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壬申,第12243頁。。此舉表明了宋廷非奪取青唐不可的決心,也令王贍壓力倍增。
看到朝廷的強硬姿態(tài),王贍在繼續(xù)拖延時間之余,又“乞差將兵及差中使招納”。他“乞差將兵”,還是希望通過索要更多資源,來促使朝廷放棄;乞“差中使招納”,則明顯想將責(zé)任推給朝廷。宋廷頗為不滿,下詔王贍“顯屬違越,特罰銅二十斤”(48)《曾公遺錄》卷8,第167頁。。
可以說,八九月間,王贍與宋廷在青唐一事上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轉(zhuǎn)變。之前是王贍不斷鼓吹速取青唐,而宋廷態(tài)度謹(jǐn)慎;而此時卻變?yōu)樗瓮⒔吡ν苿樱踬爠t一再拖延。宋廷態(tài)度如此堅決,原因有二。一方面,此時宋軍占領(lǐng)了宗哥、邈川等地,又接納了瞎征,即令就此止步,溪巴溫、隴拶父子也未必愿與宋和平共處。既如此,則不如乘其立足未穩(wěn),將之連根拔除。另一方面,對困難缺乏了解。這又包括兩點。第一,認(rèn)為隴拶被立只是偶然事件,低估了青唐諸部抗衡宋師的實力與意志。章惇在得知隴拶入青唐后,稱:“隴拶小兒無能為,乃心牟欽氈妄作爾,必旦夕可了。”(49)《曾公遺錄》卷8,第164頁。后兩府進(jìn)呈招降青唐之策,“隴拶出漢與瞎征一等推恩”,哲宗“疑太重”,宰輔稱“不緣隴拶爭立,則瞎征豈肯出降,兼隴拶乃董氈之侄,是當(dāng)?shù)们嗵普摺保茏凇澳藦闹?50)《曾公遺錄》卷8,第166頁。。在推恩問題上斤斤計較,說明哲宗也不將隴拶被立看得多么嚴(yán)重。看來此前王贍等反復(fù)奏稱當(dāng)?shù)刂T酋多欲降宋,形勢對宋軍十分有利,對宋廷影響極深,以至于后者即便獲知到一些相異信息,也無法改變先入之見。第二,對青唐的地理形勢缺乏認(rèn)識。哲宗朝以前,宋軍從未深入過青唐腹地。王贍攻克邈川后,曾“畫到西番地圖”,然“地圖殊未得實”(51)《曾公遺錄》卷7,第141頁。。當(dāng)時王贍正積極推動攻取青唐,他奏進(jìn)不實地圖,應(yīng)有誤導(dǎo)朝廷、以圖進(jìn)取的考量。宋廷依據(jù)此“殊未得實”之地圖,自然很難明了攻取青唐的難度。總之,直到九月,宋廷仍認(rèn)為奪取青唐比較容易。王贍一再拖延,僅被宋廷視為是其個人專橫(52)《曾公遺錄》卷8,第169頁。的表現(xiàn)。之前,王贍一再以不實信息誤導(dǎo)朝廷,造成了朝廷的決策失誤;而朝廷的錯誤決策,反過來又令王贍陷入窘境,這是后者始料未及的。
也應(yīng)看到,宋廷雖有必取青唐之心,不斷用增添兵馬、“罰銅”以及“令王厚與王贍同管勾青唐招納事”(53)《曾公遺錄》卷8,第166頁。等方式,給王贍施加壓力,卻又一直沒有頒降明確指揮,很大程度上還是規(guī)避風(fēng)險的策略。畢竟其距離青唐太遠(yuǎn),硬性指揮,難保不出差錯。此外,從上文可知,宋廷雖調(diào)集大軍,卻一直期待隴拶能主動來降。其沒有硬性要求王贍迅速進(jìn)軍,亦與之有關(guān)。然無論如何,宋廷指令的不明確,使王贍能在宗哥遷延多日。這段時間內(nèi),青唐城中原本充裕的存糧,被各部落私掠殆盡,增大了此后宋軍面臨的困難。
九月辛亥,王贍與朝廷僵持之際,新任熙河帥胡宗回抵達(dá)熙州(今甘肅臨洮)。“宗回怒贍反復(fù),日夜督贍出師,且遣使者戒之曰:‘我已知青唐軍單馬寡……隴拶幼稚,何能為,第以心牟欽氈等立之為名,其實欲盜府庫,非有堅拒我之心。贍駐兵宗哥,怯懦之情可見。若為我至宗哥語贍,吾已點集兵馬來,即以軍法從事矣。’又遣王愍復(fù)至邈川,聲言欲使代贍。”(54)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壬子,第12243頁。在胡宗回的逼迫下,王贍不得不出兵。胡宗回敢于嚴(yán)令王贍出師,關(guān)鍵在于他獲知了青唐“軍馬單寡、隴拶幼稚”等信息。此后在給朝廷的章奏中,他又提及了上述情況,并稱這是自己“體問”(55)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戊辰,第12261頁。所得。此前從未踏足熙河的胡宗回,其信息究竟從何而來?
瞎征降宋后,于八月二十三日被送至熙州(56)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4,元符二年八月壬辰,第12227頁。。九月初,胡宗回到達(dá)熙州時,瞎征恰在城中。不難推斷,這位青唐舊主是胡宗回最主要的信息來源。或許是出于對溪巴溫父子的怨恨,瞎征十分希望宋軍能直搗青唐。他“語人曰:‘吾蓄積甚多,若漢兵至,可支一萬人十年之儲。’”(57)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己未條下小注,第12248頁。這明顯是想勸誘宋人盡快發(fā)兵。胡宗回甫一到任,即斷定青唐容易攻取,必是受了瞎征影響。另一方面,胡宗回急于令王贍進(jìn)軍,也與之前孫、王之爭有關(guān)。王贍利用朝廷逐走孫路,顯示出較強的政爭手腕,胡宗回必對其有所忌憚。孫路被罷,表明朝廷有速取青唐之心,又不免對胡宗回造成壓力。對于胡而言,拖延的時間太久,難保王贍不會嫁禍于自己,令自己變成第二個孫路,速戰(zhàn)速決才是保身之道。正是在上述急迫心情的影響下,胡宗回未仔細(xì)對自己所獲信息進(jìn)行甄別。事態(tài)的后續(xù)發(fā)展,證明他的決斷并不完全合理。
王贍、胡宗回先后上報不確切信息,推動著青唐之役走向失敗。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狀況,不能僅僅歸因于兩人品行才干的缺陷。宋廷默許將官不經(jīng)帥臣直接與自己溝通,無形中給予了將官借助朝廷權(quán)威壓倒帥臣的機會。這既會刺激將官以下克上的野心,也會令帥臣壓力倍增,從而加大將帥矛盾。將帥一旦發(fā)生沖突,勢必要爭取中樞支持,難免不會為迎合中樞意志而對信息加以取舍乃至扭曲。宋廷直接與將官溝通,本含有“防壅蔽”的意圖,結(jié)果卻造成了自己被壅蔽,實在具有諷刺意味。
恰在王贍出兵時,青唐城中又生內(nèi)亂,隴拶被囚禁,心牟欽氈等與王贍聯(lián)絡(luò)請降。九月己未,王贍到達(dá)青唐,諸部首領(lǐng)出降(58)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己未,第12248頁。。宋軍似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吞并了青唐。消息傳至開封,朝廷異常興奮。哲宗舉行盛大慶典,建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宗哥為龍支城,青唐舊地全被劃入熙河路版圖(59)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6,元符二年閏九月癸酉,第12267頁。。元符時期的開邊業(yè)績,至此達(dá)到頂峰。宋廷此前設(shè)想過若攻取青唐,不置州軍,而是“置一都護總領(lǐng)”(60)《曾公遺錄》卷8,第145頁。進(jìn)行松散管控。此時不顧前議,將青唐主要城鎮(zhèn)皆建為州郡,說明在其看來,對青唐進(jìn)行直接統(tǒng)治是十分容易的。毫無疑問,宋軍“不煩寸戟,坐定一邦”(61)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6,元符二年閏九月壬申,第12266頁。的戰(zhàn)績,極大地增強了決策者的信心。此外,九月以降,宋廷好事不斷,先是西夏遣使謝罪,態(tài)度極其恭順,令君臣頗為滿意(62)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0頁。。此后,哲宗又以皇子滿月為由,冊立自己寵愛的劉氏為皇后(63)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丙寅,第12260頁。。吞并青唐,可謂喜上加喜。在這樣的氛圍中,決策者很難保持頭腦冷靜,無法以理性的態(tài)度去思考后續(xù)方略。
就在中樞喜不自勝之時,青唐的宋軍卻發(fā)現(xiàn)自己陷入了危機。王愍等指出,青唐有四不可守:“道險地遠(yuǎn),緩急聲援不相及,一也;羌若斷炳靈之橋,塞省章之隘,我雖有百萬之師,倉促不能進(jìn),二也;提孤軍以入,四向無援兵,羌人窺伺,必生他變,三也;設(shè)遣大軍,而青唐、宗哥、邈川,食皆止可支一月,內(nèi)地?zé)o糧可運,難以久處,四也。”此外,王贍帶領(lǐng)的是從會州趕來的疲憊之師,“皆憔悴,衣履穿缺,器杖不全,羌視之,益有輕漢之心”(64)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6,元符二年閏九月壬辰,第12286頁。。然宋廷既已大肆慶賀,前方將領(lǐng)也就不敢將“不可守”之說申奏。而沒有朝廷的支持,宋軍很難對己方劣勢加以彌補。一場軍事災(zāi)難,悄然臨近。
四 前功盡棄
閏九月戊寅,青唐山南諸部暴動,“明日諸羌皆應(yīng)”,“滿四山而呼,晝夜不息”(65)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6,元符二年閏九月戊寅,第12287頁。。同時,諸部圍攻邈川,西夏遣三監(jiān)軍助之,“合十余萬人。斷炳靈寺橋,焚省章峽棧道,四面急攻”,宗哥城亦被包圍(66)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6,元符二年閏九月壬午,第12288頁。,局面驟然變得岌岌可危。
經(jīng)過王贍、王愍等人的苦戰(zhàn),當(dāng)?shù)夭孔鍖η嗵频瘸堑膰ィ谑鲁醣粫簳r擊退。十月壬寅,宋廷得熙河所奏“青唐、邈川解圍捷書”(67)《曾公遺錄》卷8,第176頁。。慶幸之余,朝廷開始重新評估形勢。以前一些被屏蔽掉的信息,至此始有機會上達(dá)天聽。十月庚戌,熙河路進(jìn)奏青唐河南北地圖,宋廷方對當(dāng)?shù)氐乩硇纬奢^全面認(rèn)識(68)《曾公遺錄》卷8,第179頁。。丁巳,曾布“進(jìn)呈姚雄與姚麟書,云:‘青唐去大河五百里,道路險隘,大兵還邈川,而青唐路復(fù)不通。朝廷進(jìn)筑城寨畢,方有休息之期,今復(fù)生此大患,如何保守?深為朝廷憂之。青唐非數(shù)萬精兵不可守。’上亦深然之”(69)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7,元符二年十丙辰,第12301頁。。此前的樂觀,至此已經(jīng)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章惇的舉動。曾布稱,十月己亥,兩府因“青唐、邈川信息不通”而焦慮時,“夔遂有卻欲以青唐還溪巴溫之說”;曾布、蔡卞認(rèn)為形勢尚未惡化到如此地步,否定了這一看法(70)《曾公遺錄》卷8,第175頁。。然而,章惇還是“以書令胡宗回如府州折氏措置”,要將實際統(tǒng)治權(quán)交給當(dāng)?shù)厝恕6嗵平鈬南⒁坏剑聬帧耙詴钭诨兀瑢⒆鬟^首領(lǐng)家族一處拘管,先執(zhí)其首領(lǐng),便先從嬰孩以至少壯者,一一次第凌遲訖,然后斬首領(lǐng)” 。按曾布所記,他所指陳的章惇“罪狀”,都有胡宗回“錄到惇書”為證,應(yīng)屬可信。章惇何以會有如此“輕易反復(fù)”(71)《曾公遺錄》卷8,第185-186頁。的舉動?個人性格、局勢劇變造成的壓力,都是重要原因,但又都不足以完全解釋上述現(xiàn)象。筆者認(rèn)為,章惇的舉動,應(yīng)與他對青唐形勢有較其余決策者更透徹的認(rèn)識有關(guān)。
如前所述,在宋方介入青唐內(nèi)亂之初,王贍就與章惇保持著私下聯(lián)絡(luò)。青唐的真實情形,王贍雖不敢通過公文上言,卻定然會如姚雄、姚麟叔侄通信那樣,用私書在諸部暴動前后告知其庇護者章惇。章惇較哲宗、曾布等人更早、更全面地獲悉青唐的真實情況,難免產(chǎn)生畏難情緒。他私下給胡宗回下達(dá)的兩項指令,表面上前一軟弱、后一強硬,其實都表明他已無信心用常規(guī)方法守住青唐,故忽而打算放棄,忽而想用屠戮恫嚇這種非常之術(shù)來冒險一試。無論如何,他的上述舉措都給戰(zhàn)局造成了不利影響。屠殺使當(dāng)?shù)厝烁鼮閿骋曀诬姡弧傲詈诨厝绺菡凼洗胫谩保瑒t使前方將帥知道朝廷有棄守之意,難免影響士氣。此后,宋軍一遇挫折,即“氣奪,無敢復(fù)言戰(zhàn)者”(72)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7,元符二年十月己未,第12304頁。,與此有關(guān)。宰輔與將帥之間私書往還的負(fù)面影響,至此終于顯露無遺。
十月底,形勢再度惡化。郎阿章等當(dāng)?shù)厥最I(lǐng)圍攻一公城,胡宗回先后派王吉、魏釗前往討伐,皆全軍覆沒。胡又令驍將種樸前往討擊,結(jié)果種樸遇伏身死。自此,熙河將士斗志皆無,“青唐道路不復(fù)通”(73)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7,元符二年十月己未,第12304頁。。十一月一日,朝廷聞知種樸死訊,“夔聞兵敗,氣沮矣”(74)《曾公遺錄》卷8,第183頁。。最高決策層對能否守住青唐,信心更加低落。
中樞在青唐問題上倍感焦慮,西北帥臣中亦出現(xiàn)了異議。十月底,宋廷因青唐吃緊,下令征調(diào)涇原路精兵前往增援。十一月二日,涇原經(jīng)略使章楶密奏哲宗,稱熙河兵馬暴露日久,苦不堪言;青唐諸部利用地勢屢挫宋軍,熙河將帥“措置似已技窮”,無從應(yīng)對;西北府庫“內(nèi)外一空”,難以贍軍(75)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辛未,第12317-12322頁。,暗示哲宗棄守青唐。
章楶在拓邊問題上一直持穩(wěn)健立場,這是他主張棄守的主要原因。不僅如此,朝廷征調(diào)涇原精兵,削弱了該路的守御力量,這也是身為主帥的章楶所不愿見到的。在章奏中,他稱:“萬一西賊張聲欲襲鄯、湟,卻來本路作過,臣曉夕竊憂之。”(76)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辛未,第12322頁。現(xiàn)實利益考量,亦是促成他上奏的因素。還應(yīng)看到,自紹圣時起,涇原、熙河兩路在拓邊活動中即齟齬不斷,同時兩路背后分別有曾布、章惇為后盾(77)關(guān)于此問題,筆者擬另文述之。。元符元年,宋廷曾承諾一旦奪取天都山,就允許章楶離開西北前線,然孫路奏請經(jīng)營青唐后不久,曾布即以新得之地“未可闕人”為由,將章楶留在了涇原(78)《曾公遺錄》卷7,第106頁。。這一舉動明顯含有以章楶制約、監(jiān)控熙河路之意。結(jié)合這些情況看,章楶上密奏,可能也與中樞內(nèi)部的分歧有關(guān)。總之,章楶的密奏,折射出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及中央、地方內(nèi)部的多重矛盾。在西北諸帥中,章楶戰(zhàn)功最為出眾,素為哲宗倚重,他的意見對哲宗產(chǎn)生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在多種因素的推動下,十一月初,朝廷下詔,令:“熙河經(jīng)略使胡宗回相度賊勢,如王贍在鄯州糧草果是闕乏,即令拘收統(tǒng)制林金、安兒等處城守,將蕃漢兵馬還湟州駐扎。”從這份詔令看,宋廷已傾向于放棄青唐,但“相度”云云,又有模糊之處。《長編》即稱:“時朝廷已議棄青唐,獨未曉然行下耳。”(79)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第12324頁。何以宋廷不“曉然行下”?除了想為自己保留一些顏面外,更為重要的原因還是不想負(fù)放棄之責(zé)。十二月初,胡宗回奏稱自己得到詔書后,“但行下王贍相度施行,不肯果決”;曾布等均認(rèn)為:“宗回當(dāng)如此施行,若便令王贍歸湟州,若贍異日以為可守,是今日不當(dāng)棄去也。令相度可否,申取帥司指揮,若不可,待報,即一面依朝旨?xì)w湟州駐扎,亦曲盡之矣。”(80)《曾公遺錄》卷8,第200頁。對胡宗回的肯定,表明宋廷也有同樣的想法,希望邊臣自行提出撤離,以便將責(zé)任全推給后者。傳統(tǒng)看法認(rèn)為,宋廷奉行“將從中御”原則,總是傾向于收奪將帥的指揮權(quán)。但在青唐之役中,卻多次出現(xiàn)中樞為了規(guī)避責(zé)任,故意不下達(dá)明確命令,從而變相將部分權(quán)力下放給將帥的事例。這表明在不同的具體境況中,宋廷的利益考量往往并不相同,因此其所采用的策略也常具有一定的彈性。當(dāng)然,這種放權(quán)未必對軍事活動有益。
朝廷不想擔(dān)責(zé),熙河將帥亦然。宋廷指令的不明確,又為邊臣創(chuàng)造了拖延時間的余地。詔書頒降后,胡宗回“不肯果決”,等待王贍自申,王贍則遲遲不肯申請,在全無勝算的情況下困守青唐城等幾個孤立據(jù)點。另一方面,宋廷雖“未曉然行下”,但觀其舉措,上下皆知棄守的可能性極大。為了應(yīng)對棄守后必然要進(jìn)行的追責(zé)以及借機打擊政敵,十一月以降,朝堂內(nèi)外各政治人物加緊彼此攻訐。在朝中,曾布與章惇互相諉過(81)《曾公遺錄》卷8,第185頁。;在西北,陜西轉(zhuǎn)運判官秦希甫指責(zé)王贍、王厚盜取青唐府庫,激起當(dāng)?shù)乇﹦?82)《曾公遺錄》卷8,第201頁。,而熙河走馬承受公事李彀“多攻胡宗回”(83)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甲午,第12338頁。,后又指王贍為“罪魁”(84)《曾公遺錄》卷8,第203頁。。可以說,十一、十二月中,不僅宋軍與吐蕃人在僵持,邊臣與朝廷以及二者內(nèi)部不同勢力也在角力。
宋軍不撤回,熙河路明知“道路不復(fù)通”,也不得不繼續(xù)向前方運送補給。在政爭氛圍中,一些本應(yīng)得到重視的問題卻被忽略。如高永年指出,鼐宗堡地勢險要,“得之則足以為吾捍蔽,而省章峽道路無阻。然主者略不加意”(85)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9,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第12342頁。。此時宋軍深入青唐已久,“主者”未必全然不知鼐宗堡之意義,只是忙于內(nèi)斗,無暇顧及。“略不加意”的結(jié)果,則是造成了更大損失。如十一月底,邢玠運糧前往龍支城,在省章峽遇伏陣亡(86)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19,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第12342頁。。延宕至十二月下旬,青唐形勢越發(fā)危急。
十二月癸丑,宋廷終于下詔將青唐交給當(dāng)?shù)厝耍耙噪]拶為河西節(jié)度使,知鄯州”,令宋軍撤出。曾布稱:“今日青唐之變,擾攘未定,排難解紛,固當(dāng)如此,若更守株,贍等陷沒,或更有不測之變,則朝廷更難處置。”(87)《曾公遺錄》卷8,第202-203頁。無奈之意,溢于言表。庚申,胡宗回章奏至朝廷,“已差使臣催王贍回湟州”(88)《曾公遺錄》卷8,第206頁。。癸丑、庚申相距僅七日,從文書流轉(zhuǎn)的時間看,胡宗回上奏時絕不可能接到朝廷令隴拶知鄯州之詔,必是自主決斷。朝廷和邊臣的僵持,令青唐形勢日漸惡劣,而形勢的惡化,最終使二者不約而同地打破僵持。元符青唐之役,以怪異的方式劃上了句號。
棄守青唐,使得數(shù)月前的盛大慶典淪為笑柄,這對哲宗的打擊不可謂不大。八、九月間,哲宗的身體狀況已很糟糕。閏九月,皇子、公主接連去世,又令他備受痛楚(89)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122頁。。放棄青唐,更如雪上加霜。元符三年正月,哲宗撒手人寰,其弟徽宗繼位。君主的變更,使得政局發(fā)生變化,進(jìn)而為此后第二次青唐之役埋下了伏筆。相關(guān)問題非本文能詳述,擬另文論之。
五 結(jié)語
以上,筆者以最高決策集團與前線將帥之間的交流溝通為切入點,分析了元符青唐之役進(jìn)行過程。不難看出,在戰(zhàn)役中,中樞與前線之間始終存在著惡性互動。將帥常常對信息加以屏蔽、扭曲,中樞則時而盲目決斷,時而故意不下達(dá)明確指令。這種惡性互動,可說是導(dǎo)致青唐之役失敗的關(guān)鍵因素。
惡性互動何以出現(xiàn)?原因比較復(fù)雜。如前所述,不同人物的利益考量、政壇上的派系關(guān)系,以及朝堂內(nèi)外的政治氛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樞與將帥之間的溝通。而溝通交流活動在被上述種種因素影響的同時,也推動、刺激著這些因素的變化。兩者彼此激蕩,互為因果,共同造就了宋軍先勝后敗的戰(zhàn)果。以往研究者也關(guān)注到了影響宋代軍政信息交流的多元因素,但在分析問題時,往往傾向于將各因素從歷史進(jìn)程中抽離出來逐一加以論述。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各因素之間的動態(tài)聯(lián)系,使我們難以確切理解它們是如何發(fā)揮作用的,更隱含著將復(fù)雜歷史簡單化的危險。在以后的研究中,或許應(yīng)該回歸到事件本身,在具體過程中對復(fù)雜動因加以把握,以便更透徹地理解宋代軍政信息交流。
從整體上看,對青唐之役影響最大的是宋廷在與將帥進(jìn)行溝通時所采用的兩項舉措。其一,按常規(guī)制度,前線統(tǒng)兵將領(lǐng)所獲信息,應(yīng)先上報路級帥臣,帥臣裁斷后奏報朝廷;朝廷的指令,則需下達(dá)給帥臣,再由帥臣相機向統(tǒng)兵將領(lǐng)發(fā)出更具體的命令。而在青唐之役中,宋廷時常繞開帥臣,直接與王贍等前線將領(lǐng)進(jìn)行聯(lián)絡(luò)。這種做法看似能提高交流效率,強化中樞對前線的指揮力度,其實蘊含著不小的風(fēng)險:沒有帥臣的助力,中樞很難對統(tǒng)兵將領(lǐng)奏報的信息做出準(zhǔn)確研判;直接對統(tǒng)兵將領(lǐng)下達(dá)指令,容易造成前線軍政秩序的混亂。青唐之役中,上述風(fēng)險最終都變?yōu)榱爽F(xiàn)實。其二,在使用各類公文獲取信息、下達(dá)指令的同時,宋廷也默許某些宰輔用私人書信與將帥進(jìn)行溝通。公私文書并行,本可能拓展朝廷的信息來源,增加中樞與前線溝通的靈活性,但由于宋廷未能合理地對私書加以控制,結(jié)果導(dǎo)致公私文書不僅未能形成互補,反而經(jīng)常彼此抵牾。某些公文未曾明言的信息,經(jīng)由私書在部分將帥和宰輔之間暗中流轉(zhuǎn),使得中樞與邊臣兩大群體內(nèi)部的信息分布變得很不均衡,加大了各人物之間的不信任,刺激著業(yè)已存在的種種矛盾,進(jìn)而影響到軍事決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
可以認(rèn)為,元符時期,宋廷是希望在維系既有軍政體制框架的前提下,運用若干靈活變通手段,以彌補制度不足,從而更為有效地應(yīng)對軍事問題,同時維護自身利益。然對于伴隨“靈活變通”而生的種種問題,例如體制的穩(wěn)定性受到?jīng)_擊、上下級權(quán)責(zé)關(guān)系趨于模糊等,宋廷卻缺乏預(yù)判,在戰(zhàn)役進(jìn)行中亦未找出應(yīng)對之策。這在無形中加劇了朝廷與邊臣的權(quán)力博弈,也為雙方推卸責(zé)任創(chuàng)造了更多機會。不成功的權(quán)力運作,造就了不成功的交流互動。
總之,青唐之役折射出哲宗親政時期最高決策集團在政治、軍事上的不成熟。以往論者著眼于宋軍的對西夏戰(zhàn)績,對紹圣、元符時期的西北拓邊活動評價較高,然由青唐之役視之,當(dāng)時北宋中樞決策者的信息收集、處理能力以及與下屬官員溝通協(xié)調(diào)的能力都存在較大缺陷。在以后的研究中,或可對紹圣、元符時期的西北拓邊再作評估。尤其是對西夏進(jìn)攻的成功,是否事出偶然?這值得重新分析。還應(yīng)看到,青唐之役中出現(xiàn)的某些現(xiàn)象,例如中樞與最前線統(tǒng)兵官之間“直貫”式的溝通,宰輔與將帥在戰(zhàn)時頻繁進(jìn)行私書交流等,在神宗朝的軍事活動中就已見端倪(90)方震華《和戰(zhàn)之間的兩難:北宋中后期的軍政與對遼夏關(guān)系》,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20年版,第148-176頁。。相似現(xiàn)象在不同時期一再出現(xiàn),其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層次的原因?這或許也值得進(jìn)一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