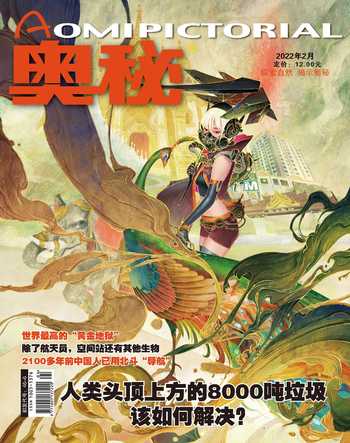你的“社死”時刻可能和這種疾病有關
鄭昱虹

不少人可能有過以下的“社死”經歷:考試馬上開始,肚子卻突然一陣絞痛,只能不管不顧地帶著扭曲的表情沖向廁所;想要專心思考和干活,但數日沒有排便讓人坐立難安;在靜得出奇的自習室里坐著,卻因為腸道頻繁排氣而“社死”…… 這些問題看似不要緊,但是當它們在一個人身上頻繁出現,就會顯著影響其生活質量。但不幸的是,科學家還沒有找到這種癥狀出現的真正原因,能幫到患者的還很有限。
有些人可能對上面的描述瘋狂點頭,但有些人也可能覺得匪夷所思。其實,這些癥狀可能是腸易激綜合征(后文簡稱“腸易激”)的表現,這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疾病,在全球范圍內約有10%的人會受其困擾。更易出現在20~50歲的年輕人群中,且女性的發病率約為男性的2~4倍。
嚴格來說,腸易激并不是一種獨立的疾病,而是一組會同時出現的癥候,包括反復且持續的腹部疼痛和排便異常,但是這些癥狀又不是消化道潰瘍、炎癥、感染或癌癥等導致的。也就是說,患者雖然存在癥狀,但檢查結果往往是器官功能一切正常。
即便如此,腸易激的危害也不容小覷。有研究表明,腸易激會顯著降低生活質量,在嚴重的情況下,其造成的影響甚至與腎臟損害和糖尿病無異。除此之外,腸易激患者還可能存在其他的健康問題,包括纖維肌痛、慢性疲勞綜合征等慢性疼痛,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等消化系統疾病,焦慮、抑郁等精神疾病等。
目前,醫生還無法通過一些特定的生物手段來檢測腸易激,只能將其他可能的疾病排除后確診。根據最新的羅馬IV診斷標準,如果你的腹痛與排便行為、排便頻率以及糞便形態有關,三條標準至少滿足其二,癥狀持續6個月以上,且最近3個月內每周至少1天有癥狀,才可以被診斷為腸易激。
從一緊張就肚子疼,到腸易激患者還可能患有的一些精神相關疾病,我們或許能想到心理和生理過程在相互影響。其實,包括腸易激在內的功能性胃腸道紊亂又被稱作“腸-腦互動障礙”。當大腦與腸道的協同出現問題時,腸道肌肉的收縮方式也會受到影響,進而導致腹瀉或便秘;腸道也可能會變得更加敏感,使人更容易感覺到腹脹或疼痛。
但大腦和腸道如何溝通呢?在人類的消化系統壁上,有一個由多種神經元組成的神經網絡——腸神經系統,內部具有獨特的神經回路,能夠獨立于中樞神經系統協調胃腸道功能。因為其規模、復雜性和其與大腦使用的信號分子的相似性,腸神經系統也被稱為我們的“第二大腦”。
在大腦與“第二大腦”之間存在腸腦軸,它是中樞神經系統與腸神經系統雙向通信的渠道,受神經系統、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和腸道微生物等因素共同調控。科學家認為腸易激綜合征的出現,正是因為各種因素之間復雜的關系被破壞了。
腸易激綜合征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在家族群體中聚集,如果一個人的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患有腸易激綜合征,那么他患腸易激綜合征的可能性會增加2~3倍,這提示腸易激綜合征可能存在遺傳因素。在一項發表于《自然·遺傳學》的新研究中,一個國際研究小組通過一項大型的全基因組分析研究,為腸易激綜合征的病理生理學原因提供了線索。
研究人員對53400例患者和433201例普通人進行了全基因組關聯研究,確定了兩者之間存在6個較為常見的遺傳差異。盡管腸易激綜合征主要表現為腸道癥狀,但其實多種組織都會受到這6個基因變異的影響。增加腸易激綜合征風險的基因構成,也會增加一些常見情緒障礙的風險,如焦慮、抑郁、神經質和失眠。有可能是共同的遺傳起源導致神經細胞出現了生理變化,同時影響了情緒和腸道。
不過總體而言,腸易激綜合征的遺傳性很低。也就是說,其他因素對腸易激綜合征的影響可能更重要,如飲食、壓力和行為,而這些也可能會影響所有家庭成員。
目前還沒有針對腸易激綜合征的特效藥或特效療法,但它也并非是讓我們束手無策的“絕癥”,存在一些治療方法可以緩解部分患者的癥狀。這些思路迥異的療法也反映了腸易激綜合征在治療上的復雜性。對于患者來說,它們的療效也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從改變生活方式的角度,醫生可能建議患者多吃膳食纖維、避免食用麩質、或少吃易于在結腸中吸水和發酵的食物,多進行身體鍛煉,盡可能減少壓力,保證睡眠充足。從直接緩解癥狀的角度,醫生可能會針對患者所患腸易激類型和嚴重程度,開具緩解便秘或腹瀉的藥品,或者止疼藥。
從恢復腸道菌群的角度,益生菌療法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從恢復大腦與腸道的正常“溝通”的角度,醫生可能推薦心理健康療法,如認知行為療法,腸道導向的催眠、放松訓練等。此外,針灸、按摩、草藥等傳統醫學療法也可能對部分人有效。
我們的身體是一個很復雜的系統,有時我們并不能完全理解它出現“故障”的原因。通過科學研究,我們能不斷加深對腸腦軸的認知,增加對腸易激病理生理學的理解。或許有一天,這種疾病將不再成為一場場影響患者正常生活的噩夢。
3314500218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