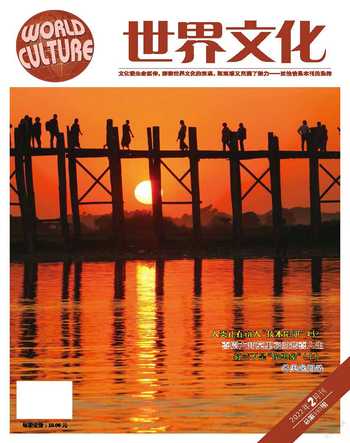《包法利夫人》中的19世紀法國女性服飾時尚
朱一婷 劉麗嫻
法國文化史大家丹尼爾·羅什曾經說過,服飾文化首先是一種秩序,透過服裝語言的嬗變,可以看到道德價值的轉化。小說《包法利夫人》首版發表于1857年,正值以歐仁妮皇后為中心的法國宮廷流行時尚文化的時代。19世紀初期西方社會主流觀點對女性在照顧家庭、培育后代方面有著重要的肯定,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19世紀中葉新興的中產階級崛起,西方女性為了博得男性青睞,紛紛追求時髦的造型,突顯獨特的女性魅力。福樓拜在其小說《包法利夫人》中,透過女性視角去觀察社會,傳達同情、關切、批評、欣賞等復雜的情感態度,這一點在當時男性主導、物欲橫流的社會是極為可貴的。
19世紀40年代,正是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歐確立的時期,法國的資產階級也在“七月革命”后取得了統治地位。而法國是當時西歐的時尚中心,所以法國的文學作品中不乏對浮華奢侈的上流社會生活的各種細節描寫。當時的法國文化界可謂“神仙打架”,巴爾扎克、雨果、司湯達、莫泊桑、福樓拜、左拉等享譽世界的文學巨匠先后活躍于文壇,而福樓拜更是獨樹一幟,他不僅繼承了法國歷史悠久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傳統,更在此基礎上進行反思與創新,形成了一種后來被稱作“自然主義”的新型文學樣式,引領了一個時代的文學創作。
事實上,福樓拜眼中的文學與同時期其他作家的理解有著很大區別,對福樓拜而言,文學是一門科學,他以科學的嚴謹態度從事文學創作,維護文學中的“真”。以《包法利夫人》為例,當同時期的其他作家都在爭相描繪那些美景之時,福樓拜卻在作品中呈現著平淡生活的真實感:
桌上有幾只蒼蠅順著用過的玻璃杯往上爬,滑到杯底浸在喝剩的蘋果酒里,嗡嗡直叫地掙扎。從壁爐里透進來的日光,照得煙炱有如蒙上絲絨那般柔和,冷卻的灰燼也抹上了一層淡幽幽的藍色。

《包法利夫人》描寫了1848年資產階級取得全面勝利后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的社會風貌,小說取材于真人真事——一個鄉村醫生之妻的服毒案。福樓拜的創作用了4年零4個月,每天工作12個小時,正反兩面的草稿紙寫了1800頁,最后定稿不到500頁。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受過貴族化教育的農家女愛瑪的故事。她瞧不起當鄉鎮醫生的丈夫包法利,夢想著傳奇式的愛情。可是她的兩度偷情非但沒有給她帶來幸福,反而使她自己成為高利貸者盤剝的對象。最后她積債如山,走投無路,只好服毒自盡。愛瑪是19世紀法國外省一個富農的女兒,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學過鋼琴,童年時飽讀浪漫派作品,她有過纏綿悱惻、琴瑟和鳴的幻想,但成年后只能嫁給一個平庸、遲鈍、老實的鄉鎮醫生包法利。于是向往浪漫的愛瑪為自己營造了區別于現實環境的理想世界:她不斷沉浸在舞會之行的回憶中,她購買巴黎地圖,訂購潮流雜志報紙,懷著如饑似渴的欲望,幻想自己身處巴黎上流社會……包法利夫人代表著資本主義興起時,對“靈魂”和“自我”有所追求的女人。正如福樓拜在書中寫到的:一切事物都得能讓她有所得益;凡是無法使她的心靈即刻得到滋養的東西,就是沒用的,就是可以置之不顧的。

從176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極大地加速了西方的工業化進程,西方文明得到進一步發展。這一時期,人們對于服裝的認知與審美,也從原先以宮廷貴族們的著裝為效仿對象,逐漸轉移至崇尚個性與實用性上來。
19世紀的歐洲服飾經歷了新古典主義時期、浪漫主義時期、新洛可可時期、巴斯爾時期和“S”形時期幾個主要階段。1804年,拿破侖稱帝后,他本人對于華美的推崇令法國宮廷一度掀起對奢華工藝的追求。此時,高腰身、泡泡袖、直線外形并附有層疊裙擺或藕節裝飾的細長裙裝成為女性服裝主流。緊身胸衣由新式的女性內衣所替代,但仍舊突出了女性的曲線美。而此時的男服則復辟了舊時貴族的風格:奢華繁復的花飾與刺繡布滿整個服裝,外衣背部仿制了燕尾服的流線型。1825年進入服飾的浪漫主義時期,人們精神上對詩意和無憂生活的向往,都體現在服裝上。裙擺逐漸發展成吊鐘形和A字形,蓬松的裙裝與纖細的腰肢形成對比;領口的設計分為極高與極低兩種極端形態,但均附有蕾絲、花邊等鑲飾。此外,如同斗篷般的“曼特”(Manteh)在女性群體中同樣受歡迎。在《包法利夫人》中,經常出現的闊擺裙裝就融合了帝政風格的泡泡袖與浪漫主義時期的X形款式,在突出腰線的同時以色彩的變化來襯托人物性格及其內心情緒。
《包法利夫人》中有大量的裙裝描寫,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主人公的矛盾個性和當時歐洲女性的服飾審美。
19世紀90年代的時尚特質可以精簡地用兩點來概括:一是原本緊身合體的裙子堆砌裝飾大量花邊和褶裥,這種花邊相較于蕾絲花邊顯得粗獷大氣,有一種浮雕效果;二是用機器縫制的、合體緊身的短上衣。
19世紀末期,褶皺被廣泛應用在袖口和底擺上,用錦緞或其他面料堆疊壓褶,厚重而又強調邊緣的弧線,呈現一種浪漫華麗的氣質。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就極為青睞帶有褶皺裝飾的裙裝:
包法利夫人拿起臉盆,把它放到桌子底下去;彎下腰去的當口,她的長裙(一條有四條鑲褶的夏季長裙,黃顏色,腰身較長,裙幅很寬)蓬開攤在身邊的地磚上; ——由于愛瑪彎下去時身子一晃,張開了雙臂,蓬開的裙幅隨著上身的動作,在有些地方癟了下去。
同時,作為19世紀時尚期刊的忠實訂閱者,包法利夫人也對花邊、蕾絲等表現出熱忱。花邊裝飾成為無可替代的“女性氣質”,它的柔媚與性感、單純與可愛散發著難以抵擋的誘惑。在婚紗禮服中花邊也被大量使用,使各階層女性都能圓自己的“公主夢”。
19世紀時,女性服飾對于上半身的收緊效果由內而外彰顯。在《包法利夫人》中有這樣的描寫:
轅馬緩緩而行,因為路面是大塊石板鋪就的,沿途撒滿身穿紅色緊身褡的姑娘拋給你的花束。
這里不難看出19世紀中期法國廣大女性對緊身上衣款式的喜愛。其中提到的 “緊身褡”也常被譯為 “緊身胸衣”,此處的胸衣顯然是可以外露示眾的。我們再對比另一處對包法利夫人晨起時所穿胸衣(即下文所譯襯衣)的描寫:
愛瑪穿一件開胸很低的便袍,前胸的圓翻領間,露出皺裥襯衣上的三粒金紐扣。細細的腰帶墜著挺大的流蘇,纖小的紫紅拖鞋上一綹寬寬的緞帶,覆在足背上。


實際上,這兩類緊身上衣的用處不同:前者是外穿的女式馬甲,起到視覺上收緊上半身的效果;后者是作為身體塑形器的內穿緊身胸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當時的法國社會,具有收緊上身效果的服裝已蔚然成風,顯示了19世紀女性對于 “細腰”身材的推崇。
此外,睡衣作為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開始盛行的服裝,在流行之初只有貴族和上流社會女性才有資格享有。對于熱衷追逐貴族時尚的包法利夫人來說,這樣的穿著也是必不可少的:
愛瑪身穿凸紋細平布罩衫,頸背枕在舊扶手椅靠背上;黃澄澄的墻紙在她身后宛如一道金色的背景……
這里福樓拜為我們展現了睡衣的紋理和樣式,也從側面展現了那個時期女性的優雅精致,她們從頭武裝到每一根腳趾頭,僅僅睡衣就分為晨衣、睡裙和睡袍三種。
在19世紀,紫色和黑色幾乎是男性服飾的專屬色彩,代表著沉穩、莊重,是在政府工作以及出席社交場合的男性的首選色彩。事實上,顏色的選擇也具有強烈的政治含義,比如貴族們樂于以炫目色彩強調自己的特權地位,從而與新興的資產階級劃分界限。為彰顯包法利夫人身上叛逆不羈的特質,也體現其對于自我價值的追尋和個性的放逐,福樓拜為包法利夫人所選的長裙色彩也是趨于男性化的紫與黑:
萊昂在屋里踱著步;瞧著這么位漂亮夫人待在這寒磣的小屋里,他似乎覺著不對勁兒。
黑色長裙的下擺,扇子也似的攤了開來,使她顯得更加苗條而修長。

無論是紫色還是黑色,均與當時突顯女性嬌俏特質的粉色、白色等顯得格格不入。正因如此,我們得以從中窺見19世紀對于服飾及其色彩選擇的包容與接納,男性化的著裝標準逐漸為女性世界所接受。引用法國文化史家佩羅的觀點:色彩的消失意味著由新倫理道德所決定的新審美趣味的出現,這種倫理道德表彰退隱、節儉以及貢獻。男性選擇鮮艷度較低的色彩是為了將自身更明確地與女性相區別,通過服裝上的差異,樹立自身性別的肅穆與莊嚴;而女性在19世紀也逐漸接納了標志著肅穆與莊嚴的色彩,這從側面揭示了動蕩時局中女性對于自身從屬地位的逐漸覺醒,寓意著暗流涌動的時代格局與先鋒精神。
自人類發明鞋子起,其使用價值就與男女性別的分工定位以及社會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19世紀女性對男性和家庭的依附仍然是主流,與此相適應,女性鞋履的顏色、材質和樣式,無一不體現其柔弱與居家特質。比如,女性對于絲綢、緞面等具有柔軟質感和淑女氣質的材質十分青睞,體現在顏色上則是對粉色、白色的追捧:
她梳著辮子,穿著雪白的長裙和開口薄呢軟鞋,模樣是那么可人,等她回到座位上,男賓們紛紛俯身過來祝賀她。
材質柔軟、顏色柔和的鞋履,實際上反映的都是19世紀法國女性在社會中扮演的從屬角色。從當時女鞋的款式及其附帶的飾物中,我們也可以對當時主流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會角色略知一二。19世紀女性多喜愛穿女靴和平底鞋,且多為居家場合穿著,因此往往綴以蕾絲、綢帶等裝飾,除美觀外更突顯了女性的溫柔顧家。《包法利夫人》中,福樓拜在描述一些精致的小飾物時,總會突顯它超出物品本身的魅力:
這雙粉紅緞面的拖鞋,用天鵝絨毛緄著邊。她坐在他膝上,腳夠不到地,只能懸在半空;這時那雙小巧玲瓏、鞋跟不包革的拖鞋,就單靠光腳的腳趾點著。
這雙拖鞋在“緞面”“天鵝絨毛”“不包革”的多重強調下變得尤為玲瓏柔美,盡顯愛瑪溫柔嬌弱的女性特質,而這正與當時法國社會主流觀念所頌揚的女性義務完美契合。主要負責照顧家庭的女性,既要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行動能力,又要懂得依附并取悅于家中的男性,基于此,強調實用性的鞋子會在款式和配飾上大做文章,體現其特殊的審美性和時代意義。
與精美的居家型鞋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因生活境況而不得不從事生產勞動的女性所穿的鞋履,這類鞋履多取黑色且材質更加耐用。有趣的是,《包法利夫人》中多個社交場合為我們呈現了愛瑪夸張奢侈的穿著和樣式多變的鞋履,盡顯其高貴優雅;但作為“鄉舍貴婦”,包法利夫人的“農婦”形象也在幾處家庭生活場景中得到展現:
她從膝蓋處起雙手拎起長裙,正好露出足踝,然后抬起一只穿著高幫黑皮鞋的腳,從緩緩翻轉的烤羊腿上面伸向爐火。
透過中性化的硬朗的“黑皮鞋”,小說從側面表現出包法利夫人不得不適應環境、從事一定勞動的身份局限性。鞋履的強烈反差,不僅增強了包法利夫人形象的真實性和飽滿度,為其游離在兩種生活與追求之間,因產生強烈的內心矛盾而導致悲劇命運埋下伏筆,同時也充分展現了不同階級的女性的穿著風尚。
在《包法利夫人》中,帽子、圍巾、遮陽傘等彰顯包法利夫人品位的配飾細節有很多,其中帽子作為重要的時尚配飾,貫穿于女性的各個生活場景中。例如,小說前半部分寫包法利先生在經歷第一段婚姻時其前妻所戴的帽飾,與甜蜜美好的婚姻狀態相對應,其帽飾偏于溫柔、恬靜的風格:
她一只胳膊摟緊他,另一只胳膊挎著籃筐,戴著本地傳統的帽飾,長長的花邊隨風飄舞,有時拂到他的嘴上,他回過頭去,望見她那張紅撲撲的小臉蛋偎依著他的肩膀,在金色帽檐下悄沒聲兒地笑著。
花邊帽盡顯居家女性的恬靜與溫柔,也為這段婚姻平添了一絲浪漫氣息;這種浪漫特質在包法利先生后來再次開啟與愛瑪的新婚生活中也延續下來,從包法利先生的觀察中我們得以對新娘子愛瑪的狀態一窺究竟:
她戴著頂橢圓形女帽,白色的系帶宛似蘆葦的葉片,整張臉的側影在明艷的陽光中勾勒得很分明。
除去絲帶,面紗也是帽子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當時帽子的款式之多樣:
透過從男式帽檐斜垂到腰間的面紗,只見她臉上蕩漾著藍瑩瑩的光影,仿佛在蔚藍色的水波中游動似的。
帽子作為配飾,在小說中極佳地呼應了家庭女性所展現的女性氣質。
而當包法利夫人經歷過生育、情人離去、借貸等多樁事件后,粉色、白色以及絲綢、緞帶等配飾帶給她的浪漫唯美氣質已經不甚適用,這時作家福樓拜也對其帽飾進行了適當更換,選取女性身處更加莊重、正式的社交場合時精妙搭配的帽飾。比如在化裝舞會上,包法利夫人的裝扮是這樣的:
四旬齋狂歡節那天,她沒返回永鎮,當晚去了化裝舞會。她身穿天鵝絨的長褲,鮮紅的長襪,假發在頸后扎著根緞帶,三角帽斜扣在一側的耳朵上。
而當包法利夫人前往借貸處與借貸人周旋,也就是一步步邁向黑暗的生命漩渦時,作品描述道:
她立即更衣,穿上黑色長裙,佩戴飾有烏黑發亮珠子的系帶女帽;她不想讓人瞧見(廣場上仍然有很多人),就取道鎮外,沿河邊小路而行。
事實上,除了包法利夫人,我們從尋常女性的服飾穿戴上也可看出,19世紀中期帽飾已然在法國女性中形成風尚。比如下面這個尋常的生活場景:
女客們頭戴軟帽,身穿城里款式的長裙,掛著金表鏈,短披肩的下擺掖在腰間,或者披塊花方巾,背后用別針別住,露出后面的頸脖。
軟帽從中世紀延續至今,大多為女性使用。女性們喜愛戴著裝飾有精致褶邊的絲質軟帽,出入于各種公共場合。帽子在裝飾上用了很多精美的蕾絲和緞帶,帽身用透氣的面料和蕾絲線鉤織出貼合的形狀。當軟帽發展至有帽舌后,帽舌的前部開始延伸,包覆住前額、下頜和臉頰兩側。
19世紀初,法國社會主流觀念頌揚女性溫柔賢惠的品質,賦予她們家庭內部的職責,將她們放置在依附于男性的社會角色上。這些觀念反映在服裝上,便是那些能夠鮮明體現女性性別特征的元素更為盛行,暗示著女性處于取悅男性的較低社會地位;夸張累贅、令人行動不便的裝飾同樣顯示著上流社會女性不事生產的閑暇生活狀態。無論是材質、色彩和款式,所有的服裝要素都是為了突顯女性外形上的特征,強調其性格中溫柔、感性、嬌弱的一面。因此,公共事務與家庭事務之間的區分導致了兩性在外觀裝束上的分道揚鑣。換言之,正是新的統治階級的道德價值觀以及由其決定的性別角色地位,導致了兩性服飾從此時開始向著不同方向發展。
19世紀的服裝時尚風格經歷了較多轉變,反映在色彩、款式和穿著的舒適度上。女性服飾的款式變化多端,令人眼花繚亂:袖子忽長忽短,時寬時緊;領口有時高到抵著下巴,有時又低到袒露出雙肩;尤其是浪漫主義時期,女裝開始流行膨大的袖子,這種仿佛鼓滿了空氣的袖子與整體看起來非常不協調,但卻恰好突顯出女性腰部的纖細。縱觀整個19世紀的西方女裝,不乏戲劇性和過度奢華的特點,女性時尚也大多詮釋了資產階級和有閑階級追求時髦、奢侈的生活方式。但處在變革的時代背景下,當時的時尚也體現出一種既傳統又變革的雜糅意味。因此在時尚領域,可以把當時女性服飾的時代精神概括為:傳統而先鋒,包容又界限分明。
通過福樓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對女性服飾的細致描寫,我們不僅可以看到19世紀經歷了工業革命的法國女性的精神風貌及其穿著風尚,更能夠一窺當時女性的生存狀態和社會角色仍舊是從屬、依附于男性,其服裝、配飾的用色與款式多是為了取悅男性,對高端的衣著追求實則體現了女性對主流價值觀的附和,以及對社會地位、社會權力的追求。
本文為浙江理工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19世紀西方時尚研究(項目編號:2020Q082)。
1460501705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