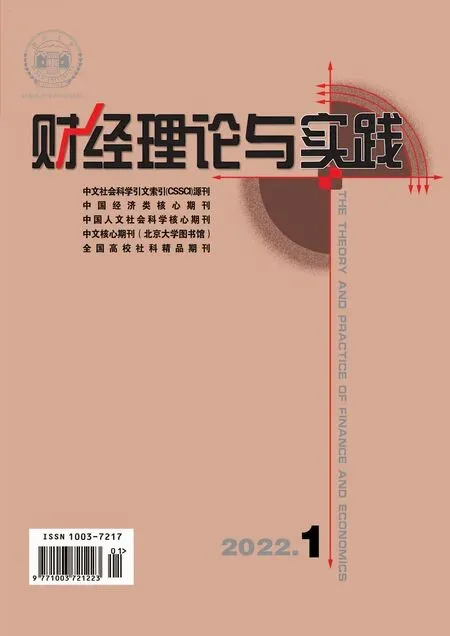授信風險視角下鄉鎮企業融資困境及其法律對策
作者簡介: 孟大淇(1992—),男,安徽亳州人,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借貸法律制度。
摘 要:對鄉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可以結合我國現有法律有關規定,通過在合同中約定鄉鎮企業具體的資金用途、約定貸款人在危機時刻擺脫合同的終止權、引入授權額度框架協議、完善農村土地抵押流轉的制度規范以及通過立法和政策的共同努力構建鄉村系統信用等方式,有針對性地提高鄉鎮企業的融資能力,促進鄉村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
關鍵詞: 鄉村振興;《民法典》;借款協議;授信風險;信任體系
中圖分類號:F832.4;F27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22)01-0139-07
近年來,隨著我國鄉村振興政策的不斷深入,鄉鎮企業規模及其產量也在逐年增長。而鄉鎮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常常會因技術缺乏、人才流失等競爭劣勢,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基于此,許多鄉鎮企業面臨著融資難的問題,而資金困境進一步使得企業陷入惡性循環之中。本文將從民事合同風險防控的視角,系統分析鄉鎮企業在融資過程中,貸款方所面臨授信風險的具體要素構成,并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簡稱《民法典》)的相關規則提出針對性解決建議。
一、我國鄉鎮企業融資風險研究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現有的相關文獻廣泛關注鄉鎮企業的融資困境,并積極探索解決鄉鎮企業融資難的路徑。學者們普遍認為,鄉鎮企業陷入融資困境主要由于:一方面,鄉鎮企業規模小、科技含量低等因素造成競爭力不足,且融資模式多為傳統的銀行借貸或民間借貸,融資模式單一[1]。另一方面,銀行融資門檻較高,且由于鄉鎮企業存在規模較小、缺乏必要的擔保、財務管理不規范等問題,銀行很難批準對中小型鄉鎮企業的融資貸款[2]。此外,政策層面缺乏對鄉鎮企業的貸款扶持,進一步加劇了鄉鎮企業的融資困難。學者們提出了克服上述融資困難的路徑:首先,在企業層面,鄉鎮企業應當加強管理,規范企業財務制度。其次,在商業銀行層面,應當大力發展多元化融資模式,擴大基層銀行的審批權限,拓展融資服務。最后,在政策扶持層面,應加大對涉及民生利益的鄉鎮企業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完善擔保機構制度體系等[3,4]。
上述研究雖然指出了中小型鄉鎮企業融資的困境及其解決之道,但上述對策建議過于寬泛,涉及到政策風險、法律風險、會計風險、管理風險等諸多方面,故而在實踐中欠缺可操作性。事實上,任何抽象的理論均是基于對具體實踐的總結。在鄉鎮企業融資的實踐中,貸款人在放款之前無論從哪些方面對風險控制作出安排,其所面臨的最直接風險就是鄉鎮企業不能或者不愿償還借款資金的風險,也即鄉鎮企業不能按約履行合同的風險。從獨立的鄉鎮企業融資過程來看,上述文獻分析未能全面系統研究貸借雙方的合同風險,對策建議并未體系化分析在何種法律風險環節上進行控制。故而,本文以《民法典》為背景,通過對貸款人的授信風險進行分析,歸納風險構成的核心要素,并在具體要素基礎上結合《民法典》的相關規則提出對策。
二、授信風險視角下鄉鎮企業融資困境成因分析
鄉鎮企業借貸融資本質上是貸款人向鄉鎮企業授予信賴的過程。在具體的貸款審批案例中,貸款人基于對鄉鎮企業資產和信用的審核而達到下列信賴:鄉鎮企業在一定期限之后有能力且有意愿償還借款資金。授信風險在此也可以解釋為鄉鎮企業不能以及不愿支付借款本息的風險。這也是貸款人所實施的授信行為中“信”的核心內容。我國相關法律對紛繁復雜的信貸授信問題關注較少,與其他民商分離的大陸法系國家通過《商法典》對授信風險進行調整不同,鑒于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集中對《民法典》中借款合同及其相關的擔保規范部分關于授信風險進行分析探討。鄉鎮企業融資過程中最為直接的授信風險為借款合同的履行風險,貸款人的合同風險始于貸款人放款之時,這是由借貸合同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
(一)貸款人實施授信行為面臨的典型合同風險
典型的借款合同授信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借款關系與其他轉移使用合同關系不同,貸款人必須將資金轉移給借款人供其自由處分,貸款人一旦完成放款,則喪失對資金的所有權,而對這筆資金的控制只能停留在約定期限屆滿之后要求借款人償還的償還請求權。貸款人喪失對借款資金物權的控制而僅僅剩余債權請求權,顯然易于遭受資金不能收回的風險。而其他移轉使用合同,例如租賃,出租人將租物移交給承租人之后,仍然保持對出租物的所有權,同時擁有物權和債權的控制。故而,借款合同具有獨特的風險范疇。第二,貸款人履行義務是一項持續給付的過程。貸款人完成放款并非完全履行其義務,貸款人的義務還包括在約定期限內容忍借款人使用借款資金的義務,時間的因素對貸款人容忍給付義務的范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給付范圍隨著時間的延長而擴大,否則無法解釋利息隨資金使用時間的增加而增多。這種持續性債務關系依賴于他人良好的意愿以及保持和諧的關系[5]。同時這種長期性以及給付范圍的不確定性也增加了借款風險。第三,金錢之債本身的特點也會產生特殊的風險。貸款人負擔先行支付借款資金的義務,在一定期限之后,借款人償還的資金僅為名義價值,而非具有相同購買力的實際價值[6]。在當今實踐中,貸款人往往會面臨著購買力下降的風險。由于貸款人放款之后面臨上述風險,貸款人只能通過自身的評價體系來衡量風險是否處于可控的狀態。只有當貸款人信賴借款人到期能夠并且愿意償還借款資金時,方可實施授信行為。
(二)平衡授信風險的要素
雖然借款融資的授信風險本身根植于典型借款合同的結構之中,但當事人可以通過特定的方式來控制或者平衡授信風險,這主要涉及以下要素:
首先,信用風險控制要素。一方面,借款人信用程度具有決定性意義。借款人的信用程度越高,則意味著借款人更有能力且愿意在期限屆滿之后償還借款資金。此時,貸款人風險程度更低,實施授信行為也即放款的可能性越高。另一方面,擔保可以彌補人格信用具有的主觀性的不足,借款人若能夠提供足額的擔保,尤其是不動產擔保,貸款資金的安全性則較高,借款人獲取資金的可能性就越大。
其次,借貸協議控制要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信貸資金的額度。借款資金的額度越高,貸款人放貸的風險越大,貸款批準則更為困難。第二,借款期限。借款期限越長,借款人財產狀況以及還款意愿發生較大變故的可能性越大,借款風險也隨之增高。第三,借款資金的用途。若在借款合同中未約定借款資金的用途,任由借款人處置,則貸款人會面臨較高的風險。相反,貸款人可以通過在合同中約定借款用途的方式來控制預期風險。第四,貸款人是否具有終止借款合同的可能性。若在合同中約定,在擔保物價值貶損或借款人有陷入不能償還之虞時,貸款人可終止借款關系,則貸款風險置于可控的范圍之內,此時貸款人更樂意放款。
再次,費用平衡要素。若借款人信用程度不高,且希望獲得預期的借款資金使用,則只能以支付高額的資金使用費為對價。若借款人愿意支付更高的融資費用,收益與風險相一致,貸款人也愿意承擔更高的風險。
最后,借款人對貸款人的依賴性要素。這種情況尤其發生在特定政策性貸款,或者長期的工程融資合作中。
上述要素均對借款關系中貸款人的風險發生著動態作用,在融資實踐中需要對上述要素整體衡量把握。
(三)鄉鎮企業在平衡授信風險要素方面的不足
對鄉鎮企業融資困境的成因分析,同樣也需要以上述特殊借款合同風險為視角。鄉鎮企業欲獲得融資資金,需要與貸款方簽訂借款合同,但借款合同本身的特殊風險要求貸款方首先需要對鄉鎮企業的相關要素進行審核判斷。
首先,一方面鄉鎮企業的信譽不足。鄉鎮企業經營規模較小、注冊資本少、技術落后,且管理不規范、財務混亂,造成鄉鎮企業無法獲得貸款方的信賴[7]。另一方面鄉鎮企業擔保不足。在融資實踐中,銀行往往需要企業的不動產或者汽車等作為抵押方可貸款。而鄉鎮企業并無太多固定資產,一些企業廠房為臨時租賃,且農村土地產權流轉存在限制。上述問題直接導致鄉鎮企業無法提供穩定足額的擔保。
其次,信貸資金的額度和使用期限需根據企業具體發展目標來確定。通常情況下,鄉鎮企業資金需求額度雖然不高,且使用周期較短,但在實踐中融資頻率較高,往往很難獲得足夠資金支持。此外,除銀行信貸之外,其他融資模式較少約定融資用途,即使有約定,往往也比較籠統。例如:將借款資金用于企業經營,缺乏具體使用明細,不利于約束鄉鎮企業對借款資金的使用。另“終止權”約定往往基于銀行的格式合同條款,但在終止權行使時,需要受到誠實信用等原則的約束。
再次,正是由于上述要素的缺乏,鄉鎮企業融資成本往往較高,只有支付較高的對價才能換取融資資金。但鄉鎮企業本身的盈利能力不足,以高額的費用換取融資資金無異于飲鴆止渴,經營易陷入惡性循環之中,不能持續穩定發展。
最后,鄉鎮企業分布范圍廣泛,多數鄉鎮企業面臨著政策扶持不足,且許多并非長期投資項目,故與貸款人之間并無依賴關系。
綜上所述,鄉鎮企業在融資過程中,難以讓貸款人對其償還能力以及償還意愿產生信賴。由于借款合同本身具有極強的風險性特征,而這種授信風險鄉鎮企業無法通過其他方式予以降低或平衡,故而在實踐中鄉鎮企業經常陷入融資困境之中。
三、《民法典》背景下授信風險控制的應對機制
要采取針對性的策略,同樣需要從影響授信風險高低的要素著手。其中部分要素鄉鎮企業無法加以控制,例如:借款資金的額度以及資金使用時間,往往需要根據企業經營計劃予以安排。鄉鎮企業由于缺乏金融支持以及自身缺陷,難以與貸款人建立固定的依賴關系。而如上文所述,以高融資成本為代價獲取資金的方式也并不可取。故而,以《民法典》規范為視角,從提高鄉鎮企業擔保能力、完善借款合同的風險控制要素、完善鄉村信用體系幾個方面來控制授信風險。
(一)以《民法典》規定的土地經營權為契機,增強農村不動產的擔保增信能力
《民法典》第386條的規定為擔保物權優先受償權提供了法律保障。擔保權利人能夠就擔保物權行使優先受償權,在借貸的法律實踐中,尤其是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往往需要借款人提供足額的擔保物才會放款。鄉鎮企業在融資過程中,無論是以企業還是企業主的名義進行融資,能夠提供最為核心的不動產通常為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而在法律層面,提供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作為擔保物,面臨著諸多不確定的問題。
根據原《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簡稱《物權法》)第184條第2項的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禁止作為抵押財產。該規定極大限制了農村土地的價值,不符合農村經營模式新的發展需要。基于此,2016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了《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提出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的制度模式,以盤活農村土地,更好、更快促進城鄉經濟一體化發展。此后,新修訂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先行在立法上明確承包人可以將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向金融機構融資擔保。《民法典》物權編雖然在抵押財產范圍的規范體例上與《物權法》具有相似之處,均采用正面列舉以及反面禁止的規范方法,但《民法典》第399條的規定刪除了《物權法》第184條第2項的禁止性規定。同時,根據《民法典》第395條兜底條款的規范思想,土地經營權并不屬于法律以及行政法規禁止抵押的財產。
《民法典》的此次關于農村土地規則修改對鄉鎮企業融資的意義還體現在,進一步明確了承包地土地經營權的物權屬性。在以承包地土地經營權抵押融資試點過程中,一些地區出現將土地經營權進行融資的模式難以推廣的情況,有學者在實證研究基礎上總結出導致上述問題的直接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土地租金不是一次性付清,導致土地經營權沒有抵押價值;二是出現違約時,一年一付租金所獲得的土地經營權不能作為抵押品進行處置[8]。在實踐中出現推廣困難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物權性質的承包地土地經營權和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所獲取的收益。舉例來說,房屋本身具有的物權的權能,能夠作為抵押物融資貸款,而將房屋在一定期限內予以出租所獲取的收益則是債權性權利,同樣可以在借款過程中將其作為擔保。即使在“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兩權分置的時代,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用益物權的一種,同樣可以從中分離出具有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之權能。而《民法典》在物權編部分規定土地經營權,顯然是希望建立一項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相平行的用益物權架構,只有作物權流轉性質的安排,方能凸顯出農村土地之價值。
《民法典》的相關規定雖然明確了“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的法律結構,然而這種“一個所有權、兩個用益物權”并行的結構本身存在諸多不明確的內容。《民法典》第339-342條關于土地經營權的規定為原則性的或者說為框架性的,僅選擇設定對于土地經營權制度確立具有關鍵作用的有限規定,而不進行具體規則的展開[9]。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并不存在這種三層次的物權制度,認為這種疊床架屋的構造有違一物一權原則[10]。該制度與英美法系中的財產制度也不相同。故而,這種三層疊加的物權權利模式是在我國國情之下特有的制度產物,流轉層面土地經營權的具體內容尚不明確,需要留給實踐繼續發展探索。因此,土地經營權在融資過程中如何承擔擔保的功能,尚需進一步予以發展完善。此外,《民法典》僅規定了農村承包地的土地經營權,而在許多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村宅基地及附屬其上的建筑物同樣具有較大的價值,亦可以作為融資擔保的抵押物。如何在制度層面上進行設計,以促進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市場流轉,也是現階段農村金融從制度構建到具體實踐中需要解決的難題。
(二)借助《民法典》規范降低借貸協議履行風險
在鄉鎮企業融資過程中,由于信息渠道的不通暢以及資信狀況的限制,實踐中存在許多民間融資或者向小型金融機構融資的情形。基于農村法律意識相對淡薄,加之鄉村熟人社會的影響,在上述融資過程中,當事人之間的合同往往會存在一些約定不明或者沒有約定的情形。《民法典》對此提供了諸多的補充性規范。例如:在當事人未約定借款期限時,且當事人又不能通過事后補充協議的方式確定借款資金的使用期限時,應當允許當事人以妥當的方式擺脫借款合同的束縛。根據《民法典》第675條的規定,此時借款人可以無需貸款人同意隨時償還借款,貸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在一定的合理期限經過之后償還借款。除此之外,熟人社會之間的借款對利息的約定可能并不明確或者根本沒有約定,此時《民法典》第680條第2款和第3款的規則可以填補該合同的漏洞。
《民法典》第680條第1款禁止高利借貸的規定,具有保護鄉鎮企業的功能,防止鄉鎮企業陷入高息借貸的惡性循環之中。鄉鎮企業在降低借款合同風險要素方面存在較多的不足,貸款人向鄉鎮企業放款會面臨較大風險。鄉鎮企業在缺乏控制風險要素能力的情況下,根據風險與收益相對應的原則,要獲得借款資金的使用只能以支付更高的資金價格為代價。而正規融資渠道往往對利息上限予以明確規定,加之農村金融資源的匱乏,這為鄉鎮企業高利借貸提供滋生的土壤。
銀行信貸資源之所以不愿意進入鄉鎮企業,很大原因在于農村領域貸后風險管理難度較大。雖然《民法典》第672條規定了貸款人對資金使用的檢查、監督權,但由于鄉鎮企業的管理模式不完善以及熟人社會的影響,貸款人對鄉鎮企業檢查、監督的成本較高。然而,當事人可以通過將監督、檢查的內容以當事人意思表示的方式直接在借款合同中予以約定。根據《民法典》第672條規定,貸款人可以要求鄉鎮企業按照約定的方式和內容,定期提供企業相關財務會計報表或者其他相關資料。此時鄉鎮企業按照約定內容提供審核所需資料已經轉變為借款合同的義務,違反該項義務的鄉鎮企業應當承擔違約責任。通過該方式來實施銀行的檢查、監督權,一方面可以降低貸款人檢查的工作量;另一方面還可以督促鄉鎮企業如實提供企業相關資料。
雖然《民法典》制定了諸多預防借款合同風險的規范,但合同風險控制主要還是基于當事人對合同內容的約定。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商業環境的復雜性以及人的優先理性,人們不可能完全將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寫入合同之中,此即不完全契約理論。借款合同的風險雖然同樣受到不完全契約理論影響[11],但在實踐中仍可以將控制合同風險的典型要素予以明確約定,盡最大可能控制合同風險。合同約定主要包括:
1.約定借款資金的具體用途。
在鄉鎮企業融資實踐中,貸款人通過約定資金借款用途的方式,可以將資金使用限制在風險可控的范圍內。這種風險控制方式不僅成本低,而且法律保障方面也極為全面。正是由于上述優勢,在大型銀行提供的融資借貸協議中,一般會將資金用途予以約定,但有些合同雖然提及資金用途,但約定內容并不具體明確,也會影響相關法律約束規則的適用。故而,在鄉鎮企業融資合同中,應當明確約定具體的資金用途,例如:可以約定所借用的資金用于某項技術開發、原材料的購買、企業廠房的修繕等,不宜籠統約定借款資金用于企業經營。
《民法典》中的相關規范,為鄉鎮企業融資的貸款人提供一套“事前—事后”的完整保護體系。貸款人在鄉鎮企業違反資金用途使用之前進行控制,是實現融資用途效果所必須的、基本的法律保障。如果貸款人不存在此種方式的控制,則喪失鄉鎮企業對借款金額使用的直接約束,貸款人只能基于違約進行救濟。在事前控制領域,一方面,貸款人有對鄉鎮企業資金使用的檢查、監督權。《民法典》第672條第1款規定了貸款人的檢查、監督權。貸款人對借款人資金使用狀況的檢查、監督是由借款關系的繼續性以及當事人受信關系特點所決定的[12,13]。另一方面,貸款人具有要求鄉鎮企業依據用途使用資金的履行請求權。借款發放之后,鄉鎮企業在約定期限或合理的期間內未按照借款用途使用借款,應當賦予貸款人履行請求權,以督促鄉鎮企業繼續按照約定用途履約。《民法典》雖未對此種情況下貸款人履行請求權直接作出規定,但約定用途作為合同內容,貸款人的履行請求權的法律基礎為《民法典》第577條當事人應按約履行之規定。
《民法典》直接規定了貸款人在鄉鎮企業未按照約定使用借款之后的救濟性權利。《民法典》第673條規定借款人未按照約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法律后果,即貸款人可以停止發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此外,貸款人還可以行使代位請求權。如果鄉鎮企業已經將借款實際挪作他用,則貸款人除上述的救濟權利外,在通常情況下亦可以要求鄉鎮企業移交該項資金因違反使用用途而獲得的財物或者法律地位,即代位利益。應當讓鄉鎮企業意識到,無論其如何違反目的使用借款資金,所獲得的利益并不能允許其持有,使其違約的投資沒有意義。這種結果可強化鄉鎮企業和貸款人之間的信賴關系,降低貸款人先支付時所承擔的風險[14]。
2.約定貸款人的終止權。
融資借款協議作為繼續性債權,終止權的約定可以使當事人擺脫合同義務的束縛。在鄉鎮企業融資實踐中,由于鄉鎮企業大多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市場中并不具有競爭優勢,因此,鄉鎮企業未來可能遭受市場風險導致財產狀況惡化,從而出現資不抵債的情形。正是基于對借款合同約定期限內出現上述風險的擔憂,許多融資機構并不愿意向鄉鎮企業放款。而在融資協議中約定“終止條款”則可以排除上述風險,貸款人在鄉鎮企業出現資不抵債或者存在嚴重資不抵債風險時,有排除合同束縛的權利,能夠及時止損。
在借款當事人未約定貸款期限,且當事人又不能就借款資金的使用期限達成協議時,借款合同作為以信賴關系為基礎的繼續性合同關系,應當允許當事人在信賴基礎不存在的情況下擁有擺脫借款合同約束的權利。基于此,《民法典》第675條規定當事人在未約定借款期限時的一般終止權。在當事人約定了貸款期限,在貸款人對鄉鎮企業的信賴基礎破裂時,同樣也需要賦予其擺脫合同束縛的權利。在許多外國立法條例中對此直接進行了規定,例如《德國民法典》第490條第1款賦予了貸款人在“借款人的財產狀況……,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重大毀損,使得貸款的償還……受到危害”的情形下,具有終止借款合同的權利。我國《民法典》雖然未對此作出直接規定,但在簽訂融資協議過程中,如果當事人可以通過約定,允許貸款人在出現上述危機時終止借款合同,則鄉鎮企業更容易從貸款人處獲取資金。
3.授信額度框架協議的引入。
鄉鎮企業融資有其獨特性:融資數額小、周期短,但融資頻率高。在這種情況下,若每次的融資均需簽訂獨立的協議,則一方面,貸款人在鄉鎮企業每次申請貸款的情況下,均需對鄉鎮企業資信狀況以及其他風險要素進行審核,而短期內這些要素并不會發生較大變化,貸款人徒增無益的審核成本,而增加的成本勢必轉由鄉鎮企業來承擔,加重鄉鎮企業負擔。另一方面,在每次均需要簽訂獨立協議的情況下,鄉鎮企業也可能面臨著貸款人審批不通過不予放款的風險,從而破壞鄉鎮企業的資金安排,影響其進一步發展。
通過簽訂授信額度框架協議的方式,可以克服傳統融資模式中“一貸一簽”在鄉鎮企業融資過程中存在的缺陷。授信額度框架協議是指,貸款人作出在借款人特定條件下、一定額度范圍內提出申請借款時支付借款承諾的協議[15]。我國《民法典》雖然未對授信額度框架協議作出直接規定,但《民法典》合同編部分的相關規則可以作為授信額度框架協議的規范基礎。通常情況下,授權額度框架協議本身已經包含貸款人支付貸款的義務[16]。但其給付的內容并不具體確定,需要由鄉鎮企業申請提款,將給付內容予以具體化。因此,在授權額度框架協議中,鄉鎮企業存在一項申請提款權,該權利性質上為一項形成權,即通過單方權利的行使,可以確定貸款人具體放款的數額。
授信額度框架協議是銀行實踐的產物,在銀行貸款領域的應用較為廣泛,對于擁有較好資信狀況的長期客戶,銀行通過與客戶簽訂授信額度框架協議,一方面可以提高對鄉鎮企業貸款審核的效率,大大節約放款的成本;另一方面,鄉鎮企業也可以對銀行貸款資金數額存在穩定的預期,有助于銀行與優質鄉鎮企業保持長期的合作關系[17]。互聯網金融雖然是一種新興金融模式,但仍然以傳統金融為基礎,網絡貸款領域也存在大量的授信額度框架協議,尤其是在貸款人為中小型銀行或銀行關聯小額貸款公司的情形中極為常見。故而,授信額度框架協議能夠較好地適應鄉鎮企業融資需求,可在相關領域廣泛推廣。
(三)以《民法典》為背景促進鄉村系統信任建設
鄉鎮企業融資難最為核心的原因在于信譽低下,長遠來看,提高鄉村信用水平方為解決鄉鎮企業融資難的根本之道。
中國傳統社會以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世世代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基于這種幾千年來安土重遷的農業經濟文化,產生了獨特的熟人社會關系網。在中國傳統鄉村,許多鄰里和鄉親幾代之前很可能是從同一個家族或同一個祖先那里分離出來的,因此熟人關系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擬親屬網絡。相較于其他社會或市場網絡,共同體中的網絡是相對封閉而持久的[18]。傳統社會成員之間彼此熟悉,此時信任并不需要締約和法律,違背集體社會內部的信任意味著對該社會系統的冒犯。從熟人社會中產生的信任更多地體現于人與人的關系,而非人與制度的關系。在這一層意義上,信用一般也被認為是君子的口頭協定及人格擔保[18]。
當今社會為經濟的高度分化導致傳統小農經濟基礎瓦解,中國鄉土社會的結構也處于轉型階段,傳統熟人社會的人格擔保信任體系土崩瓦解,而系統性的社會信任模式尚未完全滲透到鄉村。從熟人社會到陌生社會,并不意味著信任體系的崩潰。相反,高度分化的復雜社會比傳統社會需要更多的信任,以簡化其復雜性,同時也需要創立多樣且穩定的社會信任機制[19]。否則,人們時時刻刻會陷入對身邊相關事務“無法控制”的恐懼。例如,不再相信出租車司機能夠安全將顧客送到目的地,不再相信基金投資資金能夠很好地被專業人士管理等。缺乏信賴的社會經濟體系完全無法正常運轉。信賴制度的本意在于減少人們對上述“無法控制”的恐懼。與傳統社會的中的人格信任與人情擔保不同,系統性信任必需以制度構建為基礎,也即需要以制度為擔保[19]。《民法典》在構建社會系統性信任方面是關鍵性的制度創建,可以起到社會信任倍增器的作用[20]。
以借款相關的規范為例,《民法典》構建系統信任首先表現在合同履行的保障方面。貸借雙方將自身的需求安排在合同中:貸款人希望通過放棄一定期間內的資金使用而獲取相應的報酬或者幫助他人走出困境,并預期在期限屆滿后借款人能夠償還借款本息。鄉鎮企業則希望通過借款合同安排以獲取資金的使用。貸借雙方均可基于合同得到《民法典》的法律保障,進而實現預期利益,鄉鎮企業可因信守合同獲得更多交易機會,進而相信遵守承諾既有道德價值亦有經濟價值。
然而,合同特點在于個體的逐利性,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本質上帶有自私的基因。社會信用的構建并不能僅僅建立在合同保護的層面,在追逐個人利益的同時,良好社會信用的建立還需要受信人承認、尊重并實現他人的利益,即“無私”的利他要求。對此,《民法典》以誠實信用原則為基礎,對借款合同的保護有別于一般合同規則的調整。例如:根據《民法典》第669條規定,訂立借款合同時,鄉鎮企業應當按照貸款人的要求,提供與借款相關的業務活動情況和真實的財務狀況。該規定的目的在于防止借款人提供虛假材料、對貸款人實施欺詐行為。信賴往往與欺詐共存,這在借款關系中表現得極為典型。在具有特殊信賴關系的情形中,沉默行為本身也可以構成欺詐。因此,基于當事人信賴而導致披露義務的提升,是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滲透于民法的各個領域[21]。以信賴為基礎的借款關系,同樣擴大了借款人的信息披露義務,對借款資金償還與否有重要影響的事項均屬于披露義務的范疇,此時借款人沉默即構成欺詐。《民法典》為加強對熟人社會之間的信賴保護,在第679條規定了自然人之間借貸的要物性規則,只有貸款人實際放款時,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才成立,借款人并不能基于貸款人單純的允諾要求其支付借款。《民法典》第679條的立法理由認為:“自然人之間往往為親朋之間數額有限、內容簡單的借款,多為無償的互助行為,且并不需要復雜的程序,對合同的形式也不太在意,往往是一手交錢、一手寫借條,應結合實際考慮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不宜給貸款人賦予過重的責任。”[22]由此可見,本條立法目的在于通過對互助行為提供更高層次的法律保障,從而進一步構建熟人社會之間的信用體系。除此之外,《民法典》中關于借款原則應當為要式合同的規定以及理論上關于支付借款請求權強制執行的限制[6]等特殊規則,均對加強鄉村信用體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但《民法典》對鄉村系統信用建設仍有其局限性。一方面,作為傳統大陸法系國家,《民法典》的規范基礎原則上仍然是以個人理性為指引,鼓勵人們通過個人意思來安排自己的事務,追求自身利益并承擔相應的風險。而對當事人更高要求的利他性信賴原理并非《民法典》的規則基礎。因此,《民法典》缺乏信賴原理的一般性規范。雖然《民法典》中存在誠實信用原則,其內涵要求當事人恪守承諾,但其只是規定了社會信用的底線,而良好社會信用體系的構建應當對規則有著更高的要求[19]。對此,起源于英美法系的信賴原則為將來《民法典》在發展過程中要求更高層次的信用體系構建指引了方向。另一方面,鄉村信用體系的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信任本質上具有主觀上的脆弱性,傳統人格信任體系崩潰后,系統信任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就外部獎懲機制而言,除《民法典》相關規范之外,完善鄉村信用管理體系尤為重要。基層政府監督機構應當加強信用監管,督促鄉鎮企業完善企業管理制度,規范企業財務賬簿。對違反信用的鄉鎮企業依法予以相應處罰。在政策層面,鄉鎮企業作為鄉村振興的關鍵驅動力,應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積極開發政策性貸款產品,為鄉鎮企業降低貸款門檻。除此之外,相關機構還應當積極引入互聯網信用評價技術,完善鄉鎮企業信用評價體系。鼓勵信用級別較好的企業優先獲得政策性貸款或政策主導型擔保借款。因此,鄉村新型系統信任的構建需要通過立法與政府規制的共同努力。
四、結 語
鄉鎮企業的繁榮作為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對鄉村振興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國現階段的鄉鎮企業的主體仍然是中小型企業,規模小、技術落后、經濟基礎薄弱是鄉鎮企業的普遍現象。因此,鄉鎮企業在資金融通過程中會面臨困境。在實踐中,鄉鎮企業融資問題需要以授信風險本身的特點為視角,詳細分析貸款人在與鄉鎮企業簽訂借款合同之前需要考慮的內容:從授信風險相關平衡要素出發,確信鄉鎮企業到期后能夠且愿意償還借款資金。并在分析這些要素的基礎之上,篩選出當事人可控的風險要素,并以《民法典》的相關規定為契機,不斷在實踐探索中發展、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融資路徑。
參考文獻:
[1] 楊儒楷.金融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現存問題及破解路徑[J].領導科學,2021(8):86-89.
[2] 佘傳奇,張羽.農村中小微企業地位與融資不平等的實證分析[J].企業經濟,2012(9):84-87.
[3] 中國人民銀行京山縣支行課題組.對農村銀行業擔保融資模式的研究[J].武漢金融, 2011(6):36-38.
[4] 尹超.鄉鎮企業融資困境與民間金融優化路徑探析——基于對現行金融體制抑制效應的分析[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2(4): 69-73.
[5] Karl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AT Band I[M]. München, 1987.
[6] 張谷.商法,這只寄居蟹——兼論商法的獨立性及其特點[J].清華法治論衡,2005(2):32-51.
[7] 肖萍.鄉鎮企業融資供需失衡成因及其均衡實現[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3):115-117.
[8] 胡小平,毛雨.為什么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推進難——基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的案例[J].財經科學, 2021 (2):109-120.
[9] 龍衛球.民法典物權編“三權分置”的體制抉擇與物權協同架構模式——基于新型協同財產權理論的分析視角[J].東方法學, 2020(4): 90-106.
[10]高圣平.民法典視野下農地融資擔保規則的解釋論[J].廣東社會科學,2020(4):212-226.
[11]王桂堂.融資結構與不完全契約視閾下小微企業融資排斥分析[J].金融理論與實踐, 2014(1):19-23.
[12]Voglis E G. Kreditkündigung und Kreditverweigerung der Banken im Lichte von Treu und Glauben[M]. München 2001.
[13]Claus-Wilhelm Canaris. Kreditkündigung und Kreditverweigerung gegenüber sanierungsbedürftigen[J]. ZHR 143(1979):123-126.
[14]Thomas Behrmann. Zweckgebundene Darlehen[D]. Erlangen 1992.
[15]王澤鑒.債法原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1.
[16]Staudinger/Mülbert. BGB Kommtar[M].§ 488. Berlin, 2015.
[17]李春.論銀行業務實踐中的授信額度合同[J].上海金融, 2008(3):80-83.
[18]翟學偉.誠信、信任與信用: 概念的澄清與歷史的演進[J].江海學刊, 2011(5):107-114.
[19]周淳.商事領域受信制度原理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20]陳甦. 民法典促進國家治理機制優化增效[J].社會治理, 2020(7):11-18.
[21]許德風.欺詐的民法規制[J].政法論壇,2020(2):3-19.
[22]黃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釋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
(責任編輯:王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