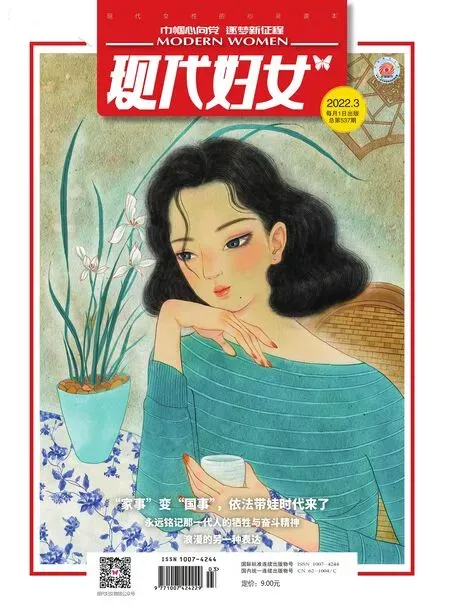生命里的駱駝井
王建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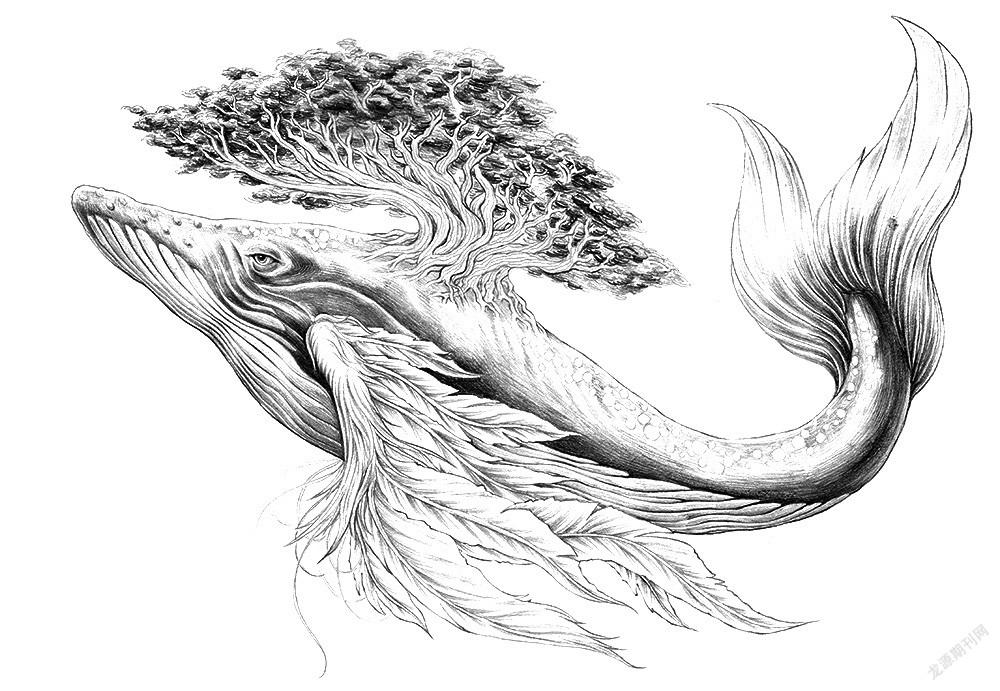
駱駝井,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六師曾經一個不起眼的小農場109團的別稱,坐落于準噶爾盆地的東南邊緣。名叫駱駝井,卻沒有駱駝,只有井。遍布田間地頭的坎兒井、機井,是綠洲得以存在的前提。
記憶中,駱駝井的標志性物產有無籽葡萄、炮彈西瓜、金皇后甜瓜;最熱鬧的地方是工農兵商店,寬闊的烏奇公路從商店門前的十字街口穿過。每年9月,誰家有孩子考上大學,鄉親們就熱熱鬧鬧地把他們從商店門前的十字街口送走上學。由于新疆地廣人稀,且昔日又少有汽車,通常外出上大學是年輕人第一次離開家鄉,而烏奇公路也成了他們走向未來的希望之路。
生于斯長于斯的我,也是從這條路走出來的。參軍后,我回駱駝井的次數越來越少。記得有一年春節,因值完班假期也快結束了,我犯了懶,便沒有回家。誰知正月十五剛過,家人出差路過烏魯木齊,一見面就責怪我:“過年為啥不回家?吃團圓飯的時候,爸都落淚了……”
我聽后,心頭發酸,連忙接過家人捎來的父親寫的家書,裝作拆信走到一邊,雙眼卻濕潤了。
父親年輕時響應建設祖國大西北的號召,從中原腹地西出陽關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干就是一輩子。
兵團創業之初一窮二白,自然條件、生活條件都非常惡劣。父親他們那一代人開荒地、建水庫、修公路,在沙漠腹地建起一座座新興小鎮,也鑄就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奮斗、開拓進取”的兵團精神,被后人親切地稱為“兵團一代”。
高強度的工作之余,父親還要打土坯、蓋房子,做家具、建庭院,后來又養豬種菜、栽果育苗,像參天大樹一樣撐起了這個家。我兒時的記憶里,熹微的晨光和落日的余暉中,總有父親不停歇的腳步和奔波忙碌的身影。
由于工作、生活的壓力大,父親臉上鮮見笑容。我中考時考了全校第三,第一次看到了父親的笑容。
可惜我后來不爭氣,急功近利想放棄學業,和幾個伙伴偷偷約定好去外地闖蕩。就在出發前,我們的行動被一個立場不堅定的同伴“出賣”了。這個同伴的家長特地來到我家找我父親詢問此事,我一看不妙,匆匆逃出家門。
時值隆冬,父親騎著單車在零下30攝氏度的冰天雪地里到處找我。由于心里著急,加上腿腳不靈便,他連同自行車一起滑倒在路上,半天爬不起來。我在角落中看到這一幕,再也不忍心躲下去……
到家后,父親什么也沒說,久未下廚的他竟親自為我做了一桌豐盛的飯菜。我顫抖著雙手拿起碗筷,不安地偷看了父親一眼。他低著頭一言不發,幾乎不被察覺地嘆了一口氣。那一刻,我的心也跟著一顫……
在那之后,我開始發奮努力,最終考上了軍校。
臨行前,父親讓我早早休息,自己卻為我仔細打點行裝,一直忙到深夜。我在迷迷糊糊中睡去,第二天一早又在熱氣騰騰、滿屋飯香中醒來。天還未亮,父親就在為我做行程飯了……
待我匆匆吃過,父親又像送孩子遠行的鄉親們一樣,一手提著我的行囊,一手拎著大兜食品,把我送到商店門前的十字街口,卻一路無語。從未出過遠門的我,有些惴惴不安,很想聽父親說幾句鼓勵的話,囁嚅道:“爸……還有什么要囑咐的嗎?”
父親深情而慈愛地看了我一眼,拍了拍我的肩頭,說了一句如響鼓重錘般讓我至今銘刻在心的話:“你已經長大了,今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不管走到哪里、走得多遠,你要記住,你是兵團的孩子。”
參加工作后,風里來雨里去,隨著歲月的沉淀,我逐漸體會到這句話蘊含的深意。人生之路,不可能永遠有親人陪伴指引,也不可能一直按既定規劃走下去,唯有擁有積極進取、勇于吃苦、不畏挫折的精神,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從軍近30載,多次參加急難險重任務,我從未掉過鏈子,也從不覺得苦,我要感謝父親帶領我從小歷練、鍛造的兵團精神。
多年以后,即將跨入大學校門的孩子打電話,問了我同樣的問題。我把父親曾對我說的話又說給他聽。孩子愣住了,顯然他沒有想到我會這么說。他沉默了片刻,很認真地回答:“知道啦!”
蓋因人之垂暮,難免漸趨傷懷。步入耄耋之年的父母,變得敏感、脆弱。我常常聽到兄妹們說,每到周末,母親就守在電話旁,生怕漏接我的來電;每次聽說我要回家,父親就掐著指頭算日子,到了那天早早地領著孫輩在十字街口等。而粗心的我有時忙起來,兩三個星期也給家里打不了一次電話。父親生怕我遇到什么難事,主動來電確定無恙才放下心來。
由于林林總總的事情,這些年我很少回家。每每問起需要什么,父親總說啥也不缺;每每問及二老身體,父親總是報喜不報憂,母親幾次病危都是事后才告訴我。父親八十大壽,我回不去,打電話表示歉意。父親反過來安慰我:“自古忠孝不能兩全,軍中男兒當以四海為家。記住,你是兵團的孩子!”
是的,我是兵團的孩子。兵團的孩子,要像父輩們那樣,不畏艱苦、開拓進取,內心永遠火熱。
新冠肺炎疫情和工作的原因,我已經很久沒有回家探親。連線問候時,看到父親日漸蒼老瘦削的面容,我不禁淚目,蒙眬中仿佛看到了年邁的父親,正牽著年幼的孫兒,立于駱駝井的十字街口,翹首盼望著兒子的歸來……
(摘自《解放軍報》)(責任編輯 王艷)
356950190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