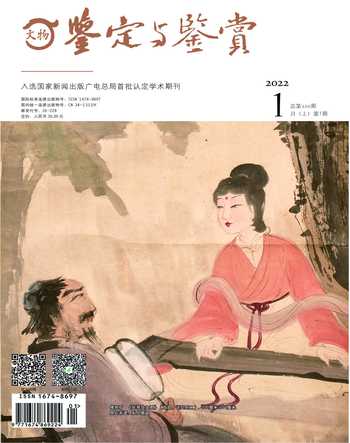北方地區所見金屬器虎紋的初步研究
馮雅楠




摘 要:虎紋是北方地區最常見的動物紋飾之一。早在商代,中國北方地區的銅戈上就出現了虎紋裝飾。文章對于金屬器上所見的虎紋,按照地理環境分成東、中、西三個區域分別進行論述。東區以燕山南北為中心,中區是鄂爾多斯和岱海為主的內蒙古中南部以及晉陜高原,西區以甘寧地區為中心。研究表明,金屬器上所見虎紋裝飾起源于北方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繼而在春秋中期廣泛發現于燕山南麓,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則在岱海地區興盛,戰國中期又在鄂爾多斯高原區及甘寧地區流行,之后又逐漸向西傳播至新疆及歐亞草原中部區。
關鍵詞:北方地區;虎紋;歐亞草原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1.035
北方地區,狹義指的是“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這一概念并非指歷代所筑長城經由的全部地區,而是自古以來生活在中原的農業居民與北方游牧民族互相接觸的地帶。北方地區東起西遼河流域,經燕山、陰山、賀蘭山,到達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中描述的“逐水草遷徙”,正是對北方草原人群的真實寫照。
生長在北方地區的人群,其生產、生活與中原地區有著極為顯著的差異。發達的武器與工具、大量的車馬器、豐富的動物紋主題裝飾構成了所謂的“斯基泰三要素”,這也正是早期游牧民族特征的體現。而這其中,動物紋裝飾(animal style)是歐亞草原文化最為典型的特征之一,其發源地也最具爭論。隨著歐亞草原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入,動物紋裝飾成為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
在國內,最早系統研究動物紋的學者是烏恩岳斯圖,在20世紀80年代發表的《我國北方古代動物紋飾》一文中,他將出土地點明確的遺物按年代加以區分,將不同時期出現的動物紋飾特點及造型加以歸納整理,并探討其與斯基泰—西伯利亞野獸紋的關系。進入21世紀后,越來越多的學者投入到北方地區動物紋飾的研究中。
1 北方地區金屬器虎紋的分類
北方地區多兇獸猛禽,先民們將它們記錄下來,反映在自己的生產、生活中。這些動物紋飾多表現在裝飾品、武器等方面。北方地區常見的動物紋包括鳥紋、鹿紋、羊紋、虎紋、馬紋等。其中,虎作為最兇悍的動物形象也頗具代表性。虎是東亞地區常見的一種哺乳綱的大型貓科動物,圓頭、短耳,尾粗長,四肢健壯有力,棕黃皮毛上有黑色橫紋。虎紋在我國古代紋飾中占有很大比重,為北方地區最常見的動物紋之一。早在商代,我國北方地區就出現了虎紋裝飾。下面將對北方地區出土金屬器(包括銅器、金器及銀器)虎紋進行研究。首先,根據金屬器上虎紋裝飾的不同特征,將虎紋題材分成以下幾類:
第一類,單體虎紋。形象多為蹲踞式或半蹲踞式,少數為站立或行走式。這兩類單體虎紋主要以四肢直立與否作為明顯區別標志。此外,前者通常虎尾下垂,而后者通常虎尾上卷。這種單體虎紋在北方地區最早的發現是在燕山北麓的夏家店上層文化。
第二類,虎首裝飾。此類裝飾主要在劍、刀、戈等武器與馬銜、馬鑣、節約等車馬器上。發現數量相對較少。主要流行時期在西周晚期至戰國早期。
第三類,對稱雙虎紋。這種紋飾通常表現為左右對稱的兩個虎形圖案。此類對稱形紋飾對于后世的裝飾品藝術影響較大。戰國開始,其他對稱形動物紋飾在北方地區大量涌現,如雙鳥回首劍等。
第四類,虎噬食草動物紋。這一類紋飾主要表現為虎撕咬或捕食鹿、羊等食草動物的畫面。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戰國晚期,且分布范圍很廣,是歐亞草原典型的動物紋飾之一。虎噬食草動物紋最早發現于夏家店上層文化中。
第五類,虎與動物搏斗紋。該類型主要是虎與動物組合搏斗的畫面,具體表現有虎狼搏斗、虎豬搏斗、虎牛搏斗等。這種題材的紋飾流行時代主要在戰國中晚期,分布地域在鄂爾多斯高原區和甘寧地區。此類紋飾出現時間較晚,很可能是虎噬食草動物紋興起之后,由其演變出的。
第六類,卷曲虎紋。這種卷曲成環的虎形,首尾相接,頭部分為正視和側視兩種。該類虎紋起源于夏家店上層文化,且虎腿上部常常飾有同心圓。這種卷曲成環的猛獸形象題材在歐亞草原分布廣泛。
2 北方地區金屬器虎紋的分期與分區研究
關于北方地區金屬器上虎紋的發展脈絡,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時間范圍為商至戰國時期。
第一階段:商至西周中期,公元前16至前10世紀。這一階段是虎紋的萌芽階段,發現較少,且多集中在武器和工具上,幾乎不見虎紋裝飾品。早商時期目前只在朱開溝遺址發現一件銅戈,商文化因素明顯,但其內部一側鑄有的虎頭形圖案說明了此時北方草原文化的特色開始顯露。晚商時期中原青銅器進入鼎盛階段,與此同時北方地區的虎紋裝飾開始增加,但僅在較小的范圍內,如晉陜高原地區。到西周早中期,虎紋在北方草原的發現仍呈幾乎停滯的狀態。
第二階段: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公元前9至前8世紀。這一階段是北方虎紋的發展期,集中于北方草原的東區,尤其以夏家店上層文化中發現的最為集中。這一時期多為卷曲虎紋、單體虎紋和對稱雙虎紋,且虎身流行同心圓裝飾。
第三階段:春秋中期至戰國晚期,公元前7至前3世紀。這一階段是虎紋發展的繁盛期,主要集中于北方草原的中區和西區。春秋中期后,在夏家店上層文化地區,虎紋開始消亡,轉而在燕山南麓和岱海地區開始發展。戰國中期后,上述地區的虎紋開始銳減,取而代之的是以鄂爾多斯高原為主的中區和以甘寧地區為中心的西區開始大量發現。戰國中期開始,虎紋裝飾幾乎不見于武器、工具、車馬器上,相反在裝飾品上開始大量發現,尤以金銀牌飾最為多見。
眾所周知,北方地區是一條南北窄、東西長的條帶狀區域,下面按其地理環境分成東、中、西三個區域分別進行論述。
東區以燕山南北為中心。該地區的虎形紋飾主要來源于夏家店上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是長城以北地區最為發達的青銅文化之一,其繁盛期在公元前9—前8世紀(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寧城小黑石溝石槨墓出土有多件虎形銅牌飾。其中一件典型的蹲踞式虎紋牌飾上的虎的形象,立耳圓目,長尾下垂,屈肢呈趴臥狀(圖1:1)。另有一件卷曲式的虎紋牌飾,前后虎腿上部都有同心圓(圖1:2),這種以同心圓做裝飾是夏家店上層文化動物紋裝飾的重要特征之一。這種同心圓裝飾在良渚文化也有發現,如瑤山M9∶4,該器物為一件神獸紋玉琮,紋飾頗似虎頭,其眼球是由多組線刻同心圓組成(圖4:5)。此外,寧城小黑石溝出土的一件對稱雙虎紋形象的牌飾也極富北方草原特點,從虎的眼睛至頭被化為同心圓的形式,腿上部也以同心圓做裝飾(圖1:3)。該墓地的年代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實際上,這種對稱的動物紋裝飾在北方系青銅器中極為普遍,如雙鳥回首劍等。其中在寧城南山根的石槨墓中也發現有這種對稱的雙虎紋裝飾,是一件雙虎紋銅柄劍,虎紋飾于劍柄,二虎呈對臥狀(圖1:4)。另外,在寧城小黑石溝還出土有帶虎紋裝飾的馬銜M8501∶172,兩端各銜一件蹲踞狀虎形飾,虎腿上部飾同心圓(圖1:5);另一件M8501∶173的其中一端為圓環狀并銜一卷曲虎紋的飾件,虎腿上部飾同心圓(圖1:6)。
冀北地區的延慶玉皇廟墓地出土有臥虎紋牌飾(圖1:7),虎腿的上部和爪部也飾有同心圓。楊建華先生認為這種虎形牌飾與一種形制特殊的“花格劍”都在玉皇廟以及中山國遺存出土,鑒于此,她認為玉皇廟文化與狄人建立的中山國和代國有著文化上的聯系。玉皇廟文化的開始年代在春秋中期,晚到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冀北的隆化縣轉山墓地出土有一件銅質的虎形飾片(圖1:8),虎作蹲踞式,肌肉健碩,虎牙外露,仿佛準備捕食。對于該墓地的年代,原報告上只提及為春秋至戰國時期。燕山南麓的西部地區的平山一號墓出土有一件錯金銀飾銅器,為圓雕虎吞鹿的造型(圖1:9)。這種圓雕動物撕咬或相斗的題材十分罕見,仍保留北方民族文化的傳統作風。該墓定為中山王厝之墓,年代為公元前4世紀末。戰國中期開始,東區的虎紋裝飾就極少見了,這與春秋中期以后夏家店上層文化的衰落有關。此后,虎紋裝飾多在中區和西區發現。
中區是鄂爾多斯和岱海為主的內蒙古中南部以及晉陜高原。目前北方地區發現的最早的虎紋裝飾是出自朱開溝墓地的一件銅戈(圖2:1),年代屬于早商時期,這件銅戈內部的一個側面鑄有虎頭形圖案,圖案的上、下和后側飾有連珠紋。除了武器上的虎紋裝飾外,在晚商時期的晉陜高原區還出土有少量虎紋裝飾的工具。延川用斗出土一件羊首銅匕(圖2:2),其上裝飾有一只佇立狀虎,虎前一人跪坐,匕的柄端鑄有一盤角羊首。清澗解家溝出土一件羊首銅勺(圖2:3),柄上一前一后鑄有虎逐鹿形象,柄端同樣鑄有一盤角羊首,與延川用斗的銅匕的整體造型頗為相似。鄂爾多斯高原發現的出土北方系青銅器的重要匈奴墓地,主要有桃紅巴拉墓地、西溝畔墓地、阿魯柴登墓地、玉隆太墓地等。在西溝畔墓地出土有兩件相同的虎豕咬斗紋金牌飾(圖2:4),虎張口咬住野豬的后肢,野豬也同時咬住虎的后肢,造型生動活潑,金牌飾的背面邊緣處,均有刻畫文字。另外還出土有多件銀虎頭節約(圖2:5),該墓在年代上定為戰國晚期。阿魯柴登墓地出土多件裝飾有虎紋的金牌飾,其中一件著名的匈奴王金冠(圖2:6),冠飾為一只鷹,冠帶上飾一猛虎正在撕咬馬。另外還出土有虎牛相斗紋、虎鳥紋及虎形牌飾和銀虎頭等。該墓葬的年代定為戰國時期。玉隆太墓葬出土有一件虎頭形骨鑣(圖2:7),雖不是金屬器,但具有參考性。原報告上寫,從眼、耳觀察,類似虎頭,但下頦又類似魚鰓。背凹肚圓,尾上翹,呈連珠形。該墓的年代定為戰國至漢代。但同出土的鐵鶴嘴鎬、銅刀、帶扣、鳥形牌飾等均與桃紅巴拉墓葬出土器物類似,可以判定該墓的年代應在戰國晚期。毛慶溝墓地M5出土兩件蹲踞式虎紋銅牌飾,一件半蹲踞式虎紋銅牌飾,一件虎形銅牌飾,兩件虎紋鐵牌飾,年代為春秋至戰國早期。其中蹲踞式虎紋銅牌飾(圖2:8),正面以陰線紋刻畫出虎的形象,虎腿與虎爪呈線條狀,牙齒呈鋸齒狀,背部與尾部上飾平行短斜線紋以表示虎紋,造型簡練。半蹲踞式虎紋銅牌飾(圖2:9),陰線紋刻畫,線條狀腿、爪與蹲踞式相同,張口露齒,虎舌外露。另有一件側面的虎形牌飾(圖2:10),頭部略呈方形,立耳,張口露齒,虎爪呈螺旋狀,比上述蹲踞式和半蹲踞式更加寫實。崞縣窯子墓地出土兩件虎羊紋牌飾,上端一虎作撕咬狀,虎爪下一羊作掙扎狀(圖2:11),該墓的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納林高兔出土有金虎、銀虎各一對。金虎四肢前后交叉,作行走狀,虎尾向上彎曲,與蹲踞狀虎紋的下垂虎尾明顯不同。兩只金虎互相靠攏,一號比二號略小,一號應當是雌虎,二號應當是雄虎(圖2:12)。銀虎的形狀、大小、制法同金虎。還出土銀環兩件,環體扁平,正反兩面各浮雕四只虎頭(圖2:13)。
西區以甘寧地區為中心。馬家塬墓地被認為是商周西戎的遺存,該墓地出土有一件虎紋金帶飾,虎呈行走狀,尾翻卷至背上方,踩踏卷云(圖3:1)。還出土有一件金腰帶飾,帶飾上首尾兩端較大的飾件均為虎噬羊造型(圖3:2)。馬家塬墓地的年代在戰國晚期。清水劉坪出土有七件虎噬羊造型(圖3:3),虎身飾有規則的斑紋來表現皮毛上的花紋,該墓地的年代在戰國中晚期。慶陽吳家溝圈出土的虎噬羊銅帶飾(圖3:4),該遺址的遺存大多為春秋至戰國中期。寧縣宇村墓中出土了三件虎形牌飾(圖3:5)和一件立體銅虎飾件(圖3:6),該墓的年代在西周晚期。西吉縣陳陽川出土一件虎噬羊透雕銅牌(圖3:7),這里出土的青銅器與固原楊郎墓地出土的同類器物相對照,可以大致判斷該處墓葬的年代在戰國中晚期。彭陽縣張街村出土有一件單體虎形牌飾(圖3:8),一件虎噬鹿牌飾(圖3:9),墓地的年代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在固原楊郎鄉馬莊墓地出有一件猛虎噬獸紋透雕牌飾(圖3:10)、兩件平面虎紋帶飾(圖3:11),該墓的年代判定為戰國晚期。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燕下都西城中部的辛莊頭墓區30號墓中,發現有兩件形制紋飾相同的虎噬鹿紋金牌飾(圖3:12)。整體呈半球形,器表頂部正中浮雕一頭鹿,周圍浮雕幾組老虎,做工十分精美。這種金牌飾很可能是當時燕國與北方山戎交流的證據。該墓葬中發現了許多北方系青銅器,是一項重大發現。
3 關于虎紋起源與文化傳播的相關問題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盡管北方地區金屬器上最早的虎紋起源于商代,但虎紋真正開始有意識地出現卻是在商末周初。早商時期朱開溝文化出土的虎頭形銅戈,是典型的中原文化武器,帶有明顯的商文化因素。銅戈的內部常有夔紋和獸面紋做裝飾,朱開溝的這件銅戈紋飾與商文化的獸面紋和夔紋類似,應當是受到中原地區文化的影響出現的,但很明顯這個時期生活在北方地區的人群已經有意識地選擇具有自身特色的動物紋作為裝飾,這件器物體現了商文化與北方文化的融合。可見,北方地區動物紋飾最早階段可能受到了來自南部的中原文化的影響。從西周晚期開始,夏家店上層文化進入繁榮期,虎紋裝飾由此正式發源,這時,虎紋與中原文化的聯系就減弱了。
商代前期,中原地區處于強有力的政權中,北方地區在其控制下則處于弱勢,發展緩慢。而到了商代末期,中原統治者焦頭爛額,無暇顧及北方,才迎來了北方地區的大發展時期。這時北方地區廣泛吸收中原地區的青銅器風格,并用于武器和工具,然而尚未形成自身的特征。再到春秋中期時,禮崩樂壞,中原發生大變革,北方地區又一次進入了蓬勃的發展期,與此同時北方系青銅器又一次進入了繁榮期,并且在動物紋飾方面有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通過對于動物紋裝飾的研究,北方地區與中原地區關系的變化體現得淋漓盡致。
我國北方地區屬于歐亞草原東部區的一部分。相對于東部區,歐亞草原西部區因為地理環境,幾乎沒有虎的存在,故而也鮮少有虎紋裝飾,其作為裝飾的貓科動物紋主要是豹紋。在歐亞草原中部區,出土有少量裝飾虎紋的典型器物,如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爾文化中發現有虎噬食草類動物形象的牌飾(圖4:1)。在薩卡文化的典型遺址—天山七河地區的伊塞克古冢也出土有單體虎紋的裝飾(圖4:2),墓葬的年代在公元前5—前4世紀。阿爾泰地區的巴澤雷克文化,年代約在公元前6—前3世紀,其中既發現有虎噬食草動物紋的形象(圖4:3),也發現有排列在一起的虎紋(圖4:4)。但在巴澤雷克文化中幾乎不見單體虎紋牌飾,多是以木器、皮革等作為載體。虎噬食草動物紋在歐亞草原中部區的各文化中的確普遍發現,但形制較晚,均不早于戰國時期,這些動物紋很可能受到中國北方地區的影響而出現的。
關于我國北方地區動物紋的起源,究竟是發源于本土還是從歐亞草原西部傳入,意見不盡相同。許多西方學者認為我國北方地區的動物紋是受到歐亞草原西部區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而現如今,越來越多的學者支持動物紋的多地起源說。林沄先生認為,歐亞草原上的卷曲動物紋有三個各自獨立的起源,并且彼此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才形成一個整體。而其中,關于金屬器上虎紋的淵源,我們通過它的發展脈絡可以明顯看出是起源于北方草原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從兩周之際伊始,虎紋在燕山北麓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開始集中出現,繼而在春秋中期廣泛發現于燕山南麓,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則在岱海地區興盛,戰國中期又在鄂爾多斯高原區及甘寧地區流行,之后便逐漸向西傳播至歐亞草原中部區。可以說,虎紋的出現與發展代表了我國北方地區對新疆和歐亞草原地區的影響。
綜上所述,歐亞草原金屬器上典型動物紋之一的虎紋裝飾起源于我國北方地區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大約從西周中期開始不斷向西傳播,其傳播的結果是覆蓋面除了歐亞草原東部區和中部區。北方地區的虎紋有自己的特點及發展脈絡,這為研究我國北方與歐亞草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借鑒。可見虎紋的出現與大面積流行,正是晚期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文化交流的證明,而我國北方地區也在中原地區與歐亞草原的文化交流之間起到了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林沄.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J].燕京學報,2003(5):95-145.
[2]邵會秋,侯知軍.百獸率舞:商周時期中國北方動物紋裝飾綜合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3]魏堅.涼城崞縣窯子墓地[J].考古學報,1989(1):57-81,145-152.
[4]遼寧省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寧城縣南山根的石槨墓[J].考古學報,1973(2):27-39,148-159.
[5]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城縣遼中京博物館.小黑石溝—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6]勒楓毅.北京延慶軍都山東周山戎部落墓地發掘紀略[J].文物,1989(8):17-35,43,97,100-102.
[7]戴應新,孫嘉祥.陜西神木縣出土匈奴文物[J].文物,1983(12):23-30,100-101.
[8]郭素新,田廣金.西溝畔匈奴墓[J].文物,1980(7):1-10,98-99.
[9]許成,李進增,衛忠,等.寧夏固原楊郎青銅文化墓地[J].考古學報,1993(1):13-56,152-157.
sdjzdx20220323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