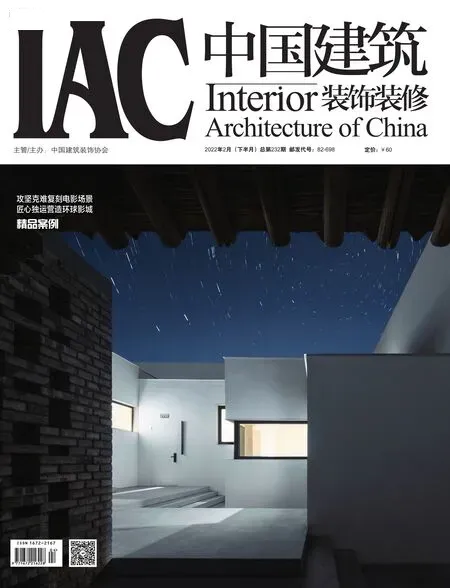從“延碧堂”看胡雪巖故居建筑修復的“原真性”
程嘉敬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碩士在讀
俞 超 中國聯合工程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師
胡雪巖故居建筑群建于1872 年,坐落于杭州上城區望仙橋畔,占地面積7 000 m2,建筑風格融匯中西,在傳統建筑的基礎上融入西方建筑材料和構件樣式。此后故居幾經易手,不少價值不菲的建筑構件遭洗劫盜賣,建筑損毀嚴重。1999 年,杭州市政府決定對其進行搶救性修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舊貌,但也帶來關于“原真性”的討論,即修復后的胡雪巖故居是否是歷史上的本來面目,修復的價值何在。下文將通過對修復過程的描述,對上述問題進行討論。
1 修復前遺址殘存情況
1999 年搶修時,胡雪巖故居已面目全非,多數建筑物被夷為廢墟,芝園內的假山被削去頂部,水池子亦被填平。其本體性歷史價值岌岌可危,經過文獻整理,列出遺址殘存情況如下。
故居布局分為東、中、西3 部分(圖1),東部僅剩下新、老房屋7間以及東下房和破屋,其余皆已不在。殘存的遺址有拼花卵石地面、花壇、小水池、曲橋橋墩、亭子、曲廊、小假山、鴛鴦廳以及僅有輪廓基礎的兩個花廳和一個廚房[1]。中部是禮儀活動區,除轎廳外,其余都已不存在。

圖1 胡雪巖故居平面分區及延碧堂平面
清理過后發現的遺跡有:正廳百獅樓,基礎破壞嚴重,僅存輪廓;廚房和水井,情況與正廳相同;西下房,基礎保存略好,并有鋪設木地板的痕跡;東、西四面廳的基礎輪廓;東、西四面廳的園林遺址內,2 ~3 cm 不等的鵝卵石地面殘存,拼花圖案殘破,曲廊基礎殘存,西四面廳西北角的亭子基礎已毀;水池遺址尚存,且中部有曲橋的橋墩殘存。西部存有游廊、水池、假山以及溶洞,建筑部分除了花廳四以外,其他均不復存在。經工作組清理后,于百獅樓遺跡的西面發現延碧堂遺跡,遺址屋內基礎受損嚴重,僅存青石板側砌包邊的輪廓,水井和小水池遺跡、大水池和橋亭遺跡以及臨水曲廊遺址僅有部分橋墩存留。此外,一并出土的還有大量磚雕、石刻構件及其他出土遺物。搶修前的胡雪巖故居保存情況很差,情況復雜,進行修復需要從考古、工藝建造、園林等多方面進行研究,難度很大[2]。
2 從“延碧堂”看胡雪巖故居的修復
“延碧堂”是故居內“芝園”的主要建筑,東、西兩側為天井,南為臨水露臺。因建筑材料為珍貴的紅木,故別名“紅木廳”。由于胡雪巖故居修復工程量巨大,本文僅對“延碧堂”的修復進行詳細敘述,以點窺面來反映胡雪巖故居的整體修復思路。
2.1 平面修復
“延碧堂”坐北朝南,平面方整,為廳堂式建筑,面寬六柱五間、進深四柱三間,室內有南、北兩進,通向二層的樓梯位于北進東側。建筑東、南、西三面均有副階,而獨缺北側副階,建筑柱形為方形。
工作組在搶修時,將“延碧堂”面寬定為12.15 m,進深為9.30 m,明間部分面寬為3.31 m,次間面寬為3.00 m,東、西副階均為1.42 m,而進深方向則依次為南側副階1.42 m,南間深4.66 m,北間深2.47 m,再向北為深0.75 m 的走道,并將東、西、南三側檐柱與臺基邊緣的間距定為0.75 m。
具體實施過程中,參考了體量相當的“洗秋堂”立柱尺寸(23 cm×23 cm),石質磉墩的形狀和尺寸參考“洗秋堂”及其他留存建筑中使用最多的磉墩式樣,柱下石質磉墩和柱頂石均為方形。地坪依據故居內留存建筑中所采用的材料和形式而設計,樓梯扶手的式樣則依據“和樂堂”的扶手形式,采用“萬字紋”的宮式圖案。“延碧堂”南側露臺的復原設計是在原遺址考古發掘的基礎上,參考胡雪巖故宅平面圖而設計[3]。
由于胡雪巖故居的細節修復是在對存留建筑細部形式歸納和推測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柱子粗細、磉墩形狀和大小、扶手樣式的建筑細部的處理必然會與原狀有差異。
2.2 立面修復
“延碧堂”的立面修復充滿了爭議與不確定性,在最重要的屋面形式上,修復工作小組決定采用歇山的形制進行重建。
“延碧堂”是園林建筑,且緊鄰水池,因此要強調其輕盈、靈巧的建筑屬性。據有關文獻記載,胡雪巖故居西部存在多種屋頂形式,如水榭屋頂是歇山式,樓閣和方亭屋頂為歇山卷蓬式,花廳的屋頂為硬山,此外還有攢尖式的橋亭以及圓形的半亭,這其中歇山式屋頂等級最高,出現最多,而在江南園林中類似的臨水建筑大都采用歇山造,并通常分為歇山和歇山卷蓬兩種形式。不僅如此,同處杭州的胡雪巖其他房產“胡慶余堂”中也存在歇山建筑群。修復團隊采用了歇山式作為“延碧堂”的屋頂形式,轉角采用老戧和嫩戧發戧的形式[4]。因為故居內保留下來的其他建筑大多都使用銅質隔漏進行組織排水,所以“延碧堂”一層副階檐口采用了銅質隔漏排水,二層歇山屋面的檐口部分以常見的勾頭和滴水進行自然排水。
在細節處理上,立面的柱間連接及細部裝飾等的修復參考了“洗秋堂”的形式,南側露臺的迎水壁面上用塊石砌成的冰裂紋圖案,參考了在“和樂堂”內有保存完好的冰裂紋隔扇,而屋脊部分則參考了胡慶余堂建筑群的屋脊做法,采用正脊、垂脊及戧脊[5]。“延碧堂”從屋頂形式到裝飾構件、壁面圖案乃至屋脊,都只能說是一種基于歷史線索的“再設計”,而非“忠實還原”,其現在的樣貌大概率與歷史相去甚遠。
2.3 木架構及標高修復
“延碧堂”木架構的修復也參考了周邊建筑,一層副階的修復采用了“和樂堂”前檐廊相同的結構形式。設計楞木的數量和規格時,不僅考慮了“延碧堂”的尺寸和特點,還參考了故居內其他留存建筑內楞木的數量和規格。二層前后檐的設計與一層前檐柱的外構架相同,即月梁前端伸出前檐柱作象頭狀。室內木構架的設計參考了“洗秋堂”的梁架,考慮到“延碧堂”與“洗秋堂”的體量相當,所以其室內的樓板、軒梁、軒頂等標高的設計基本都以“洗秋堂”的標高為依據。經仔細測繪后發現,留存的“洗秋堂”“清雅堂”以及破屋等建筑的樓板厚度基本上為4 cm,只有“和樂堂”的樓板厚度為3.8 cm,因此最后將“延碧堂”的樓板厚度設計為4 cm。
“延碧堂”無論是結構還是立面,都無法保證與其歷史樣貌一模一樣,必然會有所出入。但是這種修復因大量參考了同一建筑群內其他建筑的樣式與細節,使得建成效果能夠跟周圍環境相和諧,仍然有一定的價值[6]。
3 胡雪巖故居的修復與保護
從“延碧堂”的修復中可以看到,胡雪巖故居的修復并非對歷史的完全還原,由于在部分建筑與細節的處理上缺乏詳細的圖紙和史料基礎,因此只能在修復過程中對建筑形式、細節進行科學卻又不可避免帶有主觀想法的推測。歷次修繕工作中,修復組經過大量的歷史考古調查,發掘了許多歷史資料,提出了許多有科學依據、切實可行的修繕方案,貫徹了“最小干預”原則,盡量少動存留的原始建筑遺址保留了后期持續修繕工作的重要依據。
胡雪巖故居的搶救性修復意義重大,象征著一代徽商輝煌的胡雪巖故居如果真的消失,將是無法挽回的損失。修復前,故居已毀壞嚴重,不少建筑只剩遺址,若放任不管則很可能盡數消失。歷史遺產、建筑的最大價值在其本身,如果本體消失,那么其所附帶的一切價值便失去了載體。若胡雪巖故居不復存在,那么它所體現的建筑樣式,西方材料與傳統建筑局部的融合,作為紅頂商人的生活環境等都將無處可尋。因此,歷史建筑最終還是要以具體形象來展示其所承載的歷史價值,這是文字、照片所不能取代的。基于此,胡雪巖故居搶救性修復工程中實施“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文物(歷史建筑)保護方針是實事求是的體現。
4 原真性
4.1 原真性與價值
“原真性”由“Authenticity”翻譯而來,也可譯為真實性,是歷史建筑保護的核心概念之一。對胡雪巖故居修復與保護的主要爭論點就在“原真性”上。以《威尼斯憲章》的標準來看,胡雪巖故居的修復有“臆測”的嫌疑,并沒有反映出建筑原本的樣子,沒有“原真性”,對于缺失部分的修補未區別于原作,不具備“可識別性”。但事實上,該憲章是站在西方建筑遺產體系的角度看待問題,制定的原則是從歐洲古代石材建筑的角度出發,沒有考慮到東方建筑材料和結構的特殊性。東方的木結構建筑與西方的石制建筑不同,若不及時進行修復,而僅對殘余部分進行露天保護的話,剩余的部分也會很快被腐蝕而倒塌。在具體修復時,也無法像西方一樣用不同的石材進行區別,與原物保持明顯的分界。木建筑的結構部件十分精巧復雜,其價值更多地體現在斗拱、屋架等的結構和形制上,包含隱性的遺產工藝。因此,東方木建筑的原真性不僅體現在原材料的終始如一,更體現在工法的原汁原味上。
胡雪巖故居的價值不僅在于本體性歷史價值,如建筑園林布局、立面形式、建造工藝等,還在于其對特殊歷史階段的見證,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發展過程中的實物例證之一,有著極大的符號性歷史價值。胡雪巖故居的修復是一種本體復原,對其進行的搶救性修復則更看重符號性歷史價值,而一定程度上犧牲了本體性歷史價值。在本體性歷史價值即將消失殆盡的情況下,重塑其符號性歷史價值,進行復原,也是當時形勢下的合理折中手法。但對故居進行的干預過多反而損壞了其本體性歷史價值,也是引來批評的主要原因。
4.2 真文物還是假古董的爭議
文物是我國特有的概念,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歷史建筑也是一種文物。關于胡雪巖的故居,由于進行了較大程度的干預和修復,因此帶來了是“真文物”還是“假古董”的爭議。
修復的過程是否科學嚴謹,布局、結構、形式、工藝等是否原汁原味是判斷“真假”的重要標準。經過嚴謹考證并修復的古建筑,盡管本體性歷史價值受到了損害,但不是“假古董”。胡雪巖故居修復前,不僅建筑基礎保存完整,且主體建筑構架及裝飾尚在,也有測繪圖紙、歷史照片作為參考,因此對其進行修復是有相當的科學依據的。盡管如此,也要清晰地認識到,修復過后的胡雪巖故居無法被稱為一種“真文物”,因為仍有很多新建部分形制與樣式的真實性無法保證。
5 結語
胡雪巖故居的修復過程體現了“原真性”的沖突,從中、西方兩個視角進行審視可以得出不同的結果,繼而產生不同的價值導向。因此在對我國傳統木構歷史建筑進行修復保護時,要對其社會影響、歷史價值、專業價值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具體分析。一方面不能簡單以西方標準來界定“原真性”的“真”與“假”,另一方面也不能僅以“原真性”來作為判斷歷史建筑修復價值的依據,這既是歷史建筑保護的復雜之處,也是實事求是態度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