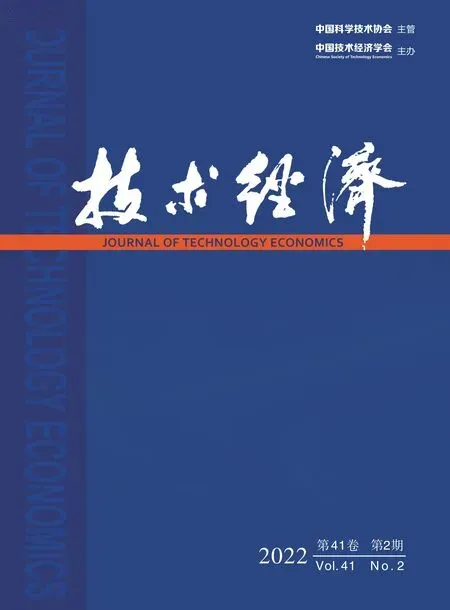公眾參與如何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基于中介效應和空間效應的分析
秦炳濤,郭援國,葛力銘
(1 上海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093;2.復旦大學 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3.上海財經大學 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上海 200433)
一、引言
當前,環境問題已然成為制約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瓶頸”。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綠色技術創新必將成為環境污染防治和企業綠色發展的有效手段,《中國制造2025》和《“十四五”規劃綱要》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明確指出把創新放在企業發展的核心位置,并通過合理的環境政策推動企業綠色發展。
然而,盡管環境規制是實現環境和經濟協調可持續,推動企業綠色發展的重要手段,但是最優的環境規制往往難以選擇,以往“政府規制,企業治理”自上而下的二元協作體系對于環境治理及促進綠色創新的能力有限:政企之間信息不對稱導致政府難以根據企業的污染行為實施最優的環境規制;同時政企因為利益相投,可能會出現尋租行為而發生政企合謀導致政府失靈,不利于企業提升綠色技術創新能力(Zheng 和Kahn,2017;Harmon,1995)。僅靠政府約束企業行為難以滿足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需求,近年來,大量研究表明公眾參與作為一種“軟手段”具有彌補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獨特優勢(Jiang 和Zhang,2018;郭進和徐盈之,2020;張艷純和陳安琪,2018)。黨的十九大也明確指出要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三方共治體系,公眾參與在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愈發明顯。因此,探討公眾參與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作用機制及實現方式對于政府完善公眾參與政策,最大化公眾參與效用,以及提升綠色創新積極性,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誠然,學界關于公眾參與的研究由來已久。通過梳理已有研究和文獻,可歸納為兩種觀點:一是公眾參與的多重優勢。隨著信息化社會的到來和公眾法治權利意識的勃興,政府與公眾協作已經成為解決環境危機的重要手段,通過公眾參與限制政府權力濫用也已經成為常識(王柱國,2014)。公眾作為環境污染的切身感受者,會特別留意企業的污染行為,加之公眾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愈來愈高,環保意識也不斷增強,公眾就污染問題會向政府施壓,政府在受到地區內公眾的壓力后加大環境規制,提高環境服務(Wang 和Di,2002)。公眾參與有利于加深地方政府關注環境的程度,通過環境治理投資,改善產業結構來改善環境污染狀況,公眾的積極參與和環保行為也是進行污染治理政策成本效益分析、提升環境規制效果的重要方式。與僅考慮政府環境規制政策的情形相對比,政府征收環境稅和社會組織參與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會福利提高(趙黎明和陳妍慶,2018),公眾參與對于政府環境規制的影響逐漸體現,較高的公眾舉報概率可以促進企業生態技術創新,節省政府的監管成本(張同斌等,2017;游達明和楊金輝,2017);二是公眾參與發揮有效性的過程中面臨著諸多挑戰。首先,由于環境監管需要消耗大量的資源,公眾無法得到資源消耗帶來的全部收益導致公眾參與的積極性較弱。其次,公眾參與的機制不夠健全,政府對企業的治理手段較為單一,效率低,成本高,同時公眾參與行為多基于自愿,不具有強制性,以致這類規制工具發揮效力的時滯較長,容易流于形式,公眾環境利益訴求無法得到滿足(Yang 和Zhang,2011),會導致公眾的參與熱情降低。最后,公眾缺乏財政資源和專業知識技能,難免會造成無效參與(Kahila-Tani et al,2019)。激發公眾參與熱情,健全公眾參與機制,提高公眾參與技能至關重要。
同樣地,政府實行環境規制管制企業的污染行為倒逼企業技術創新也是屢見不鮮的話題。學術界對環境規制與綠色創新之間的關系一般持有三種觀點,一是基于“波特假說”的促進論,嚴格的環境規制將激勵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Porter 和Van der Linde,1995);二是傳統經濟學認為,環境規制降低污染的同時會帶來“遵循成本”,擠出了技術研究和生產要素投入,不利于綠色創新(Gray,1987);三是二者關系的不確定,不同的環境規制會對綠色技術創新產生不同的效果,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在短期時間內對企業技術創新具有積極作用,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具有激勵企業技術創新的持續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在中長期不利于企業技術創新,推動綠色創新的關鍵在于環境規制工具的選擇(郭進,2019;張國興等,2021)。
綜上所述,理論研究方面,大多文獻基于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合理性、基本途徑及面臨的問題展開研究,鮮有文獻關注到公眾參與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也未能揭示政府環境規制在其中的中介機制。實證研究方面,大多把公眾參與作為非正式規制研究其對綠色創新的研究,忽略了其與政府環境規制這一正式規制的內在聯系;針對綠色技術創新對象不同探究公眾參與對其影響的文獻不多,且大多忽略了公眾參與的空間溢出效應,同時未細分區域深入研究,有待進一步細化。本文可能的創新之處在于:①基于綠色技術創新的不同,分別探討了公眾參與對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工藝創新的直接影響。同時鑒于公眾缺乏行政權力,無法直接干預企業創新行為,提出了公眾參與依賴政府環境管制間接影響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工藝創新的路徑;②發現了公眾參與在不同地區發展水平及不同公眾參與度下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異質性效果;③為了使結論更有說服力,引入空間計量模型,研究了公眾參與的空間溢出效應。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公眾參與與綠色技術創新
根據公共物品理論,生態資源屬于廣義公共物品范疇,在使用過程中難免會產生“搭便車”行為。對于企業而言,通常只考慮自身的利潤最大化,享受到環境資源帶來的種種權利,卻很少對環境盡應盡的義務,這就導致種種環境污染問題的產生。同時,環境污染具有負外部性,社會成本大于企業成本,這就需要政府制定一系列嚴格的環境政策與法規來約束企業的行為,調節企業的經濟活動,讓其履行自己的義務,承擔環境污染成本(Kriechel 和Ziesemer,2009)。由于信息不對稱,政府不能根據企業產生負面作用的程度實施最優的環境規制,只能利用現有的信息資源實現“次優”的結果。同時,盡管我國環境監測督察機構及環保人員配置已相對完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追求GDP 和稅收的現實需求及地方“官員競升”,政府往往會放松管制(潘峰等,2014),滋生了為完成績效而出現的環保腐敗和政企合謀等種種問題,公眾對于政府、企業的監督迫切需要。環境權理論指出每個人都有在良好環境下生存的權利,也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公眾是環境保護利益的切身相關者,環境污染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健康,公眾會密切關注企業的行為(劉帥和孔明,2020)。公民有權依法行使監督權通過環境信訪、環境維權、環境訴訟、媒體曝光等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對污染企業進行道德譴責。再就是公眾更容易接受負面信息,企業一旦產生負面信息不僅會使公眾對企業聲譽和價值產生質疑,引發輿論壓力,而且引致而來的是政府更為嚴苛的環境規制。因此企業會選擇提前考慮公眾的利益,先于政府通過改進工藝或產品創新減少污染行為,迎合消費者需求,樹立公眾形象,以規避輿論壓力帶來的負面效應,維持企業的長期利益與競爭力。另外,公眾參與通過直接或間接對企業施加壓力,將環境責任意識內化在企業經營決策中也可以提高創新積極性(寧金輝,2020)。隨著綠色消費觀念的提升,公眾對綠色產品的需求提高會促使企業進行綠色產品創新。由此可見,公眾參與對污染企業的道德譴責、輿論壓力等隱性約束及綠色觀念的提升對企業的工藝和產品創新產生一定的誘導作用,如圖1 所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1:
公眾參與對綠色工藝或產品創新具有正向影響(H1)。
(二)環境規制與綠色技術創新
企業迫于政府環境規制的施壓,考慮自身長期發展與利益,傾向于通過綠色技術創新,通過生產工藝、設備改造及新產品的研發和制造來形成自身先發優勢,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以期獲得更多的收益來彌補自身所要承擔的污染成本。即用綠色工藝或產品創新帶來的創新“補償效應”彌補企業因“遵循成本”產生的負面影響(圖1)。另外,國家制定和實施環境管制政策,也旨在圍繞原料投入、生產包裝和廢棄物處置等全過程活動,引導和激勵企業積極開展生產工藝流程的改造和升級,通過源頭控制、清潔生產和末端治理等手段,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和排放(王鋒正和郭曉川,2016)。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
環境規制對綠色工藝創新或綠色產品創新具有正向影響(H2)。
(三)公眾參與依賴于環境規制間接影響綠色技術創新
作為第三方力量,公眾參與能夠補充信息、約束權力,完善社會輿論監督,解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和權力不對稱問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由于信息不對稱和“搭便車”帶來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涂正革等,2018)。公眾的輿論壓力和綠色觀念能夠對企業的創新產生積極影響,然而目前公眾雖有獲取環境信息,參與環境決策及環境監督的權力但不具備執法能力,從而無法直接制約企業的生產行為(張輝,2015)。再就是公眾主要是通過投訴上訪或是建言獻策來反饋企業的污染行為,政府部門以這些污染活動為依據進行規制,刺激企業進行綠色產品或工藝創新。因此,在公眾-政府-企業多元共同治理的情況下,政府一方面引導公眾參與事前政策制定,事后反饋監督,另一方面規制污染企業,刺激污染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政府在此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Innes 和Booher,2004)。即公眾通過環保訴求為地方政府提供依據,政府根據公眾需要調整環境規制政策約束企業的排污行為,迫使企業污染成本內部化,刺激企業創新(圖1)。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公眾參與綠色技術創新間接路徑:

圖1 研究機制路徑圖
公眾參與依賴于政府環境規制迫使企業污染成本內部化,進而間接影響企業綠色工藝或產品創新(H3)。
三、研究方法
(一)模型構建
1.公眾參與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基準回歸
針對H1、H2,為了驗證公眾參與與環境規制對綠色工藝創新和綠色產品創新的總效應,構建以下基準模型:

其中:i代表地區;t代表年份;GTI代表綠色技術創新,包括綠色工藝創新(GTIS)和綠色產品創新(GTIP);er代表環境規制強度;pub代表公眾參與;control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νi代表不隨地區變化的地區效應;ηt代表不隨時間變化的時間效應;μit代表隨機擾動項。
2.政府環境規制的中介效應檢驗
為驗證H3,即政府環境規制在公眾參與與綠色產品創新或綠色產品創新之間中介作用。本文在Baron和Kenny(1986)等提出的逐步法的基礎上,借鑒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等的做法進行中介檢驗,檢驗的步驟如下:第一步,計算公眾參與(pub)對綠色技術創新(GTI)的總效應,如果模型(1)回歸系數β1顯著,則進行下一步,否則中介檢驗停止;第二步,依次檢驗方程(3)和方程(4)中的回歸系數λ1和γ2,如果二者都顯著,則表明中介效應檢驗通過,進行第三步;如果有一個不顯著則轉到第四步;第三步,檢驗方程(4)回歸系數γ1,如果該系數顯著且與γ2λ1同號,則存在部分中介效應,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如果γ1不顯著,則屬于完全中介。第四步,進行bootstrap 檢驗,檢驗通過則說明中介檢驗通過,否則中介檢驗不通過。模型設置如下,其中ξit代表隨機擾動項,其余變量同上。

(二)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綠色產品創新(GTIP)和綠色工藝創新(GTIS)。綠色產品創新(GTIP)旨在開發節能環保產品以減少污染排放,是節能減排的終端技術創新,旨在獲得最小的單位產出能耗或最大的單位能耗產出。因此,本文參照張倩(2016)、王鋒正等(2018)的做法,用新產品銷售收入與能源消耗的比值來衡量綠色產品創新,該比值越大,代表綠色產品創新能力越強;綠色工藝創新(GTIS)專注于新技術的研發,主要是指采用更新的生產工藝和設備改造以減少污染的新技術開發,是投入創新和生產過程創新的反應,參照畢克新等(2011)的設定,用技術改造經費投入與R&D經費內部支出來衡量綠色工藝創新,該指標越大越有利于綠色工藝創新。
核心解釋變量——公眾參與(pub)。目前對公眾參與的衡量沒有確定的指標。張志彬(2021)、黃永源和朱晟君(2020)等用百度指數來衡量公眾參與。雖然隨著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高速發展,人們傾向于通過網絡表達自己的訴求,但是網絡信息具有虛假填報,惡意投訴,重復收集等種種弊端。相比而言,我國擁有相對完善的環境信訪的法律和制度,還有真實有效的環保投訴平臺,公眾可以通過上訪上信,電話網絡平臺表達自己的訴求,信訪較網上舉報信息更正式,更具普遍性。因此,本文在占佳和李秀香(2015)、王懷明和王輝(2018)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了一種衡量地區間相對公眾參與的方法pubit=,其中publicit代表i地區t年環境來信與電話投訴之和,E(publicit)代表t年全國各省環境信訪與電話投訴之和的均值,該指標可以反應公眾參與的動態變化,該指標越大,說明其公眾參與度越高,反之公眾參與度越低。
中介變量——環境規制(er)。關于環境規制的衡量,梳理現有文獻可以分以下幾類:一是采用單一指標,以排污費,污染治理投資額,頒布的環境法規數為代表,此外還有部分學者以人均收入作為環境規制的間接指標;二是采用綜合指標法,主流即是用SO2去除率,工業粉塵去除率等多項指標采用熵值法或線性加權法構建指數來反應環境規制強度。但是,單一指標或從成本面衡量,或從效果層面衡量,不能全面衡量環境規制強度。綜合指標雖然比較全面,但由于統計口徑或歸一計算的過程中存在較大誤差。因此本文借鑒Ben Kheder 和Zugravu-Soilita(2008)的方法,用來衡量環境規制強度,他認為該指標可以度量一系列環境法規和規章的真實效果,該指標越大,其地區環境規制越強,其中GDP代表地區生產總值,energy代表地區能源消耗。
為了提高結果的可信度,結合已有研究,本文選取了以下控制變量:人力資本(rd),用R&D 人員全時當量與地區就業人數的比值表示;外商直接投資(fdi),用實際利用外資占地區GDP 的比重表示;對外貿易水平(eo),用地區進出口總額占GDP 的比重表示;經濟發展水平(pgdp),用地區人均GDP 表示;固定資產投資(fa),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占地區GDP 比值表示;產業結構(ind),參照郭然和原毅軍(2020)等的研究,用產業結構層次系數來衡量,具體計算方法為ind=,其中Mijn表示i省份j時期n(n=1,2,3)產業生產總值占該省GDP 的比重。
(三)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2006—2017 年中國30 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由于西藏、港澳臺地區部分數據缺失嚴重,不予考察)。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及國家統計局、各省統計年鑒和各省環境統計公報,并以2006 年為基期對各價格指標進行平減,整理計算可得。同時為消除異方差帶來的影響,對部分變量進行取對數處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
為避免計量模型可能出現的“偽回歸”問題,對各個變量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各變量均為平穩序列;同時為避免多重共線性,用方差膨脹因子對模型進行檢驗,結果發現最大的VIF 為5.64,遠小于1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Hausman 檢驗表明應選用固定效應模型。表2 報告了基準回歸與中介檢驗結果。

表2 基準回歸與中介檢驗結果
(一)公眾參與對企業綠色創新的總效應分析
表2 列(2)和列(6)結果顯示,公眾參與與綠色工藝創新呈顯著正相關,而對綠色產品創新正向影響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我國公眾參與的形式決定的,面對環境問題我國公眾主要是通過上信上訪、網絡、電話等形式進行參與,這些大多是污染事后上訴反饋,投訴問題主要集中于末端治理和清潔技術過程中發生的環境問題,投訴渠道及群眾多集中于后端治理。綠色產品創新作為終端創新,短時間完成創新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伴隨的引致成本較工藝創新更高,同時,公眾綠色消費觀念雖有所加深,但覆蓋面較窄,對綠色產品的認知和接受度不高,難以對企業綠色產品創新形成驅力。因此企業傾向于運用綠色工藝創新來解決公眾投訴反饋的環境問題。
表2 列(1)和列(5)顯示無論是綠色工藝創新還是綠色產品創新,政府環境規制對其都呈顯著正相關,支持了本文的H2。說明政府的環境規制越強,越能夠激發企業綠色創新的積極性。強有力的環境規制會向企業發出環境保護的信號,企業為了彌補環境規制所帶來的遵循成本,會遏制污染物的產生。通過增加技術改造經費來改造或研發自身的工藝設備,以期達到政府環境規制的要求,同時企業會通過減少單位產品的能耗來降低對環境的負外部性,進而增加了企業綠色產品創新的活力。
對于控制變量而言,人力資本,固定資產投資和產業結構調整對綠色工藝創新均產生了顯著的正向作用。外商直接投資,經濟發展水平對綠色工藝創新產生了負面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會使傳統工藝被新工藝取代,再加上國內創新能力較弱,使得企業只能被迫接受或面臨淘汰,這導致企業再加大經費投入工藝技術改造的積極性也可能不會提高。人力資本對于綠色產品創新也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資對綠色產品創新的影響呈現與綠色工藝創新相反的效果,呈顯著正相關。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為我國企業帶來新的設備、技術、制度和管理經驗,為產品創新提供了條件和方向,同時外商先進的產品會刺激國內廠商,進而通過產品創新提高自身競爭力。再就是外商直接投資會擠占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而加劇競爭,為此企業會加快產品創新效率。
(二)政府環境規制的中介作用檢驗
表2 同時報告了以政府環境規制為路徑的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列(2)結果顯示,公眾參與可以顯著促進企業進行綠色工藝創新;列(3)結果顯示公眾參與與政府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列(4)在同時加入環境規制和公眾參與的情況下,公眾參與和環境規制顯著促進綠色工藝創新。依據上文敘述的中介效應檢驗機制說明:政府環境規制在公眾參與與綠色工藝創新之間發揮了部分中介的作用。這驗證了公眾參與綠色工藝創新的間接路徑,公眾參與可以通過引致更強的環境規制來間接達到促進綠色工藝創新的目的。
但是,表2 列(6)顯示公眾參與對綠色產品創新的作用并不顯著,據上文敘述的中介效應檢驗機制說明:政府環境規制在公眾參與與綠色產品創新之間并沒有起到中介作用。原因可能是:公眾參與提高政府環境規制的效果有限,由列(7)所示,公眾參與對環境規制的影響系數僅為0.006。綠色產品創新會導致新的消費和投資熱點,較綠色工藝創新更難實現,同時綠色新產品與現行其他產品的非兼容性,需要較高的成本來磨合,公眾參與強化的環境規制難以對綠色產品創新形成較強的驅動作用。
(三)異質性分析
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異,2017 年北京的人均GDP 為128994 元,而甘肅僅為28496 元。同樣地公眾參與度也存在較大差異,如圖2 所 示,2006 年、2012 年和2017 年我國公眾參與高的地區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區,總體而言大都位于“胡煥庸線”右側區域,地區間公眾參與度呈現出顯著差異。對比2006 年,2012 年、2017 年的公眾參與度分布更加均勻,中部地區山西、河南上升較快。

圖2 不同省份公眾參與度
基于此,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公眾參與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是否存在異質性?公眾參與的度高低會不會對綠色技術創新有著不同的影響,不同公眾參與度下“波特效應”是否存在差異?解答這些問題可以進一步研究和把握變量之間的作用關系。因此,文章首先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進行樣本分組,以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值35766 元為界,將研究區域劃分為經濟較發達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①較發達地區:上海、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廣東、內蒙古、福建、山東、遼寧、吉林、重慶;其余地區為欠發達地區。深入探討公眾參與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異質性影響,其次本文將公眾參與強度均值大于1的劃為高公眾參與的地區,均值小于1 的劃為低公眾參與的地區進行分組回歸②高公眾參與度地區:北京、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南、廣東、廣西、重慶、四川、陜西;其余地區為低公眾參與度地區。,以此來探討不同公眾參與強度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差異及不同公眾參與度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差異。根據劃分結果顯示,高公眾參與地區與經濟較發達地區高度重合,原因可能是經濟較發達地區受教育水平和人均收入引致而來對環境質量的需求較經濟欠發達地區更多。因此其公眾參與的程度也較高。表3 報告了異質性分析的結果。

表3 異質性分析
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公眾參與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呈現出顯著的區域異質性。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其公眾參與與綠色工藝創新呈顯著正相關,而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公眾參與對于綠色工藝創新的作用并不顯著。原因可能在于經濟較發達地區由于經濟高強度的發展會帶來更多的人企矛盾,公眾的輿論壓力,以及對于環境質量的訴求也會高于欠發達地區,其公眾對企業的壓力程度較欠發達地區更大,更容易迫使企業進行綠色工藝創新;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公眾參與機制與渠道不夠健全,導致公眾參與程度普遍偏低,難以對綠色工藝創新形成“驅動效應”;無論經濟較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其公眾參與對于企業產品創新都沒有明顯的作用,此結論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
公眾參與程度異質性。由于地區公眾參與程度的不同,公眾參與對企業綠色工藝創新的影響也呈現出顯著差異。公眾參與越高,其對企業綠色工藝創新的作用越明顯。同樣地無論是高公眾參與度地區還是低公眾參與度地區,其公眾參與對企業綠色產品創新都沒有顯著的作用。此外,表3 的列(5)和列(6)的結果表明,在高公眾參與的地區,環境規制對綠色工藝創新和綠色產品創新均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列(7)和列(8)結果表明,在低公眾參與的地區,環境規制對綠色工藝創新影響不顯著。雖然低公眾參與度的地區環境規制對綠色產品創新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相較于高公眾參與度的地區,其促進程度要小(0.646<0.752)。因此,公眾參與度越高的地區,其波特效應就越強。公眾參與度越高,環境規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被監督的越多,企業在嚴苛的環境規制下更容易加大對創新的投入,同樣,企業在嚴苛的環境規制下也會減少單位產品能耗,加強綠色產品創新效率。
(四)內生性與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檢驗
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雙向因果關系是造成計量模型內生性的一個重要原因。內生性的存在會導致結果有偏且不一致。公眾環境參與和政府環境規制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同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區域污染程度,從而影響公眾的參與強度和政府環境規制,即公眾參與和環境規制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可能具有雙向因果關系,同樣地,公眾參與與環境規制之間可能會存在雙向因果關系。雖然文章采用了控制時間和省份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遺漏變量的問題,我們也盡可能控制了其他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因素,但仍可能忽略了一些其他影響因素,變量的測量誤差也可能導致內生性的存在。對此本文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來控制可能出現的內生性問題,將公眾參與、環境規制看作內生變量,使用滯后一期值或二期值作為工具變量對模型進行估計。滯后期的公眾參與、環境規制是前定的,當期綠色技術創新不與其存在反向因果關系。模型估計結果見表4,工具變量內生性檢驗K-P rk LM 統計量及相關性檢驗C-D WaldF統計量均顯著拒絕原假設,說明本文所選擇的工具變量在統計上滿足工具變量選擇要求。公眾參與仍可以顯著促進綠色工藝創新,對綠色產品創新的效果不顯著。這與前的研究結論保持一致,排除了內生性問題對實證結果的干擾。

表4 2SLS 估計結果
2.穩健性檢驗
排除奇異值。為減輕異常值對研究結果的干擾,本文對主要解釋變量進行了1%分位數以下99%分位數以上縮尾處理,再次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5 中列(1)~列(4),結果顯示經縮尾處理后主要解釋變量的系數均有提高。因此上文的結果是可靠的。
替換核心解釋變量。本文用環境來信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的比值(rpub)作為公眾參與(pub)的替代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該指標既可以反應公眾參與的絕對量,同時也剔除由于企業規模導致的參與程度偏誤。表5 中列(5)~列(8)報告了該結果,可以看出結果與上文研究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再次驗證了上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表5 穩健性檢驗
五、基于空間效應的進一步討論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公眾參與一方面可以通過輿論道德壓力等隱性約束迫使企業進行綠色工藝創新;另一方面依賴政府對企業進行規制迫使其污染成本內部化間接影響綠色工藝創新。在區域間經濟活動日益頻繁的情況下,公眾參與對一個地區企業形成的隱性約束可能會通過人員流動、信息溢出等傳播到其他地區,對其他地區產生“警示效應”,其他地區通過模仿該地區企業預先進行綠色技術創新,以此來規避隱性約束帶來的負面影響。本文進一步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進行驗證。
(一)空間計量模型設定
本文重點關注公眾參與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空間溢出效應,不僅考慮本地區公眾參與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同時還要考察鄰近區域公眾參與對本區域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空間杜賓模型(SDM)相較于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滯后模型(SLM)更能捕捉各類溢出效應,更具一般性。通過Moran’sI檢驗發現綠色工藝和產品創新的主要變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通過LM 檢驗發現綠色工藝創新選用SDM 模型較為合適而綠色產品創新選用SLM 較為合適。綠色工藝創新的Wald 檢驗和LR 檢驗均拒絕原假設。因此用SDM 模型對綠色工藝創新進行回歸。同樣地,綠色產品創新的Wald 檢驗和LR 檢驗也拒絕了原假設。因此選用SDM模型對綠色產品創新進行回歸比較合適。綜上,本文選擇采用固定效應空間杜賓模型對綠色工藝或產品創新進行回歸。
空間杜賓模型設置如下:

其中:W為空間權重矩陣;其余變量同上;Wpubit為公眾參與的空間滯后項;Wlnerit為政府環境規制的空間滯后項;Wlncontrol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的空間滯后項;εit為隨機擾動項。
由于公眾參與和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較大,而經濟距離矩陣正好刻畫了兩個地區的經濟差異大小。因此本文使用空間經濟距離矩陣進行回歸分析,矩陣具體設定如下:

其中:Gi表示i地區2006—2017 年人均GDP 的均值;Gj表示j地區2006—2017 年人均GDP 的均值。在矩陣中,人均GDP 均值差距越小,該元素就越大,兩地區在經濟上越“接近”。
(二)回歸結果分析
表6 列(1)和列(2)報告了公眾參與對綠色工藝創新和綠色產品創新的SDM 回歸結果。

表6 SDM 回歸結果
表6 結果顯示綠色工藝創新的空間相關系數ρ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0.215),表明存在綠色工藝創新正向溢出;而綠色產品創新的空間相關系數ρ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負(-0.197),表明存在綠色產品創新負向溢出。根據經濟距離矩陣定義表述,工藝創新溢出僅存在經濟差距較小的區域。這可能是由于經濟差距較小的區間具有相似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其地區間的技術工藝交流更加頻繁;綠色產品創新對經濟差距較小的周邊地區產生負向溢出的原因可能是一個地區的產品創新帶來的潛在優勢會產生“虹吸效應”,吸引經濟差距較小區域的人力資本,同時會壓縮其地區的產品市場,從而不利于其他經濟差異較小地區的產品創新。同樣經濟相似區域通過引進產品的模式也不利于企業綠色產品創新。
表6 列(1)公眾參與的空間交互效應顯著為正,表明區域內企業綠色工藝創新受經濟差距較小的其他地區公眾參與的正向影響。此外與表2 列(4)和列(8)結果相比,表6 中核心解釋變量公眾參與和環境規制對綠色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的效果沒有發生變化。進一步表明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當存在空間溢出效應時某個影響因素的變化不僅會使本地綠色技術創新變化,同時也會對鄰近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影響,并通過循環反饋作用引起一系列的變化調整。因此,本文利用Lesage 和Pace(2009)提出的方法將存在空間效應的各因素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直接效應表示本地公眾參與對本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其包含了空間反饋效應,即本地區公眾參與通過影響鄰近地區綠色技術創新,鄰近地區綠色技術創新反過來影響本地創新這一循環往復過程:間接效應表示本地公眾參與對鄰近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總效應在數值上等于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之和。空間分解結果見表7。

表7 各自變量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與總效應
從直接效應來看,公眾參與對綠色工藝創新的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公眾參與顯著提升了本地區的綠色工藝創新能力。且與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相比,SDM 模型中公眾參與對綠色工藝創新的直接效應更大,說明固定效應模型由于沒有考慮空間效應而低估了公眾參與的直接效應。公眾參與對綠色產品創新的直接效應不顯著,這與上文的研究一致。
從溢出效應(間接效應)來看,公眾參與對企業的綠色工藝創新的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公眾參與對經濟差距較小的其他區域產生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由于經濟差距較小的區域之間產業結構及技術結構的相似,公眾的道德譴責和輿論壓力對本地區企業產生震懾作用的同時,容易通過信息溢出對其他具有相似結構的區域產生引致作用,促使其他地區企業預先通過綠色工藝創新減少輿論壓力帶來的負面效果。公眾參與對企業綠色產品創新的間接效應為正但不顯著,說明公眾參與的提高對經濟差異較小的其他區域綠色產品創新的作用效果并不明顯。這可能是由于通過目前主要的公眾參與形式不能很好地表達公眾的綠色消費觀念來引導企業通過終端技術創新來彌補企業的“遵循成本”。同時由于綠色產品創新兼顧經濟與環境,高成本的特性,企業難以用綠色產品創新來彌補環境污染成本。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綠色技術創新依然是實現環境與經濟雙贏的最強有力手段,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問題依然亟待解決。本文基于公眾參與具有解決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獨特優勢,分析了公眾參與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理論基礎和實現途徑,把公眾-政府-企業三方納入同一框架,利用中介模型和空間計量模型對2006—2017 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結論:①公眾參與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綠色工藝創新能力,而對綠色產品創新的效果不太明顯。說明通過信訪、網絡電話形式的公眾參與主要對費用較低的,通過技術更新和設備改造減少污染的綠色工藝創新有提升效果,對成本較高的終端技術創新綠色產品創新的效果不太明顯;②公眾參與依賴于政府環境規制迫使企業污染成本內部化,進而間接影響企業綠色工藝創新;③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公眾參與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綠色工藝創新,而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公眾參與對綠色工藝創新的效果并不顯著。此外,無論經濟較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公眾參與對企業綠色產品創新都沒有顯著的影響;④公眾參與度越高的地區,其政府環境規制對綠色工藝創新或產品創新的正向促進效果越明顯,即“波特效應”越強;⑤在經濟距離矩陣下,綠色工藝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空間相關性,綠色產品創新卻呈現出負向空間溢出。本地公眾參與對本地綠色工藝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對周邊經濟差距較小的地區也具有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根據主要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加強企業信息披露,擴大公眾參與途徑。研究表明,以環境信訪,電話投訴為代表的公眾參與有助于提升聚焦于生產工藝的設備改造與升級的綠色工藝創新。因此政府應完善公眾參與機制,縮減參與成本,約束企業建立更加透明、公開的信息披露機制,以便公眾可以第一時間把握企業的環境行為及時監督,反應問題。同時鑒于我國公眾參與渠道較為單一,須通過依托互聯網大數據的優勢開拓更多的公眾參與渠道,建立多種事前事后的監督渠道,與此同時優化網絡參與環境,制定網絡參與的相關規定,減少虛假惡意參與的產生,充分發揮公眾的優勢。
第二,政府作為連接公眾和企業橋梁,一方面應根據公眾反應做出及時的調整,設置最優的環境政策;另一方面應對企業秉公執法,設置適合區域長遠利益和可持續發展的官員考核機制。同時加大政府間信息公開,杜絕環保腐敗,政企合謀等情況的發生。
第三,縮小地區間經濟差距。研究表明經濟差異阻礙了公眾參與的有效性和正向溢出性。實行差異化的公眾參與政策,較發達地區進一步下放公眾參與的權力,充分發揮其經濟優勢,技術優勢及人才優勢,提高公眾參與效率,最大化公眾參與的作用,經濟欠發達地區政府應加大政策支持,健全公眾參與機制,同時加大經濟薄弱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基礎設施投資,促進其資本積累,縮小與經濟發達地區的差距。經濟薄弱的地區應依托優勢產業,重構自身貿易定位,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帶來的便利條件,縮小經濟差距,充分發揮公眾參與對綠色創新的助推作用。鑒于公眾參與本身的外溢性,應推動跨區域交流合作,推出公眾參與“標桿城市”,充分發揮區域之間的聯動性和示范性,加強公眾參與政策間的相互溝通與協調,進一步提高公眾參與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