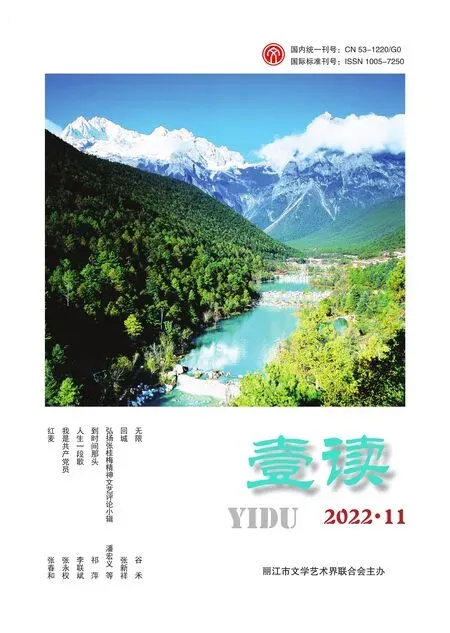人生一段歌
◆李聯斌
恢復高考的第3年,也就是1979年,全國高考錄取率不到6%,大多數考生未能如愿擠上“獨木橋”,而在麻栗坡縣八布中學高中畢業的我,不幸也在其中。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臨待業、復讀、當兵等選擇。當時我像泄了氣的皮球,情緒低落,心里茫然,不知未來的人生與命運將會如何。
時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改革開放的大幕已經拉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制度已經停止,國家的建設與發展亟需人才與人力,而各條戰線的干部職工隊伍又青黃不接。在這樣的背景下,9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去縣里參加分工的通知,猶如白日好夢來襲,心中的喜悅無以言表。我們那批分工的達90人之多,縣人事局長在會上講完話之后宣布了分工名單。有的分到黨政部門,有的分到金融系統,有的分到商業系統,有的分到公路系統,有的分到鄉村學校,我等6人則分到縣廣播站。分到工作的每個人,臉上笑容都發自內心,慶幸趕上了好時代,黨的陽光暖到了心里。
分工會結束后,我依然帶著喜悅,跟著帶路人來到了縣廣播站。不曾想到,這一來,就在廣播站工作了整整5年。5年時間,在人生歷程中雖不算長,而我這5年時光,卻如人生一段歌。
這一年,我剛好16歲,一時難以適應工作身份的轉變。天真無知的我,就像一個匆忙上車的旅客,手忙腳亂,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單位里,不時向“大人們”問這問那,都是些不著邊際、無關痛癢的話題,偶爾會因自己的幼稚輕浮引來大家的發笑。我不時在單位旁邊的小廣場上跑去跑來、玩耍打跳,一點不像工作人員的樣子。一次,我跳上用于架設廣播線的絞線機上劇烈搖玩,不小心踩滑跌倒,機柄戳到我的大腿,疼痛難忍,滾在地上,半天沒能爬起來,當時我就罵自己,都是“少年黑發不知愁”惹來的禍。從那以后,我慢慢學會收斂,規矩了許多,不再亂跑亂跳。
我一直在中越邊境農村長大,從未出過遠門、沒見過世面,工作了來到縣城,頓覺陌生而又新鮮。出于好奇,有空我就東游西逛、找人閑聊,并借助于縣志,對麻栗坡縣及這座縣城的自然和歷史人文有了些了解。
麻栗坡縣地處祖國西南邊陲,位于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東南部,東西長100公里、南北長40公里,東西北部與州內其他5個縣相連,南部與越南河江省的“五縣一市”接壤,國境線長227公里。當時全縣有12個公社,大約14萬人,壯、苗、瑤、傣、仡佬等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38%。
縣份雖小,位置卻很重要,歷史也算久遠。早在新石器時期就有人類繁衍生息,西漢時期納入祖國版圖,之后歷朝歷代都為邊境要塞。光緒年間,設麻栗坡為副督辦,直隸于省。1914年(民國3年),改副督辦為對汛正督辦,第二年又改設為省轄特別區,又過了兩年即1917年,改稱為特別行政區對汛督辦。1949年3月,全縣解放,廢除對汛督辦特別行政區建制,成立縣人民政府。
縣城因地勢山高坡陡、環山多有麻栗樹而得名。縣城不大,也就兩萬來人。房屋依山而建,稱得上街道的就兩條,一條是老街,建在一條狹長的斜坡上,早先的對汛督辦設置于街頭,算是縣城的制高點,街道兩側主要是民居,街尾右側是縣電影院和籃球場,左側為縣一中;另一條為沿河街,因前些年縣城人口增多而新設,兩旁主要是縣級相關部門辦公樓。“麻栗坡,山大石頭多、出門就爬坡”,是其最大的特點。幸好上蒼給這個“夾皮溝”式的縣城賞賜了兩條河,一條叫疇陽河,在城中蜿蜒穿流,還有一條叫小河,從城邊山腳洞中流出,匯入疇陽河跨境流向越南。碧波蕩漾、清澈見底的大小兩條河流,給這座邊城增添了不少靈氣、帶來生機。
小河出水口名叫小河洞,高2米、寬8米、長千米以上。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省有關部門的專家在洞內清理發掘,出土有石斧、石刀、石錛、石印模和印紋陶片等物,這是滇東南地區首次發現的距今四千年前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繁衍生息的遺址。我曾多次出入,探尋、感悟祖先們生活的蹤跡,敬仰祖先們的生存智慧與能力。聽好多人都說,縣城東郊的大王巖巖畫很古老,于是,在一天下午,我獨自一人,沿著崎嶇山路,蹣跚而行,爬到巖腳,慕名探訪。巖畫在一座叫羊角腦山的石壁上,由于年代過于久遠,又受巖漿侵蝕、自然風化,看上去已不清晰,只能看到由紅、黑、白等色彩繪制的圖形。過后我查看專家考證結果得知,巖畫可辯圖像25個,其中人物11個、牛3頭、小動物2只,還有其他圖案。畫面完整,為新石器時代巖畫作品,迄今大約4千余年。后來我又多次去觀仰巖畫,贊嘆不已,反復猜想,也許這就是當時居于小河洞內祖先們留下的珍跡。再后來,它被國際巖畫學界譽為“代表著一種巨大的原始創造力”的巖畫,為國務院批準公布的第七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縣委會坐落在疇陽河東岸,而縣廣播站則在縣委圍墻內的東北角,準確點說,房子是蓋在一個旮旯里。我清楚地記得,縣廣播站也就十四、五個人,加上我們新來的,也就20多人。全站就一幢長型小樓房,白墻青瓦人字木頂兩層樓,橫面有門、中有通道,兩層總共20間,每間不過20平方。這幢房子,既是辦公室又是宿舍,其中一樓有2間連通為廣播室、另有2間為辦公室,樓上2間為倉庫堆放廣播器材,其余就是宿舍。
當時我就在想,這是什么單位啊,房子又小、職工又少,我們幾個剛來的人,吃在哪住在哪恐怕都成問題。好在站里早就把吃的問題協調解決好了,就在縣委食堂搭伙。住的嘛,安排在縣中波發射臺籌建處的簡易房。籌建處離縣城不遠,在一座名叫彎擔坡的山頂上。男的自帶行李住二樓,女的住一樓。白天到站里學習工作,晚飯后各自回來住宿,一天上下要跑兩三趟。住下不幾天,我觀察了周邊環境,工地左邊有片冬瓜林,下有溝壑,壑中有溪,潺潺流淌;右邊有個大山凹,旁邊有個小山包,上面長著棵大榕樹。
住在山上的感覺真好,朝看東升旭日,暮看西邊霞姿,夜聽鳥啼蟲鳴,空氣清新、帶著甜味。還可進入樹林中,靜聽音樂般的流水聲,或坐在榕樹下,鳥瞰縣城全貌,盡賞四周山水,給人一種身在塵世外、心若閑云飄的感覺。只是冬天難在一些,天氣陰冷、山風呼號、雨打樹林,夜里時而會被刺骨寒風吹醒。至今我還忘不了,住在簡易房的那些日子。
開初,站里并沒安排具體工作,主要組織我們學習,既學時事政治、又學業務知識和技術。站長多次給我們講解廣播室機房全套設備的功能和使用,包括調頻機、功放機以及話筒、電唱機、磁帶錄音機等設備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術、簡單故障排除方法。副站長主要講無線電的基本原理和收音機的修理技術。有一個分來不久的大學生,主要講收錄機的原理及其集成電路、檢修方法。還有一些工作老道的同志,主講有線廣播線路的架設和維護、各種喇叭的連接安裝和修理等實用技術。為了讓我們從理論和實踐上掌握基本知識,站里買來相關書籍和檢測儀表、修理工具發到各人手上,要求我們抓緊自學。
這些技術設備和書籍,以前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還真來了興趣。在家時常聽老人們講,“天干餓不死手藝人”,當時我就一直在想,分來廣播站,算是來對了,要倍加珍惜,學會這些技術,即便沒了工作,也可在社會上混碗飯吃。所以,師傅講解,我專心聽、認真記、主動學,有事無事也跟在師傅后面轉,目的就是想多學點技術,以防日后不測。
那段時間,免不了要我們做些臨時性工作。比如,哪段廣播線路出問題、信號送不出去了,就去突擊搶修、排除故障。因為才來不久,我只能給師傅們拉拉鐵絲、遞遞工具。有一次,要將城郊廣播線路的木電桿換成水泥電桿,站里職工全動員、齊上陣,有的拉線、有的挖洞、有的抬桿。水泥電桿又粗又長又重,要從公路邊順著小路抬到山坡上栽起來,一次抬桿需要8人,其中前后端各2人、中端4人。我參加抬桿,在后端,橫杠放在肩上剛邁出幾步,因年少體力不支,突感眼冒金星支撐不住,站長立即叫停,我被換下,由于用力過猛,臉上發青半天緩不過氣來。過了2個多小時,抬到了目的地,大家七手八腳把事先裝有瓷瓶的橫檔安在電桿頂端,再把桿子栽入洞中。一個師傅動作嫻熟,腰系安全帶、腳踏鐵扣、肩杠鐵線,爬到桿頂,把鐵線安置在瓷瓶上,另外的同志用絞線機把線絞緊,最后測試廣播信號,確認能夠傳輸,才算完工。
縣廣播站為縣委宣傳部直管(當時未設縣廣電局),下屬12個公社廣播站,主要任務是放廣播、架設維護有線廣播線路,籌建縣中波發射臺和電視差轉臺,管理全縣廣播工作人員隊伍。與此同時,縣委宣傳部還布置了一項重要任務,那就是要縣廣播站開辦自辦節目。面對新老任務,站領導研究后給我們作了崗位分工,有的到中波發射臺,有的籌備縣電視差轉臺,有的安排到外線組。而我,則安排在廣播室,做新聞采編、開辦自辦節目。
面對崗位分工,我壓根兒就沒想過,新聞咋寫、采訪咋搞、節目咋編,我連一點最基本的概念都沒有,當時心里很矛盾、顧慮重重。一來搞技術是手藝,何時何地都需要,而且越老越吃香,開初學技術、做技術工作的想法泡了湯;二來編自辦節目、搞文字工作,政治性強、責任重大,一不小心還容易犯錯誤;再則還得離開已經適應的山頂環境,有些不舍。后經領導點撥,我忽然醒悟,這是在單位不是在家里,還得服從組織的安排。沒有誰生下來就會做事,不會就要學,人的潛能都是通過學習釋放出來的。于是,我再沒多想,搬宿舍、學業務、編節目,一切從零開始,當起了“小編輯”、“土記者”。
當時不曾想過,那樣的分工,賦予了我生命不同的意義,影響了我人生的走向。后來,我被調到縣、州、省的一些部門工作,都與在廣播站的這段工作經歷緊密關聯。更想不到的是,25年后,峰回路轉,我調到省委宣傳部門工作,直到今天。
那個年代,全黨工作重心已經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改革開放的號角,催人奮進,各行各業你追我趕,都在爭著把“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為祖國“四化”多作貢獻。那時的年輕人,充滿朝氣、充滿活力,以“80年代新雷鋒”張海迪為榜樣,進取奉獻是青春最美的狀態,“創造奇跡要靠我們80年代的新一輩”是那一代青年的標識。可像我這樣的人,在學校又沒學到多少文化知識、在單位又沒工作基礎,面對時代召喚,我反復追問自己,拿什么來為“四化”作貢獻呢?總不能碌碌無為、虛度年華吧!受時代精神的熏陶,我不斷告誡自己,唯有加緊學習,才能跟上時代、做好工作,不負青春好年華。
邊工作、邊學習成了平常,書籍成了好朋友。已記不清,有多少個夜晚,我守住孤獨、忍耐寂寞,卯足勁頭學習。黨的基本知識和時事政策成為必學內容,它能幫助我在工作中不偏航、不走調。我曾仔細研讀《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云南日報》一、二版頭條新聞,分析其內容、結構和語言表述方式,力圖快速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同時,自學《新聞記者入門》(孫世愷著)、《采訪與寫作》(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主編)、《新聞采訪方法論》(艾豐著)及《新聞報道與寫作》(美國麥爾文·曼切爾著,廣播出版社出版)等書籍,對新聞特點、要素、寫作基本要求和采訪基本方法、以及如何增強新聞敏感、識別新聞價值、提煉新聞主題等有了大致了解。還自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韓樹英主編)、《文學的基本原理》(以群主編)等書籍,逐步擴展知識。只要有機會,站領導也支持我參加相關培訓。記得在1980年參加縣里舉辦為期3個月的寫作培訓班時,我將記敘文六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情起因、經過、結果)與新聞五個“W”(何時、何地、何事、何因、何人)作了對比,發現二者寫作雖有不同,但基本要求大體相似,慢慢消除了采寫新聞心理障礙。之后也參加過省、州舉辦的一些業務培訓。
心里有了點底氣,我就大著膽子外出采訪。值得慶幸的是,采寫的第一條新聞《豆豉店大隊購銷店承包給個人經營成效明顯》被上級主要媒體采用,給我增添了工作信心與激情。隨后幾年,我在完成自辦節目編輯的同時,不斷到基層和群眾中采寫新聞,除在自辦節目中播出外,省州主要新聞媒體也采用刊播了不少。
1984年4月28日收復老山戰役打響前3天,縣委安排我陪同一名副縣長到老山腳下的猛硐至磨刀石一帶,看望配屬部隊作戰的民工民馬連。當時,縣委和縣武裝部組織了3個民工連、4個民馬連,安扎在不同的指定位置。我同副縣長一個連一個連地走訪慰問,再次進行戰前動員,并及時協調解決生活、擔架、馬料等實際困難。這批民工民馬連在參戰中運送彈藥到位、搶救傷員神速、表現英勇頑強,出色完成配屬作戰任務,為勝利立下汗馬功勞。隨后我寫的新聞報道被刊發在省報刊上。
那幾年,我采訪了不少當地群眾支前參戰、軍民共建的典型事跡,參戰軍民共同培育的“老山精神”,深深教育了我,切身感到,國家若不安寧,哪來家庭的安寧。以愛國奉獻為核心、以不怕苦、不怕死、不怕虧為主要內容的“老山精神”,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如今,“老山精神萬歲”的主題雕塑,依然聳立在老山主峰。
當時廣播室就3人,每天按規定廣播3次,早晨6:20開播,8點結束;中午11:50開播,13點結束;晚上17:50開播,20點結束。開頭都是用電唱機播放歌曲《歌唱祖國》,隨后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少年兒童節目》和云南人民廣播電臺《云南新聞》《對農村廣播》等節目,晚上18:30插播《自辦節目》,中間用電唱機插播群眾喜愛的歌曲, 19:50播送縣氣象站提供的《天氣預報》。另外,還按要求錄播有關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律法規以及農業科技等知識,播出涉及人民群眾工作、生產、生活的內容。每天每次播出的節目內容,都要進行規范登記、歸檔。
我們辦自辦節目要求嚴格、態度認真,但有時也會出現疏漏。有天晚上,我們的《自辦節目》還沒播完,縣委宣傳部分管副部長急匆匆跑來廣播室,指出剛才播出的一則消息,廣播員把我邊防偵察小分隊“邊打邊撤”的“撤”讀成“散”,意思完全變了,嚴厲地批評我們。我快速核對邊防守軍通訊員采寫的稿子,確定是讀錯了。那一瞬間,我們無地自容。問題嚴重、教訓深刻,我們作了檢討。從那以后,播音員在錄制節目時,對拿不準讀音的字,都會先查字典,我在審聽時,增加了次數,嚴防類似問題再次發生。
那個年代的有線廣播,是黨委宣傳、發動、組織、教育群眾的主要工具,在促進農村改革、包產到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豐富群眾文娛生活、推進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干部群眾聽廣播也成為一種習慣,偶爾停電、聽不到廣播聲,一些聽眾會打電話尋問,我們得耐心解釋、說明。有的覺得哪首歌曲好聽,也會打電話來要求安排再次播放。《自辦節目》受到歡迎,有的聽眾還積極爭當業余通訊員,踴躍采寫廣播稿、提供相關宣傳材料。我們順勢而為,發展、培訓了上百人的通訊員隊伍,新聞稿件源源不斷。我們的自辦節目,越辦越紅火。
我在學習工作中的點點進步,得到相關領導和同志們的認可與支持,縣里開展專項性工作,也常“點”我參加,讓我從中得到不少鍛煉和提高。1981年,我參加縣委小分隊到基層宣傳黨的農村政策,我按分工要求,搜集整理資料、編成宣傳節目送審后,讓廣播員錄制好節目,帶著廣播器材,跟隨小分隊到各個公社,利用街子天巡回宣傳。廣播器材就擺放在露天,不少趕街群眾圍坐靜聽廣播的聲音。1982年,大坪公社廣播員休產假,派我去頂崗。在半年多時間里,除了放廣播、維護線路外,還要完成公社黨委交辦的臨時性任務。秋收后,有個生產隊遲遲未交公糧。一天中午廣播結束剛關機,黨委書記要我跟他去這個村催公糧。我陪他坐在隊長家火塘邊,邊吃刨花生、邊喝包谷酒、邊拉家常,書記只是偶爾提及公糧一事。第二天我去公社糧管所察看,結果有8張小馬車在排隊交公糧,一問都是那個隊的,我暗自佩服書記的工作方法,跟他學得了做群眾工作的一招。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召開后,縣委組織相關人員到農村開展宣講,我被抽去與縣委宣傳部和黨校的同志一個組,到地處中越邊境的董干公社馬崩大隊村寨宣講。當時農村已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白天群眾下地干活,晚上才便于集中,我們每天都要到夜里十一、二點才宣講結束。到苗族村寨,由黨校的老師用苗語宣講,到了漢族村寨,則由宣傳部的同志或我宣講。在宣講時,我都會留心觀察,現場秩序井然、鴉雀無聲,忙活一天的村民們,身上還帶著田地里的氣息,可每個人的精神都很飽滿、聽講的神情十分專注,我仿佛感受到,群眾對國家大事的關心和急需得到致富政策的迫切心情。
在工作與生活的交往中,站里新、老同志從不認識到熟悉,從同事到朋友,在生活上相互關心、學習上相互幫助、工作上相互支持、接人待物上相互理解,人際間沒有虛情假意,也沒有爾虞我詐、勾心斗角,關系融洽、相處和諧,全站就像個大家庭。
有個同事,大我一歲,在山頂簡易房二樓居住時,3個男生打的是通鋪,我在左邊,他在中間,另一個在右邊。他的理科知識比我好,聽不懂、看不會的無線電知識,我常常請教于他,他則不厭其煩地給我講解。他家就在縣委,不時帶我到家里做客。他還備有一套理發工具,頭發長了幫我理。有時工資接不上趟,他也會解囊相助。我們的關系日益密切,親如兄弟。我從山頭上搬到廣播站時,曾與一同事同室住了一段時間。他當過回鄉知青、在過縣委農村工作隊,3年前到了縣廣播站,主要搞外線。他大我10歲,起初我叫他叔叔,沒過幾天,讓我叫他大哥,就一直叫到了今天。他雖只是初中生,但看上去文質彬彬,待人接物都很得體。從他身上,我學會了一些做人的社會知識。只可惜,他因家在農村,一直沒談上對象,好在不久前天保農場職工因戰撤進縣城,有一年輕漂亮的女職工看上了他,一年后組建了家庭。
站里的領導都是搞技術的,他們對同志很和善,大家也愿意接近他們。站長個子不高、40來歲,性格不溫也不火。他的辦公室桌上擺滿各式各樣的破舊收音機和修理工具,我常去看他修理。一個沒有任何聲響的收音機,經他用起子左敲敲、右敲敲,再焊一烙鐵,然后打開開關,就有了聲音。我覺得他技術高超,對他尊重敬佩有加。我們幾個年輕人,不時受邀到他家蹭飯、小酌。
年輕人愛熱鬧、愛交流。有一段時間,我們幾個單身漢學會了“打拼東”(類似于AA制)。到了周末,為湊熱鬧、解嘴饞、過酒癮,我們商議,你打酒、他打飯、我買菜,聚在一間宿舍,飯菜擺在地板上,喝開水的玻璃杯當酒杯,有的坐著、有的蹲著,邊吃邊聊,工作上的事、生活上的事,愉快的事、煩心的事,天大的事、雞毛蒜皮的事,無可不說。當時大家的工資都很低,頭年試用期就29塊半,還加上了2塊糧價補貼,一年轉正后也就39塊半,可到“打拼東”時,似乎都忘了節約,只想多打點菜飯和酒水,好讓大家交流個痛快。后來,“打拼東”改為“輪流坐莊”,這個周末我負責,下個周末你安排,再往后是他準備,大家爭先恐后,不亦樂乎。
多年以后,雖然有的同志調到不同地方、不同單位工作生活,但心里都有著那份惦記。
最初的愛戀如此美妙而又青澀無果,就像一篇有了激情而又沒有動手寫成的文章。我來到廣播室,與兩個女廣播員成為同事,其中一個工作了3年,我們都叫她“大姐”,另一個與我同批分配進來,因她音質較好、普通話說得相對標準,之前就安排做了廣播員。編、錄、審、播自辦節目,以及值守廣播室等工作,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與我同時分進的廣播員,在縣城長大、畢業于縣一中,那時正值花季年齡,不僅聲音甜美、做事靈巧,而且身姿婀娜,面色桃紅,臉上常露微笑,還有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自辦節目的編排,需要一起商量確定,錄音節目的審聽修改,需要相互協作,邊聽邊改。縣里召開大會,站里也常安排我們倆去搞廣播服務。商量工作所見略同,遇到問題見解一致,工作中的配合默契而順暢。如此一來,工作也就常常在輕松、愉快、和諧的氣氛中完成。
忙完工作,我們也常在廣播室一起欣賞音樂。比如李谷一演唱的《邊疆的泉水清又純》《心中的玫瑰》,王潔實和謝莉斯演唱的《九九艷陽天》《外婆的澎湖灣》等等,優美的旋律、形象的歌詞,滋潤著我們的心靈。每每聽到我國民族音樂家王洛賓演唱的《在那遙遠的地方》,我的眼前都會呈現湛藍的天空、無邊的草原、潔白的羊群、美麗的姑娘、還有她的帳房……我仿佛覺得,身邊的這位同事,就是歌中的那個姑娘,讓我心馳神迷。
我在那個年齡段,并未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愛情,而在工作與交流中,我朦朧的內心,產生了不一樣的感覺,喜歡上這個參加工作遇見的第一個女人。工作時趁她不注意,我則會多看幾眼。從她工作專注的神情里,我能夠感覺到她呼吸的氣息,仿佛看到了她心靈帶著的那份清純,我的心田好似吹過春風蕩起漣漪。那段時間,我初感青春的美妙工作的美好,生活里有了更多的陽光。自然而然,她的身影、她的音容,會不斷浮現在我的眼前、印入腦海。時而外出,也會心有所思,想著盡快返回,能夠早點看見她。雖然羞于告白、又從未牽手,可這份情感,在我內心驛動。
人世間的一些美好,或許就只一瞬間。隨著時光流轉,我慢慢學會了一點點觀察、一分分思考。再往后的一些時間里,我便意識到,她的內心有我無法預知的世界,與她之間,就像隔著一堵無形的墻,人挨得很近,心卻離得很遠。正因如此,我心中飄過一絲淡淡傷感,往日的快樂難以重現,活潑的個性里多了一份老成。我找來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力圖從中找到安慰。曾有不少夜晚,我獨自來到疇陽河邊,借助如洗的月光,平我心中的憂傷。還曾主動“坐莊”,邀友豪飲,把酒潑到心里,澆滅春愁,任憑窗前雨滴到天明。
一覺醒來,我忽然明白,不屬于自己的就不要勉強,青春的綻放不只是愛情,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自己的心魔“反側自消”,心胸豁然開朗。悠悠歲月,會帶走曾經美好的季節,多年后與她偶然相遇,交流如昨,只是那份情感早已隨風而去。
43年如電抹,往事回首已云煙。改革開放給我們國家帶來的發展變化日新月異、天翻地覆,而那時曾經輝煌的農村有線廣播,早在80年代后期,隨著收錄機、電視的普及,已離人們漸行漸遠、淡出了視線,當年廣播站的功能,如今也被縣融媒體中心所取代,而我在廣播站工作的那些時光,則變成永不消失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