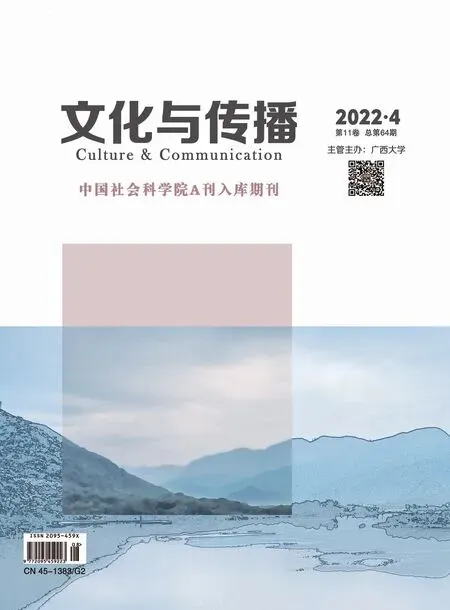筆掃千軍:《新華日報》在“壽郭沫若”事件中的文化領導權生成路徑探析
汪苑菁,唐 玲
1941年11月16日,《新華日報》特辟《紀念郭沫若先生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拉開了“壽郭”活動的序幕。這次活動從籌備策劃到正式開展長達半年之久,輻射范圍從重慶到全國,可謂聲勢浩大。此次祝壽活動打破常規①負責籌備紀念活動的陽翰笙也曾直言“我們共產黨人一般是不作壽的”,摘引自陽翰笙.回憶郭老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和五十壽辰的慶祝活動[J].新文學史料,1980(2):126-131.,意義特殊,承擔著歷史使命。
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了各方的認可與支持,“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的旗幟得到眾多人員的擁護。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蔣介石公開破壞國共合作關系,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與廣大民眾對于國共合作抗日的熱切期望背道而馳,其在意識形態領域上的領導權開始“漂移”[1]。在這個關鍵節點,周恩來及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的《新華日報》組織策劃了“紀念郭沫若五十壽辰暨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活動。“壽郭沫若”活動的最初提議人是周恩來,他曾言這次活動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政治斗爭”“一場重大的文化斗爭”,希望借此“發動一切民主進步力量來沖破敵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統治”[2]。
現有的對于“壽郭沫若”活動的研究,一是關注其文學意義,從文章的內容看,活動是郭沫若從“政治活動家”到“文化人”的形象的建構儀式[3],其中的文化因素可展現抗戰時期重慶文化生態[4];二是側重其政治意義,該活動是《新華日報》在“皖南事變”后采取的一種斗爭方式[5]。伍靜認為中國共產黨以報紙為中介,將一系列祝壽活動轉化為一種聯絡和團結國統區文人的媒介儀式,構建出共產黨人領導文化界的政治現實[6]。此次祝壽活動既可以看作是文化領袖的建構儀式,也是政治斗爭的儀式,但回到領導者周恩來的“文化斗爭”預想上,“壽郭沫若”活動更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文化領導權的一次斗爭實踐。
那么,《新華日報》為何能將私人內部的祝壽活動轉變成一個公共性的媒介事件?又是如何在封鎖的環境下以民間儀式的祝壽來“發動一切民主力量”,沖破“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統治”?這些都需要深入的研究。本文從文化領導權的研究視角出發,分析《新華日報》在“壽郭沫若”活動中前臺與后臺的運作①戈夫曼把社會結構比作一個大舞臺,并提出了 “前臺 ”與“后臺”的理論。“前臺”指演員演出及賓客與服務人員接觸交往的地方 ;“后臺 ”指演員準備節目的地方,這是一個封閉性的空間。本文將此引用至報刊場景中,將報紙的公開化傳播即報道內容的刊載稱之為前臺,將報紙背后的傳播網絡即報館工作人員的交往實踐稱之為后臺。引自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黃愛華,馮鋼,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03-107.,嘗試從生成路徑探究《新華日報》對文化領導權的奪取。
一、從文化領導權到中國共產黨的祝壽活動
“文化領導權”的概念提出者為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安東尼奧·葛蘭西,他以探討國家的結構為出發點,將廣義的國家概念分為“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兩個范疇,無產階級領導權在這兩個范疇中具體表現為“政治統治權”和“文化領導權”。前者著重“強制”,以軍隊、監獄、法院等國家機器,訴諸行政甚至暴力手段進行統治;后者意在“同意”,通過學校、教會、工會、媒體等社會組織,借助意識形態潛移默化的滲透,獲得廣大民眾的“贊同”來實現領導[7]。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的創造性發展,其理論的源流可上溯到馬克思、列寧等無產階級理論家。“文化領導權”的一個核心概念“市民社會”即從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分化而來,并承接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列寧第一次明確提出“領導權”理論,著重于“政治領導權”的奪取和建設,葛蘭西稱贊其“所完成的領導權的理論化和實現是偉大的‘形而上學’的事件”[8]41,承認其思想受益于列寧,并將其引申到意識形態領域,提出了“文化領導權”。
“文化領導權”作為理論設想在中國又有著更進一步的實踐發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十分注重文化領導權的奪取。瞿秋白首次提出中國共產黨革命領導權問題,認為要在政治與文藝有機統一的基礎上構建貼近生活、通俗易懂的大眾革命文藝,在思想文化戰線的斗爭中爭奪文化領導權,從而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務[9]。毛澤東亦將文化領導權的建設視為奪取和鞏固政權的一個路徑,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建立“文化統一戰線”,《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是著重強調文化領導權的戰略意義,提出革命斗爭中有“文武兩個戰線”“干革命不僅靠槍桿子,還要靠筆桿子”[10]。中國共產黨從思想和實踐②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正是把文化領導權的建設置于審視中國社會革命的視野之內,獲得了民眾的思想認同,最終實現了國家政權的更迭。具體內容可參見劉紅.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文化領導權思想與實踐研究[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8.雙重維度對文化領導權進行整體把握,調動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發揮巨大效用的報刊更是中國共產黨爭奪文化領導權的一個利器。有學者認為,1942年《解放日報》的改版不僅是黨報的歷史性變革,亦是中國共產黨文化領導權的建構[11]。
《新華日報》作為一份被國民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報,身處于政治、文化和軍事都牢牢被國民黨掌握控制權的國統區,要面臨不同于根據地的極為復雜的文化斗爭局面。特別是在“皖南事變”后,要想沖破國民黨的政治和文化封鎖更是極為困難。也正是在這種困難和復雜的歷史形勢下,以周恩來為核心的《新華日報》突破重重封鎖,通過“壽郭沫若”活動發起了爭奪文化領導權的一次特殊的戰役。
文化領導權的奪取需要通過“陣地戰”的方式長期進行。所謂陣地戰,與運動戰相對,這兩者也是軍事上的概念的引申。相較于后者需要直接進攻的強硬方式,前者則是著重長期的文化宣傳,這就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同其他社會集團合作,滲入其中并潛移默化地獲得市民社會對政黨意識形態的認同[12]。
在“壽郭沫若”活動中,《新華日報》采取“陣地戰”的方式,既以作為前臺的新聞報道在公眾中進行傳播,擴大傳播范圍;也以作為后臺的報館組織在社會上實現互動,壯大報道聲勢。
二、前臺之“報”:紀念文章和活動報道
“抗戰時期國共兩黨關系發生重大變化,是從‘皖南事變’開始。”[13]《新華日報》發行工作人員稱《新華日報》的發行工作分為“皖南事變”前和“皖南事變”后兩個時期。在第二個階段,“反動派對《新華日報》的迫害、封鎖、鎮壓驟然嚴重起來,他們采取各種卑劣手段鉗制我們的言論,封鎖我們的發行”[14]。在白色恐怖下,作為共產黨“合法代言人”的《新華日報》被國民黨軍警憲兵交織的黑網嚴密包圍著,人員的減少加上被減扣的稿件過多,報紙版面由對開一大張縮減為四開一張,發行量也大減,《新華日報》以至共產黨在國統區亟須重新奪取話語權。在“皖南事變”后的復雜局勢下,此次祝壽活動報道也正是對國民黨方面的反動宣傳“采取攻勢”①周恩來提出“我們必須應戰,并要采取攻勢,這是非常重要的中心問題”,并要求改善報刊的內容和形勢,輔助上述任務的完成。引自周恩來.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1年4月15日至5月22日)[M]//金沖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1898-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508。。
1941年11月16日,《新華日報》第一版以半版篇幅刊載周恩來《我要說的話》一文,并于第三版和第四版特辟《紀念郭沫若先生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刊登郭沫若的半身像和相關紀念文章,此次特刊并非《新華日報》祝壽專刊的首例。此前兩天適逢愛國民主人士馮玉祥的壽辰,《新華日報》在14日刊登《慶祝煥章先生六十大壽》專刊,郭沫若也曾題祝壽詩,但與時隔兩天的祝壽活動的對比仍能看出《新華日報》對“壽郭沫若”活動的重視。
一是將周恩來親自撰寫的代論發表在頭版。代論是《新華日報》的一種特殊社論,一般由享有崇高威望的人士針對當時的形勢需要撰寫,并以個人署名的形式發表,“比之一般社論具有更大的權威性、重要性。”[15]憑借周恩來在國共兩黨中的名望和《新華日報》“頭條”位置,代論的影響力可想而知。二是由于人員和稿件的減少,此前《新華日報》的篇幅已由四版縮減為兩版,為了刊登“郭沫若”活動,擴大活動影響力,《新華日報》在處境艱難的時刻專門增加兩版作為活動特刊。
《新華日報》對于“紀念郭沫若五十壽辰暨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活動的報道主要從紀念文章和活動報道兩個方面出發。
(一)刊載文人志士的紀念慶祝文章
歷數紀念慶祝文章,作者群龐大,有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人,有《新華日報》報社負責人潘梓年、救國會民主人士沈鈞儒,也有蘇聯大使潘友新等。他們創作紀念詩篇和文章,以表達對郭沫若五秩壽辰和二十五年創作生涯的慶祝之意。
縱觀紀念文章,主要是從郭沫若的文學修養與革命精神兩個角度進行論述,盛贊郭沫若“一方面提筆一方面戰斗”[16],既是一位學者,更是一名革命家。文學性方面,潘梓年對郭沫若的總體評價是“詩有才,史有學,書有氣度”[17];歐陽凡海提出紀念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建議,就是要重視研究郭沫若的文學作品,并將其繼續擴大發行[18]。革命性方面,艾云稱郭沫若在創作、研究、翻譯、行動上都具有革命性,可謂為“革命者郭沫若”[19];鄧穎超肯定郭沫若在婦女運動中的貢獻,稱“沫若先生即是這樣從歌贊中國歷史上叛逆的革命女性中,燃燒著這樣一支中國女性革命的光明的火炬的”[20];瀟湘從反法西斯時代背景出發稱贊郭沫若為國際反法西斯文化統一戰線的“主要推動者和領導者”[21]。
在這之中,周恩來以個人名義發表的代論《我要說的話》,對郭沫若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完整的評價。
“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起前進的向導。魯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遺范尚存,我們會愈感覺到在新文化戰線上,郭先生帶著我們一道奮斗的親切,而且我們也永遠祝福他帶著我們奮斗到底。”[22]
周恩來并論魯迅和郭沫若并非一時興起,而是有著深刻的含義。“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一方面是文化界的推崇,蔡元培有言“為新文化開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魯迅先生”[23],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共產黨的加冕,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4]。中國共產黨認可并大力推崇魯迅“新文化運動中堅強的革命戰士”的身份,并以魯迅為首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這個革命文學團體領導革命力量。“魯迅的歷史化,恰好為當下的郭沫若提供了歷史合法性。”[3]在魯迅“新文化運動的導師”的歷史地位已經獲得普遍承認的前提下,《我要說的話》將魯迅與郭沫若作對比,賦予郭沫若“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身份的合法性。
從文化領導權的思想出發,統治階級的政權合法性一是政治合法性,二是思想文化合法性[25]。周恩來的發聲包含了彼時對魯迅的加封以及此時對郭沫若的推崇,這種加封和推崇顯示出中國共產黨在無產階級文化中的“領頭羊”位置。
(二)對重慶及各地紀念活動的報道
《新華日報》對重慶及各地相關的紀念活動進行了持續的報道。1941年11月15日,即紀念活動前一天,重慶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會,臧云遠、常任俠等學者相繼作報告并朗誦郭沫若的詩篇[26]。16日,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大樓舉行的紀念茶會上,馮玉祥、老舍、黃炎培等一一上臺祝詞頌禱,周恩來更是高度評價郭沫若無愧于“五四”運動中長大的一代[27]。
除重慶外,在香港,各界人士在11月16日舉行慶祝大會,成為香港文化界近幾年來的一大盛事,《華商報》《救亡日報》《星島日報》等報紙刊登紀念特輯,登載文化界人士對郭沫若的祝賀和敬仰的文章和詩句[28]。在新加坡,星洲華僑文化界于11月15日舉行慶祝郭沫若五旬大慶的聚餐會,并募捐沫若獎學金作為壽禮[29]。
此前郭沫若作為特殊黨員,并不參與黨內的活動,即使在黨內也僅有周恩來等少數負責人了解其真實的身份[30]。而在社會大眾看來,郭沫若先后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對外一直是國民政府官員的形象,蔣介石還告誡他不要在赤色的刊物(《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將郭沫若和《新華日報》以及中國共產黨進行分割[31]。
作為共產黨在國統區唯一合法的日報,《新華日報》已成為“共產黨人格象征”[6],正如其總編輯章漢夫所言,“別的報紙有錯誤,只影響報紙本身的聲譽,而我們黨報發生錯誤,則會影響到黨的聲譽”[32]27。在集中的紀念文章和連續的活動報道中,《新華日報》對郭沫若親昵的稱呼、贊賞的口吻以及滿含期待的話語,無不在向外界宣告郭沫若與共產黨的親密關系,從魯迅著手,賦予郭沫若 “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的身份標簽,這一系列紀念文章和報道完成了郭沫若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文化旗手”的大眾化宣示。
三、后臺之“館”:傳播網絡的建構
在周恩來的構想中,祝壽活動不僅是一種短時的媒體儀式,更是作為“文化斗爭”的現實實踐。除了“前臺”報紙文章的宣傳造勢,《新華日報》后臺層層傳播網絡的鋪展也不容忽視。從個人到新聞界再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動員和組織,使“壽郭沫若”活動最終成為插在國統區的一把利劍。
(一)人際網絡:“勤交友”“交朋友”
郭沫若本人與周恩來私交甚密。在二人之間的書信來往中,周恩來以“沫若”“沫若兄”為頭,以“弟豪”“弟恩來”落款。在重慶期間,郭沫若“無論是住在郊區或市內天官府”,周恩來都經常去看望他,與其進行探討。有學者認為,1938年黨中央“以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的決議來源于周恩來的提議[30],此提議大有可能是周恩來與郭沫若日常工作和交往過程中得出的結論,可見周恩來與郭沫若相交甚深。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與郭沫若的交往并未止步于逢知己的私人情誼,二者在工作上也往來密切。郭沫若出任國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周恩來則擔任政治部副部長一職,初期有關第三廳的機構設置、人事安排等籌備工作以及工作開展等問題,郭沫若都向周恩來進行了請示[33]。此前第三廳領導的10個抗敵演劇隊成立之際,周恩來親自到場給演劇隊做報告,號召全體隊員們“到前線去,到民眾中去,為抗日戰士和廣大人民服務”[34],對郭沫若及第三廳的工作給予了相當的支持。
周恩來經常鼓勵黨內的同志“勤交友”“統一戰線就是交朋友,盡量多交朋友”[35]。在朋友間的交往中來進行思想的影響,擴大隊伍,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工作的一種特殊方式。
(二)同業網絡:“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
除《新華日報》外,《新民報》《新蜀報》《大公報》以及國民黨的《掃蕩報》和《中央日報》都刊載了賀壽祝辭或者對紀念活動進行報道。在這些報紙之中,《新民報》《新蜀報》表現得更為積極。它們在當月13日就對三天后在天官府七號舉行的郭沫若壽辰紀念會進行預告和報道[36]185,與《新華日報》的報道相互呼應形成祝壽輿論,其后更是在刊載紀念文章和賀電方面熱情不減,《新民報》還刊發了蘇聯大使潘友新和蘇聯對外主席凱緬諾夫對郭沫若的賀柬[36]188-189。陽翰笙也在回憶籌備工作的過程時提及了這兩份報紙,“這些報館的記者多半是我們的朋友和同志”,活躍的報道背后是新聞界的統戰工作。
《新華日報》和《新民報》《新蜀報》之間保持著友好的合作關系。1939年的“重慶各報聯合版”事件中,《新華日報》早日復刊的要求得到了《新民報》的積極支持,兩報在爭取新聞自由斗爭方面成為并肩戰斗的戰友[37]。在《新蜀報》資金難以周轉之時,《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拿出三千元現金幫助其渡過難關[32]417。
同時遵循著周恩來“勤交友”的指示,《新華日報》負責人和記者在新聞界中廣泛交友。《大公報》著名記者陸詒、《新民報》著名記者浦熙修、趙超構以及《新民報》負責人陳銘德、鄧季惺等,都與《新華日報》工作人員有著密切的來往,成為《新華日報》的朋友[32]65。
“皖南事變”發生當晚,潘梓年和石西民的等報社負責人分頭到各個報館說明“皖南事變”的真相,爭取同業人員的支持。此后,一些報紙并未刊登國民黨誣蔑新四軍的反動命令,部分登載了命令的報紙則將其放在不起眼的版面進行邊緣化處理,還有的報紙通過報道標題表示對該命令的不滿[32]106。
可見在國統區,《新華日報》并非單打獨斗,而是在新聞界建立了“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32]13,由《新華日報》牽頭發起的“壽郭沫若”活動輻射至其他報紙,在非黨派的民間報紙上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三)組織網絡:“集體組織者”
要把個人的祝壽紀念辦成“全國性的紀念活動”,周恩來提出要建立“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籌備組織,由各方面的人來參加籌備工作”[1],《新華日報》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8年5月11日,創刊僅四個月的《新華日報》探討作為革命報紙的“理想”,借用列寧“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而且也是集體的組織者”[38]一言,提出報紙除了傳達政策和口號之外,還需對如何實行政策和口號的斗爭形式和組織方法進行指導,以實現“綜合各種實際行動和組織實際的斗爭”[39]的目標。此次祝壽紀念活動中《新華日報》亦是展現出“組織者”的角色形象,為黨外動員工作付出不少的努力。
中國共產黨對國統區文化界的領導一方面是通過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及其下設的文化組來進行,另一方面主要通過《新華日報》來展開工作,實現“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開宣傳和秘密宣傳相配合,黨外的聯系和黨內的聯系相配合”[40]。《新華日報》的公開合法性為相關組織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基礎。曾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張穎就說:“我們不少作統戰工作的同志,都用《新華日報》人員的名義進行公開活動。”[35]負責南方局文委工作的夏衍同時是《新華日報》社論委員會中的一員,主要負責文藝方面的寫作[32]79。除相關負責人之外,《新華日報》的基層工作人員也是統戰方針的執行者。周恩來曾就《新華日報》采訪科的工作計劃告知總編輯吳克堅和陸詒,明確指出特派員不能僅僅以完成采訪報道工作為唯一要求,而是更應收集資料,向同情中共的各界人士約稿與征求意見[41]。“報道只是手段,統戰才是目的”[42],將采訪報道的過程作為與各界人士進行交流的方式,并極力爭取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同情與支持,將“統一戰線”的方針滲透進報館工作人員的社會實踐中。
得益于此,負責籌備紀念活動的陽翰笙高興地稱大多數人士“都是我們的同志和朋友”“他們都高興地表示愿意大力支持”[1],祝壽紀念活動不僅“動員了幾乎是整個文藝界、文化界和新聞界”,還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著名人士如鄧初民、黃炎培、章伯鈞等的支持,轟動全國。
四、“報”“館”縱橫:奪取文化領導權的范本
在“壽郭沫若”活動中,《新華日報》 以“報”與“館”相交、縱橫交錯的“陣地戰”[8]172的斗爭方式,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奪取文化領導權的一個范本。
“報”是以前臺(公開)的報刊內容進行宣傳造勢,是報紙在特定歷史時機下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反擊。適逢郭沫若五十壽辰和創作生涯二十五周年,《新華日報》紀念文章和活動報道的登載完成了郭沫若作為中國共產黨有機知識分子①葛蘭西以社會生產的視角來關注“傳統的”知識分子和“有機的”知識分子之別,前者獨立于社會階級之外,后者則與所屬的階級有著緊密的聯系。引自約爾.“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18.的大眾化宣示。在民族危難的時刻,久別歸國的郭沫若“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珠血都要與國族有所效益”②此為歸國前,郭沫若給四川達縣城區第二小學全體師生的復信《復達縣縣小同學書——郭氏回國前的一封信》中的話。轉引自何剛,王開志.“回首故鄉”:郭沫若不同時期的四川敘述[J].當代文壇,2015(3):136-140.,他的身份與志向都與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相契合。而在政黨沖突的背景下,此次活動明面上是對郭沫若本人的加冕和推崇,背后則是以此來沖破國民黨的政治和軍事封鎖,“發動一切民主進步力量來沖破敵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統治”[1],從文化領域突破重圍,實現對國統區文化界的引領。
“館”是以報社同仁努力編織的后臺傳播網絡,推動了祝壽活動的聲勢。從內部觀察,中共中央南方局與《新華日報》之間的溝通交流并不局限于前者對后者的領導,還存在著兩者之間以個體的交往為基礎,編織出傳播網絡,實現了上傳下達。1938年在《中共中央關于黨報問題給地方黨的指示》中,黨中央明確要求各地方黨部將《新華日報》上的社論作為重點進行討論和研究,其后還提出“每個支部應有一份《新華日報》,每個同志應盡可能定一份《新華日報》”的要求[43]。早期《新華日報》的傳播網絡是基于黨組織的組織網絡來建構的,其不僅僅是簡單的信息傳播,也是中央組織領導支部的一種方式、支部之間連接的一種共同載體。
從外部出發,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傳統的熟人社會[44],個體的人際交往成為社會格局的基礎,中國共產黨“勤交友”的指示也正是遵循著這一基本原則,《新華日報》管理層和報社工作人員從新聞界小圈子到社會各階層,從文藝界到普通大眾中都有著很多朋友。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交往搭建了《新華日報》與其他報刊合作交流的橋梁,并以《新華日報》為中心向社會其他階層群體蔓延,密切了《新華日報》與各組織、各階層的聯系,最后通過報刊刊載的內容進行大眾性傳播,從而完成了報刊與社會大眾的對話。
“壽郭沫若”活動的現實踐行與傳播網絡的鋪展密不可分,文化領導權的奪取是沿著人際網絡、同業網絡、組織網絡三者交織而形成的“陣地”展開的。而在此之中,《新華日報》扮演著“通道”的角色,搭建從一個傳播網絡到達另一個傳播網絡的橋梁,完成三重網絡之間的聯結交疊,建立了“一個廣大縱深的陣地”[32]64。
此次祝壽活動打破了“皖南事變”后文化界沉悶陰暗的局面,沖破了國民黨的政治封鎖,成為中國共產黨奪取文化領導權的一個范本。后《新華日報》又陸續為茅盾、老舍、洪深、沈鈞儒等文化名人舉辦了壽辰祝賀、創作紀念等活動,成了“一種擴大影響的新的斗爭方式”[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