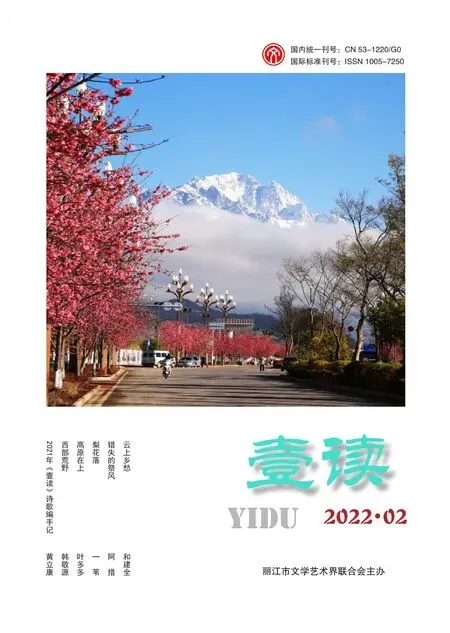西部荒野(組詩)
◆韓敬源
聯系人
在手機通訊錄里
看到一個已經辭世的朋友
我順勢把整個通訊錄
翻了一遍
已經有好多個
辭世的人
在我的通訊錄里
我不敢再撥打他們的電話
我知道打也打不通
有的注銷過的號碼
可能能打通
但已經換了人
包括我的母親
愛穿亞制服的老人
那個我記憶中的人
在今年春節再見時
老了
唯一沒變的是
他身上的亞制服
從撕掉領章的軍服
到警式襯衣
沒有標識的運政服
沒有標識的保安服
他都穿過
不知道他從什么途徑
搞到這些舊服裝
在孩子們零零星星的爆竹聲中
他穿著一件警式羽絨襖
靠著鄉村的墻根
睡著了
奔跑的牦牛
一頭牦牛在滇西高原上奔馳
視覺里真實的印象
是這樣的
一頭牦牛的四條腿
被繩子穿過腳骨
牢牢固定在門店的柱子上
全身的肉已被剔除
填充它身體的是塑料
老板希望買它肉的客人
清楚地看到
是一頭牦牛
在滇西北高原上奔馳
爆竹瀑布
響了一晚上的爆竹
讓早睡的孩子們
紊亂
更遠處的爆竹
像一陣急雨
打芭蕉
這多少有點像我走過的路
在早春二月里
才能聽到
逝去人們的骨頭
崩裂爆炸
延綿成河
西部荒野
我們喝了那么多酒
接了那么多吻
做了那么多愛
地球毀滅
也一起看過了
孩子尚未長大
沒有自然遠去
忍不住打噴嚏時
該麻木的也麻木了
獅王酒店的老板
換了三茬
我的魚人小姐
燃燒平原上的孤獨女孩
毫不回頭
那么倔強
芭蕉黃了又綠
去老年公寓探望父親
對面床上的老人
已經不見了
護工悄悄跟我說
那老人走了
2019年我從新世紀詩典江油詩會
受詩人趙克強邀請參觀北川地震遺址
返回昆明探望父親的時候
這個老人像從廢墟中
向我伸出過手
我緩緩走過去
坐在那張空空的床上
看著我爸
我爸看著我
中間什么都沒有
我爸已經認不出我
而我認不出這個世界
賣菜的人多數都有個陽光的網名
經常到菜市場買菜
刷微信付款時
我都會留意一下
對方的網名
今天刷到的六個網名分別是
會飛的魚腥草
不辣人的小辣椒
開花洋芋
我的蘿卜不花心
煮熟的鴨子
最后一個網名叫傷心傷肝
我留意了一下
是個手腕處
紋著蝴蝶的中年婦人
像一條魚一樣豐滿
讓早晨的菜市場
不停地在地板上跳躍
清明節的蜜蜂
清明節這天
一只蜜蜂
闖入我家
我熟悉這個世界里的蜜蜂
在父親沒有癡呆
母親也還健在的那些日子
與蜜蜂打了一輩子交道的父母
指揮蜜蜂
釀出花蜜
供我和胞弟念完大學
清明節這天
一只蜜蜂
母親的精靈
從時間的縫隙中
冒了出來
圍著我家客廳的燈泡
翩翩起舞
南京
看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時
有個老人的口述
讓我至今記憶猶新
在入侵的日本獸兵
糟蹋過當時的國都
一年之后
一個年輕的女人
幸存下來的
我的女同胞
親手掐死了
剛出生的嬰兒
我必須信任理發師
我到麗江工作十六年來
都沒有換過理發師
電話號碼也沒有換過
學校搬遷過一次
他也追到附近
繼續開店理發
后來房子也買在
同一個小區
他知道我老婆
知道我孩子
知道我父母
知道我同事
除了不知道我有沒有存款
最近風聲比較緊
十六年的熟人了
每次理發到最后
他按著我的頭
手起刀落
剔除我鬢角的絨毛時
我越來越緊張
生日
他是荷花開的時候出生的
他是包谷花開的時候出生的
她是谷子熟的時候出生的
她是挖土豆的時候出生的
她是太陽出的時候出生的
他是雞叫的時候出生的
她是麥子黃的時候出生的
他是米線只賣三毛錢一碗的時候出生的
我誕生于這個世界的準確日期
至今是個謎
我從一張木框鑲嵌的
父母結婚時
南京長江大橋落成
通車紀念的畫框上
一行紀念的小字中判斷出
從父母結婚那天算起
我的出生日期怎么都對不上
在那個嚴打一切的時代
我的出生
非常幸運
非常清晰
我是母親
在12年前她辭世的那天
順著她出嫁的路回去的那天
重生的
我特別能感受一滴水的恩情
詩人左右(真名)
替我在微信微店
賣詩集和詩論
銷售廖廖
今晚他發信給我
留了一個地址
附加留言
“他是你的鐵桿粉絲”
我喝了點酒
我會規規矩矩
簽下自己的姓名
親自寄出
我兒時在昆明石林
一個邊疆民族地區
還在使用戰國時候
就使用過的
食不果腹的
牛耕鐵犁的現代生活
幾乎淚下
我特別能感受一滴水的恩情
哪怕你嘲笑我如此幼稚淺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