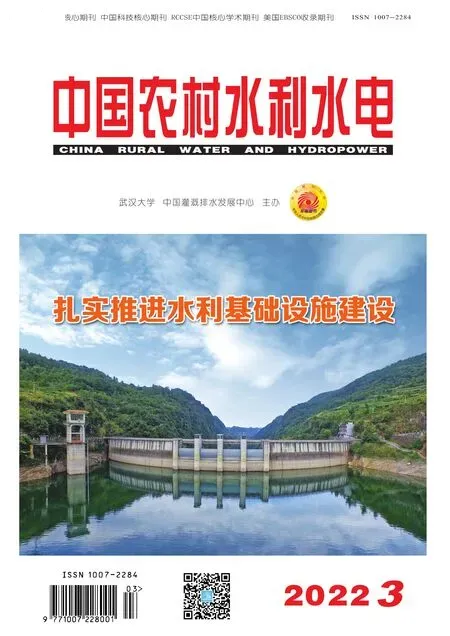黃河上游近60年水沙演變及影響因素分析
王鴻翔,楊克非,劉靜航,黃樸凡,郭文獻(xiàn)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xué),鄭州 450046)
0 引 言
流域產(chǎn)水產(chǎn)沙通常會受到自然條件的劇烈變化、水文循環(huán)及流域內(nèi)人類活動的影響而變化,使得徑流序列發(fā)生變異并呈現(xiàn)出階段性的特征,具體表現(xiàn)為突變年前后的水文序列統(tǒng)計特征值發(fā)生顯著改變。黃河作為中國第二大河,同時也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其特點(diǎn)有水少沙多、水沙異源等。對黃河水沙變化成因進(jìn)行量化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加深對黃河水沙關(guān)系的認(rèn)識,同時也有利于黃河水沙調(diào)控機(jī)制的發(fā)展與完善。趙陽[1]等對黃河干流的蘭州、頭道拐、龍門及潼關(guān)站4 個水文站及7個主要一級支流把口站的水文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析時運(yùn)用了運(yùn)用雙累積曲線等方法,得出上述四個水文站年的徑流、輸沙量均呈顯著減少的趨勢的結(jié)論,主要成因為人類活動的影響。李勃[2]等采用Mann-Kendall 趨勢檢驗法、Pettitt 變點(diǎn)檢測法和累計距平等方法,對黃河干流九個水文控制站點(diǎn)徑流數(shù)據(jù)資料進(jìn)行分析,研究發(fā)現(xiàn)黃河干流徑流量整體呈現(xiàn)下降趨勢。馬超[3]等運(yùn)用變化范圍法對龍羊峽、劉家峽水庫運(yùn)行前后黃河頭道拐水文站日均徑流量和輸沙量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析,研究發(fā)現(xiàn)龍、劉水庫運(yùn)行后,頭道拐水文站徑流和含沙量均減少,整體均發(fā)生中度改變。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徑流泥沙長時間序列的趨勢性突變,對于水沙不同時間尺度下的變化缺少相應(yīng)的研究。本文選取黃河上游為研究區(qū)域,在對黃河1960-2019年來的實(shí)測徑流泥沙序列進(jìn)行變化規(guī)律系統(tǒng)分析的基礎(chǔ)上,在分析黃河上游水沙變化趨勢性和周期性的同時,通過定量計算來得到黃河上游流域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水沙量變化的貢獻(xiàn)率[4],以期揭示黃河上游水沙量的變化規(guī)律及引起上游水沙時空演變的影響因素。
1 研究資料
黃河上游區(qū)域包括從黃河源區(qū)到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托克托縣河口鎮(zhèn)及其集水區(qū)域,上游總面積達(dá)55.06 萬km2,河長3 472 km。其位于我國一、二級階梯的交替地帶,具有復(fù)雜多樣的氣候類型,從黃河源區(qū)向下為高寒濕潤區(qū)逐步向荒漠干旱區(qū)過渡,具有鮮明的區(qū)域氣候特征。同時該區(qū)域地貌特殊,地形起伏大,氣候復(fù)雜多樣,降水量分布極不均勻。唐乃亥水文站作為龍羊峽水庫的入庫站,是黃河干流上的控制站,同時也是黃河上第一個洪水編號站,是國家重要水文站和黃河重點(diǎn)報汛站。蘭州水文站也是黃河上游流域一個重要的水文站,集水面積占整個黃河流域面積的29.6%。頭道拐水文站位于黃河上中游水沙變化的主要轉(zhuǎn)折點(diǎn),水文站下游約10 km處的河口鎮(zhèn),是黃河上中游的分界點(diǎn),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是黃河上游水沙變化的把口站和控制站。在對黃河上游水沙演變分析時本文選用黃河上游唐乃亥、蘭州及頭道拐三個代表性站點(diǎn)的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析。本文中1960-2019年60年間年降水量序列數(shù)據(jù)均來源于中國氣象數(shù)據(jù)網(wǎng);1960-2019年實(shí)測徑流泥沙序列數(shù)據(jù)來源于唐乃亥水文站、蘭州水文站和頭道拐水文站及《中國河流泥沙通報》。
2 研究方法
根據(jù)研究區(qū)內(nèi)徑流泥沙資料,采用Mann-Kendall 非參數(shù)檢驗法、累積曲線法[5]、均值差異T 檢驗法[6]和小波分析法[7]分析黃河上游水沙控制占徑流泥沙變化情況。在檢驗水文要素長期變化趨勢時采用Mann-Kendall 非參數(shù)檢驗法統(tǒng)計,結(jié)合累積距平來判別確定水文時間序列可能存在的突變點(diǎn),對可能存在的突變點(diǎn)采用均值差異T 法進(jìn)行檢驗。在周期性分析上,利用小波分析法揭示水沙時間序列在不同時間尺度下的多種變化周期。在分析導(dǎo)致黃河上游水沙變化的各種影響因素時,采用雙累積曲線法分析水沙序列的階段變化特征,并通過累積量斜率變化率[8]量化分析自然因素與人類活動對水沙量演變的影響。
3 水沙變異特征分析
3.1 水沙趨勢性變化分析
使用Mann-Kendall 趨勢檢驗法來定量評估黃河上游徑流量和輸沙量的年際變化趨勢(表1)。黃河上游三站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的Zc值均小于0,表明各站年徑流量及年輸沙量均呈現(xiàn)下降趨勢。頭道拐站徑流量、輸沙量和蘭州站輸沙量對應(yīng)的|Zc|值大于顯著性水平α=0.01 所對應(yīng)的臨界值2.32,即通過了99%顯著性檢驗,說明均存在顯著減少趨勢。蘭州站徑流量|Zc|值大于顯著水平α=0.1 對應(yīng)的臨界值1.28,通過90%顯著性檢驗,即蘭州站徑流減少趨勢比較顯著;唐乃亥站徑流、輸沙量|Zc|未通過檢驗,所以減少趨勢不顯著。為揭示黃河上游多年徑流及泥沙變化趨勢,繪制唐乃亥、蘭州和頭道拐水文站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變化曲線(圖1)。唐乃亥水文站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均呈波動趨勢;蘭州水文站年徑流量多年變化大體上呈波動下降趨勢,年輸沙量也呈波動下降趨勢;頭道拐水文站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總體呈波動性下降趨勢;三站水沙在各時間段的變化趨勢基本保持一致。

圖1 年徑流、輸沙量趨勢Fig.1 Variation trend of annual runof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表1 徑流量和輸沙量Mann-Kendall非參數(shù)檢驗Tab.1 Mann-Kendall non-parametric test of runof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3.2 水沙突變特征分析
運(yùn)用累計距平法對黃河上游唐乃亥、蘭州、頭道拐3個水文站1960-2019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進(jìn)行距平累積,其年際變化過程如圖2所示。

圖2 年徑流、輸沙變化距平累積過程Fig.2 Accumulative anomalies process of annual runof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change
使用累積距平法,由上游三站距平累積過程圖,可以判斷唐乃亥站年輸沙量突變時間與年徑流突變時間相同,突變年份都為1989年;蘭州站年徑流量的突變發(fā)生在1985年,年輸沙量則于1968年和1999年發(fā)生突變,年輸沙量與年徑流突變時間不同。頭道拐站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突變年份都為1985年,年輸沙量突變時間與年徑流突變時間相同。
采用均值差異T檢驗法對檢驗過程中出現(xiàn)的突變可信度不高的或多個的突變點(diǎn)的突變結(jié)果進(jìn)行驗證。選取顯著水平α=0.05,對應(yīng)臨界值tα=2.00,統(tǒng)計量結(jié)果見表2。可以看出,3 個水文站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對應(yīng)的統(tǒng)計量值都通過了0.05 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突變發(fā)生在對應(yīng)時間。即唐乃亥站年輸沙量突變年份和年徑流量突變年份均為1989年,根據(jù)檢驗結(jié)果選取蘭州站年輸沙量的突變年為1999年,年徑流量突變年為1985年,頭道拐站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突變年份均為1985年。

表2 年輸沙量和徑流量均值差異T檢驗Tab.2 Mean difference T test of annual sediment discharge and runoff
3.3 水沙周期性變化分析
在對黃河上游水沙周期性變化分析時,使用黃河上游3 個水文站點(diǎn)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的Morlet小波分析來繪制小波系數(shù)實(shí)部等值線圖和方差圖(圖3~圖4),它們代表了時間序列中周期性波動的大小。黃河中一系列徑流和泥沙序列包括幾個不同時期,這三個站的徑流和泥沙序列顯示出明顯的年際變化。結(jié)果顯示,1960-2019年以來,黃河上游水沙變化具有多時間尺度特性,且上游3 個代表站周期規(guī)律較為相似。年徑流量的周期變化主要存在準(zhǔn)4~7 a、準(zhǔn)9~14 a 和準(zhǔn)19~32 a 三種年際尺度,其中最為顯著的是以9~14 a 為主周期的變化,年徑流量在該時間尺度上經(jīng)歷枯豐多次循環(huán)交替,且該尺度的周期變化在整個分析時段表現(xiàn)得相對較為穩(wěn)定,具有全域性;年輸沙量的周期變化存在準(zhǔn)3~7 a、準(zhǔn)9~15 a和準(zhǔn)20~32 a三種年際尺度,其中以9~15 a 為主周期的變化最為顯著,尺度周期變化也具有全域性。水沙之間周期性變化既有一定聯(lián)系也存在一定的差異[9]。


圖3 徑流小波分析等值線、方差圖Fig.3 Wavelet analysis isonline and variance diagram of runoff

圖4 輸沙小波分析等值線、方差圖Fig.4 Wavelet analysis isonline and variance diagram of sediment discharge
3.4 徑流泥沙雙累積分析
河道徑流量與輸沙量的因果關(guān)系密切,表現(xiàn)為二者的累積曲線具有顯著的直線關(guān)系。根據(jù)上游徑流泥沙趨勢性、突變性分析的結(jié)果及繪制的唐乃亥、蘭州和頭道拐三站水沙雙累積曲線圖(圖5),并以徑流量和輸沙量的突變年為界限將三站徑流泥沙時間序列劃分,建立輸沙量與徑流量累積直線的擬合方程,各個階段的擬合關(guān)系式的擬合程度良好(決定系數(shù)R2均在0.96 以上)。同時3 個水文站的雙累積斜率均向累積徑流量軸發(fā)生了偏折,表明上游累積輸沙量發(fā)生了趨勢性減少。

圖5 水沙雙累積曲線圖Fig.5 Double mass curve of runof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唐乃亥站2019年在曲線轉(zhuǎn)折前的累積輸沙量為8.40 億t;突變之后累積輸沙量7.33 t,由此可得,1989-2019年的累積減沙量為1.07 億t,該時段31年年均減沙量為0.03 億t;蘭州站在1998年突變之前的累積輸沙量為30.09 億t,1998年實(shí)際輸沙量24.60 t,即1960-1998年的累積減沙量為5.49 億t,該時段年年均減沙量為0.141 億t;2019年在曲線轉(zhuǎn)折前的累積輸沙量為35.02 億t;2019年實(shí)際輸沙量29.51 億t,1999-2019年的累積減沙量為5.51 億t,該時段年年均減沙量為0.26 億t;頭道拐站2019年在曲線轉(zhuǎn)折前的累積輸沙量為69.78 億t;2019年實(shí)際累積輸沙量為53.25 億t,1985-2019累積減沙量為16.39 億t,該時段34年年均減沙量為0.48 億t。
4 徑流泥沙演變影響因素分析
4.1 自然因素
黃河上游水沙關(guān)系變化受氣候變化、人類活動、自然災(zāi)害、下墊面條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10]。降水和人類活動[11,12]作為導(dǎo)致黃河上游流域水沙變化的主要因素,本文考慮這二者的干擾對黃河上游徑流輸沙的影響。
按照黃河上游水文突變特征繪制3個站點(diǎn)發(fā)生突變前后時段內(nèi)的降水與輸沙、徑流的累積變化關(guān)系曲線如圖(圖6~圖7)所示。3 個站點(diǎn)每個階段的擬合關(guān)系式的擬合程度良好表3、4是使用累積量斜率變化率法定量計算得出的人類活動和降水兩種因素對上游3個水文站水沙量變化的貢獻(xiàn)率。上游地區(qū)降水量的大小、多少是水沙產(chǎn)量的主要影響因素,當(dāng)短期內(nèi)降水過多時甚至?xí)茐臉?biāo)準(zhǔn)較低的水利水保工程從而改變水沙量。統(tǒng)計顯示,20 世紀(jì)80年代后,黃河中上游年均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日數(shù)均減少[13],其中,大暴雨和特大暴雨日數(shù)減少更多,暴雨量的減少會直接影響進(jìn)入黃河的泥沙量。對于黃河上游3 個水文站在突變年前后兩個時期相比,發(fā)生突變前后降水量對輸沙量減少貢獻(xiàn)率分別為8.41%、-0.6%、4.43%;降水量對徑流量減少貢獻(xiàn)率分別為17.27%、-41.37%、8.70%。由此可得主要是人類活動對水沙量的變化產(chǎn)生了影響。

表3 不同時段各水文站降水和人類活動對徑流量貢獻(xiàn)率Tab.3 Contribution rate of precipitation and human activities to runoff at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圖6 累積徑流量、累積降水量圖Fig.6 Cumulative runoff and precipitation in three different hydrological locations

圖7 累積輸沙量、累積降水量圖Fig.7 Cumulative sediment discharge and precipitation in three different hydrological locations
4.2 人類活動
黃河上游水沙演變與流域人類活動存在密切聯(lián)系。各種黃河上游沿岸城市用水量的增加、水土保持措施的實(shí)行[14]以及水利樞紐的建設(shè)等等人為因素都會影響黃河到上游水沙變化。這些人類活動不僅導(dǎo)致了水文時空分布規(guī)律和循環(huán)過程的改變,同時對黃河上游徑流的產(chǎn)沙條件的影響巨大。
黃河上游多個水利工程的建設(shè)是水沙變化的重要原因。1960年以來,黃河上游相繼修建了青銅峽、劉家峽、龍羊峽等一系列水利樞紐。黃河上游青銅峽以上的河段是主要的來沙段,且輸沙量存在非常不均勻的年內(nèi)分配變化,泥沙與徑流的對應(yīng)性較好[15,16]。在大型水庫修建前泥沙流態(tài)基本保持自然形態(tài),上游三站輸沙量相應(yīng)較多,存在較多個輸沙量大的年份,且輸沙量大小隨著徑流量大小而變化,兩者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較好。劉家峽水庫運(yùn)用期間,由于水庫大量攔沙,水庫運(yùn)行后輸沙量小的年份與之前相比明顯增多;水庫運(yùn)行期間汛期會蓄水消峰,非汛期會向下游補(bǔ)水,使得徑流過程較天然徑流過程情況均更加勻,河道水流的挾沙能力降低,輸沙量減少明顯。劉家峽、龍羊峽兩水庫聯(lián)合運(yùn)用期間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了水庫對上游水量的調(diào)節(jié)能力,進(jìn)一步加大了河流泥沙輸移的難度,導(dǎo)致了河流輸沙量與天然狀態(tài)相比顯著減少;輸沙量小的年份明顯增多,輸沙量受人類活動影響非常顯著。
5 結(jié) 論
(1)根據(jù)唐乃亥、蘭州、頭道拐三個水文站徑流量和輸沙量年紀(jì)變化數(shù)據(jù)分析,各站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呈波動下降趨勢,近幾十年來黃河上游徑流量和輸沙量均呈下降趨勢。
(2)通過累積距平法分析唐乃亥、蘭州、頭道拐三個水文站徑流泥沙突變特點(diǎn),并使用均值差異T法檢驗水沙量突變特征,結(jié)果表明上游三站徑流量突變年份分別為1989年、1985年和1985年;輸沙量突變年分分別為1989年、1999年和1985年。
(3)小波分析表明,3個站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的周期性變化是相似的,年徑流量年際尺度的周期變化主要存在準(zhǔn)4~7 a、準(zhǔn)9~14 a、準(zhǔn)19~32 a 三種周期變化,以9~14 a 為主周期的變化最為顯著;年輸沙量年際尺度的周期存在準(zhǔn)3~7 a、準(zhǔn)9~15 a、準(zhǔn)20~32 a 的變化,其中變化最為顯著的是9~15 a 為主周期的變化。

表4 不同時段各水文站降水和人類活動對輸沙量貢獻(xiàn)率Tab.4 Contribution rate of precipitation and human activities to sediment discharge at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4)通過對3個水文站徑流泥沙進(jìn)行雙累積分析可知,唐乃亥站徑流泥沙時間序列可劃分為年兩個階段,累計減沙量為1.07 億t;蘭州站徑流泥沙時間序列可劃分為3 個階段,累積減沙量分別為5.49 億t和5.51 億t;唐乃亥站徑流泥沙時間序列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累積減沙量為16.39 億t。
(5)導(dǎo)致黃河上游水沙量呈現(xiàn)減少趨勢的有降水和人類活動等影響因素,其中對水沙變異起重要作用的是水利工程建設(shè)、黃河上游水土保持工程和用水量增加等多種人類活動。
黃河上游的水沙變化復(fù)雜,通過對黃河干流水文站的資料對黃河上游流域輸沙量增加的貢獻(xiàn)率變化只進(jìn)行了初步研究,區(qū)間水沙還會受到上游城市用水、各種水土保持措施等影響,自然條件下,水沙量的計算十分復(fù)雜。為深入分析上游流域水沙變化過程及水沙貢獻(xiàn)率變化,可開展長時段黃河上游流域的水沙模型研究。 □